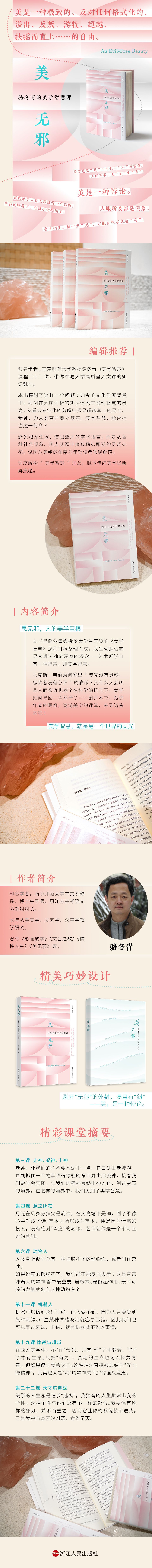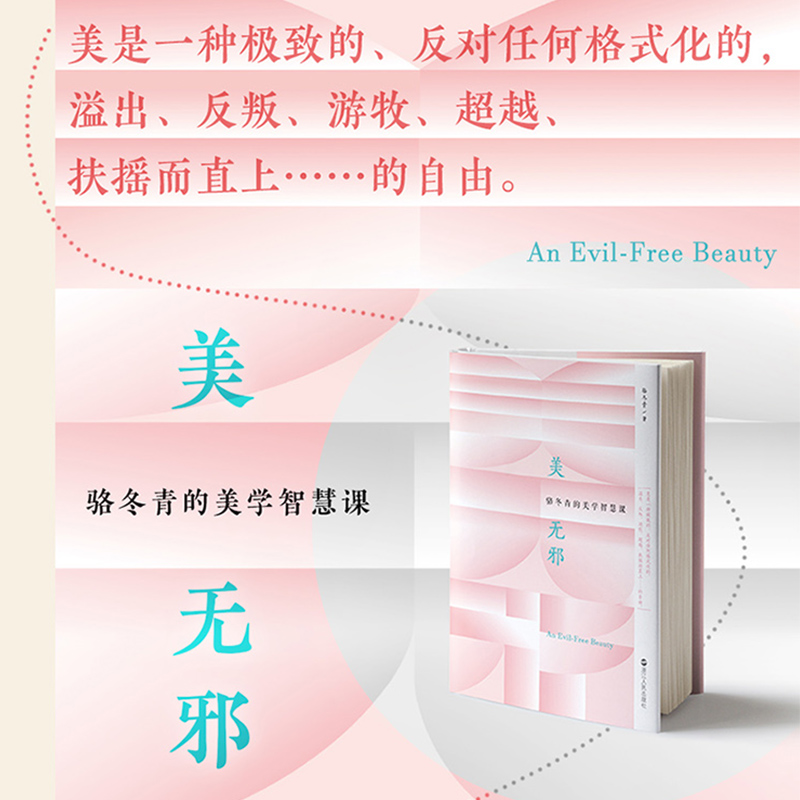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38.40
折扣购买: 美无邪(骆冬青的美学智慧课)
ISBN: 9787213114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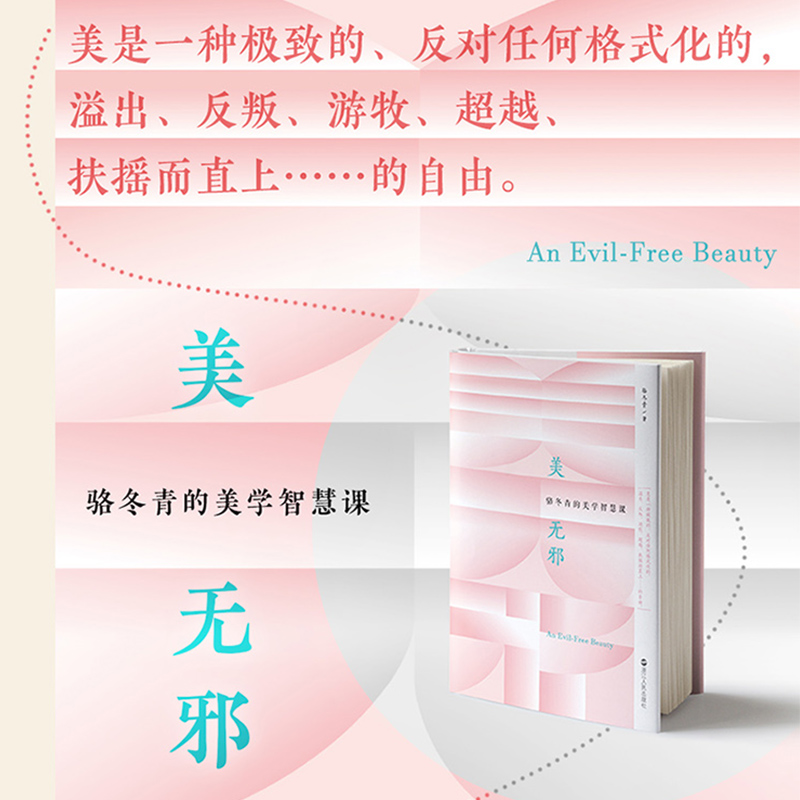
骆冬青,1964年10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华诗教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写作学会会长、美学学会副会长等。 主要著作:《情性人生:心灵美学讲稿》(中华书局2015年),《新闻眼:文化哲学的探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2015年再版),《毒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道成肉身:明清小说美学》(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再版),《文艺之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形而放学:美学新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撰写论文数十篇。
精彩课堂摘要 第三课 走神、凝神、出神 走神,让我们的心不要拘泥于一点,它四处出走漫游,直到抓住一个尤其值得停驻的东西并由此凝神,接着我们要学会忘怀,让我们的精神最终出神入化,到达更高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我们见到了美学智慧。 第四课 意之所在 月光在贝多芬指尖是旋律,在凡高笔下是画,到了歌德心中就成了诗。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便是因为情感的投入,没有绝对“零度”的写作,艺术创作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黑洞。 第六课 动物人 人类身上似乎总有一种摆脱不了的动物性,或者叫作兽性。如果说真的摆脱不了,我们能不能反向思考:这是否意味着人的精神当中最重要、最根本、最能起作用、最不可控的力量就来自这种动物性? 第十一课 机器人 机器可以做到永远正确,而人做不到,因为人只要受到某种刺激、产生某种情绪波动就容易出错,因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出错,就是机器做不到的事情。 第十九课 悖逆与超越 在西方美学中,不“作”会死,只有“作”了才能活,“作”了才有生命。只要“有为”,衰老的生命也可以恢复青春,但如果停止就会灭亡。这种想法直接被总结为“浮士德精神”,其实也就是“动”的精神或“动”的强烈意志。 第二十二课 天才的飘逸 美学的人生总是追求“逃离”,我独有的人生雕琢出我的个性,这种个性与你们总有不一样的部分。我要保有这样的部分,并珍而重之,因为它让你的系统装不进我。于是我冲出逼仄的囚笼,看到了天。 精彩样章 导论(节选) 马克斯·韦伯诊断现代社会,沉痛而警辟地一言以蔽之,曰:“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现代科学,作为分科之学,造就了大批专家,某些专业人士,在哪儿失去了灵魂?纵欲者,则是失去了形而上的终极关切,不仅是指在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中狂欢的浪荡子,更是指只为物质生活奔忙的芸芸众生。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指为了金钱而心肠冷酷、为了物质而纵情狂欢的人。 韦伯这样写道:“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有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这似乎已成为当代社会的警世通言。那么,从哪儿可以获得拯救?尤其是在现代化、后现代化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更值得追问。现代文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专业化,盛产专家;后现代文化,则打破了超越性的大叙事,于是,纵欲者成为理所当然、心安理得的存在。古典美学的超感性,被还原为潜意识、无意识的欲望,而专业化的“家”们,却失去了“家园”。 如何寻求生存智慧,成为急迫的呼唤。 在人类的知识也分崩离析时,如何在知识体系中发现智慧的灵光,从看似专业化的分解中,探寻到那种超越其上的灵性、精神,也是为人类尊严奠立基座。 美学智慧,能否担当这一使命? 一 如果,专家告诉你,《李白全集》里的诗并非全是李白的,有些是赝品,你会想,应当把赝品剔除,留下真正的李太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是按照什么准则制造李太白的?为什么能够达到难以发现的地步?制造成功李太白,比制造成功杜甫难吗?难在哪里?许多宋人制造杜甫,制造不成,也写了不错的诗。 那么,问题来了:可以按照这种原则,用机器制造诗吗?诗学,或文学理论,或美学,能够帮助机器做到这一点吗?请不要说什么诗是生命,是灵韵,是气象……最终,诗是语言,是符号,是可以运算、运演的符码。这就是诗可以用机器来完成的终极答案。比如,现在的文字,就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只不过,在电脑前,是否坐着“人”?计算机,其本意即是代替“人”计算。那么,它可以代替诗人写诗吗?若可以,那么,结论颇可怕。若不可以,那么,至少需要修改诗歌的定义,乃至艺术、美学的定义。需要一种大美学,涵盖人类生活中精神生活与科技生活思索的大美学。 一位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教授,向我慨叹:还是你们研究文艺的好,它滋润人,能养老。我打趣说:可是,传统以文学为中心的文化,已经被自然科学打得落花流水,风光不再啦!古代以文章取士,科举废除后,文章以及文艺,只能养老了…… 这是在“应急”中反映出来的某种心态——文艺学、美学“危乎高哉”!高,还是高;可是有些危殆,似乎也是实情。或曰,中国文化是审美文化;也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伦理文化。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中,美学精神占据重要地位,当是不争的事实。审美文明的衰落,恐怕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相关:科学进入中国,令美学原来的地位难保。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研究美学的人,似乎越来越“高冷”了。 有一则广告:“科技以人为本”,它宣示了科技是以“人”为中心的,似乎处于臣服的地位。这从底部“拆除”了我们的警惕,让我们以为,科技不过是人的工具。现实情况是,每个人都感受到科技带来的好处,它体贴入微,俯首帖耳,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比如,现在手机似乎成了我们延展的身体器官,离开它,我们寸步难行。在网络文化发达时,人们叹息:一切都被一“网”打尽!在更为先进的电子文化面前,思考已成为极其奢侈的事。 最可怕的是,“机器人”渐渐进入了“人”的领域,不仅在体力、脑力上,完胜了“人”,如今,更要在美学、文艺领域碾压“人”。人工智能“阿尔法狗”“阿尔法零”对围棋选手的胜利,令人寒战顿生。特别是,我小时候读了许多关于围棋的神秘主义式的描述,如“宇宙流”“自然流”,似乎围棋高手的招式蕴藏着的是“天才”的心灵。天才,这是美学、艺术的领地,现在,被“狗”打败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阿尔法零”从“零”学起,照样“打遍天下无敌手”!这就宣告:看似复杂微妙的“招式”,其实不过是“算法”,是“程序”,是科学可以越来越轻巧征服的东西。 美学最核心的文艺,也成了“机器人”或曰“智能机器”可以闯入的领地。旧体格律诗词,机器上已经制作出程序,可以根据命题来“吟诗”“唱词”;据说,甚至可以“私人定制”,写出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诗词。现代诗似乎最无规律可循,可是,机器人“小冰”竟然“创作”出一部“诗集”来!而美学最关心的感性问题,包括内在感性,在人工智能面前似乎也逐渐失去了隐秘感。 可悲的美学,简直是被科学“吊打”了!这里,当然引申出一系列问题,如科技理性对人的“奴役”、科技发展的伦理,等等。我最关心的是,在科学的挤压下,美学如何寻回一点尊严。那么,就需要找到美学独特的智慧。 智能、人工智能,与智慧、美学智慧,无疑有着本质区别。智慧,乃知、情、意与祈望的结合与升华。升华的契机,是难以捉摸的灵感。其中,最要紧的是灵感,以灵感带动整体精神力量的飞翔。美学智慧蕴含的内容丰富复杂。这里,我只拈出一端。人工智能,或电脑,最基本的特征是广义的“计算”,是“算法”, 是“计算”的准确、无误。围棋选手,之所以战胜不了“阿尔法狗”或“阿尔法零”,正是在强大的“计算”能力面前,无法以大局观和算法取胜,只好敛手服输。在可见的未来,人类脑力的许多部分,只会输得更惨。 或许,人会犯错的特点,倒是能够打败计算机的一个选项。美学智慧中的一个选项,正与此相关。意大利哲学家维科在18世纪写出的《新科学》,以“诗性智慧”论人类的原初创造,就是着眼于那种生机勃勃的野性的隐喻的创造力。20世纪哲学家波普尔更以“试错”作为科学理论发展的动力。 “错误”,有时候真是“美丽的错误”!在美学中,“正确”有时倒是“可怕的”。所以,美学有时正是以“错误”为契机,激发出“异想天开”的创造。人类智慧也往往以此为契机,把我们带入某种“迷狂”、某种“不可测”的“灵感”,某种“将错就错”的创造之中!也许可以说,这样的“错误”,从根本上看,具有了一种神圣乃至神奇的性质——指向的是不可“测”的欲望与希望。 成语“画蛇添足”形容没事找事地“手痒痒”,画出了“错误”,画出了“不存在”的“足”。所以,“添足”的这位老兄不仅没有得到奖励的“酒”,还留下了笑柄。“蛇”,“上帝”命令它“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可是,这位“艺术家”给它添上了足,它就可以抬起自己的肚皮,“走”向了某种自由,更不必因为被唆使吃“苹果”而终身“吃土”。所以,这位“画蛇”的老兄,自由地赋予了“蛇”自由!可惜,时间太短,规规矩矩的画蛇者得到了“酒”,这位老兄的创造止步于此。若赋予一个时辰或两个时辰的竞赛时间,那么,这位画蛇者是否还会发挥想象,凭空构虚,在“蛇”上添呀添呀……添上长须,添上鹿角,添上兔眼,添上牛耳鹰爪虎掌……天呀!这是什么?龙!于是,它“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这个“人”的艺术想象创造的精灵,从一个不按规矩的“画蛇”,最终竟发展成神奇的“画龙”! 于是,美学、文艺学有了名著《文心雕龙》,成语中有了“画龙点睛”。“雕龙”其实就是“画龙”。“凡雕琢之成文曰雕”,“雕龙”大抵是在金石玉器或木制品上“画龙”,是指向四维的立体的“龙”。龙这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神奇事物,就成为“文心”描画的“对象”。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黑格尔曾经说:“艺术也可以说是要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 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画龙点睛,乃艺术赋予想象物以生命的象征。所谓“点之即飞去”,是让我们的心灵通过艺术的灵眸炯炯地映照着我们,令我们的心“飞去”。“文心”之所以可“雕龙”,正因它具有的“点之即飞去”的灵性——“传神”。 从无事生非式的“添足”,想到“文心雕龙”,想到“画龙点睛”,无非是对一种狂野无羁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呼唤。“错误”之变为“非凡”,我想,正是不甘平常不甘拘束不甘受制于平庸现实的力量的表现,“不作不会死”,恰好相反,不“作”就会死!想象力会死,灵性会死,“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的龙性会死!美学的创造,在科学、学科之外、之上,开启了一个空间,一个想象的、灵性的空间。这个空间,“逸”出每个人自身的精神世界,指向了无穷的天际。我们不甘于为了现实的“一杯酒”而“画蛇”,当我们为僵化的现实“添”上一点什么“飞去”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在美学创造的境界中了! 美学智慧,应当还有诸多形态。今天,我们拈出其一,先从“外部”,在它与科学的对峙中,寻找到“人”的尊严与灵性。 三 爱似乎是柔弱的。既展现美好,也暴露耻辱。人性的一切,都在其中得以显现。美,亦复如此。懒散,拖沓,孤独(寂寞、冷),天才,疯狂,忧郁,独身,节欲,纵欲,吝啬,挥霍,野心,嫉妒。——个性的一切,都是构成“天才”的一切。关键在于,是否具有“灵性”。 反人类的标志,就是将其认为的一切人性的特点,视作弱点、缺点、病态、恶德。阿喀琉斯之踵,似乎是最大的弱点,然而,阿喀琉斯却因此是一个人。一旦全知全能,那就成了不可能的“永动机”。 美学审视人性的这一切,发现了智慧所在。哪怕是一般认为的愚笨,也会闪现出特殊的另一种智慧。“愚”而不“昧”,“蠢”而不“坏”,以诚挚、“刚、毅、木、讷”,通向另一种智慧。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不仅是伦理学,更是美学,更是创造的奥秘。 所以,人性的特质之中,包含着愚蠢、狡猾、调皮、跳脱,具有超越智力、超越已有规律的复杂!禅宗顿悟,常以美学事件开启心灵升华之密钥。道家体无,以见“独”而观“物化”。儒家的伦理性质,经由礼乐文明而彰显,其实质在于,内在的心灵秩序,通过外在的表演来达成——荀子所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由此,却进入艺术境界:“走心”! 那种“刚、毅、木、讷”的表演达到极致,却可能成为“机器人”,成为“钢铁侠”。人的特性,便被转化为机器的属性。机器无“自”,亦无“由”!在这点上人心高于机器——低于机器的人心,被计算机、电脑打败的人,尊严何在?在感觉、感情、感悟,以及由感性而连接上的“世界”。或许,非智力因素、非智能,是“人”的核心竞争力。但,“机器人”极其厉害——人的一切反映、反应、反思,均可被模仿,均可被“机器学习”。 由自然科学而推演创造出的机械的人,在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可以看到。政治机器、国家机器,看似譬喻,却有着社会科学的基础。社会科学机器的润滑,需要人文。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裂痕,似乎蕴涵着“反对机器化”的呼声。政治的“人化”,“政体”成为“人体”的比拟,均令政治秩序中留有的最大空间,乃是人的精神。自由,是美学的永恒主题。令人担忧的是,政治机器与智能机器已经有机结合——大数据以及人脸识别等,笼罩着我们的生活空间。媒体,以及媒体融合,可能会令人类生存陷入悖论情境。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是颇为屈辱的历史记忆。但是,所谓“中体西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机器不过是“器用”“长技”,尚未进入精神层面,而机器的制造却来自心灵的运作,很可能成为一种冷冰冰的理性,进而入侵人性。 在西方,“人是机器”的观念,解构了上帝的权威。启蒙运动中,科学主义的推进,其逻辑乃是从制造机器到制造“机器人”。西方关于机器、关于科学、关于技术的思想,作为思想史,是“人”史的一部分。自然,与之相伴的,就是对机器以及市场的恐惧。货币,作为金融机器运行的根本要素,似乎具有了神灵一样的意义,马克思称为货币拜物教。在一些人那里,比如芒福德所说,有了“巨型机器”。因而,毋宁说有了机器拜物教——人的机器化与机器的人化甚至神化!从而,人类社会本身也成了机器。而国家机器——这个词已经说明了一切! 于是,需要有自由人的联合体,需要生机勃勃的如大自然般的有机整体——需要加入灵性,灌注生气,调动活力。在生命性概念之上,有着精神性的自由概念。超越机械性,超越动物性,让诗性智慧的神话精神——“返魅”! 美感即被魅力唤醒。在美感中,人类的感性经验处于灵动状态。喜怒哀乐等复杂的情感,瞬息万变的情感,在变化中,有了感性的自由与智慧的飞扬——飞扬的感觉!这就是灵感。而这是机器不可能有的。感性带着灵性的飞扬,是思维层面的提升。 ——机器能吗? ——不可能!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也可简称为“不确定”)、哥德尔的“不完全”、阿罗的“不可能”。 灵动的感性经验是急切的非反应,不可模仿——超出模式的反应。如果说应当纳入“模式”中,如何“计算”呢? 只有“一次”的反应,决定了你是一个人,还是一台机器。艺术,一次性,不可重复——是“手迹”!艺术即“手迹”。他人无可替代。 人生是一次的。艺术亦然。人,会出生,生而不同;机器则批量生产, 生而相同。人有幼年、儿童、青春、成熟、衰老期——这些时期,遭遇各各不同,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一种美学,一种哲学。机器呢?哪怕临“死”,机器不会因为电力衰减而悲哀;人,却会各自“悲欣交集”。人生的不可重复性、时间性含有一次性。一次性具有美学的光华,令瞬间变为永恒。 美学中,万物熠熠闪光,焕发神采!万物生生不息的活力与灵性,正与人类智慧的激发相互回荡升华。感性所生灵性,与机器性相对抗。机器人,哪怕是智能机器人,永远不会生出灵性,从而不可能具有美学智慧。 美学是个古老的概念,美学又是个形而上的学科。本书没有艰深生涩、佶屈聱牙的学术语言,而是从各种社会现象、热点话题中摘取稍纵即逝的灵感火花,试图从美学的角度为年轻读者答疑解惑。 本书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的文化发展背景下,如何在分崩离析的知识体系中发现智慧的灵光,从看似专业化的分解中探寻超越其上的灵性、精神,为人类尊严奠立基座。美学智慧,能否担当这一使命? 著名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骆冬青《美学智慧》课程二十二讲,带你领略大学高质量人文课的知识魅力。 深度解构“美学智慧”理念,赋予传统美学以新鲜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