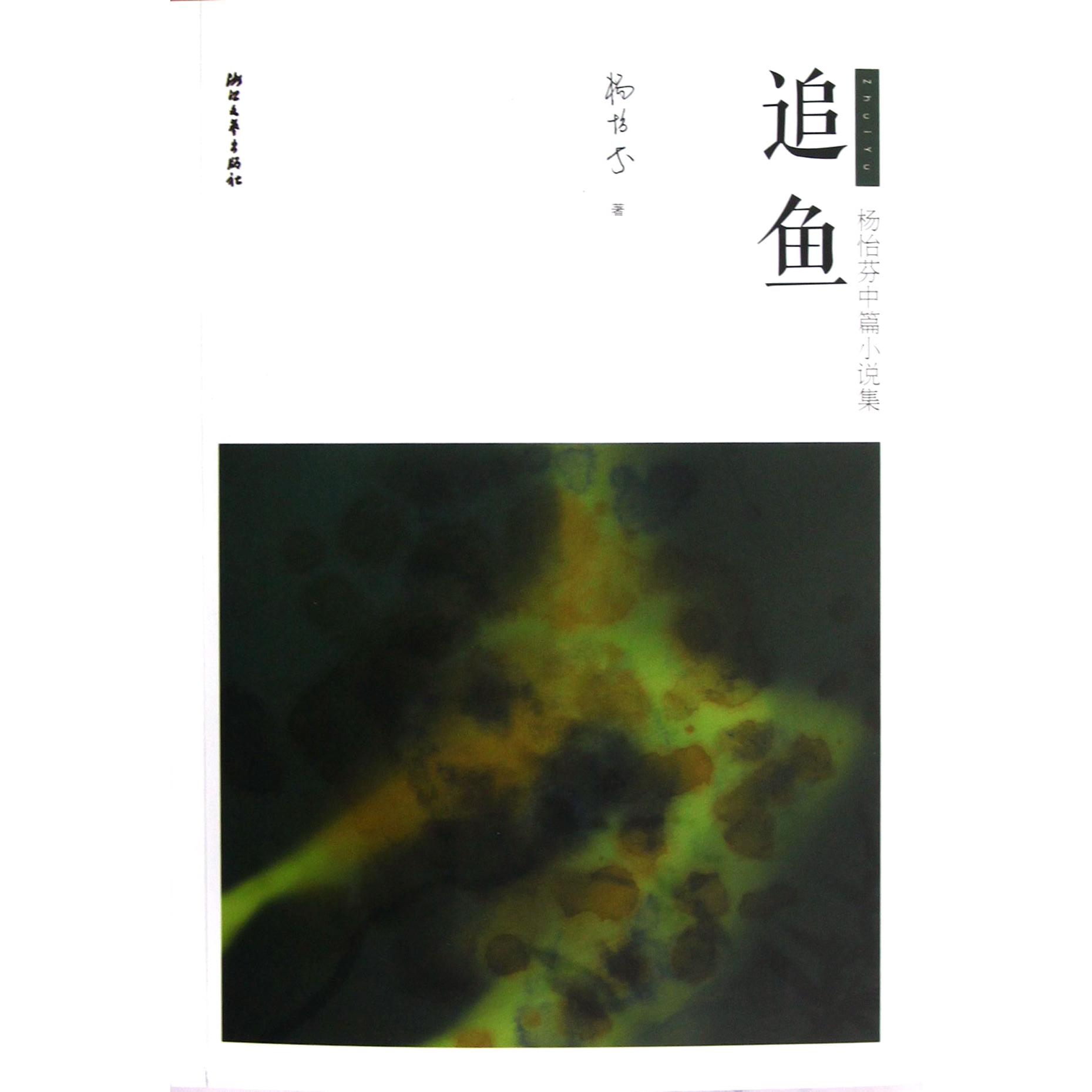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文艺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9.50
折扣购买: 追鱼
ISBN: 97875339357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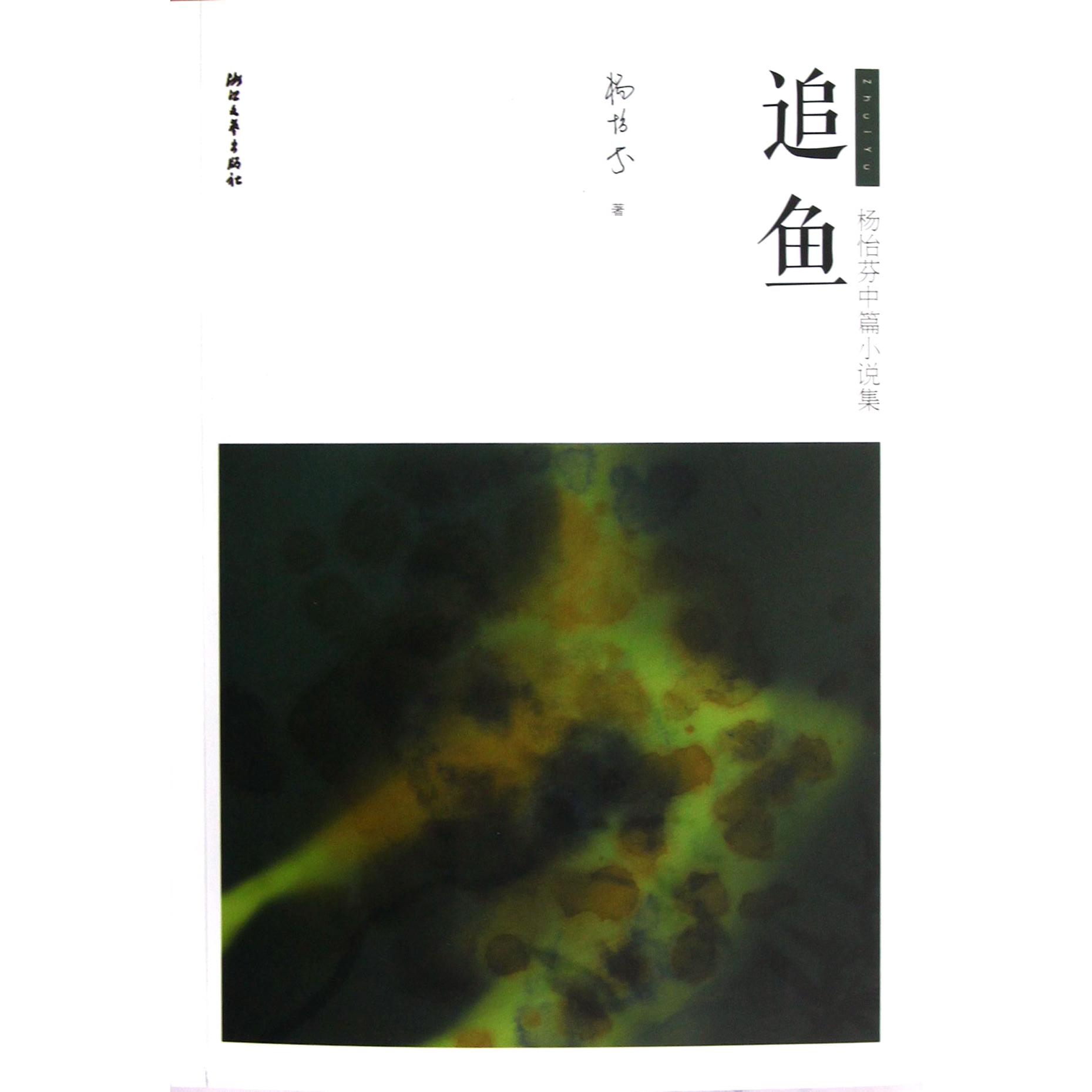
刘氏剧团向来把自己当个正规的演出团,比如,会派两个人打前站, 提前几天去演出地,在那里的热闹场所贴上演出海报。这一回也是如此。 于是,五百米街上,贴着海报了,除此之外,几个村的小卖部那里,也贴 了,诊所那里,也贴上了。刘家正叫住那贴海报的,随手把海报揭了下来 ,他说:“诊所的墙上,不好贴这样的东西,贴小卖部去吧。”刘氏剧团 的先锋说:“奇怪了,为什么这里贴不得?”刘家正就让他看墙上的板报 ,这些板报每周一换,都是提醒人们最近要注意些什么的,比如现在近年 底了,各家杀鸡宰羊,汤汤水水难免油腻,诊所就提醒家里有胆结石的病 人,一定要小心,不要让他们多沾油腻。海报一贴,就盖住板报了。 “小卖部早就贴上了。”贴海报的人多少有点委屈。 刘家正就笑笑,说:“你贴到刺棚庙去。”他这样说,算是幽了我一 默。贴海报的人得了台阶,便认真问刺棚庙的方向,刘家正一挥白袖,说 :“向东,一直向东,到了海边,没有路了,就到了。”他这一挥白袖, 把贴海报的吓了一跳,说:“太像了,你实在太像我们团长了!”这个时 候,已经聚拢几个看热闹的人了,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又飞快走开,好像 听到了很不该听到的话。 这几个背影瞬间定格在刘家正的视网膜上。 刘家正最怕那些突然转身的背影,一些旧经验壁虎一样窜上心头,他 没有马上把这只壁虎赶跑,却盯住它绿幽幽的眼睛,在那里跟自己过不去 :这就是被遗弃的感觉吗?所有的人都转身离去,他们的背影在说,我们 不需要你!是的,我们不需要你!你有学历?有学历的人,多了!你有经 验吗?你没有!甚至,连长得好看也是罪过,有个矮胖的人事处长就是这 么说的,你学什么医啊?该去当演员的!也许,他是嫉妒了,但说到底, 他们不需要他,这是千真万确的。履历表到处投,也参加过考试,有两回 都进了二选一了,最后被刷的还是他。人家给的理由,刘家正总是听不明 白,人家急速地说完,急速地转身,刘家正的眼睛里扎扎实实都是人家硬 直的背。这些背影,刘家正觉得都是从他的那些旧梦里跳出来的。他反复 地做过一个同样的梦,他走向他的爸爸,走到跟前了,他伸出手去,想碰 触爸爸高大结实的身体,还没来得及抬头看清面容呢,爸爸就急速地转身 ,飞快离开了,刘家正想追,跑不动,只好朝着那团灰色的背影大叫:爸 爸爸爸!没有一回叫出声音来。 矮胖人事处长那里,是最后一回,刘家正到现在还无法忘记他大张的 嘴巴里的龋齿,发炎的牙周,他的口腔就有了异常的红与黑,口臭自然是 症状之一,这人肠胃也不好,刘家正听他说着话,一边给他诊断着,但到 底没有把诊断结果说出去——人家不给他面子,那是人家的事,他总是给 人家面子的。你要是生活在从小被教导要给人留情面的环境里,你也会和 刘家正一样行事。刘家正也明白,这样窝囊得很。他是没有条件窝囊的, 他没有可靠的父母,他甚至没有父亲,他该强硬霸道点的,可他就是没学 会,连外表上的强硬,他也没学会,长着一张好人家孩子才有的脸,恭顺 ,纯净,透明。有人这么说过他,说他肯定是好人家出来的。刘家正也不 好硬说自己不是好人家出来的,那次求职穿的名牌西装,还是借室友的, 裤子明显太短,吊起来了,但那时候是坐着,人家看不到,或者他离开时 ,人家看到了吧?不知道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他好歹把那只壁虎摁住了,穿过这间用于当诊所的堂屋,往里面走, 一边喊着:“妈——” 小素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妈妈这就好了,饿坏了吧?快拿好筷子, 坐下等吧。”刘家正照做了,只要看到妈妈,那只壁虎,就不见了。现在 ,他是在自家的厨房里等着吃妈妈给他准备的早饭,他依然是妈妈的心肝 宝贝,无论如何,妈妈是绝对需要他的,就像他绝对需要妈妈一样,需要 和被需要,紧密粘合,就像汤团的糯米粉和芝麻馅一样。刘家正吃着汤团 ,吃着新腌好的苔条,一抬眼,看到了小素新修的眉毛,他笑了:“妈, 那么细那么弯,现在不流行了,这样吧,下回我帮你修。”小素侧过脸, 让眉弓更立体些,说:“真是太细太弯了吗?”语气带了点娇嗔。刘家正 连忙说:“还好,只是再粗直一点会更好,反正,下回我来帮你就是了。 ”两人说笑着。窗外呼呼地有北风吹过,已经是农历十二月十八了,这个 时节,海上大风多,出海的渔船都陆续回港过年来了。刘家正随口问:“ 这会儿打的是什么暴?”长白人把刮大风叫做打暴,每个时节打的暴都有 自己的名字。小素想了想才有答案:“十二月初五乌龟暴,十二月十八沙 和尚过江暴。这个暴是沙和尚。”娘俩为这个名字又笑了一回,真个奇怪 ,和沙和尚什么关系啊,戏看多了,乱联想。小素说:“年纪大了,记性 不好了,年轻的时候,一年到头的暴名,我顺口就下!也是,不记也得记 ,要估摸你爸爸拢洋日子呀。打暴前多数是回来的。” 小素现在说的“你爸爸”就是刘效懋说到过的刘卫,刘家正不知道小 素这会儿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刚才门口的这场对话,她肯定听到的。谁是 刘家正的亲爸爸,长白岛人谁不知道?小素还是接着自己的话题,说:“ 我们也得准备祭祖了,你爷爷奶奶铁定惦记着了。”爷爷奶奶是毫无悬念 的,就是刘卫的爹和娘。刘家正对5岁前海难丧生的爸爸全无记忆,爷爷是 他高二那年没的,奶奶是去年他主持葬礼送上山的,他自然都记得,爷爷 奶奶待他不坏,却也是淡淡的,毕竟,亲不起来。刘家正这会儿多少是听 明白了,妈妈不过是在提醒他,无论人家怎么说,你是堂堂正正的刘卫的 儿子,在谁面前,都不用失态的。刘家正不说话了,他又看了看妈妈的眉 毛,觉得它们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修得弯,虽然是过时的式样,但妩媚, 还是在那里的。 说起年纪,这里也明确一下,刘家正今年26岁,小素今年44岁,小素 18岁那年生的他。刘家正高中到城里读,看到同学的妈妈都是要吃惊一下 :怎么这么老?在长白时,他光觉得自己的妈妈比人家的妈妈长得更好看 ,收拾得更齐整些,也不觉得妈妈有多年轻,妈妈总是妈妈,足够老才能 当妈妈的。醒觉时,他心里一划拉,才知道妈妈原来是在和他差不多的年 纪就做了妈妈!这个发现,让他惴惴不安,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盯住女同学 的肚子出神,那里会藏着一个小宝宝吗?后来班里一个女同学莫名其妙请 了一个星期的假,回来上课时脸色惨白惨白,就有传言说她去流产了,家 里捂得严,是她自己嘴不严和最要好的女同学说了,最要好的女同学又和 最要好的女同学说了,反正就是这么回事情。那以后,刘家正看见这个女 同学总是又恐惧又怜惜,就是见她做值日倒个垃圾,他也恨不得帮她去倒 。有一回大扫除,值日组长居然派她去提水,刘家正黑赤着脸跑过去,抢 了她手中的红塑料提桶,来回帮着提了三趟水,让同寝室的哥们起哄了半 天。后来,实在熬不过,说出了理由:我妈是18岁生的我啊!从此,那女 同学就被叫做刘家正的小妈。除了这“小妈”事件,刘家正几乎是和女同 学绝缘的,只晓得埋头读书。自从刘家正开始长喉结起,妈妈就经常念叨 ,带着笑:以后可不要有了媳妇就忘了娘哦!这样的戏谑,一直在刘家正 的发育过程里重复着。难得有那么几回,刘家正和女同学近乎些,说话间 有点亲昵的意味了,对望的眼睛里开始有隐约的小火焰了,他却突然不安 起来:这个时候,妈妈一个人很清冷吧?一张脸就陡然冷峻下来,走开去 ,静默地用功了。 每学期开学前几天,夜里总能听到妈妈捂在被窝里抽抽搭搭,第二天起 来,妈妈却仍旧是笑眯眯的。刘家正也在奇怪,他们这样的人家,该有个 愁眉苦脸的妈妈才算应景,偏偏妈妈倒是笑的时候多,甚至哼着越剧做活 ——刘家正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是因为能收到汇款单吗?去城里读高中 以后,开学前几天,总会收到一张汇款单。有一回邮递员来,妈妈还在宕 口敲石子,刘家正从抽屉翻出妈妈的私章代收了,他注意了一下汇款人: 刘效懋。妈妈说那是一个远房亲戚。刘家正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从 小他就被人一再暗示他和一个叫刘小毛的有血缘关系,刘小毛,刘效懋, 一听读音就知道是他改的名。这名字倒是改得不错。前几年刘家正回家来 ,总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书,问了妈妈,说也是那个远方亲戚寄来的。寄 了有两年吧,妈还特意叫人做了个小书柜,整整齐齐码在那里。她居然也 翻那些书,刘家正那会儿才把妈妈和书本连在一起,原来妈妈也是初中毕 业的,不过,他想,她是看不懂的。却还在看。两年之后,突然就不寄书 来了。刘家正大学一毕业,学费也不寄了。这个人就突然从他们的生活里 淡出了,就像那些突然转身的背影一样。 五、白衣人 航船载着刘氏越剧团,离长白岛越来越近。刘效懋的鼻腔放开了,和 天地等大,云朵的碎边、海鸥的羽毛、礁石上的淡菜、码头立柱上密密麻 麻的藤壶,那些气息分丝分缕排着队进入他的鼻腔。色泽也在侵目而来, 天空瓦蓝太阳橘红海水蟹壳青浪花珍珠白,一浪一浪,冲着他们夹了金丝 银线的绸缎戏服而来。刘效懋用了十二分的定力,才将这些气味和颜色推 到一米线外。刘效懋有点怕了。 上码头后,刘小毛就叫乐师们拣几样嘹亮的,拣几样婉转的,前头吹 奏,两个女演员穿闪光紧身红色鱼鳞装,另外两个女的脸上涂得黑黑亮亮 扮成包拯,还有白纱衣白头巾的白衣观音,后面跟个一身红的善财童子, 最后是一列天兵天将,举着靛蓝和金黄的铁锤,随意摇摆着。一伙人在音 乐声中,在大风中,衣袂飘飘,缓缓前进。这是刘小毛的梦之队列,辉煌 ,精致,用来对抗长白岛渺小与粗糙的。一路是夹道欢迎的人。刘效懋甚 至还叫人准备了糖果,打算分给来捣乱的男孩子们,他们会扯掉演员的戏 服,会抢演员的道具。可是,这一路上就是没有捣乱的孩子来,难道是都 在上学吗?可这会儿正好是放学时候呀?刘效懋想起当初师傅的越剧团也 是这样一路招摇着,队伍里滚动着大男孩小男孩,活泼泼的,刘小毛也在 其中。 刘效懋和小茶走在队伍的最后。小茶穿着剧团新添的白色鱼鳞装,刘 效懋不喜欢,红是鲜血的颜色,是准备着受难重生的颜色,白色哪有这劲 道?但小茶喜欢。那就添了。小茶说:“像婚纱呢!”这话,刘效懋爱听 。此刻,小茶走在风中,水袖和裙摆被风鼓满,从胸口到臀部的片片鱼鳞 紧贴着身子微微起伏,这身段就显得无比玲珑无比柔软。“哦!白鲤鱼! 白鲤鱼!”一路时不时有人这样欢呼,小茶颀长的颈脖如天鹅一般仰着, 小茶挽住刘效懋的手臂,凑到他耳边说:“你这是演衣锦还乡吧?” 队伍即将进入村口,刘效懋掰开了小茶,说:“手麻了。”快步走到 队伍前头,预备着要跟村里的老前辈们打招呼了。刘效懋的心头,热辣而 又毛糙,所有神经都兴奋昂扬,像是登台前提早地进入了角色的状态。在 一个刹那,刘效懋在队伍中看到了刘小毛,他执拗地盯着他,眼珠闪闪发 亮。 队伍吹吹打打,村里的每户人家,门口都站着人了,天冷,大家都穿 得肥嘟嘟的。长白岛上,有空调的人家屈指可数,那空调,也是用来夏天 热得光了膀子还是热的日子用一用,冬天是决然不用的,多穿几件衣服就 得。这里已经进入大湾,从岛最东的大海湾吹来的风,肆意地掀动着观音 的白纱,鲤鱼精的鱼鳞。所有的人都替那几个女孩子受冻,一个个把身子 缩得更紧了。 这个时候,刘家正的诊所里,一个中年渔民正举着受伤的手指让刘家 正包扎,刚才刘家正取掉了他甲盖上几片碎指甲。趁着拢洋,他修理船上 那些平日里无暇顾及的铰链啊合叶啊,一锤子下去,就砸在自己手指上了 ,指甲都裂开了。刘家正好奇,问他:“要是在船上可怎么办呢?”他回 答:“能怎么办?海水一浸,自己包扎了,一样干活!”刘家正想想那海 水渍伤口的痛,牙根先发酸了,那渔民却是一副等闲模样,这会儿他也看 见鲤鱼精了,他嚷道:“天哪,鲤鱼精!穿那么单,还不把这些小娘们的 嫩皮肉冻紫冻僵?!”刘家正说:“她们里面穿了衣服的。” “看不出啊?” “很薄很保暖的,比如天鹅绒,比如贴身羊绒啊羽绒啊……”他没说 下去,女生宿舍窗前飘动的那些贴身衣物,现在清清楚楚地晃在眼前了。 窗外的吹打声不知怎么突然停了下来,村里各家各户都装着的有线广 播里,气象报告的声音就瞬时放大:“……西北风,七到八级……”那渔 民笑了,说:“这个刘小毛!他倒还记得这些老规矩!”这个老习惯就是 ,每到播气象的时候,岛上的一切都要安静下来。如果你有亲人在海上, 你也会这样,一到那时候,你就放下手中的活儿,屏息倾听。 包扎好了。那渔民拉着刘家正,站到门口,还来得及看到队伍的背影 。那渔民让刘家正看仔细些,一个个都这么苗条细巧的,里面果真穿着天 鹅绒啊羊绒羽绒吗?不可能! 队伍后面的小茶听到这句话了,她回过头来,对着他们灿然一笑。笑 过之后,她就愣在那里了,天,那个穿着白大褂的男的,不就是年轻的刘 效懋吗?脸上多了副黑框眼镜,皮肤更加白皙有光。她站在那里。队伍都 走远了,她还站在那里,她落单了。 “她看着你哩。”那渔民笑了,他完全知道那女的为什么会这样。这 个遗传,说来真是奇怪,你越要掩盖着,它越要显形了让你看,不单长相 像,连走路的样子,连皱着眉头的专注样子,也都像。胎里带来的东西, 最毒了。 刘家正朝她笑着挥挥手,又指了指她的身后,示意她队伍已经走远了 。小茶这才清醒过来,转身小跑着追赶队伍去了,边跑边回头,不相信似 的,那背影就带点莽撞了。刘家正看着她,心里好笑,也有点温暖,这些 女孩子,就是这样!他想起他那些活泼的女同学了。对这个背影,刘家正 居然没有平常那样的反应,因为这个背影会恋恋不舍,会频频回头。小茶 就是这样,跑两三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他一眼。刘家正一直站在门口, 迎接着她一次又一次的回眸,有一回,他甚至看到她眼睛里闪烁着的小火 焰了,就像从前在一个喜欢他的女同学眼睛里看到的那样。 小茶追上了刘效懋,气喘吁吁地问他:“你见过诊所里那个医生了吗 ?那个人长得和你一模一样!还有,那个诊所,看上去比城里的社区诊所 更漂亮哎!” 刘效懋说:“真的吗?” 上码头后,刘效懋就陷在他的恍惚里,现在,小茶也陪着他恍惚上了 。小茶的眼前,一直晃悠着那个年轻人的面容。从家里回来后,小茶一直 在傻想,如果刘效懋再年轻些,那是什么样子呢?想不到,在这个岛上, 在这个白衣人的身上,她看到了。太阳亮得耀眼,她拿水袖去遮,白色, 也笼罩住她了。 六、诊所 非说说这个诊所不可了。但还是先绕回来说我的刺棚庙。长白岛为什 么会给一个戏文班子那么高的礼遇?是因为戏文吗?当然是。茫茫大海之 上,长白岛像只小船,日听风,夜听雨,日子一日与一日何其相似,久了 ,寂寞来了,忧郁来了,只是他们不觉得,习惯了。一个戏文班子,热闹 的锣鼓,缠绵的丝弦,揪心的故事,把他们积攒了一年的眼泪和欢笑都催 发出来,痛快哭,痛快笑,一年中那些等待的日子,一些委屈,借着台上 的戏文还过魂来。那戏文,就是浇块垒的酒了。戏文散场之后,随班的医 生就会被求医的人团团围住。戏文里面,那些时运不济的读书人,往往都 做了妙手回春的医生,这个随班的医生,就像是戏文里走出来的国手,任 何疑难杂症都难不倒他,因此,伴随着戏文班子的来去,留下的往往是神 乎其神的神医故事。长白岛孤悬于海,良医难求,这样的传说便愈加神秘 ,对医生崇拜到建个庙宇来祭祀,也就毫不奇怪了。 除了电,长白岛处处自足,连乡卫生院的医生,也是“定向培养”的 :初中毕业后读了两年市里的卫校,接着就分配到长白岛做了医生。长白 人对只学了两年就会看病的医生到底放心不下,一些小毛小病,又不肯隆 重地渡海求医,于是,我这个庙宇中的木雕医生就成了长白人的良医。有 点头痛脑热,他们就搬到庙宇的小屋里睡上一两天,也许刺棚庙的鸟语花 香,有着比一般的抗生素与病毒灵更强的药效,也许,他们欠缺的就是充 足的睡眠与休息,住过两三天之后,他们就能神清气爽地回去了。我的名 声就这样越来越响亮。但,总有些清醒的人,看到了我的无力。这些清醒 的人,一听到刘家正有回岛开诊所的设想,他们就快速地行动起来,帮着 小素通融了乡政府,让小素翻新旧房。现在正是开发时期,为了赔偿土地 时少些纠纷,一切土建都被冻结,惟独对小素网开一面,起先乡政府还害 怕有人会跳出来有样学样,但他们很快放心了,没有一个人对此有异议。 一个读了五年医科大学的医生,正宗!对这样的热忱,刘家正多少是有些 感动的,但是,开一个像模像样的诊所,购置些必不可少的器材,那是要 花好大一笔钱的。这钱,居然也有了,募捐来的。长白岛上造的三座庙, 都是一帮吃斋念佛的老太太挨家挨户募捐来的,她们把这热情用在修诊所 上,居然,事也成了。 有了这笔钱,诊所就一日一日像样起来,就像小茶所观察到的那样, 这个诊所一点也不比城里的社区诊所差。最惹眼的是玻璃移门上两个鲜红 的十字,虽然这里的老太太们对信基督的天然有排斥感,可是,这两个红 十字,她们却欢喜。洁白的地砖,雪白的墙壁,蓝色的玻璃钢椅,小素每 时每刻让它们闪烁光泽;医生的办公桌甚至比大医院里还气派,靠墙的左 手边,堆着一摞医疗档案,大湾人都在那里有一份存着,因为这个,大湾 人在前岸后岸礁门人那里有了骄傲的资本。平常感觉有一点点不对头,就 可以去找自己的医生看,量血压,测心跳,化验个血常规也行啊,就是没 有B超机,不过不着急,总会有的。至于一些普通的外科,诊所里有消毒过 的镊子啊钳子啊剪刀啊纱布啊,齐整地放在橱柜里,让人看着安心。大湾 人以前对付皮肉擦伤或小疽小痈,都用白糖止血用草药吸脓,有个小姑娘 家在正发育着的乳房边生了个疮,也就是这么对付,结果小疮长大痈,大 痈最后被草药敷好了,一个乳房的组织却全烂完了。如今好了,有了这个 诊所,就不会出这样的事情了。现在,长白岛上别的那几个村落,也时兴 到诊所来建个档案,什么时候发过烧什么时候拉过肚子,这里都有记录, 不用特意珍藏病历卡了。岛上的人看重自己的档案。每个人的档案都放在 一个淡蓝色透明的文件袋里,按姓氏的拼音排列安放。他们对刘家正的记 忆力,也是佩服的,只要来过一回,第二回来刘家正就能记起他的病,就 能一下子找出他的档案袋来。 肝病或胆病,岛上最多了,刘家正开过这样的玩笑,出去我可以去做 肝胆专家了。长白人说的“出去”,就是离开岛另谋生路去,听的人就会 讪笑起来,说:“刘大夫可千万别丢下我们啊,我都在你这里上了档呢! ”说也奇怪,自从诊所开起来后,大湾的老人们这两年居然都没有病死过 ——死在自家床上睡着一样离开的,那另当别论。这岛马上要开发了呢, 据说是按人头赔偿的,老人们一下子觉得自己值钱起来,得好好活着。说 书的老先生也经常过来,他有点高血压,时不时来量一下,他说:“养病 比治病要紧呢,所以,首长们都有保健医生,现在啊,我们也有保健医生 了不是?”他说话尾音悠长,那感觉是言外之意无尽,听的人就说,是啊 是啊,言语中都是一派欢喜。小素听了也高兴,夏天,她就烧壶菊花茶凉 在那里,冬天则是热水瓶只只灌满,来人了就倒上一杯,说,暖暖手吧。 无形当中,这诊所就有点像茶馆了。刘家正对此毫无办法。他想安静看些 书,医生是要不断进修的。他的目标是要把全科医生的资格考出来。刘家 正不要那种培训一年就可上岗的“全科医生”称号,他要的是通过了25科 考试的正儿八经的全科医生资格,像他这样刚过了执业资格的,还得等六 年才能考这个“全科医生”,但刘家正不怕等。虽然是回长白岛了,但他 对自己不能马虎,刘家正从来就不是个马虎的人。刘家正仍旧像学生时代 一样,学习到深夜,要么读书,要么上网看看专业论坛,真要感谢互联网 ,即使在长白岛,他一样也了解整个“医学界”;偶尔,他也上基层医生 论坛,他就看看,很少发帖跟帖,在那里,他能看到像他这样的人,看来 ,大学毕业后回家开诊所的,也不止他一个,他看他们讨论怎样在农村行 医,怎样注意药品的配伍,甚至怎样输液——在他们这样的小诊所里,医 生同时也是护士。如果有个护士该多好啊,尽管妈妈也在帮忙,但那和一 个正儿八经的护士,完全是两码事情。 小素担心他这样过于劳累,老是要过去催他早睡,有时把他拉到自己 房间,逼他看会儿电视,刘家正也听话,乖乖过去,把台选来选去,最后 还是定在原先的戏曲频道。小素说:“你看你自己喜欢看的呀。”刘家正 说:“我真的喜欢看戏曲的。”比如《追鱼》,他既看过徐玉兰和王文娟 的1959年版本的,也看过张国凤王志萍新版的,他和妈妈一起讨论,一致 认为新版的没法和老版的比,妈妈说:“怎么可以让鲤鱼精穿白衣服呢? 又不是白蛇!”小素对越剧一直抱着一种狂热,大凡她能看搜罗到的资料 ,比如在村办公室看到有越剧方面消息的报纸,她必定讨了来,郑重地剪 下来藏好,自从有了戏剧频道,就等于又多了个窗口——尽管越剧在那里 占的份额,也是不多。她是在为日后可能有的见面积累谈话的资料吗?两 个没有共同谈资的人就分属两个世界了,妈妈这样做,大概就为了能和那 个人拥有同一个世界吧。这样的揣度,刘家正无法说出口去,想到最后, 他又会问一句:会有人这样来爱我吗?他几乎是羡慕妈妈了,她有爱,而 他,没有。 这样和妈妈一起看戏曲的夜晚一个月不过一两次,平常的日子,刘家 正总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或上网,也是值夜班——难免总得出几趟夜诊 的。长白岛的夜是安静的,他放了张CD,把音量调得低低的。这些音乐大 多是西方的经典,这方面的知识,他是读一本《爱乐》杂志得的,半懂不 懂,隔得很,总没有陪妈妈看的越剧那么天然亲近;但他依旧听勃拉姆斯 听莫扎特——这些乐曲像一层帷幕,把他和长白岛安全地隔开了。 后来,是说书老先生看出了刘家正的苦恼。他叫来漆匠在诊所墙上描 了个“静”字。漆匠很尽力地把这个字描摹得跟他在大医院里见过的一般 板正。聊天的场地,就自然又挪到小卖部去,那里本就像个茶馆,买点饼 干喝瓶啤酒,就好闲扯一个下午。 小素有点失落,刘家正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刘家正知道妈妈的想法, 这诊所是大家募捐修的呢,你怎么好意思不热乎招待人家?刘家正对着小 素的歉疚,自责就多了起来,妈妈这辈子好像总是活在对别人的歉疚中, 自己的回来,真的是对妈妈好吗?刘家正在岛外工作的几个同学,节假日 回家探亲,对刘家正的甘之如饴,他们想不通,有一个话说得有点意思: “刘家正,我看啊,以后长白人也会替你塑个像,放在刺棚庙张先生旁边 。”刘家正笑笑。说话的那个同学,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正经固定的工作, 也就是在岛外漂着,可是,他已经在鸟瞰这个长白岛了。 刘家正真的来我的庙里了。这不是他第一次来,从会走路起,他就跟 这岛上别的孩子一样,跟在妈妈身后一年到我这里来好几趟,所有的妈妈 都求我保佑她们的孩子像小狗一样活蹦乱跳,小素的祈祷特别让我感动: 刘家正一生所有的病痛,请张先生把它们转给我,我来受。 他到了我跟前,学他妈妈的样子,为我点燃了一根香烟,他自己也点 一根。一根完了,他再为我点上一根,他自己也再来一根。到第四根的时 候,他突然害怕起来,他看着我的雕像,轻轻地问:“你真的在吗?”问 完之后,他自己就笑了。他说:“我真不能再抽了,一个医生抽烟,不好 。”他就给我点上了第五根,看着烟头一明一灭。长白岛上的人都知道, 张先生是个老烟鬼,到了刺棚庙,敬烟,那是第一个表示敬意的仪式。刘 家正耸耸肩膀对我说:“喂,你不会是个鸦片鬼吧?你那个时候,你那样 的人,能不吸鸦片吗?” 我听着笑了。我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岛上 的人为什么把一个老烟鬼供为神医呢? 刘家正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多,尤其是大风暴来临前,他必到。潮头 就在离我的庙不到两百米的地方翻滚着。他和守庙的老头巡视门窗,有两 回,他还特意加固了东窗。老头和刘家正闲话:“刘大夫,你那里是诊所 ,张先生这里,也是诊所呢!”刘家正说:“是啊,他是我前辈。”这句 表示敬意的话,被那个老头转了好几道弯,转到最后,那意思竟成了刘家 正身上附着我的魂,我就是刘家正,刘家正就是我。大多数的长白人都把 老头的话当迷糊话听。P10-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