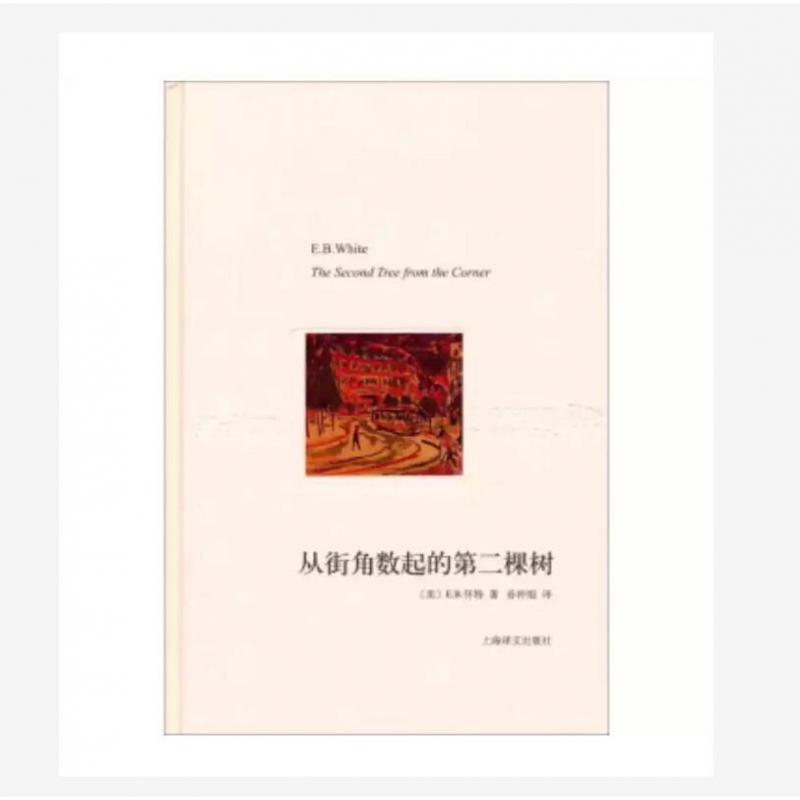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36.40
折扣购买: 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译文随笔)
ISBN: 97875327655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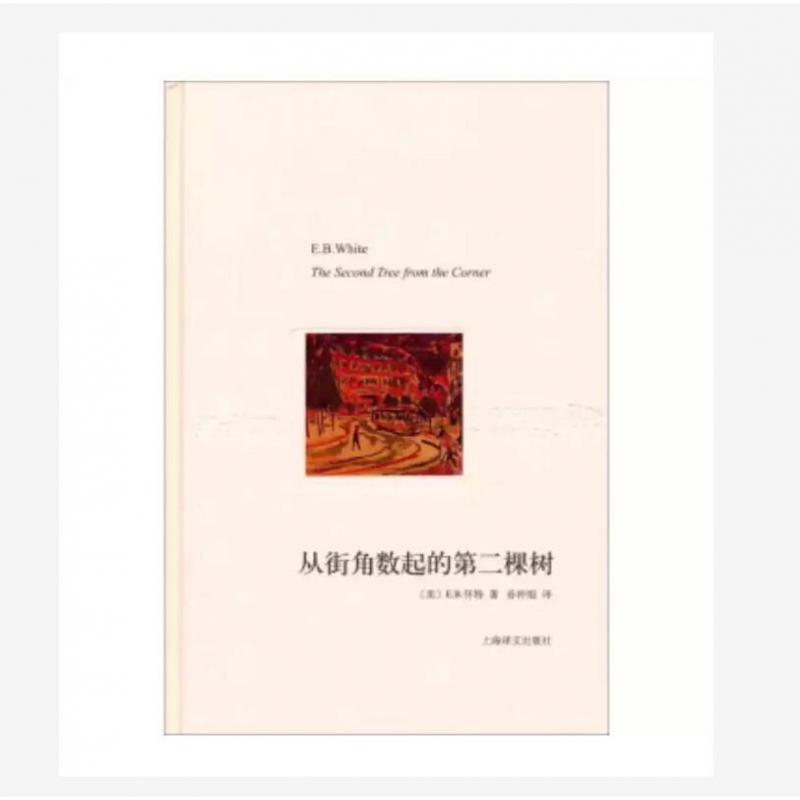
对于波士顿的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来说,动手术的 好处之一,就是有资格在手术前一天晚上就住进医院 。简而言之,这让他不再流连街头。我得到命令,须 不迟于星期四下午三点去住院部登记入住,尽管到第 二天上午八点我才会失去鼻甲骨。这让我得以在舒服 的环境下彻底休息十七个钟头,空度了后半个下午, 腋下出汗,用盖布擦干湿漉漉的手掌,让我感到惊奇 的,是一系列奇怪的事情,让一个人不偏不离地走向 一次并无大碍的不幸事件,例如鼻部手术。至于要失 去一块鼻甲骨(听上去好像海军有可能在他们的小型 巡洋舰上用得着),我根本没感到很遗憾。事实上, 人到中年,对自己身上的几乎每一部分,他都会毫不 犹豫地交给有关当局。到了我这把年纪,拿掉什么东 西正是求之不得。长着中鼻甲骨过了半辈子,除了最 斤斤计较的人,谁都会觉得够意思了。 我想医院在剑桥那边,但是又拿不准,因为我开 车出去时,情绪很低落,每逢这种时候,我从来不会 留意自己去了哪儿。不管怎么样,医院那里很不错, 靠近一条水流和缓的小河(十有八九是查尔斯河),正 好在我的窗户外面,有一棵漂亮的大橡树。病房很小 ,我也如此。床是可以摇起来的标准床,配齐了可以 抽出来的床单、橡胶垫、呼叫钮等等。我原想着床头 应该有一只天鹅,就像公园里的游船那样,不过就算 没有天鹅,比起在波士顿临时去找时通常所预期的, 这样的住处还要更理想一点。 好像没什么好理由马上就睡觉,我就只是手里拿 了本《大西洋月刊》坐在一张踏脚凳上。过了一会儿 ,有位护士进来。 “我是马尔奎尼小姐。”她通知我说。 “我叫怀特,”我回答道,“我的体温是九十八 点六,脉搏是每分钟七十二次,血压是低压八十,高 压一百四,除非我对所做的事情感兴趣时,血压会急 升。我来这儿做鼻甲骨切除术。”马尔奎尼小姐过来 坐到我旁边,她把听诊器挂到脖子上,拿出一支铅笔 和一张空白表格就冲我来了。 “你的职业是什么?” “作家。”我想了想说。 这位护士露出心知肚明的微笑,一位女士在没有 因为男士和他们小小的自负而轻易上当时,就会那样 微笑。接下来,她开始详细登记我的衣服和个人物品 。关于我的衣物,她好像有点拿不准。“你裤子里面 穿的是什么?”她问我,一边沉思着把铅笔在嘴里蘸 。 “我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道,“穿衣服好像是 很多年前的事,今天早上好像是一百万年以前。” “嗯,你肯定穿了什么。我该怎么写?” “佩斯利围巾?”我这样提议。她想一想写下了 “内衣”,然后把清单递给我让我签名。之后她为我 量了体温、血压和脉搏。我的体温是九十八点六,我 的脉搏是每分钟七十二次,我的血压是低压八十,高 压一百四。“你还是睡觉吧。”她意味深长地说。马 尔奎尼小姐就走了。 躺在床上,我感觉放松而惬意,跟我想像死后会 感到的一样。我没躺多久,又来了位护士。她身穿实 习生制服,一脸高贵的样子,一个人在干了很多活却 无分文报酬时,就会表现得那样——当然,她正是如 此。她端详了我一番。 “你的卡片上写着你是个作家,”她开口了,“ 可是我从来没听说过你。” “你是专门来念叨我没能混出名吗?”我问。 “不是,我来是给你擦背的。”她关上门,我大 度地允许她给我擦背。后来我拿到一份镇静药,混混 沌沌地一口气睡将过去。 手术做得不错。从我的病房到手术室的那一趟, 我走得很高兴,因为对于一个活动范围被严加限制的 人来说,不管怎样出去一趟,都会感到开心。吗啡让 我话多起来,我们在走廊上等手术医生赶来时,我和 护工旁若无人地猛聊了一通渔具。那间医院里有几位 身份很显赫的人做义工,这位护工看着面熟。我不能 一口咬定就是,可是我想那是索顿斯托尔州长。这年 头,就连在床上,你都永远说不准会碰到谁。几分钟 后,看到主刀医生出现在楼里的另一边,有人叫州长 继续往里推。他刚把我往通往手术室的门里推了一半 ,有位护士看到了,不满地咂嘴。“不,不,”她厌 烦地说,“那间是做胆囊手术的。” 州长又把我拉出来,我们去另外一间碰运气。我 小心地用手捂着腰,想来胆囊在那个位置。好像一切 正常。主刀医生很快来了,就开始工作。在我熟练的 指引下,就我所知,该切除的他都切除了,不该切除 的他都没切除。这次做得很完美,甚至在手术中间, 我得知他的父亲和我太太的娘家人有亲戚关系——不 是血缘上,而是在波士顿这里,神秘之线将其儿女愉 快而且令人满意地缠结在一起。 因为是战时,医院里当然也不轻松。一个平民住 进去,占用宝贵的空间,浪费护士、实习护士、护士 帮手和灰衣女士的时间和力气,仅此就让他感到难堪 。不过我发现医院里也有种新的活力,就其本身而言 ,跟以前一样仁慈和决断,但在每一方面,都称得上 离谱。病人人院时,会收到一本小册子,提醒他医院 里人手不够,要求他别去没必要地麻烦护士。但凡他 有一丝良知,就会不折不扣地照做,决心不去按呼叫 钮,除非他就要血流尽而死,要么是房间里失火。他 在惟形势紧急才算例外这方面走极端,以至于长远来 说,跟他在较为放松的情况下相比,他造成的麻烦可 能一样多。我下手术台后还不到两个钟头,吗啡的作 用还很强,鼻子还在流血,我不知不觉下了床,拄了 根撑窗户的杆,就去跟一扇气窗短兵相接了,我喜欢 跟敌人交手时荒唐的兴奋感。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 出这种力气远非我所能够,我勉强及时躺回被窝。她 们发现我下过床时,走廊上下唁闹一时。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