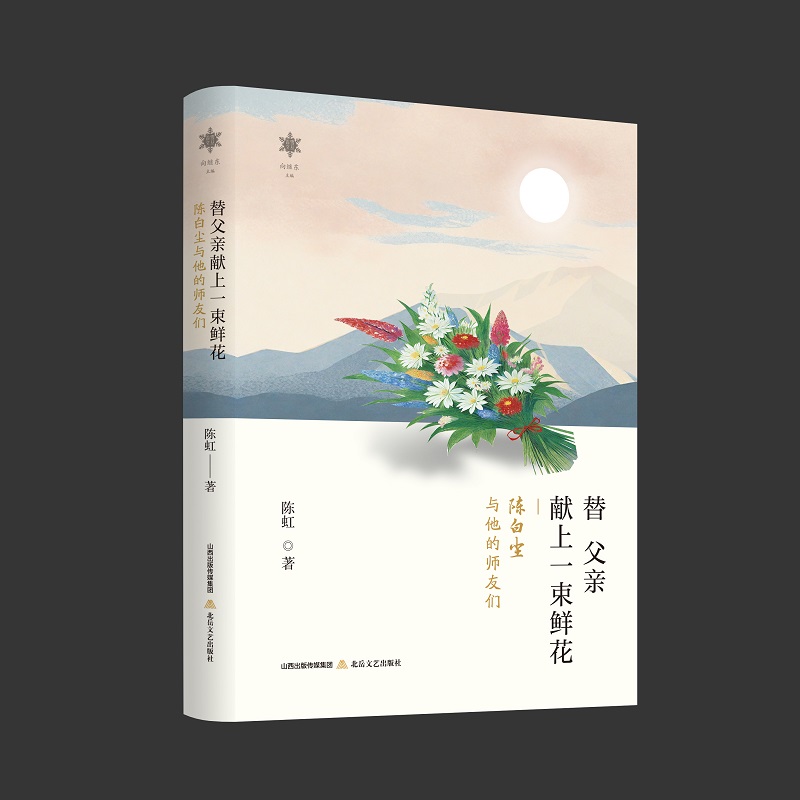
出版社: 北岳文艺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6.10
折扣购买: 替父亲献上一束鲜花:陈白尘与他的师友们
ISBN: 97875378683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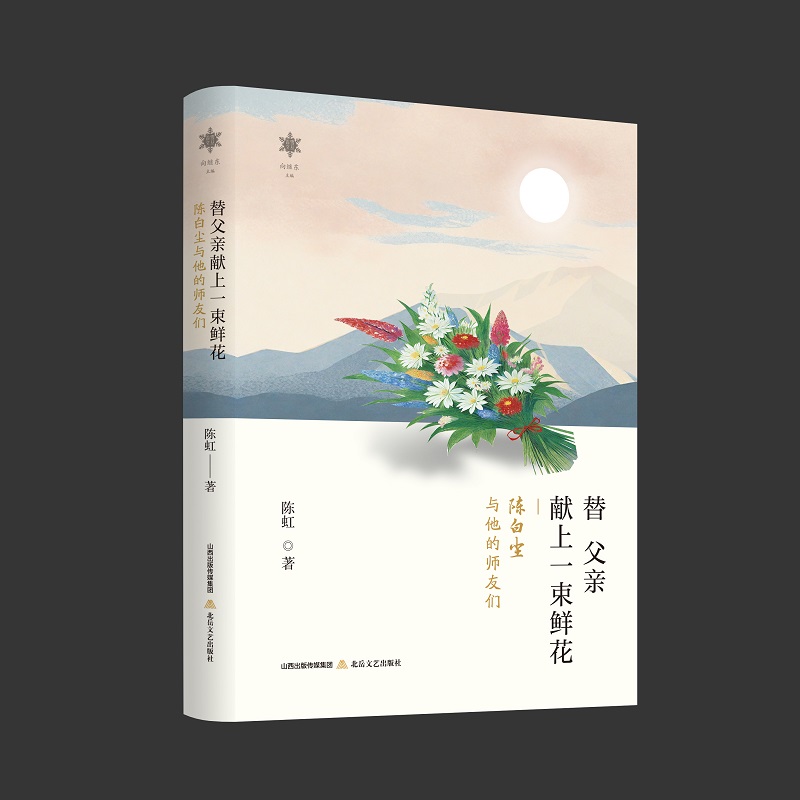
陈虹,女,,1948年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化史。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著作有:《陈白尘评传》《自有岁寒心:陈白尘纪传》《陈白尘:笑傲坎坷人生路》《日军炮火下的中国文人》《大师的抗战》等。
替父亲献上一束鲜花 ——纪念田汉先生120周年诞辰 那是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父亲在文章中这样回忆道:“在悲观失望甚至是绝望的心情之下,我和当时绝大多数的青年一样,总想找个栖息灵魂的处所。于是我在暑期招生的广告里,一眼发现上海艺术大学的文学科主任是田汉先生,便有似荒郊黑夜里发现了一丝灯光,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了……” 田汉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长的什么模样?第一次见到他时,还真让父亲颇感意外。——于无人之处时,常常紧锁眉头,但是只要和学生们在一起,便笑逐颜开。年仅十九岁的父亲情不自禁地想走近他的身边,走进他的心灵。第六感觉告诉父亲,田汉先生不仅与同学们年龄相近,而且思想也相通,都是被那场大革命裹挟进去而最终又被甩了出来的人。 然而,能够成为田汉先生的入门弟子,这究竟是有幸,还是不幸呢?一开始父亲还真的说不清楚,无论从性格作风上讲,还是从为人处世上说,师生二人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比如说录取新生吧,陈凝秋 (塞克)、左明、唐叔明等人,报名时分明都是身无分文,竟然还理直气壮,非要进来不可。田汉先生便微微一笑,不仅免去了他们的学费,而且还免去了他们的食宿费。至于父亲自己,虽说勉强凑足了学费,但其他的所有开支同样是靠田汉先生“施舍”——父亲被批准为“半工半读生”,替学校刻钢板,印教材,当会计,管伙食……就这样,让一贫如洗的他终于完成了学业。田汉先生的解释是:“他们都有一种特色,就是他们都是‘辛苦人’,他们在懂得艺术以前都已经多少懂得生活,这也是我们这私学所以能建立起来的原因。” 为此,田汉先生提出了自己的办学主张:“培养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定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新时代之先驱。”这在当时,颇令父亲琢磨了好久好久。 再比如说上课吧,田汉先生要么不带课本,口若悬河,信马由缰,可以从文学起源讲起,一扯又能扯到历史上去,而从历史又能扯到哲学,但话题一转,又说到了莎士比亚,再转则又是易卜生、梅特林格……要么,干脆不讲课,带领大家一起排戏,甚至拍电影。虽说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南腔北调,吴语、粤语、川 调、京腔,大杂烩,但他一概不问,他要的只是真情和投入。结果,堂堂的一个文学科在田汉的主持下竟不由分说地变成了“戏剧科”……又要么,索性到校外请来一批文艺界的名流,如徐悲鸿、郁达夫、徐志摩、洪深、欧阳予倩、周信芳、万籁天等等,每隔半个月开一次座谈会。这种座谈会又是没有主题的,清茶一 杯,香烟数支,从随随便便的聊天中引出不同的题目,然后各抒己见,自由论争,渐渐形成一个百家争鸣的场面。这时所有的同学均围坐在外圈旁听,这可真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授课方式。父亲一开始适应不了,这能学到什么知识?然而渐渐地也习惯了起来——那种“十八扯”式的讲课,可以各取所需;那种实 践性质的排演,可以熟悉舞台;而别具一格的座谈会,则可令大家开阔眼界拓展思维……到后来,只要是田汉先生的课,不管哪个科的学生都要跑过来旁听。父亲形容他,就像是一块磁石,就像是一丛篝火…… 田汉先生膝下有一女,名叫田野,在南京工作,每逢见到我的父亲,开口闭口都称“叔叔”,她说这是因为南国社时期父亲和她爸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父亲无论如何不肯接受,他始终叫她“师妹”——辈分不能错啊! 要说“并肩作战”,这确实高抬了他的弟子们。对于那段历 史——跟随田汉先生读书的那段历史,父亲给我讲过两个故事: 其一,来自苏北小县城的土得掉渣的父亲,虽说操着一口极浓的淮阴土话,却被田汉汉先生所看中,屡屡分派他在戏中扮演一个小角色。先生说了,父亲的相貌不错,适合扮演心地善良的人物。于是父亲战战兢兢地上台了,先后在 《咖啡店之一夜》《父归》《苏州夜话》《江村小景》 等剧作中留下了不同的身影。 最终获得了老师的夸奖: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就拿 《咖啡店之一夜》 中的那个顾客甲来说吧,把该说的台词说完之后,便默默 地坐在角落里喝咖啡。尽管此时的父亲还从未品尝过咖啡是什么味道,但他却将想象中的那杯东西喝得有滋有味。 其二,后来,父亲没有继续演戏了,而是做了编剧,要说媒援,同样来自田汉先生排戏中的“身教”,20世纪20年代,话剧刚刚传入中国,许多戏的首场演出往往是连剧本都没有的。田汉先生也同样如此,他只是告诉大家一个故事梗概,一切均由学生上台后自由发挥,大胆创造。最后再经过他的推敲和比较、思考和提炼,而形成定稿。 晚年时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写总结道:“年事稍长,才悟出我演的那些配角,正是一门戏剧入门课,而参与 《苏州夜话》 和《江村小景》 的两次演出,则应该说是我从田先生那里学到了‘编剧法’。” 父亲始终视田汉先生为自己的恩师,而非“战友”。跟着他,不仅学会了如何编剧,更学会了怎样做人——他那令人敬佩的品节和令人刮目的风格,深深地影响了父亲一辈子。 从外表来看,田汉狂放不羁,属于浪漫主义的艺术家,而父亲则沉稳坚实,追求现实主义的道路,二人差距确实很大。尽管当年父亲和他的同学们也曾一起仿效过先生——“或者长发披肩,高视阔步;或者低首行吟,旁若无人;或者背诵台词,自我欣赏;或者男女并肩,高谈阔论。他们大都袋中无钱,却怡然自得,作艺术家状。”然而这些都属于表面现象,父亲真正从田汉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则是骨子里的东西——田汉乐观豪爽,从不知道什么是失败,什么是忧愁,父亲也豪爽乐观,从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什么是失败;田汉把话剧当成了他的生命,父亲也把生命献给了他的话剧事业;还有,田汉纯正率真,待人像水晶般的透明,透明到连自己都不会保护,父亲呢,也是如此,既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心,乃至二人于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均惨遭厄运,这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啊”! 这到底是因为潜移默化,还是因为着意效仿,我搞不清楚。但是作为恩师,田汉留给他的学生们的精神财富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说他的穷干加苦干的奋斗精神吧—— 一文不名,硬要拍 摄电影 《断笛余音》,去圆他那银色的梦;家徒四壁,硬是举办起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有名的艺术鱼龙会,大大地震惊了朝野;两手空空,更是勇敢地挑起了上海艺术大学校长的重担,而且后来更于筚路蓝缕之中创办起了南国艺术学院…… 就拿拍电影来说吧,既无摄影棚与水银灯,又无必需的服装和道具,但他无所谓,场景全部利用校园内的一切——画室、课堂、走廊、草坪……服装道具也一齐来个“自然主义”——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用什么:反正是自己演自己嘛!灯光呢,一律采用自然光,再不够,就用马粪纸糊上锡纸,做个反光镜……不管怎么说,《断笛余音》 是拍起来了,因为田先生说了:“艺术运动是应该由民间硬干起来,万不能依草附木!”他可真有魄力!再拿艺术鱼龙会来说吧,这是为期一周的师生同台演出。虽说田汉先生也请来了不少名角,但是“剧场”呢?那竟是上海艺大的一个大客厅!舞台以通向隔壁饭厅的两扇大拉门作台框,下 面垫高尺许,做成个平台,有人称它是“窗户式的舞台”,还真是一点也不过分。观众席呢?找来五六十张藤椅,排排整齐也就“滥竽充数”了。然而,无论是最早的剧目 《生之意志》《画家与其妹妹》《父归》《未完成的杰作》,以及 《苏州夜话》 和 《江村小景》 等等,还是后来田汉新创作的话剧 《名优之死》,以及欧阳予倩新问世的京剧 《潘金莲》,可都是通过这个“剧场”轰动 了整个中国南部的! 父亲真是打心底里敬佩他的老师!这不,当上海艺大的校长周勤豪终于露出了他那“野鸡大学”校长的嘴脸——侵吞了同的学费,而使学校陷入岌岌可危境地之时,全校师生以巴黎公社投票的方式,一致选举田汉为新的校长。没有候选人的提名, 没有幕后者的暗示,百余张选票上竟然写着同样一个名字:田汉! 再后来,那是 1928 年之初,周勤豪又卷土重来,光天化日之下抢走了学校的所有财产。这时的田汉索性袖子一捋,在西爱咸斯路371号的大门口挂上了南国艺术学院的招牌!那时,绝大多数的同学都紧紧地跟随他而去:再穷,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师田汉先生! 父亲说了:“在田汉老师的身教下,我才懂得与大家共甘苦、 和时代共呼吸的道理,我才跟随着他走向革命。总之,向他学习到怎样做人。”的确,当初父亲投考上海艺大,完全是为了“钻进象牙之塔里,将养这受伤的灵魂”,没想到短短一年的时间,他那“受伤的灵魂”,不但没有得到“将养”,反而被田汉的热情重新点燃,他笑着,唱着,投入伟大的“南国事业”中去了! 父亲一直到晚年都没有忘记那首由田汉填词、借用 《伏尔加船夫曲》 的曲调而谱写的 《棹歌》: 划,划, 划,划, 绿波春水走龙蛇, 问西湖毕竟属谁家? 南国风光, 新兴机运, 等闲莫使夕阳斜…… 它既是南国艺术学院的校歌,更是当时同学们在田汉先生的带领下以其私学的身份向着官学公开挑战的战歌。父亲告诉过 我,当年南国艺术学院的牌子,其实就是一张写春联的红纸,堂 而皇之地贴在了被人们嘲笑为“三等理发店”的门框上;父亲还告诉过我,这时的他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被压迫者的傲骨,什么是在野者的自尊与强大。五音不全的父亲,唱起 《棹歌》 来是那么的高亢——他以他是田汉先生的门生而骄傲,他以他是田汉先生的嫡传而自豪! 2018年9月 为纪念田汉先生120周年诞辰而作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