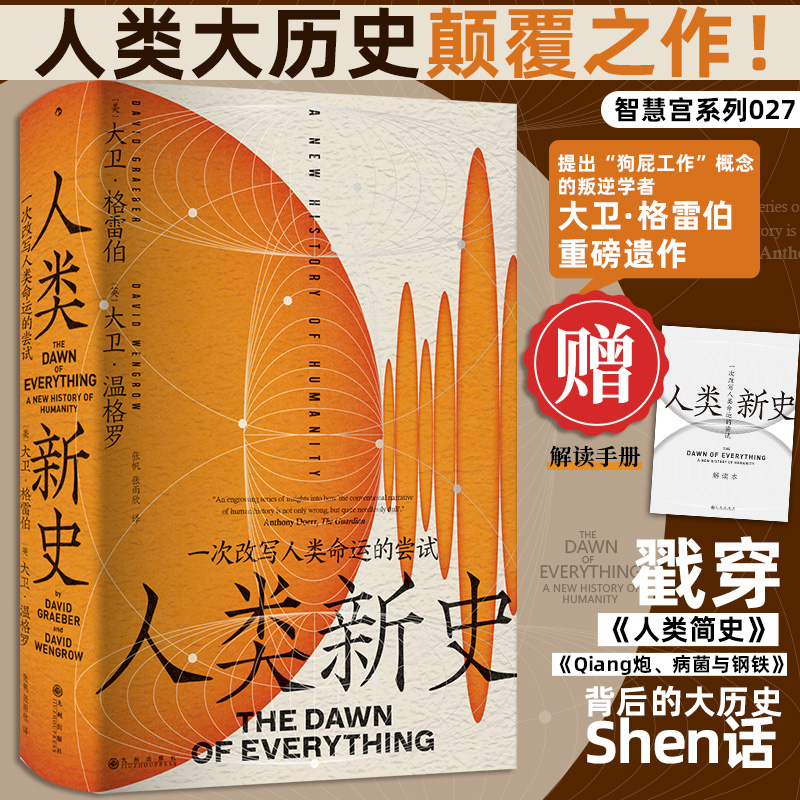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128.00
折扣价: 83.20
折扣购买: 人类新史
ISBN: 9787522527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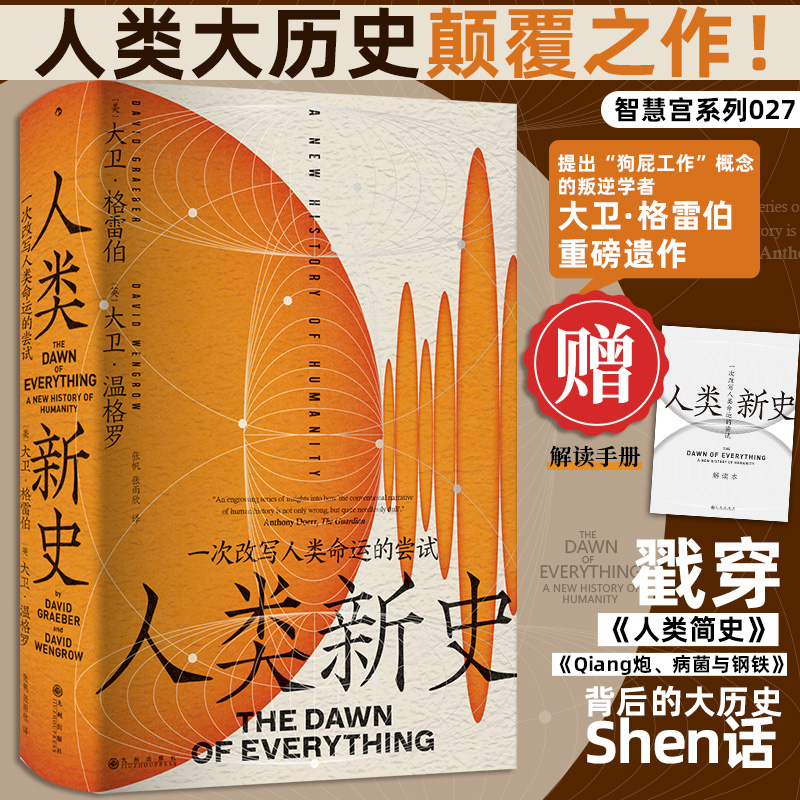
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美国知名人类学家、社会活动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生前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出版有《债:5000年债务史》、《毫无意义的工作》、《规则的悖论》等著作,其中的“狗屁工作”等概念引发社会热议。 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伦敦大学学院比较考古学教授,曾在非洲和中东多地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他在牛津大学接受考古学和人类学训练,并在那里担任初级研究员,还曾在沃伯格研究所、弗莱堡大学和纽约大学艺术学院任访问学者。著有《何以文明:古代近东与西方的未来》(What Makes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 the Future of the West)和《怪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nsters)。
第一章 告别人类的童年 或言,为什么这不是一本关于不平等起源的书 ………… 关于追求幸福 …………(第17页起) 我们很难挑战这些数据,但是正如任何统计学家会告诉你的,数据的好坏取决于它们所基于的前提。“西方文明”真的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吗?这最终要看人们如何衡量幸福,而众所周知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唯一可靠的方法似乎是,倘要决定一种生活方式是否真正更令人满意、更充实、更幸福或更可取,那就应该让人们去充分体验两种不同的生活,给他们选择权,然后观察他们是如何做的。比如,如果平克是对的,那么任何心智健全的人在①人类发展的“部落”阶段的暴力混乱和极端贫困与②西方文明的相对安全与繁荣之间做选择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但是,现在确有一些实证数据,证明平克的结论有很大问题。 ***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多次有人发现自己恰好处于可以做出这一选择的位置上——而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走平克所预测的道路。有些人为我们留下了清晰合理的解释,来说明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让我们看一下海伦娜·瓦莱罗(Helena Valero)的例子。她是一个出生在西班牙裔家庭的巴西女人,平克提到她是一个“白人女孩”,在1932年随父母沿着偏远的迪米提河(Rio Dimití)旅行时被亚诺玛米人绑架了。 在20年里,瓦莱罗都与亚诺玛米家庭生活在一起,结了两次婚,最终在她所处的社区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平克简短地引用了瓦莱罗后来对自己生活的讲述,她在其中描述了一次亚诺玛米人突袭的暴行。他忽略不提的是,在1956年,她离开亚诺玛米人去寻找她的原生家庭,重新生活在“西方文明”里,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偶尔饥渴、持续沮丧和孤独的状态之中。过了一段时间后,在有能力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时,海伦娜·瓦莱罗认为她更喜欢生活在亚诺玛米人中,并返回他们之中生活。 她的故事并非个例。南北美洲的殖民史中充满了这样的记述:殖民者被原住民社会俘虏或收养后,在有机会选择自己希望生活的地方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留在原住民社会那里。这甚至也适用于被绑架的儿童。当他们再次面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时,大多数人却会跑回收养他们的亲属那里寻求保护。相比之下,通过收养或通婚融入欧洲社会的美洲印第安人,包括那些—不同于不幸的海伦娜·瓦莱罗—享受了大量财富和学校教育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做出了相反的决定:要么尽早逃离,要么在竭力适应但最终失败后,返回原住民社会安度余生。 对这一现象最雄辩的评论之一可见于本杰明·富兰克林写给一位朋友的私人信件: 当一个印第安人的孩子在我们中被抚养长大,学会了我们的语言,习惯了我们的习俗,结果一旦他回去走亲访友,并和他们一起做一次印第安漫游(Indian Ramble),那就再也无法劝说他回来了。这并不仅仅是作为印第安人的天性,而且显然是作为人的天性——当白人,不论男女,在年轻时被印第安人俘虏,并在他们中间生活一段时间后,即便被朋友赎回并受到极尽温柔的对待以说服他们留在英格兰人中间,但很快,他们就会厌恶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支撑这种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忧虑与痛苦,并抓住下一次机会逃回林中,再也无法被找回。我记得曾听说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被带回家,并拥有了大笔产业;可当他发现要费神守住这些财产时,就把产业交给了一个弟弟,只带了一把枪和一件印第安斗篷重返荒野。 许多发现自己卷入这种文明竞赛——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人能够明确解释自己为何决定留在昔日的俘掠者身边。一些人强调他们在美洲原住民那里发现了自由的品质,既包括性自由,也包括不必无尽辛劳地追求土地和财富的自由。其他人则指出,“印第安人”不愿让任何人陷入贫穷、饥饿或匮乏的状态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害怕自己受穷,而是他们发现,生活在一个无人陷入绝望痛苦处境的社会中会愉快得多(也许就像奥斯卡·王尔德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因为他不喜欢免不了要看着穷人或听到穷人的故事一样)。对于任何一个在充满露宿者与乞讨者的城市中长大的人来说——很不幸,也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发现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时,总还是有一点吃惊的。 还有一些人注意到,被“印第安”家庭收养的外来者在其社区中很容易被接纳并获得重要地位,成为酋长家户中的成员,甚至直接成为酋长。西方的宣传家们无休止地谈论机会平等,而这些社会则似乎是机会平等真正存在之处。不过,到目前为止,选择加入美洲原住民社区最常见的原因是人们在其中体验到的强烈的社会纽带:相互关怀、爱,以及最重要的幸福,这些品质一旦回到欧洲都无法复刻。“安全”有很多种形式。有一种安全是知道自己中箭的概率极小;也有一种安全是知道一旦中箭,总会有人深切地照护自己。 人类历史的传统叙事不仅有误, 而且大可不必如此无聊 我们可以感觉到,粗略而言,原住民的生活比“西方”村镇或城市的生活有趣得多,尤其考虑到城市生活包含着长时间的单调、重复、空乏的活动。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另一种极尽迷人且有趣的生活了,而这一事实反映的与其说是生活本身的局限,不如说是我们想象力的局限。 标准的世界历史叙事最有害的一面就在于它们把一切都搞得干巴巴的,把人概括为扁平的刻板印象,将问题简化(我们是天生自私并且暴力,还是天生善良并且乐于合作?),以至于损害甚至可能毁掉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认识。“高贵”的野蛮人归根结底和野蛮的野蛮人一样无聊;更重要的是,二者实际上都不存在。海伦娜·瓦莱罗在这一点上非常坚定。她坚持认为,亚诺玛米人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天使。他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是人。 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一下:社会理论总是必然地包含一些简化。比如,几乎任何人类行为都可以说存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性心理层面,以此类推。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装游戏,在其中,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装只有一个层面在运作:基本上,我们把一切都还原为简笔画,以便发现本不可见的模式。因此,社会科学中所有真正的进步就源于有勇气说出那些归根到底有些荒谬的事情:卡尔·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成果只是其中一些最突出的例子。人们必须简化世界才能发现关于它的新知。但问题在于,在发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在继续简化。 霍布斯与卢梭向同时代的人揭示了一些惊人的、深刻的东西,为他们打开了新的想象之门。现在,这些理念却只是令人腻烦的常识。这些常识之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继续简化人类事务是合理的。如果今天的社会科学家还在将过去的世代人类化约为扁平的简笔画,这可不是在向我们展示什么独具创见的东西,而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社会科学家为了显得“科学”而应该做的。其实际后果就是使历史变得贫乏,从而导致我们对可能性的感知变得贫乏。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结束这篇导言。 自亚当·斯密以来,那些试图证明当代形式的竞争性市场交换根植于人类本性的人,指出了他们所谓的“原始贸易”的存在。早在数万年前,人们就可以找到物品被远距离转运的证据,这些物品通常是宝石、贝壳或其他装饰品。这些往往正是人类学家后来发现在世界各地被用作“原始货币”的物品。这必然证明了资本主义以某种形式一直存在吗?这种逻辑完全是循环论证。如果贵重物品被远距离运输,这就是“贸易”的证据;如果贸易发生了,就必定采取了某种商业形式;因此,如果3000年前在地中海地区发现了来自波罗的海一带的琥珀,或者墨西哥湾的贝壳被运到了俄亥俄州,这些事实便足以证明我们发现了某种市场经济的萌芽形态。市场是普遍的。因此,一定存在过一个市场。因此,市场是普遍的。如此循环往复。 所有这些作者实际上在说的是,他们自己无法想象贵重物品能以其他方式移动。但是,缺乏想象力本身并不构成一个论点。这些作者就好像不敢提出任何独创性的东西,或者一旦提出了,就觉得有必要使用听起来很科学但含糊其词的语言(“跨区域交互作用圈”“多阶交换网络”),这样就不用再去细究那些东西可能是什么。实际上,人类学提供了不胜枚举的例子可供说明,当不存在任何与市场经济沾边的事物时,有价值的物品是如何长途跋涉的。 20世纪民族志的奠基之作,马林诺夫斯基出版于1922年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描述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马辛群岛(Massim Islands)的“库拉链”中,人们如何乘独木舟在危险的大海上大胆探险,只为交换作为传家宝的臂镯和项链(每个重要的臂镯和项链都有自己的名字,也承载着前任主人的历史)。他们只是短暂地拥有它,然后把它再一次传给来自另一个岛的不同探险队。传家宝跨越数百公里的海洋,在岛链上循环不绝,臂镯和项链的传递方向相反。对于外人来说,这似乎毫无意义。但是对于马辛人来说,这是终极探险,没有比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名字传递到从未见过的地方更重要的事情了。 这是“贸易”吗?也许吧,但如果是,它将打破我们对这个词的惯有理解。实际上,有大量的民族志文献是关于这种长距离交换在没有市场的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以物易物的情况的确发生着:不同的群体可能会发展出自己的专长(一个群体因羽毛制品而闻名,另一个则提供盐,第三个群体中每个妇女都是制陶匠),以此来获得他们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有时一个群体会专门从事人与物的运输。但我们经常发现,这类地区性网络的发展往往是为了建立彼此间的友好关系,或是创造一个时常互相拜访的理由。此外,还有很多完全不像是“贸易”的可能性。 我们举几个北美洲的例子,让读者了解一下,当人们谈论历史上的“远距离交互作用圈”时,指的可能是: 1.追寻梦境或灵境:在16世纪和17世纪讲易洛魁语(Iroquoian)的民族中,实现自己的梦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许多欧洲观察者都讶异于印第安人甘愿旅行数日,只为带回他们梦中得到过的物品:战利品、水晶,甚至是动物,比如说一只狗。人们如果梦到了邻居或亲戚的财物(水壶、饰物、面具等),通常都可以要求得到它。因此,这些物品往往会逐渐沿着某种路线在村镇间移动。在北美大平原上,决定长途跋涉寻找稀有的或异域的物品,可能是寻梦之旅的一部分。 2.游医与流浪艺人:1528年,遭遇船难的西班牙人阿尔瓦尔·努涅斯·卡韦萨·德巴卡(?lvar Nú?ez Cabeza de Vaca)从佛罗里达穿越现在的得克萨斯州抵达墨西哥,其间,他发现他可以通过提供巫师和疗愈师的服务,从而在村庄之间(甚至是交战村庄之间)轻松通行。在北美洲大部分地区,疗愈师也是艺人,而且往往会发展出大量追随者;那些认为自己的生命因表演得到拯救的人,通常会献出他们所有的物质财富供戏班内部分配。通过这种方式,珍贵物品可以轻易跨越很远的距离。 3. 女性赌博:许多北美洲原住民社会的女性都是不折不扣的赌徒;相邻村庄的女性经常在一起掷骰子或梅花石,并通常会用贝珠或个人饰品作为赌注。精通民族志文献的考古学家沃伦·德博尔(Warren DeBoer)估计,在跨越半个北美大陆的遗迹中发现的许多贝壳和其他珍宝,都是在这种村际游戏中不断下注并输掉的赌注,它们在很长时间里不断以这种方式流散开来。 我们还能举出更多的例子,但估计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了我们的宏旨。当我们仅是猜测处于其他时间与地点的人类可能在做什么时,我们的猜测几乎总是不够有趣、不够新奇,总之,远远不如实际情况富有人情味。 关于接下来的内容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要展示一部新的人类历史,还要邀请读者进入一门新的历史科学,这门历史科学会恢复我们祖先全部的人性。在开头,我们不打算问人类是如何落入不平等的境地的,而是要首先探问“不平等”最初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然后逐渐建立起一个更贴近我们当前知识水平的替代叙事。如果人类进化过程中95%的时间不是以小规模的狩猎—采集游群的形式度过,那他们都在做什么?如果农业和城市不意味着陷入等级制与支配统治,那它们意味着什么?在我们通常认为出现了“国家”的那些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答案往往出人意料,并透露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可能并没有我们惯常假定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充满更多有趣的可能性。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只是试图为一部新的世界史打下基础,就像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新石器革命”或“城市革命”之类的术语时一样。这样一来,它必然是不平衡和不完整的。同时,这本书也是一场追寻真问题的探险。如果“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并非我们最该关心的历史问题,那么那个问题应该是什么?正如曾经的俘虏又逃回森林的故事所表明的,卢梭并不完全是错的。有些东西的确已经失落了。他只是对失落的是什么有一个别具一格的(而且终究是错误的)见解。那么,我们该如何描述失落之物呢?它到底失掉了多少?它对今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来说意味着什么? 大约10年以来,我们两位笔者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话。正因为此,这本书在结构上有点不同寻常。对话从探究那个问题(“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的历史根源开始,将其追溯到17世纪欧洲殖民者与美洲本土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接触。这些接触影响了我们现在所称的启蒙运动,也影响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理解,其影响比我们通常所愿意承认的要更加微妙和深刻。我们发现,重新审视它们将以惊人的方式影响今天我们对人类过去的理解,包括农业、财产、城市、民主、奴隶制和文明自身的起源。最终,我们决定写一本书,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我们自己思想的演进。在那些对话中,当我们决定完全远离像卢梭这样的欧洲思想家,转而考虑那些从根本上启发了他们的原住民思想家的观点时,真正的突破时刻到来了。 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 ◎ 万众期待的社科巨著终于有简体中文版了!国内外学者一致力荐 英文版(2021年底)一经推出即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引发各界热议!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亚马逊(美国)上6500人打出4.5分(5分制),英文版在豆瓣已有2000+想读!知名语言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乔姆斯基、《黑天鹅》作者塔勒布、《弱者的武器》作者斯科特等国外学者力荐;简体中文版得到陈嘉映、王铭铭、周雪光、张笑宇长文推荐,另有高毅、李宏图、李钧鹏、梁永佳、梁捷、梁文道、施展、王笛、周濂一致推荐(推荐语和推荐长文均收录于随书附赠的解读册)。 ◎ 人类大历史颠覆之作!挑战《人类简史》《枪炮、病菌与钢铁》等传统经典 这本书借助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有力质疑了我们所熟知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简史》等经典大历史的基本前提和很多观点,呼吁一种崭新的人类历史书写。农业的发明和城市的出现绝非什么革命性的时刻;环境与技术也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决定着文明的命运;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其说是线性进步(并伴随着相应的代价),不如说是从开放逐渐走向封闭的过程。大历史研究真正应当关注的问题,是我们为何会从曾经的灵活陷入如今的僵化,而改变的希望又蕴藏在哪里。书中引入了“季节性”“分裂演化”“人类的三种基本自由”“支配三要素”等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解释历史的新框架。 ◎ 提出“狗屁工作”概念的叛逆学者格雷伯最具野心的重磅遗作 作者之一大卫·格雷伯是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以批判官僚主义、资本主义和当代政治而闻名。他在59岁之年(2020年9月2日)突然病逝,去世前3周才完成这部历时10年的合著之作,这也是他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创造性破坏”风格,以独到的视角和大胆的姿态去质疑我们习以为常的底层逻辑,直指一些困扰着我们却又难以名状的症结,给予我们灵感和勇气去摆脱惯性、去发现和创造。 ◎ 在困顿迷茫的当下再度振奋起来,重新想象人类的可能性 两位作者在传统叙事框架之外爬梳材料,一点点拼合被忽视或误解的历史碎片:原始人类很可能季节性地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之间横跳,而不是固守某一种特定的制度,许多我们以为标志着“文明”的宏伟建筑遗址,其实只是他们季节性地建造又抛弃的东西;数量惊人的早期城市并不存在等级制或中心化的组织方式,却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文化;在一些传统社会,财产权并不意味着你绝对占有某物,而代表着你负有照看它的责任;历史上许多重要发现并不来自概念性突破,而可能来源自日常实践的累积,甚至来自玩乐或仪式…… 我们将看到,历史的发展并不存在所谓的正轨,人类社会有过各种有趣的可能性。那些传统从未中断,而它们比当前的主流秩序有着更加悠久和深厚的渊源。 获奖记录 入围奥威尔政治写作奖决选名单 获评《星期日泰晤士报》《观察家报》《BBC历史》年度图书 入选《科克斯书评》2021年度好书榜、亚马逊2021年度好书榜等各大权威图书榜单 两位作者因本书共同当选《艺术评论》(ArtReview)2021年度“当代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第10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