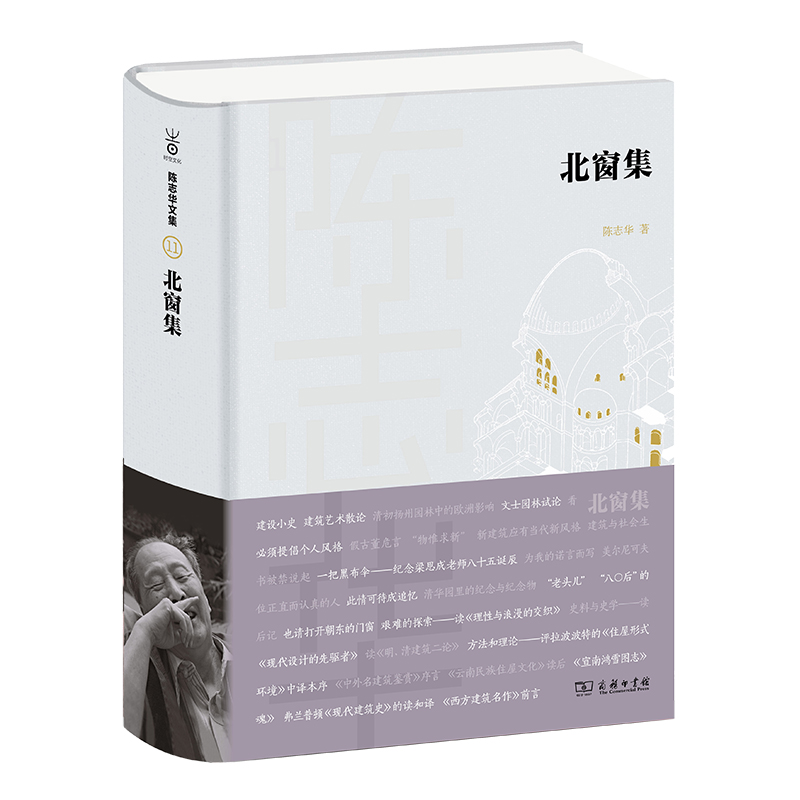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268.00
折扣价: 201.00
折扣购买: 北窗集(精)/陈志华文集
ISBN: 97871001986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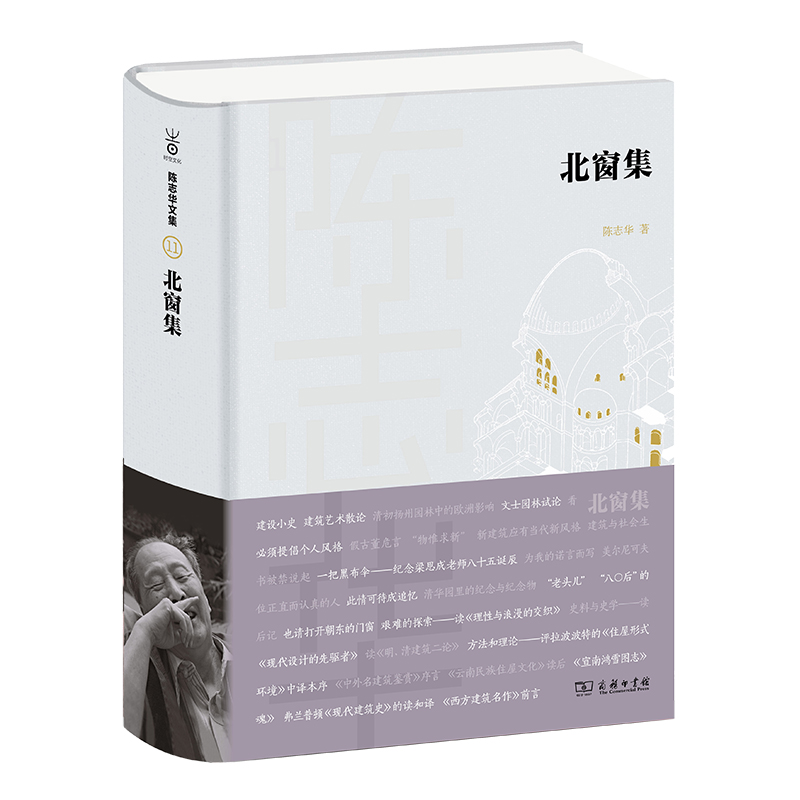
陈志华(1929— ),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留校任教。长期从事外国建筑史、园林史、建筑学理论、文物建筑保护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译了多种重要的建筑史和建筑理论作品。1989年开始,带领清华大学乡土建筑研究组从事乡土建筑研究,出版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专著。持续撰写建筑评论文章,坚守建筑发展的科学观和民主观。
为我们的时代思考(节选) ……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支真正的建筑理论队伍,有的不过是些散兵游勇、业余个体户。虽然在大形势影响之下,一时似乎文章不少,甚至已经使一些人埋怨“理论”太多,但稍稍一看,就能发现:有一些“理论”文章的底气不足,近乎茶余饭后的信口闲聊;有一些甚至犯起码的逻辑错误,概念不清楚,推理不能成立。比如,有一篇文章说“本(设计)院近年注意到建筑现代化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主要努力方向”,接下去竟说“传统是创作的根基”。这个“努力方向”跟这个“创作根基”,简直是南其辕而北其辙,满拧。难怪人家要说“理论”太多,厌烦了! 我们没有下功夫培养一支理论队伍。我们爱听建筑是艺术、是文化这样的话,但是,看看国内各个文化艺术行业,包括舞蹈和工艺美术,都在相应的高等学校里有历史理论系。虽说学生人数不多,毕竟受到了系统的理论的基本功训练,有必要的基础知识,有必要的思维能力的准备。但是,我们建筑界至今没有这样一个系。建筑界如果说也在培养理论工作者,那都是偶然机遇,靠的只是一些大学教师带的研究生。虽然也出了几个人才,知识结构却未必理想。这些人,如果自己不意识到这点而去改善知识结构的话,在理论方面的发展怕也会受到限制。 这些难得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到哪里去干理论工作?我们并没有真正认真干这工作的机构。于是,只好到设计单位去当业余个体户。分配到高等学校里的,仍然要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精力和时间去干满“工作量”和“创收”,剩给理论工作的精力和时间就很可怜了。万一吃不得苦、耐不得劳,不甘心坐冷板凳受寂寞,抵不住票子的诱惑,就连这一点精力和时间也花不到理论工作上去了。搞理论工作,光是读书,就要死死地下多少苦功夫啊! 可怜几个对理论工作有点儿傻劲的人,没有可能聚会交流,连必要的图书资料都残缺不全。要出门寻师访友、借几本书,哪里去弄车钱?口袋里装的只有老婆给的几个买菜钱。 以前好像有过一个属于建筑学会的历史与理论委员会,这几年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即便有,大概也并不能在学术工作上起多少作用。这几年写写理论文章的,好像还不见有哪一个曾经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造成理论工作不景气的原因,主要当然是有关领导的不重视,其次是整个建筑界的不重视。有些人口称重视,但他们的重视里不免常常包含着误解。 不重视理论,不重视抽象的、逻辑的思维,不了解理论思维的规律和它们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照明作用,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落后的传统之一。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太过于功利性的民族。建筑界至今还没有摆脱这个传统的束缚。 相当多的同志,片面化、简单化地理解“实践出真知”,认为一个人的理论水平跟他的实际创作经验成正比。设计过几十万平方米房子的建筑师,提起笔来写理论文章,比从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好;在生产第一线的建筑师提起笔来写理论文章,比多少有点专业化的理论工作者好。所以,没有人呼吁建立理论队伍,呼吁正规地培养这支队伍。 这种情况,恰恰反映出我们建筑界的理论意识太差,比起文化艺术的别的行业来,落后得太多了。不知道从经验到理论,是要经过鲤鱼跳龙门的那个变化的。 当然,有一些实际工作者能够写出很不错的理论文章来,专业的理论工作者也应当熟悉生产实际,但是,搞工程设计跟写理论文章毕竟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这两种工作者的气质不同,所需要的知识结构不同,平素学习和探索的问题也不同,因此,这两种工作者的选材和培养方法是不能一样的。这一点,可惜,恐怕连某些负责建筑教育工作的人都未必很清楚,而且还没有意识到应该弄弄清楚。只要看研究生招生时候的随意性就知道了。 欧洲出过一些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都有重大成就的建筑师,但数量屈指可数,一旦达到这种程度,就是一代宗师。我们总不能把我们的理论队伍的建设寄托在出现这样的大师上,这些人才是可遇而难求的。当然,我们也不必放弃希望,还应该宣传、提倡、想出点儿办法来,争取培养出一些学者型的建筑师,他们不但精于工程设计,而且善于做富有想象力的、独创性的理论思考。 因为不大了解理论的意义和理论工作的特点,有一些在第一线忙碌着的建筑师,常常喜欢用鄙薄的口气挖苦理论工作者:“哼,他懂得什么?光会耍笔杆子说废话!”其实,理论工作者对之于实际工作,恰恰需要有点儿超脱,这样才能保持一个轻灵而冷静的头脑,否则,他的想象力是飞翔不起来的。有一位建筑师写了一篇相声式的杂文,嘲笑理论工作者对他的方案提不出什么高明的意见来,解答不了他在工作中的一些难题。他不知道,理论工作者不是教师爷,也没有包治百病的祖传秘方,他的任务不是就事论事地“指教”设计者。理论工作者研究的主要对象不是一幢一幢的建筑物,而是一批一批的建筑物:或是一个人的作品,或是一个时期的作品,或是一类有共同特点的作品,如此等等。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倾向,是潮流,是规律性。因此不但要做静态的研究,更要做动态的研究,把逻辑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理论工作者即使在研究单独一幢建筑物的时候,目的也在于从它扩散开去,探讨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而不是评定它的优点缺点、经验教训,不是做设计总结。所以,不能指望读一篇理论文章就能“立竿见影”地提高设计水平。 举个例子来说,对假古董黄鹤楼的评论,不在于它仿得是不是地道,假得是不是有味儿,气势是不是雄伟壮观,色彩是不是富丽堂皇,更不在于它吸引了多少游客,赚了多少门票。理论工作者要着眼于它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民族性格,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潮流、倾向,跟当代的社会思想文化有什么样的关系。还要把这种造假古董的现象放到世界的文化历史背景上去对照考察,审定它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当世界上一些先进的国家在兴致勃勃地探索21世纪的建筑的时候,我们一些同志却在探索宋式、清式,多的是对封建农业时代的留恋,少的是对现代化的敏感和激情。这种反差,会教一切多少有点儿眼光的人不寒而栗。用 黄鹤楼收入了多少多少门票来为复古主义辩护,那是非常可笑的。如果我们的人民真的热爱假古董胜过一座有创新想象力的建筑物,那是要更加教人不寒而栗的,有什么值得自豪或者自慰? 苏联诗人安托科尔斯基(1896—1978)在他的《诗歌和物理》中激动地说:“假如我们时代的诗人听不出在当今巨大的宇宙运动中和血管中的示踪原子的运动中含有音乐和节奏,那么,他就不配是一位当代诗人!”这很值得我们参考。 理论工作的受到鄙薄,另一个原因在于理论工作者本身的缺点。主要的是,这些年来,确实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好古、炫虚、远离现实,有些玄妙高蹈的理论风行一时,似乎“高潮还在后头”。这些文章,教人读起来摸不着头脑,以致猜想,说不定作者自己也没有摸着头脑。作者着力追求建筑永恒的、终极的真理,根本没有兴趣探讨中国建筑当前发展的方向、道路,没有兴趣看一看中国人民面临的困难和任务,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不反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相反,倒不妨适当提倡一下这种非功利的、单纯以认识客观世界为目的的态度。但是,对建筑的真正客观真正理性的认识,是不能不包括建筑的功能目的性在内的,是不能不包括建筑的社会历史性在内的。没有这些,对建筑的认识就是片面的、不完全的。建筑毕竟不是“凝固的梦幻”。 也许,几百年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和迫切需要都已经不再存在,那些“永恒的、终极的”词句会发出先知般的光辉,像神启一样,而一切为当前的发展开辟道路的理论,事过境迁,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我想,我们仍然应该为现实的建筑的发展思考,决不后悔。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有由今天发展过去的那个美好的明天。人是不必为了“不朽”而工作的,何况未必! 不过,我要说清楚,我们所说的现实,是发展中的现实,绝不是停滞不变的。我们为今天现实而做的一切理论思考,应该是思考它如何更健康、更顺利、更快速地向前发展。面向今天,就得同时面向未来。因此,建筑理论的天地非常广阔,也非常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鸢飞鱼跃,得大自在。同时,需要建筑理论工作者有比较严整的基本知识和思维能力,有进击的性格,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对落后事物的决绝精神。否则,天高怕风紧,海阔怕浪高,就将一事无成。 推动建筑向明天发展的,主要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我们现在对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它跟建筑的关系研究得太少了。人口构成、家庭结构、教育水平、业余生活方式、第三产业的进步、收入的增加,以及政治民主化与社会平等化,等等,等等,都会影响建筑的发展,建筑也可能影响它们。这些问题早就应该富有远见地研究了。而研究它们,单靠目前这种业余个体户是不行的,他们连做一次最简单的社会调查都办不到。在这方面,我们需要的是整整两门体系完整的学科:建筑社会学和建筑未来学。我曾经呼吁过建立这两门学科,但是,没有人听。我不知道,除了期待,我还能干什么? 我们至今没有建筑未来学,连一篇文章都没有。相反,我们却有太多的古气盎然的理论和实践。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孔子老子、和尚道士,很有热门化的趋势。仿清仿明、仿宋仿唐,也是刊物津津乐道的“成就”,甚至还有人搞天晓得的仿汉、仿周建筑,真是鬼画符。但是至今没有听说什么地方、什么人探讨了21世纪的城市和建筑,做了什么畅想性的设计。一个民族怎么可以对未来毫无兴趣,不去探索,却对过去那么恋恋不舍,抱住不放?这是一种原始蒙昧的祖先崇拜的残余。而同时,外国人却在那里有滋有味地设想21世纪。地球只有这么一点点大,一个不追求未来的民族跟一些热烈追求未来的民族挤在一起,不觉得寒心么?长此下去,前途可卜,那是一幅不大美妙的图景。我们再也不能像蚕蛹那样躲在茧子里做安逸的梦了。 这个梦现在似乎染上了一层铜绿般的文化色彩。随着近几年的文化热,也有一些建筑理论工作者大声疾呼建筑的文化性,高倡以文化来拯救建筑的没落。这种主张很教人奇怪,建筑是一种文化现象,这本来毫无争论,为什么忽然要由文化来拯救建筑了呢?虽然至今还不曾见到什么明确的意见,我却有点儿心神不安。因为我琢磨了一阵子文化热,悟到了其中一些奥妙。简单说来,有一些人的主张大致是:仰韶时期的彩陶罐子是文化,百货大楼里的电饭锅不是文化;画符捉鬼跳神扶乩是文化,物理化学不是文化;玩弄三寸金莲是文化,研究巡航导弹不是文化;八人抬的绿呢大轿是文化,奔驰牌小轿车不是文化;山沟沟里一切愚昧落后的东西都是文化,城市里一切现代先进的东西都不是文化。这样的文化观念真叫人胆战心惊!我很害怕我们建筑界的热心于文化的同志,也传染上了这种文化观念,他们打算用来拯救建筑之堕落的文化是这种货色。也许怪我神经衰弱,杯弓蛇影。不过想起这些年的窑洞热和民居热来,也许我并没有过虑,何况今天又看到一篇文章,一位建筑师建议:“让我们的创作思想重返我们祖先美丽而古老的良知中去”。呀!祈菩萨保佑! 这样的文化观念教人想起英国工业革命之后,18世纪至19世纪流行的一种思潮,它对工业文化和城市文化痛心疾首,竭力歌颂甚至企图恢复中世纪的手工业、小农经济和牧歌风光。这是对工业革命的一种反动。虽然当时颇具气势,头面人物的声望很高,最终还是灰溜溜地退潮了。他们所指责的大工业产品的粗劣和城市生活的困苦混乱,被大工业和城市本身在前进中逐步克服了。值得一提的是,拉斯金和莫里斯反对大工业,提倡回到手工业去,主要理由是大工业产品千篇一律、简单化、没有人性,这跟我们现在一些同志批判现代建筑的话完全一样。历史证明,大工业可以逐渐在前进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产品,同时改造人们的审美观念。而回到手工业样式去是没有出路的,历史开不得倒车。 文化热虽然是近年舶来的新东西,它一进口,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把它跟封建时代的传统“全方位”地、“立体化”地融合起来了。我们三千年封建传统确实顽固得很,它能把一切外来的和创新的东西变形而纳入它的框框。如果我们错把这种顽固性当作“生命力”,加以吹捧维护,那可会大大地误事。要前进,就不能不首先打破这个传统。 近年外来的思想里还有一个“文脉”。文脉这个词也是建筑界在传统观念歪曲之下的误译。在语言学上,这个词被译作“语境”,就是使用语言时候的“此情此景”“前言后语”,也就是环境。在建筑创作中,慎重考虑建筑物所处的环境,既包括它的物质的建筑和自然环境,也包括它的历史文化环境,所谓“此情此景”“前言后语”,这当然是对的。但考虑出来的对策应该是富有创造性的千方百计,而不是只有一条“形似”“神似”的羊肠小道,一条叫人迈不开步子的独木小桥。“文脉”的译法,着眼在“脉”字。脉者,有源有流也,这是“继承传统”的一种隐晦的说法,它强迫人去走那条羊肠小道和独木小桥。这一个字的误译,连带着误译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使它们有利于传统的保守者们——“外国人如此说!”当然,context这个词内容丰富,很难用一个字、一个词来对应翻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是把它译作“外部条件的总和”更贴切一些? 理论工作者应该帮助建筑师解放思想,帮助他们看到天地之广阔,鼓励他们自辟道路疾驰飞奔,千万不可以去束缚他们的思想,引导他们钻进死胡同去。 理论工作者要为今天思考,为发展中的、向着明天迈进的今天思考,要为从今天向明天的过渡思考,要为明天思考。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枝枝节节看问题,而要在整个民族全面现代化的宏伟历史过程中去看问题。 最后,我以歌德的几句话作结。这位二百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诗人和科学家说:“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把我们的思考放到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背景上去罢! 原载《新建筑》1988年第2期论工作者要为今天思考,为发展中的、向着明天迈进的今天思考,要为从今天向明天的过渡思考,要为明天思考。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枝枝节节看问题,而要在整个民族全面现代化的宏伟历史过程中去看问题。 最后,我以歌德的几句话作结。这位二百多年前的伟大思想家、诗人和科学家说:“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把我们的思考放到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背景上去罢! 原载《新建筑》1988年第2期 半个世纪笔耕不辍,为我们的时代思考、写作和呐喊。《北窗集》是一本由出版社编选的新书,收录了“北窗杂记”专栏外陈志华散见于各处的大量学术及思想随笔文集,展现了半个世纪来作者在建筑史研究、建筑理论和实践、文物建筑保护的学术探索和努力,也反映了其学术交往和文化生活,本身已成为一笔珍贵的史料。在这些时间、主题跨度极大的文章中,无处不体现着作者严谨的治学作风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其中的真知灼见,迄今仍不过时,仍会滋养学界,启迪大众,为今天中国的城乡建设、建筑现代化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