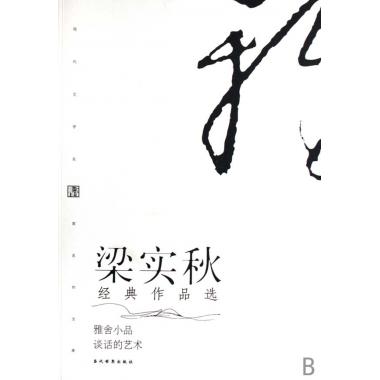
出版社: 当代世界
原售价: 23.80
折扣价: 14.10
折扣购买: 梁实秋经典作品选(雅舍小品谈话的艺术)/现代文学名家名作文库
ISBN: 9787801155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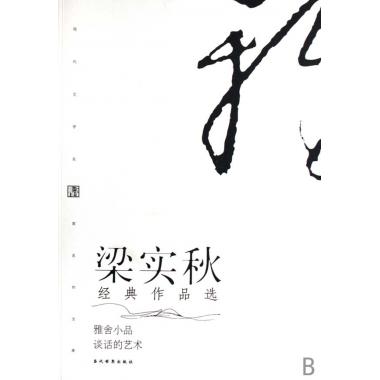
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笔名秋郎、子佳、程淑等。原籍浙江杭县,1903年1月6日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 梁实秋少年时就读留美预科的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留学归来后,梁实秋在复旦大学、中国工学、青岛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任职。1940年起,梁实秋以重庆北碚寓所“雅舍”为名,以子佳的笔名在朋友刘英士主编的《星期评论》上撰写专栏小品。“雅舍”系列小品还在1944年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和1947年上海《世纪评论》上发表。 到达台湾后,梁实秋出版了《雅舍小品》、《实秋自选集》、《略谈中西文化》、《雅舍小品续集》、《看云集》、《槐园梦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等著作。《雅舍小品》1949年在台湾出版后迅速发行至50多版,1960年时绍瀛将它译成英文,编为中英语文本,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远销北美和东南亚各地,据称目前已发行至300多版,创现代散文发行量的最高纪录。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给梁实秋的信中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个朋友来信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过。住在我的隔 壁的是一群在×××服务的女孩子,一回到家便大声歌唱,所唱的无非是 些××歌曲,但是她们唱的腔调证明她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原制曲者所要产 生的效果。我不能请她们闭嘴,也不能喊‘通’!只得像在理发馆洗头时无 可奈何地用棉花塞起耳朵来。……” 我同情于这位朋友,但是他的烦恼不是他一个人有的。我尝想,音乐 这样东西,在所有的艺术里,是最富于侵略性的。别种艺术,如图画雕刻 ,都是固定的,你不高兴欣赏便可以不必寓目,各不相扰;惟独音乐,声 音一响,随着空气波荡而来,照直侵入你的耳朵,而耳朵平常都是不设防 的,只得毫无抵御地任它震荡刺激。自以为能书善画的人,诚然也有令人 不舒服的时候;据说有人拿着素扇跪在一位书画家面前,并非敬求墨宝, 而是求他高抬贵手,别糟蹋他的扇子。这究竟是例外情形。书家画家并不 强迫人家瞻仰他的作品,而所谓音乐也者,则对于凡是在音波所及的范围 以内的人,一律强迫接受,也不管其效果是沁人肺腑,抑是令人作呕。 我的朋友对隔壁音乐表示不满,那情形还不算严重。我曾经领略过一 次四人合唱,使我以后对于音乐会一类的集会轻易不敢问津。一阵彩声把 四位歌者送上演台,钢琴声响动,四位歌者同时张口,我登时感觉到有五 种高低疾徐全然不同的调子乱擂我的耳鼓,四位歌者唱出四个调子,第五 个声音是从钢琴里发出来的!五缕声音搅做一团,全不和谐。当时我就觉得 心旌战动,飘飘然如失却重心,又觉得身临歧路,彷徨无主的样子。我回 顾四座,大家都面面相觑,好像都各自准备逃生,一种分崩离析的空气弥 漫于全室。像这样的音乐是极伤人的。 “音乐的耳朵”不是人人有的,这一点我承认,也许我就是缺乏这种 耳朵。也许是我的环境不好,使我的这种耳朵,没有适当的发育。我记得 在学校宿舍里住的时候,对面楼上住着一位音乐家,还是“国乐”,每当 夕阳下山,他就临窗献技,引吭高歌,配着胡琴他唱“我好比,……”, 在这时节我便按捺不住,颇想走到窗前去大声地告诉他,他好比是什么。 我顶怕听胡琴,北平最好的名手××我也听过多少次数,无论他技巧怎样 纯熟,总觉得唧唧的声音像是指甲在玻璃上抓。别种乐器,我都不讨厌, 曾听古琴弹奏一段“梧桐雨”,琵琶乱弹一段“十面埋伏”,都觉得那确 是音乐,惟独胡琴与我无缘。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曾说起有人一 听见苏格兰人的风笛便要小便,那只是个人的怪癖。我对胡琴的反感亦只 是一种怪癖罢?皮黄戏里的青衣花旦之类,在戏院广场里令人毛发倒竖,若 是清唱则尤不可当,嘤然一叫,我本能地要抬起我的脚来,生怕是脚底下 踩了谁的脖子!近听汉戏,黑头花脸亦唧唧锐叫,令人坐立不安;秦腔尤为 激昂,常令听者随之手忙脚乱,不能自已。我可以听音乐,但若声音发自 人类的喉咙,我便看不得粗了脖子红了脸的样子。我看着危险!我着急。 真正听京戏的内行人怀里揣着两包茶叶,踱到边厢一坐,听到妙处, 摇头摆尾,随声击节,闭着眼睛体味声调的妙处,这心情我能了解,但是 他付了多大的代价!他听了多少不愿意听的声音才能换取这一点音乐的陶醉 !到如今,听戏的少,看戏的多。唱戏的亦竞以肺壮气长取胜,而不复重韵 味,惟简单节奏尚是多数人所能体会,铿锵的锣鼓,油滑的管弦,都是最 简单不过的,所以缺乏艺术教养的人,如一般大腹贾,大人先生,大学教 授,大家闺秀,大名士,大豪绅,都趋之若鹜,自以为是在欣赏音乐!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我们的音乐(戏剧除外)也在蜕变,从“毛毛雨 ”起以至于现在流行×××之类,都是中国小调与西洋某一级音乐的混合 ,时而中菜西吃,时而西菜中吃,将来成为怎样的定型,我不知道。我对 音乐既不能作丝毫贡献,所以也很坦然的甘心放弃欣赏音乐的权利,除非 为了某种机缘必须‘‘共襄盛举”不得不到场备员。至于像我的朋友所抱 怨的那种隔壁歌声,在我则认为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恰如我们住 在屠宰场的附近便不能不听见猪叫一样,初听非常凄绝,久后亦就安之。 夜深人静,荒凉的路上往往有人高唱“一马离了西凉界,……”我原谅他 ,他怕鬼,用歌声来壮胆,其行可恶,其情可悯。但是在天微明时练习吹 喇叭,则是我所不解。“打——搭——大——滴——”一声比一声高,高 到声嘶力竭,吹喇叭的人显然是很吃苦,可是把多少人的睡眠给毁了,为 什么不在另一个时候练习呢? 在原则上,凡是人为的音乐,都应该宁缺毋滥。因为没有人为的音乐 ,顶多是落个寂寞。而按其实,人是不会寂寞的。小孩子的哭声,笑声, 小贩的吆喝声,邻人的打架声,市里的喧■声,到处“吃饭了么?”“吃饭 了么?”的原是应酬而现在变成性命交关的问答声——实在寂寞极了,还有 村里的鸡犬声!最令人难忘的还有所谓天籁。秋风起时,树叶飒飒的声音, 一阵阵袭来,如潮涌;如急雨;如万马奔腾;如衔枚疾走;风定之后,细 听还有枯干的树叶一声声地打在阶上。秋雨落时,初起如蚕食桑叶,■■ 嗦嗦,继而淅淅沥沥,打在蕉叶上清脆可听。风声雨声,再加上虫声鸟声 ,都是自然的音乐,都能使我发生好感,都能驱除我的寂寞,何贵乎听那 “我好比……我好比……”之类的歌声?然而此中情趣,不足为外人道也。 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