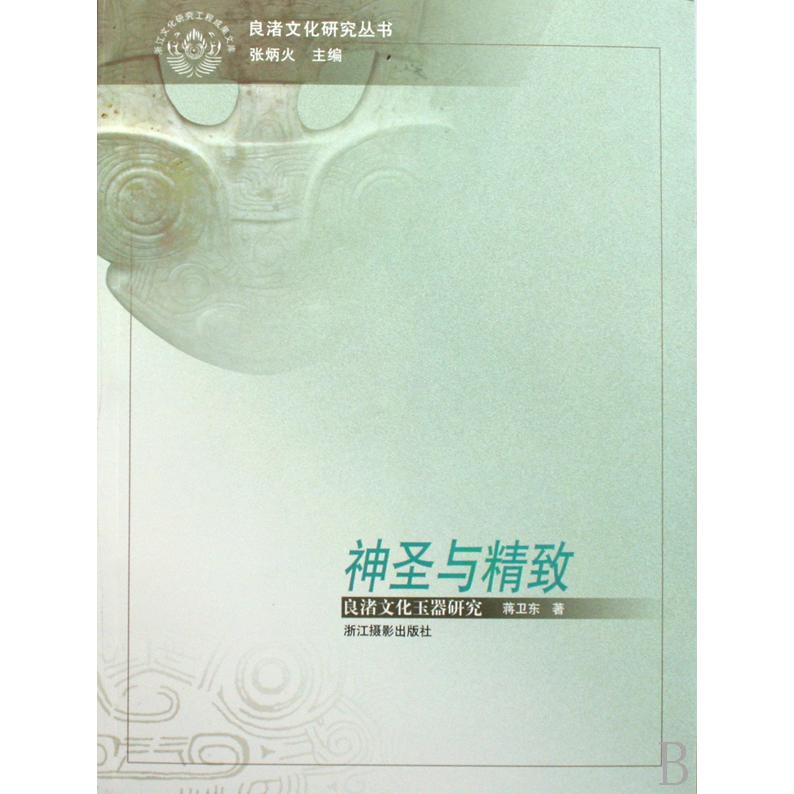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摄影
原售价: 50.00
折扣价: 35.00
折扣购买: 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ISBN: 97878068657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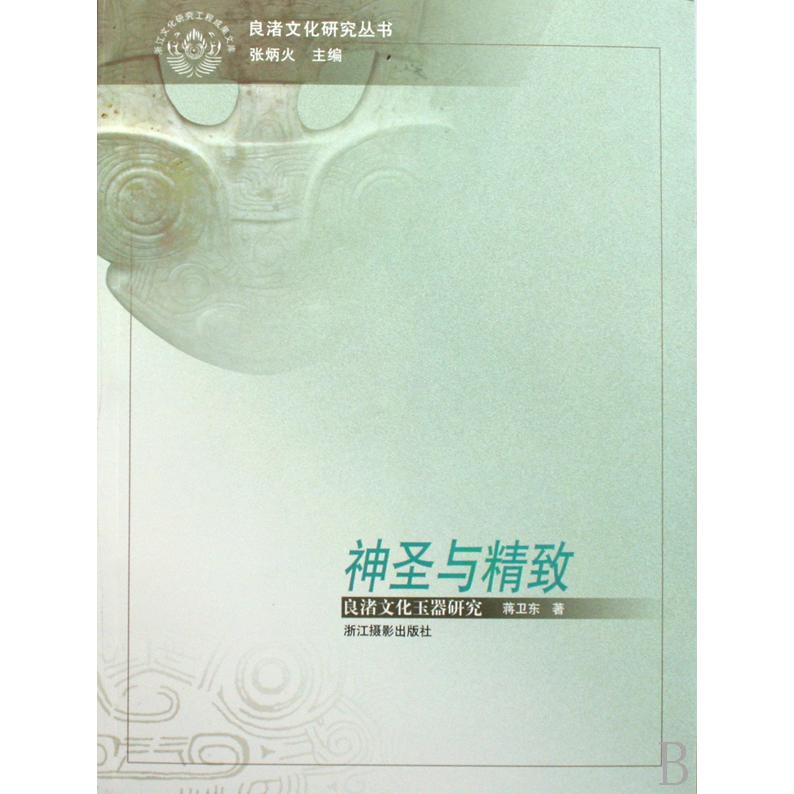
蒋卫东,1967年2月出生于浙江海盐。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现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文物局副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浙江北部地区史前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与良渚文化结缘尤深,已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编《新地里》、《良渚文化:文明的实证》等书。
上世纪20年代,随着仰韶村、西阴村、安阳殷墟等地考古发掘的先后展 开,中国考古学逐渐走过了由无到有、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由少到多、考古 发掘由外国学者主持到独立承担的拓荒过程,然而,无论是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还是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 古组,当时新成立的中国考古机构的兴趣和精力,几乎完全集中在黄河流域 ,对于“化外”的江浙地区,根本无暇顾及,于是,江浙地区古文化遗址首 次发现和首度发掘的荣冠,便戴在了一批非专业人士的头上。 1930年至1936年,以卫聚贤、慎微之、金祖同、张天方等为代表的一些 学者,先后在南京栖霞山、湖州钱山漾、常州奄城、金山戚家墩、嘉兴双桥 等地发现了江南史前文化的遗址,以上这些遗址的发现会同苏州、绍兴、平 湖、海盐等地陆续发现和采集到石器,引起了一些热心研究江浙古文化人士 的关注。 1936年2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以研究吴 越(暂以江苏、浙江两省为限)史地为宗旨”的吴越史地研究会,8月30日, 吴越史地研究会正式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推举蔡元培任会长,卫聚贤为总 干事,提出“吴越文化”的新概念,并积极倡导“吴越文化”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由卫聚贤主编的《吴越文化论丛》更是成为发表“吴越文化”最新考 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阵地,1930年以来江浙地区古文化遗址的发现成果,以 专刊或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 是年5月,古荡老和山因建造杭州第一公墓,出土一些石器,引起了吴 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经卫聚贤倡导,5月31日,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 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作了一天的试掘,参与试掘的有吴越史地研究会 的卫聚贤、乐嗣炳、金祖同和西湖博物馆的馆长董聿茂、历史文化部主任胡 行之、地质矿产组助理员施昕更等人。试掘开探坑3个,仅获石器6件、陶片 3块,另采集石器10余件,这是江浙地区第一次与史前文化相关的田野考古 发掘。 古荡遗址的发掘仅进行了短短的一天,却改变了一位年轻人的命运。时 年24岁的施昕更(图1—13)是当时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的助理员,馆方派 他参与发掘的原意是让他记录地层,然而施昕更在接触出土的石器后,意识 到家乡杭县良渚镇一带屡有出土的石器,应与古荡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基 于对探究遗址的狂热兴趣,第二天,他便匆忙赶赴良渚,至11月,在良渚镇 周围作了三次田野考古调查,“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不以为苦”。11 月3日,在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水塘边,他偶然发现了两片黑色有光陶片,采 集后对照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城子崖》发掘报告,认为与城子崖 黑陶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是年12月1日至10日、12月26日至30日, 次年3月8日至20日,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棋盘坟、横圩里、茅 庵前、古京坟、苟山东麓以及长命村、钟家村等处遗址进行了发掘,搜集到 大量石器、黑陶等古物。 充满戏剧性的是,就在施昕更闷头发掘,埋首整理资料之时,一场关于 “浙江有无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战,热热闹闹地开演了,唇枪舌剑双方的 代表人物都参加过古荡的发掘。一方是西湖博物馆的历史文化部主任胡行之 ,他根据与浙江出土石器“相伴出土之物,只有玉器、刻纹陶片而无彩陶、 土陶及其他更古之物”,提出“江南一带新石器时代未必有人类居住之可能 ,那末这些石器也只能看做金石并用时期的物品”,“时代也只可推定到周 末为止,而似不能再为提高了”。针锋相对的另一方为卫聚贤,他笔锋凌厉 地回击了胡行之的诘问,为反驳卫聚贤,对玉器和石器的关系也进行了梳理 ,得出“玉器之为殉葬物,在铜器发达之期;石器未用锋刃的为殉葬物,在 铜器的初期新石器的末期;石器锋刃已秃的为殉葬物,在新石器的中期”的 结论。虽然引用《越绝书》把石器、玉器远推于“神农”、“黄帝”之时来 反对“为周末之物”的观点,但由于跟胡行之一样持古荡出土有孔石斧的钻 孔为铜器所钻的认识,即使胆大放肆如“卫大法师”者,对于与有孔石斧共 出的玉器的年代,也未敢推断为新石器时代。 论战的双方均与施昕更有着亲密的关系,胡行之作为西湖博物馆历史文 化部的主任,是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发掘 报告的校阅者,而卫聚贤则为施昕更研究上的鼓励者,《良渚——杭县第二 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校后记”的作者,两位知名学者素为施昕更所 敬重,因而发生在两人之间的激烈辩论,定然对年轻的施昕更产生了重大影 响。在先后发表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和《良渚——杭县 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图1—14)中,施昕更没有像《杭州古荡新 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那样,直截了当地采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标 题,而使用了“远古文化遗址”和“黑陶文化遗址”这般朦胧隐晦的定性,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发表对于良渚黑陶文化的年代认识:“从其本身的文化特 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浙 江古代已孕育很早的文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这是无可疑的了”。 对于良渚镇一带时常出土的玉器,施昕更也给予了更多的关照。在先期 发表的《杭县第二区远古文化遗址试掘简录》中,施昕更对玉器的认识,几 乎与卫聚贤、胡行之两位如出一辙,虽然一再强调“杭县玉器的时代既没有 文字可考,又没有史书查据,而玉器本身亦不具任何地方特色”,却亦作出 了“由葬仪及形制看来,当在周汉之间,可无疑问”的结论。但是等到撰写 《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时,他对玉器的认识已略有 变化,“由葬仪及形制看来,在周汉之间,较为相近,而亦有较早的,更有 许多玉器流传时期极长,到唐宋之间及至近代亦有为殉葬物的”,同时还特 别强调:“一部分墓葬的仪饰石器,不为实用,很是明显,亦为解决精制石 器或与玉器先后及并行的问题之关键,但是现在大部分还不易十分明了,所 以必须找得玉器的墓葬,以供实地研究,由墓葬的仪式,及殉葬物的全部, 就可以证明了。”完全已是一副考古学者的口气。 与此同时,施昕更注重记录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关于玉器出土的详细资 料,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他列举了经调查 发现的十余处遗址的出土物,其中良渚茅庵前、苟山前后、近山前东、大雄 乡、长命桥钟家村、金家弄、安溪后湖村及瓶窑宋村一带都留下了有玉器出 土的记录。他还公布了西湖博物馆收藏的1930年出土于良渚后湖村的两件玉 璧(图1—15),详细记录了有关玉器的出土情况: 杭县的玉器,据善于掘玉者的经验,及出土时的情形看来,都是墓葬物 ,可无疑问,而墓葬的地方,无棺椁砖类之发见,据掘玉者以斩砂土和红土 为标识,也是墓葬存在的一证,在出土时所见的葬仪,亦是很值得注意,所 谓有梅花窖、板窖之称,排列整齐而有规则,每得一窖,必先见石铲,下必 有玉,百不一爽,每一窖之玉器,形式俱全,多者竞达百余件,而所置部位 ,亦俨然如周礼正义“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 ,盖取象方明神也”的情形相符节,又常因窖之所在地不同,而玉有优劣之 别,一方面固因环境不同,一方面更为当时殉葬的阶级制度不同所致。 曾汇集各处所见杭县出土之玉器,凡琮、璧、环、瑗、硅、璜、瑁、及 其他饰玉佩玉等,都一一具备,尤以璧类、哇类,及小件的填笄之类最为常 见,亦有雕琢极精致的雷纹、粟粒纹、虬龙纹等,玉之色泽亦缤纷灿烂,古 色盎然,以青绿色俗名鸭屎青者为主。 之所以能超迈卫聚贤等名头比他大得多的知名学者,获得“良渚文化发 现第一人”的桂冠,应当正是源自于施昕更具有超乎卫聚贤等人的严谨审慎 的治学之风、踏实敛约的为人原则。《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 步报告》,不仅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址 的文化面貌,而且也第一次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良渚玉器的出土情 况,成为日后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大放异彩的先声,是中国史前考古学 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P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