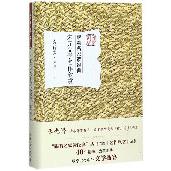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80
折扣购买: 宋元文学名作欣赏(精)/跟着名家读经典
ISBN: 97873012847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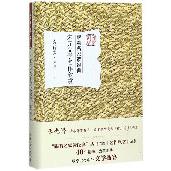
袁行霈,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1984年任教授,1986年任博士生导师。历任第十届*****、民盟中央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
宋元文学名作欣赏 是亦步亦趋,还是另辟蹊径? 宋人七*的理趣和野趣 储仲君 作者介绍 储仲君,1934年生,江苏金坛人。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 学中文系。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推 荐 词 一些**的宋人七*,或富有理趣,或富有野趣,或富有机 趣,这是宋诗比较突出的表现。本文从宋诗七*的理趣和野趣的 角度,展现了宋诗不同于唐诗的一面。 七言*句是唐人耕耘甚勤、收获甚富的一个领域。 唐人的创作既为宋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宋 人设置了一道不易逾越的障碍。是跟着唐人亦步亦趋,还是 另辟蹊径?大部分有出息的宋代诗人选择了后一条路。他们 的努力使七*焕发出了新的光彩。一些**的宋人七*,或富有理趣,或富有野趣,或富有机趣,就是比较突出的表现。 先说理趣。严羽《沧浪诗话》曾说:“诗有别趣,非关 理也。”这是针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 为诗”的倾向说的,意在强调诗歌的特点。这自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但这句话说得未免有些**化,因为诗固然可以有 “别趣”,但并不见得不可以有理趣,而且别趣与理之间也不见得没有关系。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就反驳他说: “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抒情诗在感染人、 陶冶人方面作用比较突出,一般说,它不可能像叙事作品那样,通过描绘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图画来揭示生活的本质, 但它却往往以“表态”的方式,告诉人们诗人欣赏什么、赞 美什么、厌恶什么、反对什么,从而告诉人们什么是真、 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这就是说,抒情诗归根到底也 要说出个理来,也是有它的认识意义的。当然,“理语不必 入诗中”,一般说,应该通过形象的描绘、感情的抒发,使 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这样才容易做到“含不尽之意,见 于言外”,这是为唐人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但是否只此一途,别无他法呢?是否只能含蓄,不能明快,只能让读者 去体会,而且只能让那些聪明的读者得到确切的答案,不 能*明确地把自己的意思告诉读者呢?宋人作了肯定的答 复。他们的做法就是努力去发掘和表现理趣。理和趣,两者 必须结合。有理无趣,则索然寡味;有趣无理,则流于平俗。 宋人理趣结合的方法,*常见的一种是形象地描绘眼前的景物,然后加以点破,使读者既能领略景物的诗意,同时 又因为得到某种启示而若有所悟的喜悦。这种方法,姑且称 之为描绘法。如朱熹的《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清澈的池水像明镜一样映照出天空飘浮的白云,使人心 旷神怡;池水为什么会如此清澈?原来源头有潺潺的活水! 写的是眼前的景物,讲的却是学习的道理。这显然比枯燥的 说教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多了。又如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讲了哲理,但从诗面看,作者写的却是他畅游 庐山的观感。读着这首诗,我们似乎也步着诗人的游踪,从 不同角度看到庐山所呈现的千姿百态,或高峻,或舒缓,或 秀丽,或雄浑。每一个姿态都是真实的,但对整体庐山来说 又都是片面的,因此也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为什么身在庐 山,却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呢?原因恰恰就在于:“只缘身 在此山中!”这显然是诗人在游程中一直在思索的问题。他 的体会使我们感到具体、亲切,讲的道理又使我们有顿开茅 塞之感。但还不止是如此。我们还可以从诗中隐隐体会到苏 轼在人生的海洋中沉浮的感慨。显然是山中之游使他联想到了“人生之游”。他看不透生活,理解不了生活中的风云变 幻,但现在他明白了:“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因为他执 着地站在生活漩流中的缘故。他似乎想跳出尘世,这正是苏 轼旷达的一面;但他是跳不出去的,因为他热爱生活,这又 正是他执着的一面。因此,“只缘身在此山中”,就显得有 些自嘲的意味,而苏轼积极的人生态度,则通过他所特有的 这种旷达表现了出来。再如陈与义的《襄邑道中》: 飞花**照船红,百里榆堤半*风。卧看满天云不 动,不知云与我俱东。 这首诗乍看似乎没有说理的意味,实际上却也说了一个 颇能给人启发的道理。苏诗写的是变中有不变,陈诗写的是 不变中有变。因为风行甚速,所以船行速,云行亦速。大家 都在运动,反而不觉得运动了。卧看二句,写出了诗人轻舟 直下的舒畅顺适之感,可是,人们不是经常在自以为是的顺 境中,忽视了事势的变化吗? 第二种方法是叙事,由叙事生发出议论来。如陈师道的 《*句》: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 此,好怀百岁几回开! 头两句叙述他读书待客,讲的是眼前的事,与“不如意 事常**,可与言人无二三”那样的横发议论不同。一本有 兴趣的书快要读完了,知心朋友却还没有来。这使他懊丧, 并因此而联想到一生中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于是他感慨 道:一个人一辈子能有几次高兴的时候啊!这无疑是对当时 社会现实的一种揭露。再如杨万里的《初入淮河》: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中流意不佳。何必桑干方是 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前两句叙述诗人舟行入淮,感到心情压抑。这时他也许 想起了“无端*渡柔花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这样的诗句, 不禁无限感慨地问道:何必非要渡过桑干河才算远呢?眼前 这条地处中国腹地的淮河,它的中线以北,不就已经是异国 他乡、天涯海角了吗?在这两句议论中,我们可以感到诗人 对南宋王朝**辱国、不事恢复的痛心和愤慨。 第三种方法是用形象的材料发议论,称之为“形象思维”倒颇为恰当。如刘克庄的《戊辰即事》: 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诗人用激愤的议论对南宋王朝纳贡求和的投降政策表示强烈的抗议。他指出,长此以往,连京城临安以“三秋桂 子,十里荷花”闻名的游览胜地西湖,恐怕也只好伐木填 湖、种桑养蚕,去供奉永远贪得无厌的金人了。全诗是议论 式的,但用的是形象的材料,其容量自然要比一般抽象的议论大得多。 宋人认为理有哲理之理、事理之理、性理之理。我们所说的理趣,主要指前两项而言。一首富有理趣的诗,并不 仅仅诉诸读者的理性,它也同样要拨动读者感情的弦索,并 且给读者插上想象的翅膀。因此,它并不会使人感到一览无 余;相反,除一般的诗意享*以外,它还往往使人领略到 “别有一番滋味”。 其次说野趣。这里主要讲以农村风光为题材的作品。之 所以要用“野趣”的字样,是为了表示与前此诗人所写的田 园诗中的诗趣有区别。如果说前者比较雅,那么后者就显得有些野;但正因为“野”,才比较真。其诗意是从现实的农 村生活中发掘来的,捕捉来的,不是戴着后世仿制的陶式眼 镜所能看到的;也正因为野,所以显得新,在王、孟、韦、 柳以来的一味恬淡冲远的沉闷空气中吹进了一阵清风,使人 感到一新耳目。后人的田园诗只继承了陶诗恬淡的一面,涉 及劳动生活的一面被抛掉了,田园诗成了隐逸诗的代名词。 大概真正的隐士一般未必会想到写诗,而写诗大谈山野田园 之乐的人则未必真心想当隐士,像孟浩然、秦系这样的人虽 然隐居终身,其实做官之心是很切的。所以他们的兴趣并不 在农村生活,而在美化、诗化田园风光,以抬高隐士的身 价。“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王维《山居秋暝》), 美则美矣,但浣女脸上的汗珠、渔父脚上的污泥没有了。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消*出不见人,欸 乃一声山水绿”(柳宗元《渔翁》),逸则逸矣,但如果告 诉那位风餐露宿的渔翁说这写的是他,他恐怕只会感到惘然 吧。总之,就大部分作品来说,唐人的田园诗并不能真实 地、全面地反映农村的情况。他们写的是他们感兴趣的或希 望看到的一面。在这一类诗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作者 对农村生活、对农民的思想感情是有隔膜的。 宋人的田园诗就不是这样。在这些诗里,我们往往可以 比较真切地看到农村生活,看到农民的喜悦和忧愁,情趣和 好尚;诗人流露的情趣,也往往与之较为**。例如孔平仲 的《禾熟》: 百里西风禾谷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齧*坡头卧夕阳。 这里写的是农忙后的间歇。天凉了,水清了,庄稼成熟 了,一头老牛舒坦地卧在夕阳中,懒洋洋地咀嚼着干*。我 们似乎能看到它心里的满意,以至于不禁也要舒一口气。写 的是牛,但却使我们想起终年辛勤劳动的农民。这时候农村 的气氛是安闲、恬静的,但这种安闲、恬静却说明了农民的 要求多么容易满足,也说明了他们平时的负担是多么沉重。 因此我们在舒一口气之后,又不禁要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 夕阳西下时一头老牛卧地吃*,这是十分平常的景象, 到过农村的人谁也能够看到,但高雅的诗人也许会觉得它平 庸而粗俗,避之唯恐不及。孔平仲却从中发现了诗意,这是 因为他走进或走近了农民们的圈子的缘故。无**偶,宋人 写牛的诗很不少,而且其中不乏好诗。如: 清明风*雨干时,*满花堤水满溪。童子柳荫眠正着,一牛吃过柳荫西。 ——杨万里《桑茶坑道中》 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 卧,带得寒鸦两两归。 ——张舜民《村居》 *满池塘水满陂,山衔落*浸寒漪。牧童归去横牛 背,短笛无腔信口吹。 ——雷震《村晚》 这几首诗都表现了一种悠闲的情趣,但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样的悠闲毕竟很不相同。诗里描绘的景 色也很美,但吹来的清风中却杂有青*味、泥土味,甚至牛粪味。的确,这几位诗人持的都是从旁欣赏的态度,但欣赏 较回避或厌恶,不能不说是很大的进步。如果我们用**深入生活的观念去衡量他们,那就未免苛求古人了。 如果说上面这三首诗多少带一点猎奇的意味,那么,像 下面这样一些诗,对农村生活的描绘就显得*朴实一些,深 刻一些。如: 土膏钦动雨频催,万*千花一饷开。舍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多浓的春意!但这是田舍中的春意,庄稼人看在眼里, 乐在心里,但“虽知而不能言”,诗人替他们说出来了。自 古以来,描写春浓的诗作可谓多矣,但很少有从泥上着笔的;着意渲染娇红、嫩绿、莺声、燕影的诗作可谓多矣,但还没有见过拈出一根鞭笋来作为春的标志的。因为这些诗人没有想到用庄稼人的目光来看看外面这个大千世界,自然不知道春天原来是从肥沃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不知道天下竟 然还会有鞭笋串门这样的新鲜事。再如: 蝴蝶双双入菜花,*长无客到田家。*飞过篱犬吠 窦,知有行商来卖茶。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菜花黄了,白天长了,男人们都下地劳动去了。村庄里 一片寂静,笼罩着昏昏欲睡的气氛,时间和空气都似乎凝固 了。只有行商的到来,像一块石子投入池水一样,在这种平静而单调的生活中激起了几圈涟漪。也许作者意在表现初 夏农村的宁静,但我们却感到,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压抑的宁静! 上引数诗,大都是反映农村生活中轻松、平静的一面 的,这一点倒是继承了晋唐以来田园诗的传统。严厉的批评 家也许会指责这些诗有粉饰现实之嫌。其实,农村生活并不 始终都像绷紧了的弦那样,也是有张有弛的;农民们并不始 终都在痛苦**,也有自己高兴、喜悦的时候。我国*早的 民歌《七月》就曾经全面地反映了古代农奴一年四季的生 活,包括他们艰苦的劳动和愉快的节*。问题倒在于这种恬 静的诗趣究竟是取自当时的农村生活,抑或不过是从前人的 美学趣味中贩来的赝品。应该补充说,宋诗中并不缺少正面 反映农民的劳动、贫困和*封建统治者残酷剥削、压迫的作 品,但这类严肃的题材需要体裁有较大的容量,因此以长篇 居多,不过小诗中也时有佳作。如: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 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这首诗正面写了农民们辛勤的劳动生活:男耕,女织, 连小孙子也学着老爷爷的样,在桑阴下玩种瓜。这里是没 有闲人的,这里的人从他还是“童孙”的时候起,就与劳 动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成了皤然老翁,始终是没有暇时 的。再如: 一担干柴在渡头,盘缠一*颇优游。归来涧底磨刀 斧,又作全家明*谋。 ——萧德藻《樵夫》 作者选择的显然是太平时光,是这位樵夫运气好的时 候,柴顺利地担到集市,顺利地卖了出去,又给一家老小买 回了**的口粮,这时候这位樵夫心里挺高兴。但他的高兴 是短暂的,回到家里,他又不得不为全家明天的生活皱起眉 头,磨他的柴刀了。唐人爱说“归去老渔樵”之类的话,在 他们的笔下,终*与青山为伴的樵夫总带有几分仙姿逸气, 令人赞赏;而在宋人萧德藻的眼里,樵夫的生活就显得并不 那么令人羡慕了。 拂晓呼儿去采樵,祝妻早办午炊烧。*斜枵腹归家看,尚有生枝炙未焦。 ——华岳《田家》 这位老农下地以前,对家里的活儿一一作了安排,细心 得很,*心得很。劳动**回来,他累了,饿了,但首先还 是要用挑剔的眼光看一下诸事是否都已办妥。当他看到还有 一枝生柴没有充分燃烧的时候,他一定沉下脸来了,家里气 氛也一定紧张起来了。在我们看来,这位老农的性格未免有 些古怪,但是,不正是生活的重压把它扭曲成这样了吗?在 这首诗里,农民不再是田园风光的点缀,不再是远处影影绰 绰的形象,而已经须发毕现,跃然纸上了,再如: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 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采菱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并不像唐人诗歌中写的那样, 总是伴随着悠扬的“菱歌”。采菱人躬腰探身,在菱叶密集 的水面上*作,手指经常被菱角扎得血肉模糊。他们实在太穷了,不得不放弃祖辈从事的耕作,选择这种*为艰苦的劳动,但是,“近来湖面亦收租”!叫他们到哪里去谋生呢? 在这首诗里,已经没有一点轻盈的和平之音,有的只是贫苦农民的愤怒和控诉。 从以上这些方面可以看到,宋代的田园诗人对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比唐人要熟悉得多,兴趣要浓厚得多,这正是他们的田园诗之所以有野趣、之所以能打开一个新局面的根源所在。 豪放中有沉着之致 说欧阳修《玉楼春》一首 叶嘉莹 作者介绍 叶嘉莹,1924年生,号迦陵,满族。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 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推 荐 词 “豪放中有沉着之致”不仅道中了《玉楼春》这一首词这几 句的好处,而且也恰好正说明了欧词风格中的一点主要的特色,那就是欧阳修在其赏爱之深情与沉重之悲慨两种情绪相摩荡之中,所产生出来的要想以遣玩之意兴挣脱沉痛之悲慨的一种既豪宕又沉着的力量。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以前我在《灵谿词说》中,对于欧阳修词已曾做过简单 的介绍和评述,以为北宋初年的一些名臣,如范仲淹及晏殊、 欧阳修等人,除德业文章以外,他们也都喜欢填写一些温柔旖旎的小词,而且在小词的锐感深情之中,*往往可以见到他们 的某些心性品格甚至学养襟抱的流露。就欧阳修而言,则他在 小词中所经常表现出来的意境,可以说乃是一方面既对人世间 美好的事物常有着赏爱的深情,而另一方面则对人世间之苦难 无常也常有着沉痛的悲慨。而我们现在所要评说的这首《玉楼 春》词,可以说就正是表现了其词中此种意境的一首代表作。 这首词开端的“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 两句,表面看来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其遣词造 句的选择与结构之间,欧阳修却已于无意间显示出了他自己 的一种**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句的 “尊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合,第二句的“春容”又该 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尊前”所要述说的都是指向离别 的“归期”,于是“尊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乃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 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能够体会出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 美好事物之爱赏与对人世无常之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 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其次再就此二句叙写之口吻而言,欧 阳修在“归期说”之前,所用的乃是“拟把”两个字;而 在“春容”“惨咽”之前,所用的则是“欲语”两个字。曰 “拟”、曰“欲”,本来都是将然未然之辞;曰“说”、曰 “语”,本来都是言语叙说之意。表面虽似乎是重复,然而 其间都实在含有两个不同的层次,“拟把”仍只是心中之 想,而“欲语”则已是张口欲言之际。二句连言,不仅不是 重复,反而*可见出对于指向离别的“归期”,有多少不忍 念及和不忍道出的宛转的深情。其间固有无穷曲折吞吐的姿 态和层次,而欧阳修笔下写来,却又表现得如此真挚,如此自然,如此富于直接感发之力,所以即此二句,实在便已表现了欧词的一种特点。至于下面二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 恨不关风与月”,则似乎是由前二句所写的眼前的情事,转 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 情事的感*,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 所谓“人生自是有情痴”者,古人有云“太上忘情, 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所以况周颐在其《蕙 风词话》中就曾说过“吾观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 之外,别有动吾心者在”。这正是人生之自有情痴,原不关 于风月。李后主之《虞美人》词曾有“春花秋月何时了,往 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句, 夫彼天边之明月与楼外之东风,固原属无情,何干人事?只 不过就有情之人观之,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 媒介了。所以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此二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了理念才*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则又正与首二句所写的 “尊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所以下 半阕开端乃曰“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再由 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尊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尊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至于“阕”则原是指 乐曲之一章的终了,所谓“新阕”即是另一章新的乐曲,而 “翻”则是重新演唱之意,大概古人演唱离歌常不仅只是唱 一首,而是一支曲既终,再接唱另一支曲,不断演唱下去 的。唐代王昌龄在一首《从*行》中,就曾经写有“琵琶起 舞换新声,总是关山离别情”之句,其所谓“换新声”也就 正是“翻新阕”之意。而欧词此首《玉楼春》乃曰“且莫翻 新阕”,是劝止那些演唱离歌之人不要再接唱什么另一曲离 歌了,因为仅只是一曲离歌,便已是可使人悲哀到难以忍* 了,所以下句乃曰“一曲能教肠寸结”也。前句“且莫”二 字的劝阻之辞写得如此叮咛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 的哀痛伤心。 写情至此,本已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 修却于末二句突然扬起,写出了“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 风容易别”的遣玩的豪兴,这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 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大的特色。我以前在 《灵谿词说》中论述冯延巳与晏殊及欧阳修三家词风之异同 时,就曾指出过他们三家词虽有继承影响之关系,然而其词 风则又在相似之中各有不同之特色;而形成甚为不同之风格特色的缘故,则主要在于三人性格方面的差异。冯词有热情 的执着,晏词有明澈的观照,而欧词则表现为一种豪宕的意 兴。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 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写出了“直须看 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的豪宕的句子。在这二句中, 不仅其要把“洛城花”**“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 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 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 “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 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 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其实“豪放中有 沉着之致”不仅道中了《玉楼春》这一首词这几句的好处, 而且也恰好正说明了欧词风格中的一点主要的特色,那就是 欧阳修在其赏爱之深情与沉重之悲慨两种情绪相摩荡之中,所产生出来的要想以遣玩之意兴挣脱沉痛之悲慨的一种既豪宕 又沉着的力量。我以前在《灵谿词说》论述欧阳词时,曾经提 到他的几首《采桑子》小词,也都指出过欧词的此一特色。不 过比较而言,则这一首《玉楼春》词,可以说是对此一特色*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已。 浓缩《名作欣赏》杂志40年精华 含英咀华,尽享古今中外文学盛宴 名家云集,群星璀璨,泽被几代读者 作者阵容强大:萧乾、周汝昌、施蛰存、萧涤非、沈祖棻、李健吾、程千帆、袁行霈、吴小如、叶嘉莹、余光中、谢冕、柳鸣九、陈思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