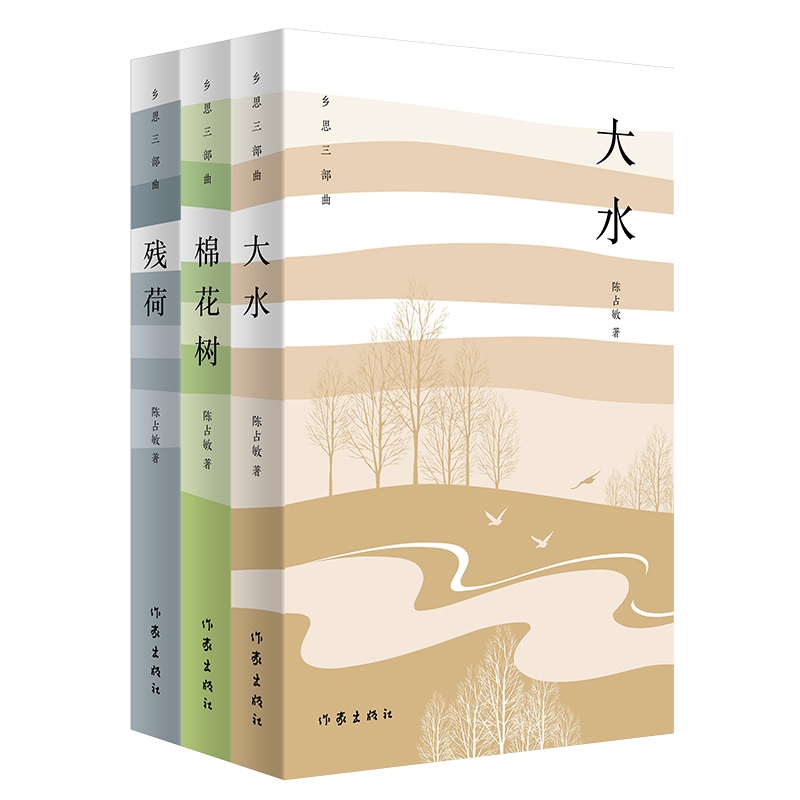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8.60
折扣购买: 乡思三部曲(全3册)
ISBN: 978752121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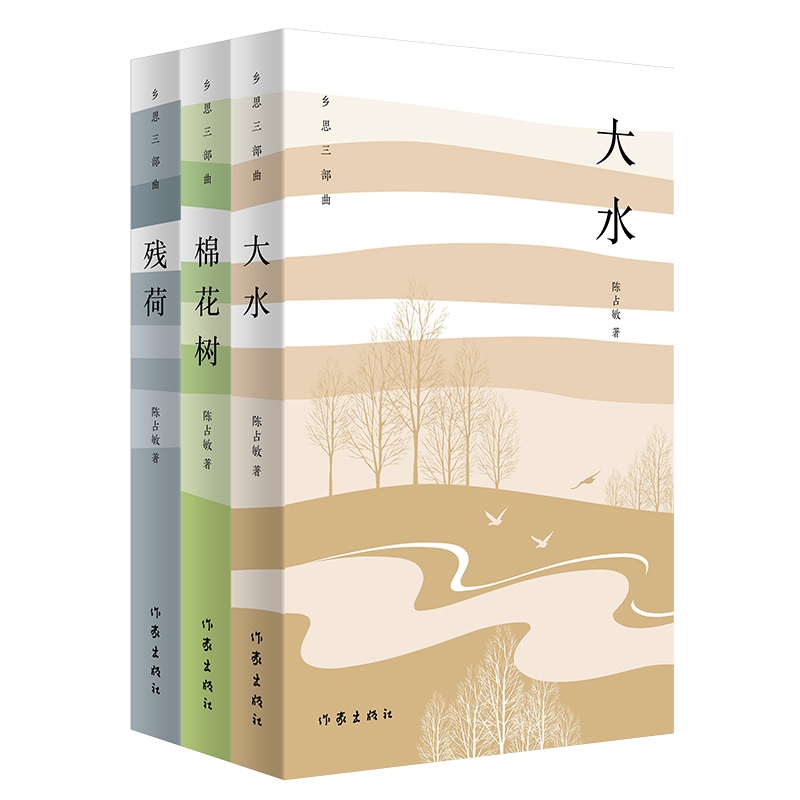
陈占敏,1952年生,山东招远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淘金岁月》《九曲回肠》,“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文论专著《忧郁的土地——俄罗斯文学笔记》《李白的选择》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七百余万字,并出版译作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还乡》等。获首届、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齐鲁文学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山东文学》创刊45周年优秀作品奖等奖项。
义 齿 野马河大洪水那年,十八岁的汪兆平要出外学艺了。男人到了十八岁,总要学艺的,不是出外,就是向内。汪兆平先沿着大水的反方向走,大洪水从高处流向低处,他相信溯着大水流下来的方向一直走向高处,会找到高人拜师,学到桃园村没有的技艺,养家糊口,济世救困。 不知道大洪水的源头会是哪里。最高处当在天上,天下大雨时,大洪水暴发,地上的水连接到天上,茫无际涯。可是大雨已止,被大水洗过的天空一片碧蓝,不见一星水的影子,野马河的水依然滔滔不息,汪兆平就不知道水是从哪里来的了。如果需要溯流而上,一直走到天上,才能找到世间罕见的高人拜师学艺,汪兆平倒正好可以看看天上的人用什么样的牙口吃饭。 河水已经变清,能看见大洪水冲下的巨石,卧在河床上,像马头,像牛头,像所有巨兽的头骨没有烂透。汪兆平用心思索,想不出野马河是因为河里的巨石样子才叫了这样一个名字,还是因大洪水暴发时的大水模样而命名。大洪水暴发时的景象触目惊心,不堪回首,想不出来,不想也罢,反正那是祖宗留下来的遗物,接过来传下去就是了。要紧的是不能失去方向感,沿河水溯源而上,离源头越来越近,离太阳也不会越走越远。可是一天天走下来,汪兆平发现他根本走不出大山。河水流经的地方,并不是全部都能容人走过去,人只能顺着河水往下走,顺流而下才能找到出口。十八岁的人生太阳挂在东南方的天上,汪兆平向高处走的信念一下子崩溃了,他不由得仰天长叹: “天哪,人和水一样,走不到高处去啊!” 人并不全是水性的,不服输的汪兆平改变方向,掉头而下,顺着河流往下走,不直接走向大海,走到河流开阔处折向西方,扔下河水不顾,想划一个圈再走向高处,最终走到那有高人传艺的地方。人烟开始稠密,汪兆平第一次看到比桃园村更大的村庄,房子也比桃园村的房子大,不是用乱石砌成,而是青茬方石以上加了青砖,有高头大马拴在墙中间圆的环石上。他走近门口,门口站立的人问他是讨饭还是扛活。他问讨饭怎么讲,扛活怎么讲。人家告诉他,要是讨饭,吃了饭还要屙在东家的土地上,要是扛活,离开大门口往四方走,走到任何一块土地上,伏下身子干活就是了,那都是东家的土地,东家自会给饭吃。汪兆平志不在此,他的志向比一个人吃饭干活远为宏大,他不会在口大口小的问题上生疑,跟人赌输赢。夸口的人跟他说同样的语言,并没有自负的高门楼腔调。他明确地告诉对方,他离家外出是要学艺。这一来对方把两只手叉到腰里,说他要学艺来错了地方。汪兆平想知道原因,此人鼻子里哼一声,说: “富人从来不教穷人致富的手艺。” 汪兆平老老实实说:“我并不想挣钱哪!” 那人瞪大了眼睛说:“学艺不挣钱,学艺干什么?” 汪兆平说出两个字来,他自己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理想。” 自古以来,有一些高尚的念头并不是什么人教会的,而是像十八岁青年汪兆平的理想一样,来自神启。佛和道都是如此。有时候并不需要坐到大树下、骑到牛背上悟道,站在大户人家的高门楼底下,也会打通天禀,尽管高门楼外边有人把门,像天上的司阍不准人随便进天堂,令人上下求索而不得。汪兆平瞬间心智大开,像打开了天门,哗啦啦显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他看见大门里边有男人女人走动,男人向男人垂首打躬,小心翼翼说“是,老爷”,女人向女人俯首请安,柔声细气说“是,太太”。男人抹一抹油亮的唇髭,闭紧嘴巴,庄严地点头,看不见牙齿。女人用手绢按一按唇膏,莞尔绽笑,露出闪亮的牙齿,比桃园村未出嫁的姑娘牙齿白,桃园村已婚女人则没有那样一副好牙齿,早已在远远未届没齿之年掉落了。汪兆平眼界大开,惊讶得合不上年轻的嘴巴,他问像牙齿一样守住大门口的人,高门楼里边的女人牙齿为什么那么白,守门人用蔑视的语气说: “刷牙嘛。” 用不着细加解释,汪兆平就明白了刷牙的道理,那跟刷锅刷碗洗刷一切污垢应当是同样的道理,不过,疑惑随之而来,即便他学了刷牙的手艺,带回去也用不到桃园女人身上,她们的牙都没有了,刷什么?他把疑惑跟守门人一说,对方就告诉他一个替代的法子: “装上义齿嘛。” 汪兆平想不明白。 守门人简明地说:“假牙。” 守门人把腰弯一弯,把嘴对到汪兆平的耳朵上,小声告诉他,看见那个穿绫着缎的太太了吗?那一口牙齿白白闪闪的,其实就是假的,装上去年纪轻轻漂漂亮亮的,拿下来就成老太婆了。汪兆平毫不怀疑对方悄悄泄露的秘密。桃园村的女人还不老,就掉落牙齿像老太太了,高门楼里边的女人实际上已经老了,却仗着一副假牙重新获得了年轻,世界不应该如此不公平。汪兆平学艺的目标当下确定了,他就要去学一门装假牙的手艺,让桃园村的女人,让他的手艺能触到的女人,都有一副假牙吃好东西。桃园村还没有这样的大房子,全世界这样的大房子也不会多,让另一些女人俯首请安说“是,太太”,就不必了。 女人们会不存妄想吗?女人的妄想距汪兆平的理想还会有多远?女人们天生喜欢吃东西,她们原来的牙齿掉光了,没牙大口,还是会咀嚼不止,慢慢咀嚼食物和时光,直到老死。她们装上了假牙,看上去比原来年轻,重新武装到牙齿,她们会不向往原本吃不到的好东西吗?看一看我们人类丑陋的远古“亲戚”,南方古猿阿法种,女性的牙齿还是比男性大,那还不是假牙。冰河时代地球上覆盖着大片苔原,像长毛猛犸象那样的巨型动物在冰冷的苔原上存活,母猛犸象的牙齿至少跟公猛犸象的牙齿一样大,才能够啮嚼着苔原,生息繁衍。巨大的猛犸象牙要是取来,装成女人的假牙,那就不仅可以在司阍守住的大门里走来走去,让另一些女人俯首请安说“是,太太”,也可以让男人们俯首称臣,跪下去口称“陛下”了,“陛下”来“陛下”去的,念念不止。说真的,汪兆平的理想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呢,可惜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一心想找到会装假牙的高人学艺,顾不得去想一部牙齿的进化史。人,往往想不到他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学艺的路程仍然无比迢遥,是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的盲目乱闯。大房子里装了假牙的女人,不吃东西的时候紧闭嘴巴,绝不泄密。守门人警告汪兆平,绝不敢在高门楼里边说假牙,任何人都不准知道女人的假牙是在哪里装的。汪兆平要学与口齿有关的手艺,附近就能找到高人。有人在东北面的小村子出生,诞出时异香满屋,母亲不痛,光彩环绕,婴儿不哭。长到会哭的时候,开口诵经,念成高道,自立宗派。带徒弟西行,在大雪山觐见杀戮无数的皇帝,劝皇帝“敬天爱民以治国,慈俭清静以修身”,皇帝听不听,他倒管不着,心意自是尽到了。还有人在西南方的古村落治学,通音韵,知《春秋》,在研究大荒山的远古动物中用力甚勤,硬是从故纸堆里找出世人谁也没有见过的动物,一一画图,说明它们产自哪里,喜欢吃什么东西,叫声是不是吓人。画出牙齿的动物却不算多,看来也与装假牙的手艺甚远,不堪为师。往南走,一直走进大山里,估计跟野马河发源的大山不远了。三座山峰尖利地插向天空,像地球的牙齿要咬嚼流云和世风。有人曾经拿一把大刀率众起义,占山抗敌,大刀柄在山岩上矗立,戳出坑窝,积水生鱼。那种起义的武艺汪兆平不想学,他祖上是朝廷的顺民王法的偃草,十八岁的汪兆平从来都没有打算造反——长出锐利的牙齿去咬官家。他的“牙齿观”——包括真牙和假牙——只停留在咀嚼食物的阶段;而当作武器,像人类的始祖那样去攻伐撕咬,已经被他远远地抛在史前时期了。 让三颗牙一样的大山去咬天吧,汪兆平沿山麓西行,跟当年官兵剿灭起义军下山班师回营的路径一样,归宿是一个大村镇。原来是枣村。跟桃园村同样以果树命名,这里吃的果子却不一样,枣是干果,比桃子坚硬,显然需要好牙口。这里的人倒未必不掉牙吧?果然,他们防患于未然了。有一家店铺的门前挂一面红色的旗幌,画了一副白牙不闪亮,黑字写了“镶牙”。 不到学艺满师,汪兆平弄不明白为什么镶牙的手艺会传到这里,到底是从哪里传过来的。想来应该与火车有关。火车那玩意儿,如同某位南美洲作家说的那样,像一个厨房后面拖着一个小村子,负责那么多人吃饭,自然会配备镶牙的手艺,火车走到哪里,就把假牙装到哪里。据说是德国人在这里修了铁道,德国人红毛绿眼睛,牙齿自然也是异色,黄色的金牙必定是他们带来的。德国人把铁路从胶州湾修过来,胶州湾靠近狼牙台,狼牙嘛,假牙有时候必定很大,咬钢嚼铁,茹毛饮血。后来知道了琅琊台是秦始皇迁三万农户用土筑起来的山,皇帝以土代玉骗人的,秦始皇本人也没有装上玉做的假牙吃东西。最确切的假牙来路大约是戏子的嘴巴,有一帮戏子从“张大口”来,女戏子演穷人家的女儿,没有咸东西吃,白了头发,一张嘴两颗金牙黄灿灿的,白发飘飘,满台舞蹈,大嘴号唱,金牙不掉。大家替戏子着急,她那么年轻漂亮,牙齿已经掉了,装上了假牙。她没有咸东西吃,舍不得以身饲虎走入娼门饫甘餍肥,她可以拿下金牙换饭吃嘛。后来知道了她原来的牙齿没有掉,是敲掉了真牙,装上了假牙,好多人不明白她到底是为什么,学艺成熟的汪兆平倒能够理解,他说: “二鬼子把门,好看嘛!” 《乡思三部曲》是作者倾注心力的作品,是对故乡的致敬之作。“乡思”是复杂的:悲叹、愁绪、焦虑、温暖、激越,一代代人活着、走过、远行,但长存的是沉默的土地,鲜灵的生命与苍茫的土地蕴蓄着历史,成为作家精神投注的可靠而具体的母体。作者是有学养的作家,文字老到,有表现力,在文字的背后,时时有作者冷峻审视的目光,使作品具有透析内里的理性色彩;在叙述上,历史 现实杂糅,一唱三叹,反复吟咏,形成一种压迫式的接受氛围;他并不追求故事性,甚至有意通过短小的人和事将故事切碎,而用某种气韵勾连。作品写了三代人,但时间近乎是静止的,只有生活在缓慢流淌,这里有社会时局变幻的投射和自然灾害的碾压,有生命的坚韧和向往的能量,人情人伦人性自然生长,生存状态、传统因袭、乡土结构在密实的铺叙中肌理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