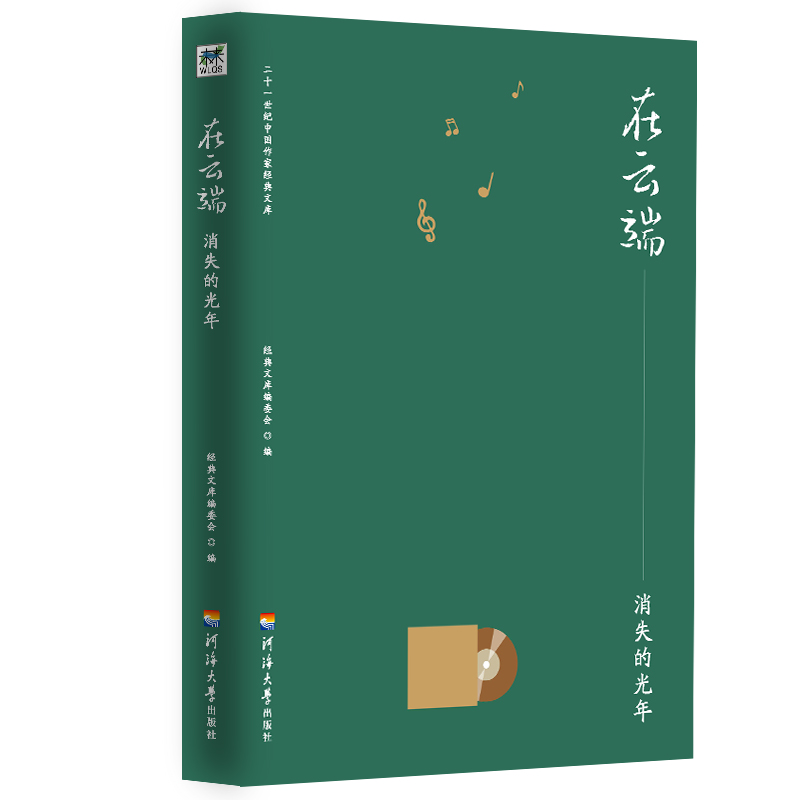
出版社: 河海大学
原售价: 59.8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在云端--消失的光年/二十一世纪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ISBN: 9787563059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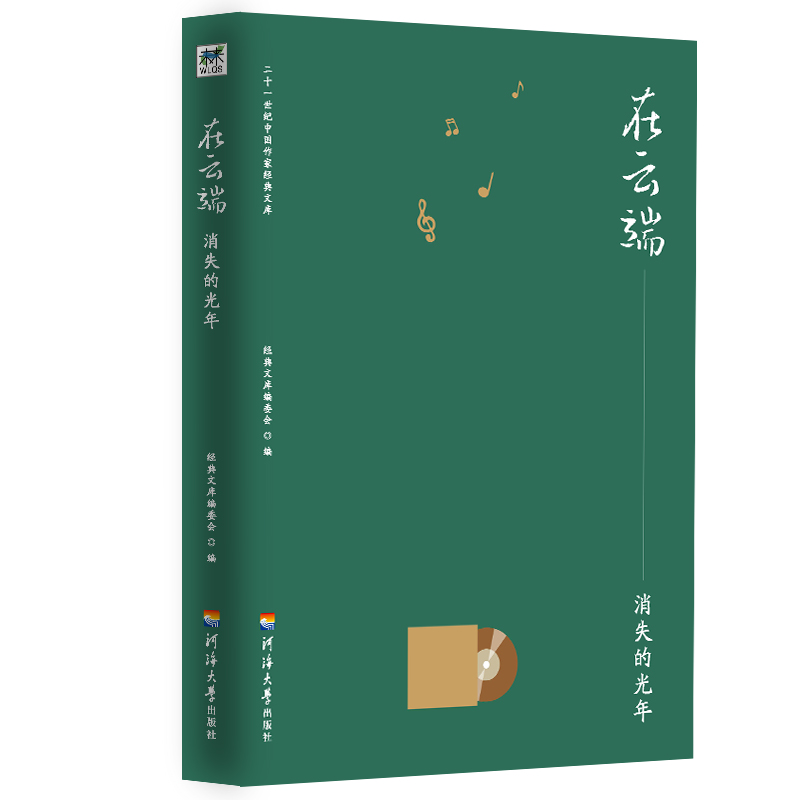
远去的笸箩 张静 外婆走的时候,棺木里放了好多东西。吃的、喝的,包括她老人家曾经喜欢穿的衣裳、用着顺手的旧物,都给放进去了。唯一的针线笸箩,被老姨们和妗子拿在手里,端详着,摸了半天,还是取了出来。大姨念叨,咱妈平日里用惯了,瞧这笸箩被使唤得油光发亮,细滑柔软,放进去,真有些可惜了。 就这样,外婆的针线笸箩被留了下来,缝缝补补,又是好多年。 后来,我婆去世了,她的针线笸箩虽然也被小婶子留了下来,但几乎不太用了。我偶尔去小叔家的时候,笸箩静静地躺在炕头一角,里面堆满了随身穿的小衣物,鼓鼓囊囊的,将笸箩压得变了形,这多少让人看了有些遗憾。 记忆里,女人炕头的针线笸箩是轻轻巧巧的,但它却盛放了太多的岁月流年。尤其是在那些缺衣少穿的贫瘠日子里,乡下人一年四季从头到脚穿的粗布衣物,长的、短的、薄的、厚的,都是用笸箩里的针线缝起来的。先是我爷前日下地干活时磨烂的袖口、松了的纽扣、刮破的衣襟;再是三叔的袜子,在生产队平地时,拉着架子车满地跑,脚后跟烂了个大洞,挑衅似的张望着;还有,小叔的裤脚又短了一截,眼瞅着天越来越凉了,需要接一截布……这些细碎的紧要活,我婆得赶着日头做。比如趁着早起窗外透进来的亮光,或者落满夕阳的窗台,不大工夫就完成了。若是整件的衣裳或者裤子,那就只能等着下雨天或者农活不紧时,摊开场面做。她早早将被子叠起来,炕头收拾利索,然后将裁剪好的布平铺。那只笸箩,就放在手边,一轱辘线,被婆不停地取出来,放进去,穿一些,再穿一些。她一针一针扎下去,袖子、领口、前襟,一片一片衔接起来,风声、雨声和婆的背影成为那个雨天里一帧温暖的水墨画。 婆的笸箩形状像一弯月,里面放着颜色、粗细各异的线,剪刀,铜顶针,碎花布,以及一本发黄的书,书中夹满了一家老小一年四季用的鞋样、窗花。对了,还有绣花用的箍圈,都一一躺在笸箩里,静静恭候,某天某时某刻它们会被派上用场,好让全家人安然度过风霜雪雨与寒来暑往的四季。 笸箩一般是用细柳条编制而成的。去掉皮的柳条白生生的,乡下人叫水柳,长在水边,与芦苇一起,沐浴溪流、日光和风。待某日,长得婀娜多姿、纤细柔曼时,村子里的篾匠张四会用一把亮闪闪的篾刀褪下它粗糙的外皮,顺着柳条的纹路经脉,一层一层割出自己需要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再经日光锻打、炉火熏烤,直到它柔韧结实,可以任意弯曲或折压为止。待农活清闲时,张四寻屋檐下一处干净的地儿,他的拇指按住刀口,柳条反复在篾刀上划过,直到被打磨得透薄光滑。用他自己的话说,篾匠活不难,细数活,主要是在一双手“砍、切、拉、编、磨”下,笸箩、簸箕、背篓、筛子、笼子等就出来了。我亲眼看到,他劈出来的柳片,粗细有致,青白分明,一点毛边都没有,可他那双手,早已糙如老树,手指头上布满了细细的口子,连关节也稍微弯曲变形。我问他,四爷,你手疼不?他笑着说,手上磨出的茧太厚了,早感觉不到了。完了,又多说一句,娃呀,你好好念书,爷这手艺养家糊口还凑合,要想过上好日子,难! 冬闲时节,家家户户的炕头上,笸箩闲不住了,它被乡下女人翻来翻去,织补着各自心头的喜怒哀乐。比如,隔壁八婆家老二刚子的媳妇怀孕了,满村子让刚子找酸杏子吃,眼见那肚皮一日日鼓起来,尖尖的,肯定是个顶门杠子。三婆一边给孙儿缝老虎枕头,一边乐得合不拢嘴。前街的秀红姑姑刚刚和镇上家境殷实的药铺老刘家订婚了,郎才女貌,村里人都说,天造地设的一对。秀红姑姑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厢房里,给心上人绣鞋垫。一双纤细白净的手在针线笸箩里刨来刨去,红的、绿的、蓝的花丝线,也在她手里比画来比画去,直到鞋垫上红的花绿的叶,活泛逼真。尤其那鹊儿,红嘴,黄脚,蓝羽,乌溜圆的黑眼,似要张嘴说话呢。 月亮悄悄爬上树梢的时候,夜渐深了,街门六婆家传来时断时续的争吵声,一声高过一声。不一会儿,那争吵声变成重重的摔门声,紧接着,是六婆的低啜声和六爷的叹息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听得出,是六婆的三个儿子为分家吵起来了。六婆很伤心,她一边抹眼泪,一边从笸箩最下面取出一个裹得严实的手帕,给六爷说,家里就两块能浇上水的水田,咋分都不能称三个人的心;再说了,水缸、面瓮、坛坛、罐罐,他们看上啥,都拿吧,咱俩一把老骨头,好凑合。要不,棺材板,先不买了,搁搁,用这钱给娃几个每家买个新锅,再添置些新碗筷,过日子嘛,不能让人笑话。六婆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的鞋底正好是最后一针。大抵是针尖使唤长了有些干涩了吧,她抬起右手,捏着针,从花白的耳鬓边上划了几下,狠着劲戳进鞋底里,拽着线拉过,打好死结,嘴上去,轻轻咬断线头,然后将针别在线轱辘上,收进笸箩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屋内灯火昏暗,两只孤单的影子落在窗户上。 快过年了,大雪纷飞,五婆家的翠红姑姑过两天就要出嫁了,火炕上,五婆从她的针线笸箩里取出一根绳子,开始给翠红姑姑“挦脸”。这是旧时关中乡下女子出嫁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被“挦”过脸的新娘子,皮肤鲜亮细滑,泛着微微的潮红,楚楚动人呢。要说的是,五婆是村里的“挦脸”高手,手中那根绳子,不知挦过多少张淳朴美丽的面庞。这一次,是她的小女儿翠红。她挦得很细。两只手使劲绷紧绳子,顺着女儿脸蛋自下而上一圈一圈,轻轻碾过,不怎么疼。大约一炷香的工夫,翠红姑姑脸上那些细密的、肉眼看不见的茸毛便褪得干干净净,整个脸蛋红扑扑、亮光光、嫩生生的,看着越发俊了。 很多年后,翠红姑姑总会想起那个风花雪月的旧历年,那个红烛摇曳的夜晚,一弯清月悄悄爬进院子,落在贴满大红“囍”字和“百鸟朝凤”的小窗轩上,透着一抹嫣红的光亮。她心爱的男人,毛毛躁躁又急急切切地进来了。他用有些颤抖的手,轻轻地、一层一层地褪去她的大红棉袄,然后,吹熄红烛,将两个人卷进柔暖的大红缎面的被子里……炕头的角落里,她的婆婆早已安放好了一只簇新的针线笸箩,里面放着簇新的丝线、簇新的顶针,以及簇新的剪刀和针,似要将小两口簇新美好的日子缝起来。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五婆早已离开人世,翠红姑姑日渐老去,耳鬓的白发跟霜染了似的。她的儿女各自成家,空闲时,孙儿孙女们围着她,叽叽喳喳,好不热闹,哪里还有闲工夫穿针引线?用她的话说,生活好了,日子日新月异,现在的孩子们哪个愿意穿手工做的衣裳?连自家娶来的两个儿媳妇,都只想着外出打工挣钱,东奔西跑,没有一个能静下心来,做几件针线活。这平日里,身上的鞋子、衣裳,全在商店里买,方便啊!说完,她的目光落在炕头的针线笸箩上,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叹息:多好的笸箩,成摆设了。 后来,再见到它,是在喧闹的城市一角,一个民俗小吃餐馆里,很多旧时的物件都摆在那里。一只很旧的笸箩,也静静地挂在用麦草和泥巴糊起来的墙上,落满了微尘,像乡下女子远去的岁月。 绛帐是一层轻幔 张静 初见绛帐,我十二三岁。 那时,乡下人穷哟,尤其是小孩子,打从娘肚子里出来,基本被窝在庄子里,除非考上学,才像一只插上翅膀的鸟儿一般飞出去。其余时间,大都围着三寸金莲的婆、大襟开衫的爷,以及爹娘和一窝子的兄弟姐妹,打发一个个长长的白日和黑夜。偶尔,小孩子会随着大人去距离村子十里八里以外的镇上,转悠几回,便是莫大的欢喜和开怀。 记得那年冬天,父亲要去绛帐镇上卖大白菜,我和妹妹央求了半天,他总算应允了。当我们父女仨拉着架子车翻沟上塬,一路小跑来到这里时,浑身上下几乎都湿透了。 顾不上擦拭额头上细密的汗珠子、拍去一路沾染的尘土,我的双眼一下子就被这座古镇的繁华、热闹和喧嚣吸引住了。 我们是从南城门进到镇子里的,很陈旧的城楼,像极了我在老电影里看到的老建筑。尤其是城楼上随处可见的雕花砖头,像一朵朵盛开的莲花,伸展在青灰的墙面或高高翘起的檐角处,多看几眼,会有一种错觉,仿若回到久远的时光深处,一种书本里称为古朴厚重的感觉,从心底缓缓升起。 镇子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那些如父亲和母亲一样勤俭节约的乡下人,从臃肿破旧的棉衣里面掏出卷得皱巴巴的票子,一斤猪肉、三斤白米、一块蜜粽糕、一捆油麻花、几尺花布或几把丝线,满脸笑盈盈的,仿若日子会在一衣一袜、一饭一粥中,火旺起来。 和我的杏林小镇截然不同的一点是,在这里,你时不时地会听到一阵又一阵的绿皮火车鸣笛声声,长啸而来。紧接着那高高架起来的喇叭里一定会传来女广播员一串甜美的普通话,听来如叮咚流淌的山泉一般澄澈和恬静。若逢节假日,还会看见一群又一群留短发、戴眼镜、背书包的莘莘学子,将乡下人贮存了太久的梦想一步一步从这里延伸出去。这长长的绛帐站台前,曾留下多少送别的身影和深情的叮咛,早已数不清了。当然,偶尔也有穿中山装、戴金丝眼镜的各色商人或干部,匆匆来匆匆去,他们像一缕清风,或者像一道靓丽的风景,给这座古朴的小镇注入新鲜的血液。一些属于城里的那种时尚和贵气,也开始一点点云集这里,一段时间,绛帐小镇的繁华和瑰丽,赛过县城的老街。 再次和绛帐相遇,是跻身窄长的独木桥上苦苦挣扎的寒冬腊月里,母亲的腿疼病犯。在县医院拍了片子,无大碍,可依然会莫名疼痛,严重时竟然无处下脚。后来,听说绛帐镇上的一位王姓大夫针灸是一绝。一日,随母亲一起寻到这里,恰逢大夫不在,问了隔壁的裁缝店的大婶,说是去吃一个亲戚孩子的满月酒,得等一两个时辰才能过来。 用一两个时辰等一个并不熟识的人,想来都是一件漫长无味的事情,倒是母亲,早已习惯了乡下的慢节拍生活。她坐在诊所门口的台阶上,冬日的太阳,暖暖地照在她的身上。母亲满脸安详,气定神闲,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而我,在焦灼中,不停地来回走动。 母亲知道我等急了,便说,我一个人坐在这里等就是了,你去街上转转吧! 你一个人,行不? 那有啥不行的,拐角的太阳这么好,正好可以晒晒,去吧! 一个人出了浅浅的巷子,来到街上。和我小时候来这里时相比,此时街道平整了很多,也宽敞了许多。尤其是东西南北两条街道在古镇中心交会,形成了繁华的十字路口。此时,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嘈杂人流声、车流声,掩在熏暖的阳光下,像一幅火旺的盛世烟火图。哦!这座在我生命里曾经留下光鲜记忆的古镇,并不曾因为时光的蹉跎而衰减,那一丝丝令我羡慕而熟悉的商业气息依旧在这里繁衍着,浓厚着。 我环顾四下,曾经陈旧的、高矮不一的门店基本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统一规划的、错落有致的砖瓦房,红色的砖,灰色的瓦,还有高高翘起的飞檐下,一扇扇干净明亮的玻璃窗,烁然生辉,这一切,无不向我传递着这座平原小镇的祥和、富足与和谐。 绛帐小镇的人,从穿着打扮到衣食住行,显然要比我的小村庄好得多。他们面色红润,心宽体胖,甚至连说话的底气都很足。你瞧,每当任何一辆火车到站的时候,满站台推着小吃叫卖的绛帐人,面带微笑,亮着嗓门,从一扇窗户跑到另一扇窗户,那一声声此起彼伏的“肉包子、菜包子、玉米棒子,还有香喷喷的茶叶蛋,不好吃不要钱,来一个吧”的叫卖声,随着火车传出老远。 那一天,我悄悄发誓,一定要挑灯苦读,争取榜上有名,从这里登上一辆火车,或南下或北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几个月后,我果真如愿以偿了,走的那一天,特意坐了火车,父亲送我到绛帐,我的眼里,有哗哗的泪水,情不自禁地涌出来。绛帐,就这样成为我生命的驿站。这驿站,藏着很多如我一样的家乡学子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情结。 在古都咸阳上学的几年里,我的老乡中有好几个来自绛帐的。有一回,大家聚在一起,讲着各自家乡的传说故事,其中,有个齐家埠的老乡给我们讲了他们村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老乡说,传说很早的时候,一户齐姓人家,生育了三个子女,男耕女织,非常恩爱,后来边关吃紧,丈夫被强征入伍,不久便传来丈夫战死的消息。妇人悲痛欲绝。面临困境,为了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她拒绝了所有劝说让她改嫁的人,独自挑起生活重担,并在渭河渡口的“十字路”边摆了一个“小茶摊”。她在经营中诚信待客,童叟无欺,赢得八方来客的赞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积攒,她开始买下一片地,盖起了旅馆和饭馆,生意越做越大、越来越红火,并赢得人们的爱戴。于是随着她的生意日隆,“齐寡妇”的人称就代替了那个地名,后感觉不雅,因渡口的地貌,便演绎成“齐家埠”。不用说,因为这个美丽的传说和齐家妇人的勤俭持家、宽容忍让、诚信为本的优良做人品德,成就了这块神奇土地上后来的繁荣和富强,也造就了祖祖辈辈勤劳朴实、智慧贤达的绛帐人。 之后,回老家,从老辈们嘴里得知,明清时,绛帐古镇名噪一时。在这里,南山的木材山货,北山的粮食,都会从方圆百里之外云集。一段时间,它一度和眉县的齐镇,周至的哑柏,宝鸡的虢镇,并称为“关中四大名镇”,从而成为关中地区商贸中心。 熟稔绛帐与马融,主要源于我的二叔,他曾是绛帐镇上宋乡的土地干部,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退休。可以说,我二叔的大半辈子光阴和热血都洒在那片土地上了,故而,他对绛帐的情感早已超过了生养他的杏林小镇。 关于绛帐,二叔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比如那里的河流、村落、土地、历史、风俗等,二叔耳熟能详,如数家珍,尤其说到马融,二叔总是满脸的兴奋和骄傲。他不止一次地托着眼镜,正襟危坐,给我们讲马融。只是,那个时候,我固执地认为,只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马融如何,他的思想如何,又不考试,听听就可以了。故而,二叔灌进我耳朵里的,只有一些关于马融的皮毛。比如,我仅仅知道,马融是东汉时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是汉代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之一,是儒学发展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有一次,回老家,去看二叔,碰上村子里的五伯正在向二叔打探镇上一户人家。五伯走后,我问二叔,绛帐镇是否还是原来的模样?二叔说,火车站撤了,热闹的镇子一下子衰败了。再问及当年马融的讲经台遗迹,他沉默了一小会儿,有些落落寡合地说,早已杂草丛生、残败不堪了,倒是街道中心乡民集资翻建的几处城楼,很是壮观。 提及讲经台,二叔的话匣子又打开了。和前几次不同的是,二叔讲着,我细细听着,听着一代宗师马融如何在自己的垂暮之年,在古镇绛帐,把东汉的儒学推上了一个无人可及的高峰。从二叔嘴里,我终于知道,马融大师,在这片曾经叫作“齐家埠”的地方,筑起高台,撑起绛色帐篷,四方儒士听讲者逾千人。这位学富五车的儒学大师,为使学生注意力集中,讲学时故意于帐后设列女乐,一边书声琅琅,一边轻歌曼舞,竟互不干涉。传说有一次,有学生按捺不住,用书卷挡住头,悄悄朝着帐后顾盼,马融执草秸怒打,鲜血染遍秸秆,掷之于地,秸秆复活,开花结果,人以为奇,便将此草称为“传薪草”,故“绛帐传薪”,至今广为流传。 起初,我对二叔讲的“绛帐传薪”的故事,打心底里是藏有几分排斥的,甚至有那么一点嗤之以鼻的,不就是一棵草,有那么神奇吗?竟然在地上只甩了几下,就能甩出淋漓的鲜血出来,胡乱诌的吧?直到后来,二伯的孩子中师毕业在县里做了文书,每每周末或农忙时分,他会拿回来一些书,其中不乏一些关于扶风人文历史和村庄故事的书籍,我空闲了会找他借来看看。看得多了,关于“绛帐传薪”的诸多疑惑被解开了,心中豁然,并为自己的浅薄和无知自惭形秽。再后来,考上学,爱上读书和写作,那些寂静的夜晚,我埋头不停歇地写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浓情厚爱,自然也会搜肠刮肚地去苦苦寻觅在漫漫的岁月长河里,那片土地上曾经有过的历史文化、习俗风情或者人物传奇。 那日,闲来读书,读到清代扶风知县刘瀚芳一首名曰《绛帐》的诗赋时,心里更加亮堂起来,不由得安静打坐,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读了起来:“风流旷代夜传经,坐拥红装隔夜屏。歌吹祢今遗韵在,黄鹂啼罢酒初醒。” 两遍下来,竟觉回味无穷,感叹不已。忽地,我的眼前浮现出当年的九州学子扬起一缕又一缕飞扬的尘埃,从四面八方齐奔绛帐、求学拜师的一幕。那些个寂寂长夜里,那个令我扶风万千子民敬仰崇拜的马融大师,一袭长袍,端坐于讲经台上,斑白的须发在夜风里轻轻飞舞。他的脚下,数千弟子,手握书卷,正襟危坐,高昂的诵书声,穿破长夜,飘向漫漫长空,这声音,久久回荡在绛帐这片热土上。不必说那些列女闲情雅雅,琴瑟幽幽,难能可贵的是马融及其弟子浸泡在粉黛雅乐里的那种淡定与超然,这正是东汉儒学文化迸发而出的魅力,也是一代大师马融独一无二的风骚。 说起马融与“绛帐传薪”,不得不提及卢植。甚至可以说,是马融的“绛帐传薪”为曹操赋予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的一段佳话奠定了基础。卢植身长八尺二寸,声如洪钟,性格刚毅,品德高尚,常有匡扶社稷、救济世人的志向。卢植年少时拜马融为师,博古通今,喜欢钻研儒学经典而不局限于前人界定的章句。马融是外戚豪族,家中常有歌女表演歌舞,而卢植在马融家中学习多年,从未瞟过一眼,马融由此对卢植非常敬佩,用真传《忠经》面授之。卢植作为马融的关门弟子之一,勤奋好学,深得马融喜欢和器重,自然得马融经学真传,学业精深,被称之为马融的“门人冠首”。其学成之后,返回家乡教学,并将马融的经学和《忠经》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传授给了刘备和公孙瓒。刘备与关羽、张飞既是结义兄弟,又是他们的师长,我们不难看出,《三国演义》中演绎而出的“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白帝城托孤”“六出祁山”等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无不体现出马融所大力弘扬的“忠义”思想。如今,让人颇为振奋的是,在河北涿州的卢植文化园中的卢植祠里,卢植画像旁边的、由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许继善手书的两幅纪念卢植的诗文,其中一篇是清乾隆皇帝写的赞颂卢植的《涿州览古》,上曰:“为政穷经事岂分,千秋名教系君臣。冒言抗董知谁氏,闻是当年绛帐人。”很显然,此诗里的绛帐,便是马融“绛帐传薪”之地。卢植后来成为汉末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其不论为官还是退居,始终不忘传经授徒,对传播儒家文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然,还有一位汉代的郑玄,为探究儒学真谛,三十岁后西入扶风,经卢植介绍拜马融为师。但当时马融名重天下,弟子众多,出类拔萃者不计其数,郑玄拜在马融帐下数日竟不得面授,但他并不气馁,便在马棚边建一草庐,“日夜诵读,未尝倦怠”。直到三年后,郑玄方才登堂入室,亲耳聆听马融讲学。 郑玄在马融帐下求学期间,没有一味地钻在书本典籍当中,而是学以致用,亲自考证史籍当中的地名人物、风土人情,他的足迹踏遍了周原故土、三秦大地。当时的马融年事已高,他与这位得意门生相见恨晚,怜爱有加,以至于到后来想留郑玄长期在绛帐讲学,传承他倡导的古文经学,使之发扬光大。无奈郑玄是一孝子,他想学成归乡。于是,郑玄在马融帐下七年之后,以“母老归养”辞别恩师。 郑玄走时,马融依依不舍,设宴饯行,他喟然感叹,对其门生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惋惜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郑玄离开绛帐回到高密是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他已四十岁。半年之后,马融溘然长逝,时年八十八岁。又过了半年,郑玄才得到马融死讯,悲痛欲绝! 时光飞逝,绛帐传薪,逐渐销声匿迹,如马融老先生留给后人的是一座愈来愈破败的讲经台,被西风寒霜吹打,被岁月时光剥蚀,以至于在很长时期,它孤寂得无人问津。2014年甲午之秋,因了一场马融文化国际论坛盛会的邀请,我的双脚再次踏上绛帐这片热土。和以往相同的是,我的眼眸间,依然寻不到与马融有关的“前授生徒,后列女乐”的琅琅书声与悦耳丝竹,也寻不到红袖翩跹与风流学士交相辉映的风骚场面。但我惊喜地感受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绛帐贤良之士,正在倾尽他们的热情和力量,一点一点复活和还原一代儒学大师马融的精神和文化内涵。相信不久的将来,“绛帐传薪”之古韵风雅,指日可待。 这样想的时候,一缕秋风正从我的身边轻轻吹过,仿若将马融老先生的呼吸和气息也一并带了过来。 马兰花开 邹安音 岁末,时令大雪。朔风呼啸而至,望长城内外,华夏大地白茫茫一片。山不言河不语,鸟儿飞绝,虫亦无声,了无人迹,仿佛天地封冻。 一个人,静静地,围炉烹茶,手捧卷本。书韵悠悠,茶香氤氲,火苗图腾。古节气令曰:大雪有三候,分别为鹖鴠不鸣,虎始交,荔挺出。“荔”为马兰草即马兰花,还有马莲、旱蒲、马帚、铁扫帚等多种称呼,又俗称台湾草。据说它来源于台湾地区,耐寒,耐旱,同中国东北的乌拉草和南美的巴拿马草齐名于世,被称为世界上的“三棵宝草”。? 看窗外,雪花漫天飞舞,仿若白色的精灵来自天宇,铺陈山川五岳,又潜入大地,涵养旷野。大地银装素裹,河面冰层在加宽加厚,树们看不见风姿,花木失却了颜色,天地间,一切静寂。可室内,沸腾的茶水却撩动了我的心思,想想在这静寂的白色天地中,在厚厚冰层的桎梏下,却有一股不可挡的热潮在涌动,那就是“荔”(马兰花)在汲取着天地精华,感受着春天的召唤,努力挺出冰天雪地,以待芳华再现。我的视线不禁随雪花无限延伸,思维和想象的空间也由此拓展开去。? 去年春天,我行走在宁夏大地,走进了最能代表“江南梦里水乡”绰约风姿的塞上著名湿地公园—沙湖。 “水光潋滟晴方好。”正午的阳光暖暖的,沐浴着公路边盛放的沙枣花袭来醉人的馨香,和风也送来鱼塘略带腥味的空气,融入我身心的便是鱼米水乡的家乡情。我贪婪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绿油油的苞谷林,才露尖尖角的小荷……风吹叶动,忘记了风沙的侵蚀,忘记了荒漠的刺痛,只想朝着前方自由游弋的蓝天白云奔跑,融化在这一方天地中。 白云下面就是沙湖了。 湖边有一蓬青葱的草叶,尖尖的,密密的,连成片,中间是蓝色的小花朵,犹如星光般点点闪烁。“那是什么花啊?”我不解地问。“马兰花!”本地人说。它居然是马兰花!我俯下身子亲吻着小花朵,像久违的亲人!“小皮球,香蕉梨,马兰花开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我手拉皮筋一边蹦跳着,一边歌唱着,这是童年的记忆,很温馨。那时候的我做梦都不会想到,在南方的竹林里唱着马兰花的我,有一天会到北方宁夏荒漠之地和它梦圆! 我的心灵顿时温润如玉,仿佛有一丛丛翠绿的马兰花在生长、在簇拥。那天我走过沙湖的栈桥,你能看见的是什么景致?是几座金黄色的沙丘!沙丘中间,是青草翠微的湿地,有蓝莹莹的小花朵星星般闪烁,那应该就是马兰花们吧。远处,贺兰山的脊骨若隐若现。那山,那丘,那湖,那花和树,就这样完美地构成一幅立体的水墨画,诠释着塞上明珠的风情。而那些赤足奔跑在沙地中的孩子们,则是天地中最动人的风景,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肤色和语言,但是所有孩子都快乐地融化在这一方天地里。贺兰山下,南北方风物也在此交融,演绎出浓浓的华夏风情。 滚滚红尘,风沙漫漫,何尝不是眼前这一幕变化多端的场景。追忆逝水年华,儿时刻骨铭心的记忆,不可缺少的还有露天影院带来的欢乐,或者爱恨。抚摸着马兰花长长的叶子,我想起了一部叫《马兰花》的电影,它占据着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至今仍然记得影片中的几句台词和片段,那纯洁无瑕的花朵,只要面对邪恶势力,它就拒绝开花;相反,面对美好,它却义无反顾地倾尽芳华!忠诚和道义,善良和邪恶,就这样播种到了我幼小的心田里。 今天的马兰花,根植于贺兰山下,生长在黄河岸边,长长的叶片舒展,编织着新的故事和传奇。我不知道它的踪迹会遍布祖国四面八方,甚至到了北方之北和南方之南。 同年夏天的一天,追寻着“鼓浪屿之歌”的音符,我有幸到了福建厦门。海风、椰树、帆船、浪花……午后,太阳炽热,我走进鲜花盛开的鼓浪屿,走过长长的小巷子,在一处青藤爬满小屋的拐角,伫立在一处挂满漂亮草帽的巷道。我拿了一顶黄色的帽子,只因卖草帽的大姐告诉我,这是用马兰草编织的。那会儿,我不免心动,想起了宁夏沙湖的马兰花,想起了《马兰花》电影中花开的镜头……我兴致勃勃地戴上草帽,再看看岛屿上每一户人家窗台上的草木,仿佛都有马兰花的英姿。我哼着“鼓浪屿之歌”,想要倾听音乐般的海涛声,隔峡望一望海那边的岛屿。那天我登上岛屿最高处,看大海中帆来帆去,沙滩上游人如织,眼睛竟然湿润。 回眸低首,炉内茶声响,像人低语,也像书的注解。原来,沙湖的马兰花和鼓浪屿的马兰草来自同一个地方,它们都耐寒、耐旱。我看的书是一本描述中华传承节令的书,书名是《春夏秋冬》。多么好的大雪天! 雪纷纷扬扬,有谁知道,此时的马兰花正吸取天地之灵气而努力挺出大地。莫如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一个“挺”字,彰显了天地万物此时的风华,这是自然界具象的“挺”。长城内外,九州方圆,青藏铁路—天路直通西藏雪域高原,这是中华大地的“挺”。宇宙茫茫,神舟飞船翱翔,这是中国向世界的“挺”……它们一如马兰花,挺住了天寒地冻,挺来了芳华岁月,挺出了灿烂星河。 春天就要来了,是马兰花最先带来了讯息!?? 光阴的渡口 曹文生 让一个人谈虎色变的,只有光阴。 它冷漠,毫无悲悯之心,一转眼就吹白了双亲的头发,顺便也把我的前三十年吃掉。 此时,南窗下,一把生锈的镰刀,紧紧咬住了光阴。它原始的样子,仍在我记忆里活着。那时的它,仍有锋芒,它包裹着农耕文明的倔强;仅仅十年之久,它就老了,被时间淡忘。 要不是我胳膊上的旧疤,我也不会对镰刀的黑铁时代如此耿耿于怀。每当风起时,我的伤口,很疼,我被这疼带到童年的安静里。 童年,有一个数蚂蚁的孩子。 他躲在梧桐树下,看一只只蚂蚁,把童年的往事,搬进蚁穴。 安静,是那个时代的名片。 安静里,还保留着我的狡黠! 那时,我一个人,在母亲监督下,去数无花果的果子,我故意漏数掉几个,母亲居然信了。夜晚,人睡下后,我用漏下的那几个无花果,偷偷果腹。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母亲的眼,是经受过苦难的,她能丈量一尺布,能估量一根针,这一眼看透的本事,是被生活逼迫的;这不算细微的无花果,她不可能数不清楚,这分明是她的关爱。 光阴,沉淀成一本字典,母亲在第一页上。时间,把她从光鲜一直写到苍老,她把自己的一生浓缩在这里。她一个人,沉默地躲在字典里,把村庄的每一条街、每一所房子,都细细地铺展开来。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都挟裹在时间的流水里。哪里是渡口,谁也说不清楚。 “渡口”,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词,或者是一个危险的词。 我想到溺水,想到晚渡。 暮色苍茫,是时候回家了。 这家,在光阴里,已变。 一个人,从母亲的此岸,被岁月摆渡到妻子的彼岸,中间的水, 一直向东流去。我想起孔夫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母亲的岸,空了,时间充当了摆渡人。 身体渡河之后,我就抛弃了村庄。 一个人,在他乡,会莫名其妙地想起一些荒诞的事,譬如我身上的味道,是否还混合有麦子的气息。 一个人把身体扔了之后,只剩下灵魂了。我不知道如何去保鲜灵魂,我把它嫁接在文字里,写诗,写远方。 喜欢一个人,独坐灯下,打开一本书。最好是余华的《活着》,或者是一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把生命的长度梳理清楚,再去分割一个纵向的河流。 也许,一个人,和一片青草,都属于村庄。只是,人面对黑暗,会怕,会自己吓自己。人远没有青草的涵养,青草,永远是安静的。 其实,先离开村庄的,永远是那条叫黑子的狗,头一歪,走了。这安静的样子,多像人啊。 狗,有渡口吗? 也许,很多人说没有。 他们从没有观察过一条狗,他们习惯于以一种高其一等的心态,来给身边的事物命名。 狗的渡口,是柴门;鸡的渡口,是土墙或者树枝。这渡口,是乡村式的。它们,把一个村庄的老人,慢慢地摆渡到生存之外,同他们一起走的,还有动物本身,它们比人安然。 世界上,最厉害的刀,是文人的笔。他们一刀刀把光阴凌迟,一笔笔,把日常的琐碎写进书里。 他们,以光阴为河,摆渡完实物,又开始摆渡灵魂。 也许,一个人,是该把光阴大写了,它,偷运过太多的禁品,譬如青年的性、老人的孤独。 我捡起一片叶子,好像旧相识,它是我的摆渡人吗? 我问自己,问风,问云。也许是,也许不是。它在春天,把一朵桃花的诗句扔给了我。它在秋天,把一秋的落叶扔给了我。我还没转身,就老了一岁。 我的渡口,有船。 母亲是摆渡人,父亲也是摆渡人,我给我的渡口起一个名字,名字就叫草儿垛—我的村庄,它一直活在我的命里。 本书中,作者们通过那些生动而鲜活的文字,去寻味那些已经消失的、不再回头的岁月。常常令读者顿生早生华发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