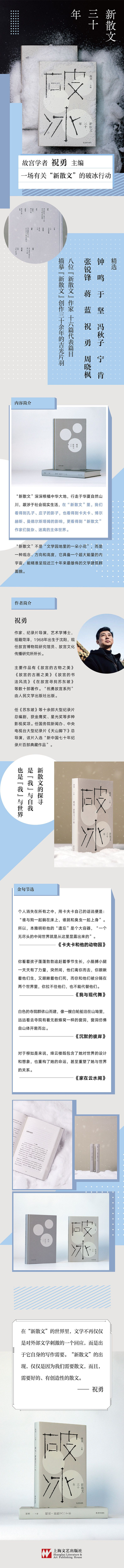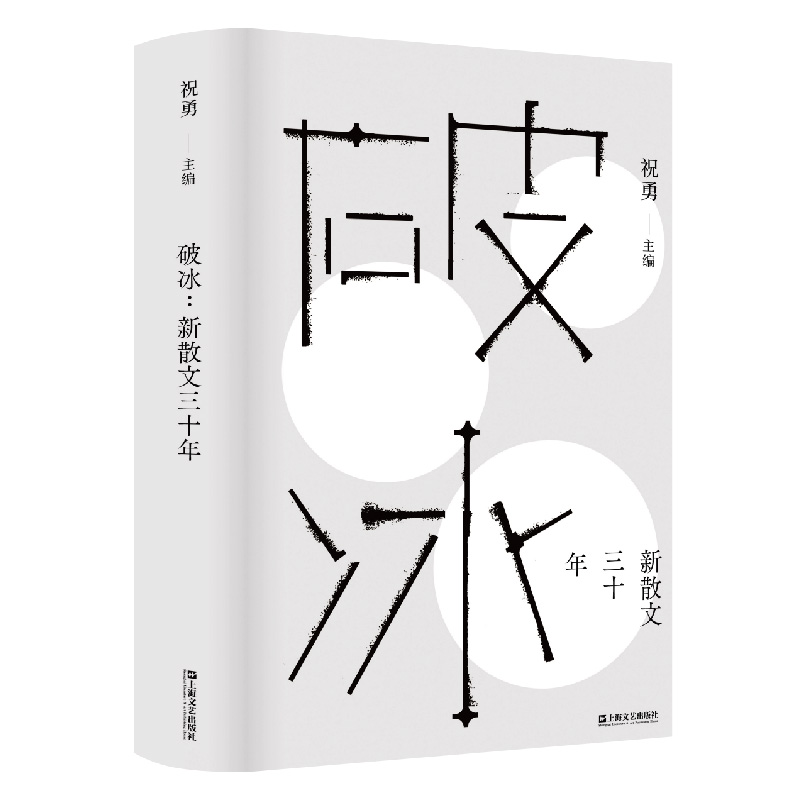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破冰:新散文三十年
ISBN: 9787532178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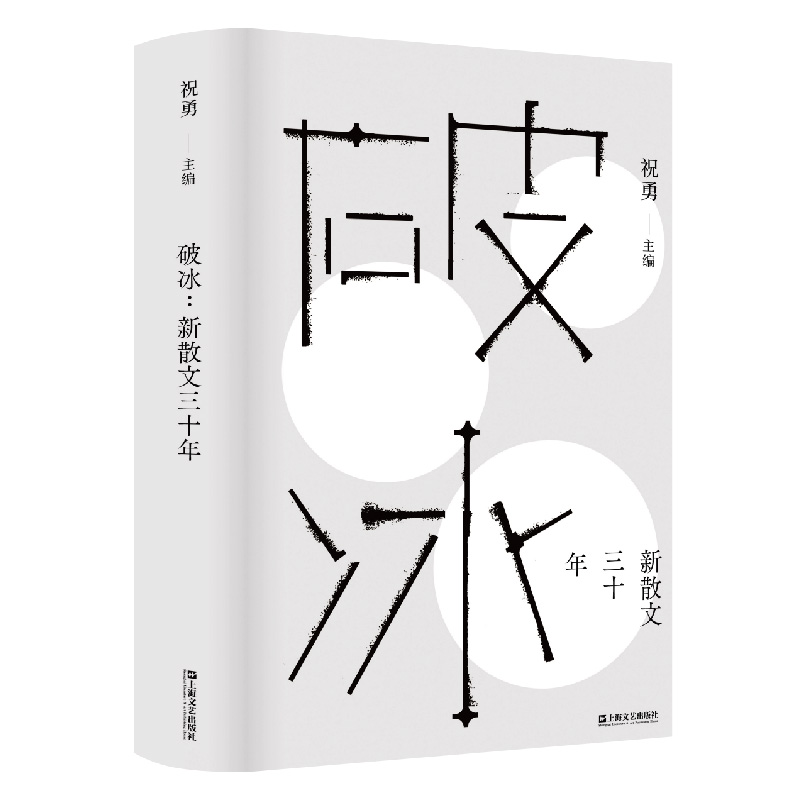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卡夫卡和他的动物园 文/钟鸣 谙熟卡夫卡的人,谁都明白,他所迷恋的“失败”,或不可能——反对父亲所象征的官吏世界,用布拉格犹太人的德语(德勒兹称之“少数文学”)把德语啃成根光骨头,这些都不全是语言的问题,所以,对后来者要作真正的联想,尚需要些勇气。生活如此无趣,而卡夫卡则率先愿意成为这注定无趣的普通人中的一员,“他时时处处被拥挤到理解的极限,他也喜欢把别人推向这极限。”而恰恰正是这极限,让人绝路逢生,弄出些迷恋来,倘若没有,便可能成为最乏味的人。卡夫卡认为,文学随着鼹鼠的死亡开始。而对于读者,则是随着解答新的问题开始。 就像我,冬日在露台晒太阳读书(蜀地多阴,晒太阳便为乐事),爱自问些傻问题,若无圆满的解答,便再读些书,侥幸又回到老话题上来。比如,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作家,而不喜欢那个,迷这本书而烦那本?低级回答,自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红萝卜,白萝卜,各有所好。问题是,都是红萝卜也存在那样的问题,则又当如何?――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我就迷恋前者,轻视后者,还有曼杰尔斯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都奉献了那时代观察最敏锐的一面,虽说生死在天,但,曼氏为了讥讽斯大林丢了命,却得到了以塞亚?伯林的最高评价,光个性是说不走的,抑或出于某种特殊的信念,又如何不是迷恋,才区别许多的不同,或即旧时的风雅。所以,《论语》叙及“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朱熹集注释曰:“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也”。这大致就是欧人说的“以文行事”,用来衡量数载诗坛,遂不能不发“当代诗歌,多为言辞胜利,而少有人性胜利”的感慨。这些不能单怪罪批评,长期不以常言执守精神所致,怕也是游戏文字大家自招的。正如《孟子》所言:“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此语境,可谓漫长。 若取这段话的意思,正面延伸,便可说,人必自己迷恋,然后人方能迷恋之。自己迷恋,不是说,迷恋自己,而是说,其人有所迷恋。所以,很多人,误读了卡夫卡,以为卡夫卡是很迷恋自己的,其实,卡夫卡的“沼泽世界”并不为自己所设,是为我们所有人而设,为所有莫名丧失了空间,或置身于荒诞的弱者所设。这些荒诞,我们每日都能碰到。他的《诉讼》《变形记》《城堡》,甚至《中国长城》,都用了旷古达今的笔法,或似中国的春秋笔法,刺官僚机器,叙说虚无与腐败,遗忘的反是自己,垂询的却是冷漠的现实。个人消失在所有之中,用卡夫卡自己的话说便是:“谁与狗一起躺在床上,谁就和臭虫一起上身”。所以,本雅明称他的“遗忘”是个大容器,“一个无尽头的中间世界就是从这里显露出来的”。他迷恋这个容器,也就是迷恋某种我们可称作“空间”的东西。最早的空间,是在他和父亲之间展开的,从他那封著名的《致父亲的信》就能看出:“仅仅你的体魄那时就已压倒了我”。还有许多小事(卡夫卡也称作“这些小事”),都看出,他父亲把他当做了一个物品,支来支去,结果,让一个完整的世界一分为三:“一个部分是我这个奴隶居住的,我必须服从仅仅为我制定的法律,……第二个世界,它离我的世界极其遥远,那是你居住的世界,你忙于统治,发布命令,……第三个世界,其他所有的人全都幸福地、不受命令和服从制约地生活在那里”。但卡夫卡认为自己的境况是“永远蒙受耻辱”,因为他面临两难,服从不是,不服从也不是。这条裂缝,深深地扩展到他几乎所有的作品,甚至包括各种各样情景下的微型动物们――地洞里的老鼠,轮船上的猴子,房间里的甲虫,亚历山大的战马,沙漠中的豺狗,阁楼上的线状动物――“奥德拉德克”,或半猫半羊的杂种……。而恰恰不见卡夫卡自己,他的名言即:“不要为自己画像”。本雅明就此曾说过,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像他那样认真地履行了这一信条。他的写作,延续了21年(从1903年写《观察》到1924年去世),而他对人类身处自己营造的处境迷恋至深,所以,也就饱和了那样长的时间。就连他的结局,――放弃婚姻,让其友人勃罗德焚烧其手稿,都很清楚地说明,他想完全遗忘掉自己,从身体之遗传,到精神的递嬗,由此告诉、或暗示世人,他是非常明白自己所迷恋的处境,是一种绵延不绝,完全令人绝望,而又人人皆知的生活方式,他一个人是永远也无法获胜的。这样,他也就把一个文化迷恋者的语境,交给了大家,其形象,也就是卡夫卡在小说中描述的“饥饿艺术家”,永远的饥饿状况,永远需要这状况的饥饿表演。创造文化,而又为文化所缚,这悖论的社会也就是一个荒谬的马戏团,“它有无数的人、动物、器械,它们经常需要淘汰和补充。不论什么人才,马戏团随时都需要,连饥饿艺术家也要”。 卡夫卡叙述的故事都很简单,读其长篇小说,跟读一则短文,没本质的区别,因为结局都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本来也就没什么结局。比如《日记,1910.—.1923年》中的一条:“对马只有着着实实地抽上一鞭子,慢慢给它一个踢马刺,然后一下子抽出,现在再用所有的力气将之刺进肉里。”事情之发生或许仅仅有人迷恋这种事罢了。《城堡》也是如此,在马克斯?勃罗德看来,小说完不完成都没什么关系,反正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无穷的可能性的故事,村长出来,最后城堡秘书出来,一级一级的,没完没了,都解决不了问题。跟K投入战斗,没任何胜算一样。两边加起来,也不过是客观上,或许所有的人都迷恋那样的胶着状态,跟我们现在机构里混饭吃的一样,一边抗拒着(包括偷懒),偷奸耍滑,又一边为其安全感着迷,仿佛是一场“战斗”,跟歌德的格言相似――“谁不停地努力奋斗,我们便可以解救他”(勃罗德语)。所以,体系里的人,有时会比外面的人表现得更加愤世嫉俗,也更加危险地玩世不恭。中国之精神财富,有多半是为油滑或阴险气稀释着的。而且,大家深深地迷恋其中。 这种迷恋,或许其深刻的背景本身就处在悖谬之中。卡夫卡有许多片段,描写了这样的悖谬。比如下面这段:“乌鸦宣传,只须一只乌鸦即可摧毁天空。这是无可置疑的,但对天空来说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天空恰恰意味着:非乌鸦的力量所能及”。类似的很多。 我也很想搞清,卡夫卡式的迷恋其本质究竟是什么,窃以为,其挚友勃罗德所写的传记中有段话疑为精要:“可以说在生活斗争的准备阶段,已经存在的童稚者的耸肩,……这些‘不切实际的人’也许会删除思想和痛苦的某些空洞无物的环节;最终人们会发现,他们不仅比别人感觉更温柔敏锐,也更接近真理和最深处的认识。因此一个‘童稚’作家的世界观能够攫住我们的心,童稚在此并非弱点;它只是对存在的不幸的基本情状的一种比较诚实、比较认真的理解”。这跟孔夫子的“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极相似。其来源,虽已有很多人谈过,涉及有德国作家克莱斯特,霍夫曼,歌德,法国作家福楼拜,巴尔扎克,英国作家狄更斯等。但根据卡夫卡自己的描述,恐怕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子,或许也是较隐蔽的影子。卡夫卡日记中有一条,就是他叙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特别的思想方法。感觉上的渗透。一切都是作为思想去感受的,即使是在最不肯定的状况中”。勃罗德也回忆过,卡夫卡的笑声,很像陀氏小说《罪与罚》中斯维德利盖洛夫的声音。陀氏也是我很迷恋的作家之一,其《白痴》《少年》《女房东》《醉》《地下室手记》最能体现此类作家之迷恋的。而迷恋的真髓,尚在他们清晰地意识到“失败者”的哲学含义,故吾类,则必准备殊死搏斗。卡夫卡下面的话就是最好的一个明证:“巴尔扎克的手杖上写着:我在摧毁一切障碍,而我的手杖上宁可写的是: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 ▼ 1998 年云南《大家》杂志推出“新散文”栏目,被视为“新散文”诞生的标志。故宫学者祝勇,以“新散文”之名,全新梳理,集钟鸣、于坚、冯秋子、宁肯、张锐锋、蒋蓝、祝勇、周晓枫八位代表作家,发起一场打破传统中国散文创作傲慢与偏见的“破冰行动”,描摹“新散文”创作自发轫至青春蓬勃三十余年的吉光片羽。 ▼ 1篇序言,16篇新散文,篇篇上乘,俯拾皆可见中华历史之磅礴、自然之秀美、生活之闲趣,在这里我们看得到孔子、庄子的影子,也看得到卡夫卡、博尔赫斯、曼德尔斯塔姆的影响,更看得到“新散文”作家们复杂、迷离的主体世界。读一卷仿若行万里路,获得精神之独立、旷达与自由。 ▼ “新散文”不是“文学园地里的一朵小花”,而是一种观念、方向和高度,它具备一个超大能量的内宇宙,能精准呈现近三十年来最雄伟的文学建筑群面貌。“新散文”为中国散文重新树立了艺术标准,寻回了生命活力,也代表着中国散文通向未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