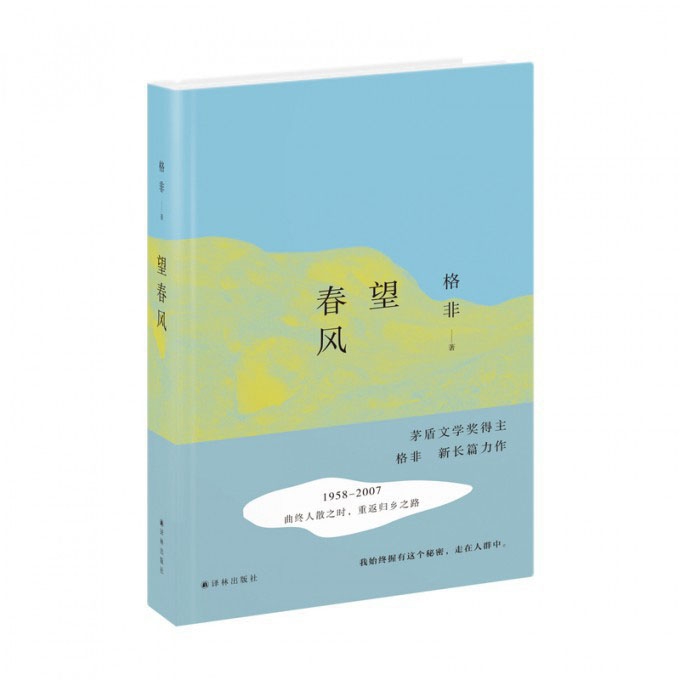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望春风(精)
ISBN: 97875447625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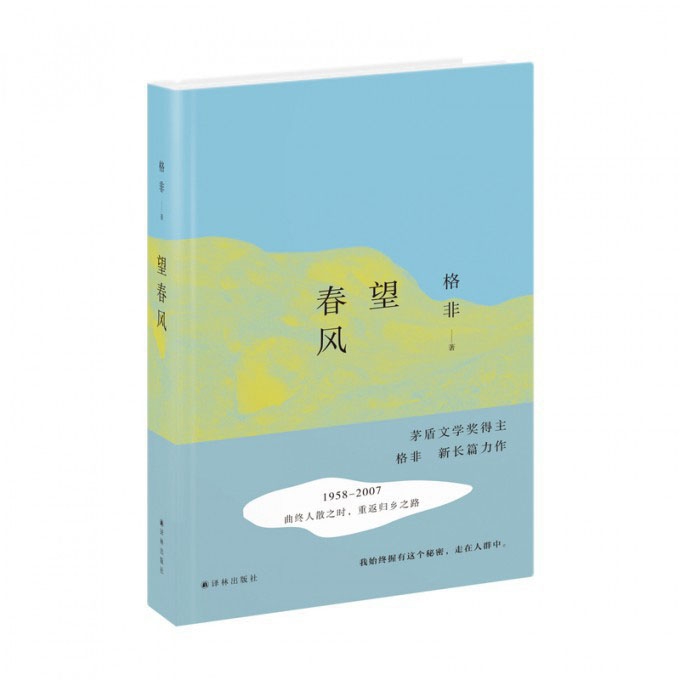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87年发表成名作《迷舟》,198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迄今著有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如梦》《春尽江南》,中篇小说集有《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等。此外,还出版有小说理论专著《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文学讲稿《塞壬的歌声》,散文集《格非散文》等,作品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履霜坚冰至 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 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顺便告诉我, 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不知去做 什么。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 喂点草,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 我刚给羊喂完草,就看见同彬踩着高跷,一颠一 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得意地 望着我笑。我问他,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吗去了 ?同彬再次让高跷离地,反向腾空,转了半圈,向前 打了好几个趔趄,这才算把高跷稳住,“屌毛!差一 点摔我一跟头。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要搞什 么大会战。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我一个人乐得 自在。” 同彬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他以前是大 队的会计,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被赵德正 给免了。会计一职,改由高定国担任。 同彬还说,“老家伙”让我去一趟,马上就去。 “谁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同彬传了话,就踩着高 跷,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说要去祠堂前的 大晒场练练后空翻,可刚走到红头聋子家的山墙边, 就摔倒在他们家的茅坑上,溅了一脸的粪。 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我低低地叫 了她一声“冯先生”,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告诉 我赵先生正在杩子上出恭,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平 常,赵锡光不让我们叫她师娘,而要叫她冯先生。称 呼女人为先生,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可赵先生说, 师娘原本也读过书,按老规矩,应该叫她先生。我们 只能照办。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 生请”、“娘子请”地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 里夹菜。可是,据同彬说,两人一旦闹起别扭来,发 了急,与村里的愚夫愚妇“一个屌样”。赵先生拍胸 打肚,婊子长、婊子短地骂不绝口,而师娘骂起赵先 生来,也是一口一个“烂屌芯子”。 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头戴绒线 暖帽,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 信。他背后的墙上,有一幅《溪山狩猎图》。旁边还 挂着一幅字,据说是周蓉曾的手笔: 履霜坚冰所由渐 麋鹿早上姑苏台 我们每天上课时,都看着这幅字,却始终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镇尺,写有 对联一副,读上去通俗易懂: 读古书变化气质 友多闻开拓心胸 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 。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 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 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 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 。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 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锡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 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锡光摘下棉桃似的 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汁液,用来熬制 鸦片膏。 “说吧,腊月二十九这一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 方去了?”赵锡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 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 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 走差的事告诉别人,只得胡编了一通瞎话来对付他, “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岁,也 是个烈属。我们去给他做寿。” 赵锡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 ,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 冷笑来,对我说: “村里人(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你 也过来坐坐),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 一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 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否认,都是极不合 适的。 “其实,你一点都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 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 没出息的爹少!”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 来。 师娘见状,赶紧打圆场说:“你好好说话,可别 吓着人家孩子。”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 过来揪我耳朵了。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 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 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跟我说话。应当说,与礼平相比 ,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 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 眼相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 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 疚,将半塘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 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 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一眼,半晌不说 话。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如今不是新社会吗 ?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 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 等上几年,把她说给定邦。她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 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嘛! 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怎好说变卦就变卦 ?再说了,他赵德正,轿夫出身,家里穷得连根针都 找不见,日子怎么过得出来?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 半塘跑一趟?”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 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 怎么说?依我看,这事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 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不简单!”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P26 -29
1958—2007,微缩五十年时代变迁,演绎幽微处世情人性。
“中国*美的书”设计者陆智昌倾情担纲设计。
《望春风》是格非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大作,亦是集其30年文学创作精华的成熟之作。《望春风》具有微缩中国乡村当代史的意义,在创作过程中备受文坛、媒体和读者瞩目。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乡村是无可回避的精神源泉。《望春风》完成了一次几乎不可能的返乡之旅,以回到“过去”来看“当下”的观念,余韵悠长、值得咀嚼的历史片段,置于时代长河背景的“桃花源”气象,如“清明上河图”般娓娓道来的手卷写法,描绘乡土中国的活色生香,发见普通人的高贵品质,定格日常生活的瞬间永恒。
“江南三部曲”写江南,《望春风》则是对江南故事更为专注、集中和彻底的表达。相对于“江南三部曲”,《望春风》更接地气,更加沉稳,更有温度,更多地关注时代洪流下乡村的人情之美。在对历史的沉思中,用宏阔又精致的结构,以及极为老辣纯熟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作了告别。同时,为读者打开一个小小的山口,“仿佛若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