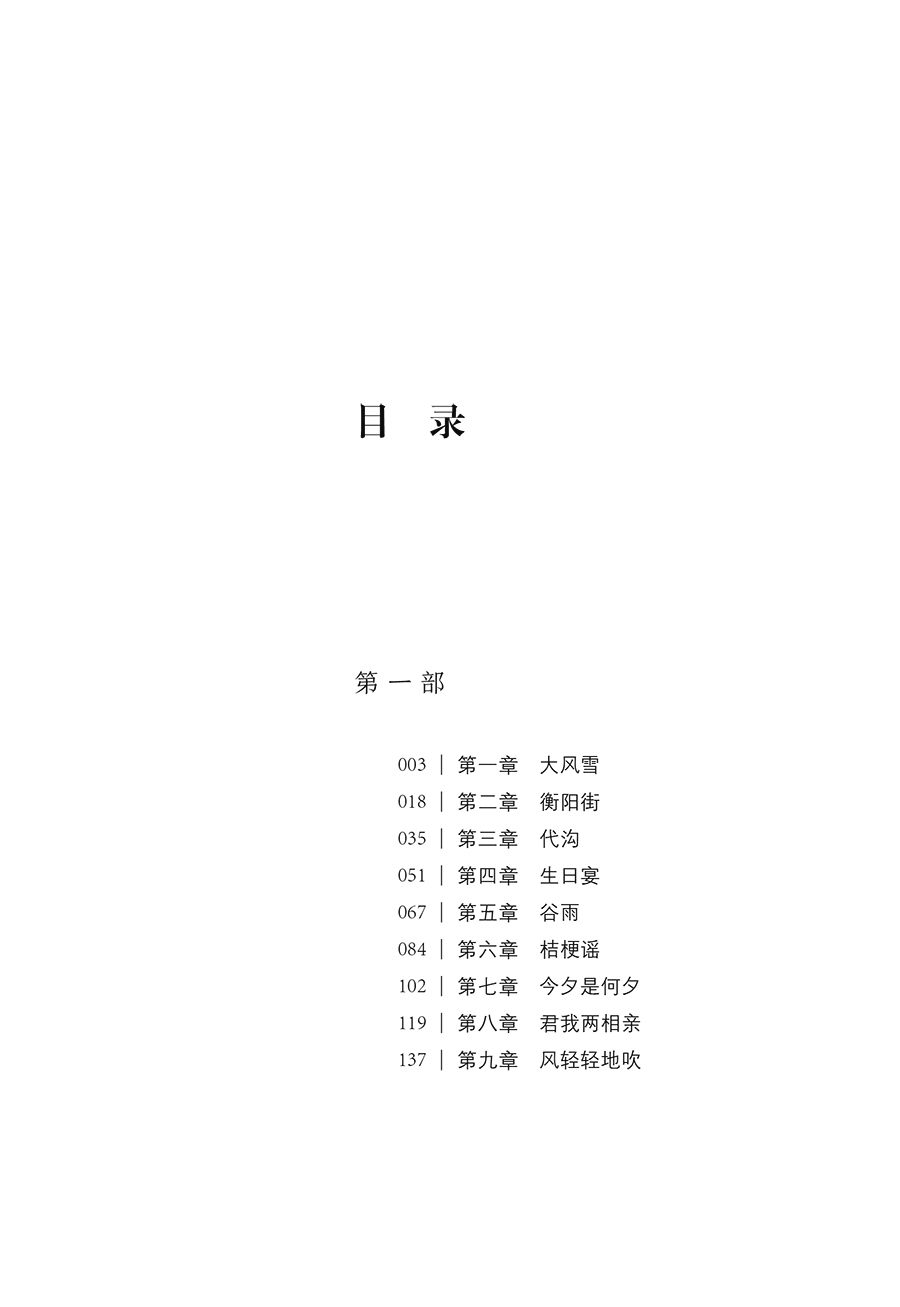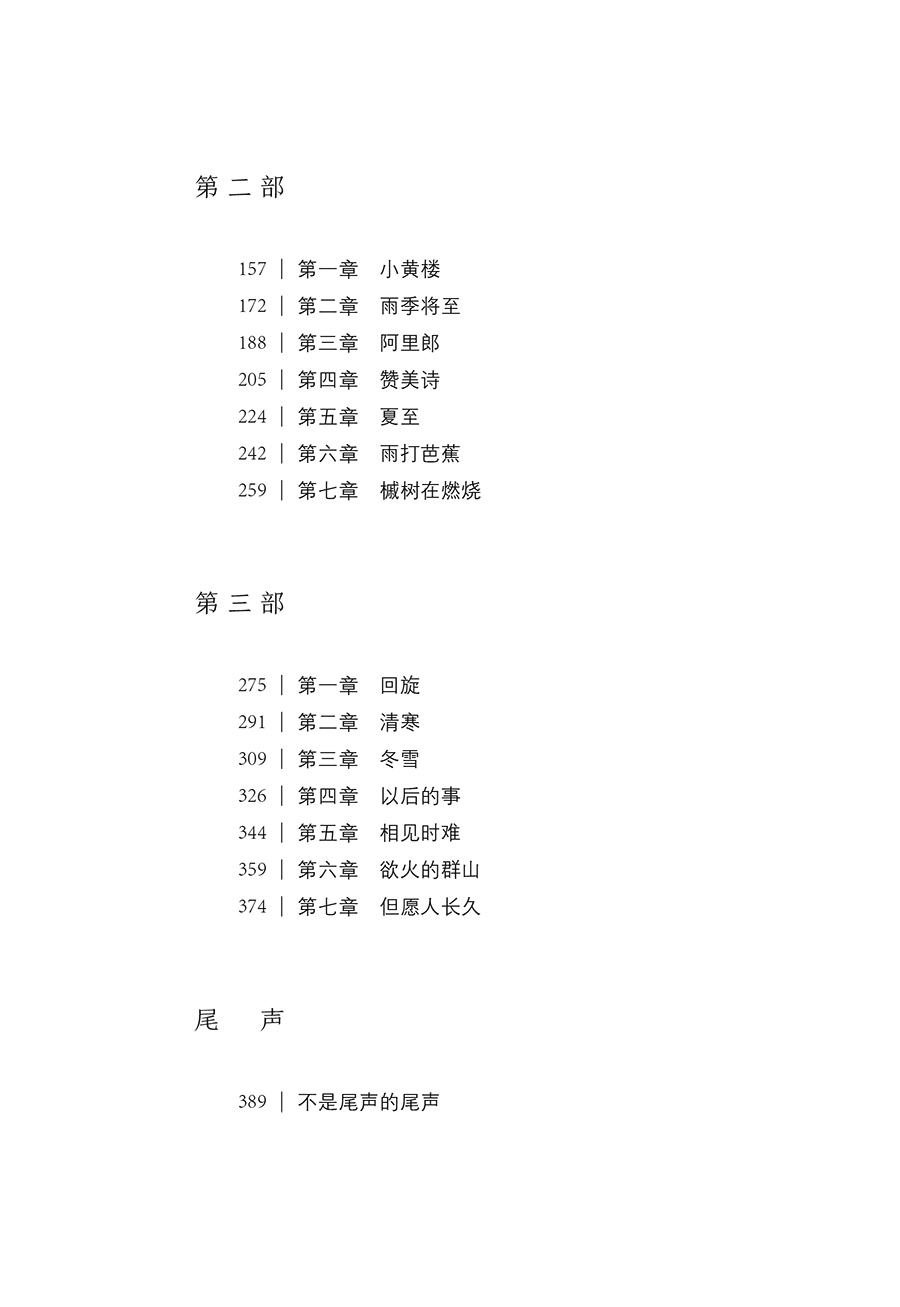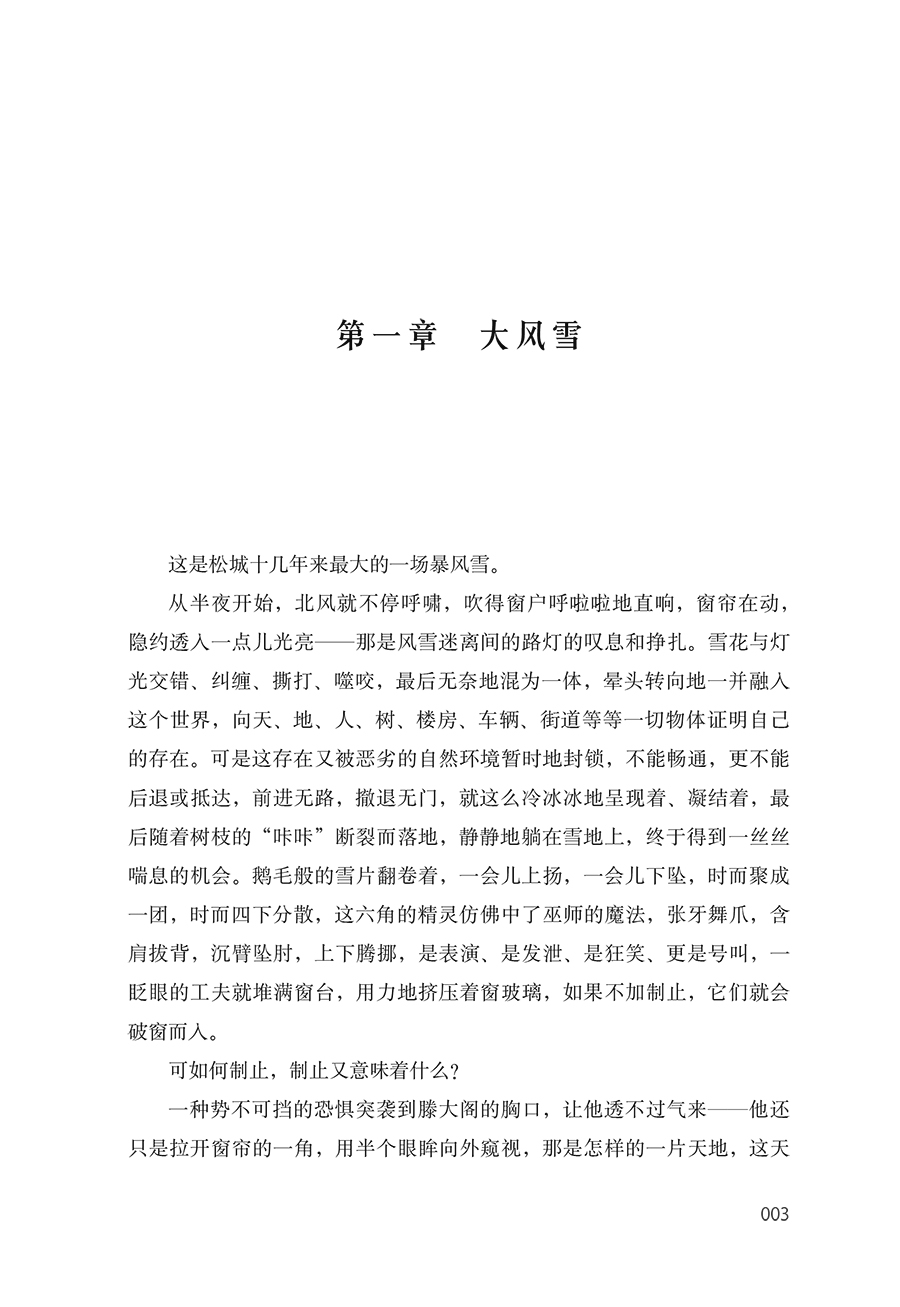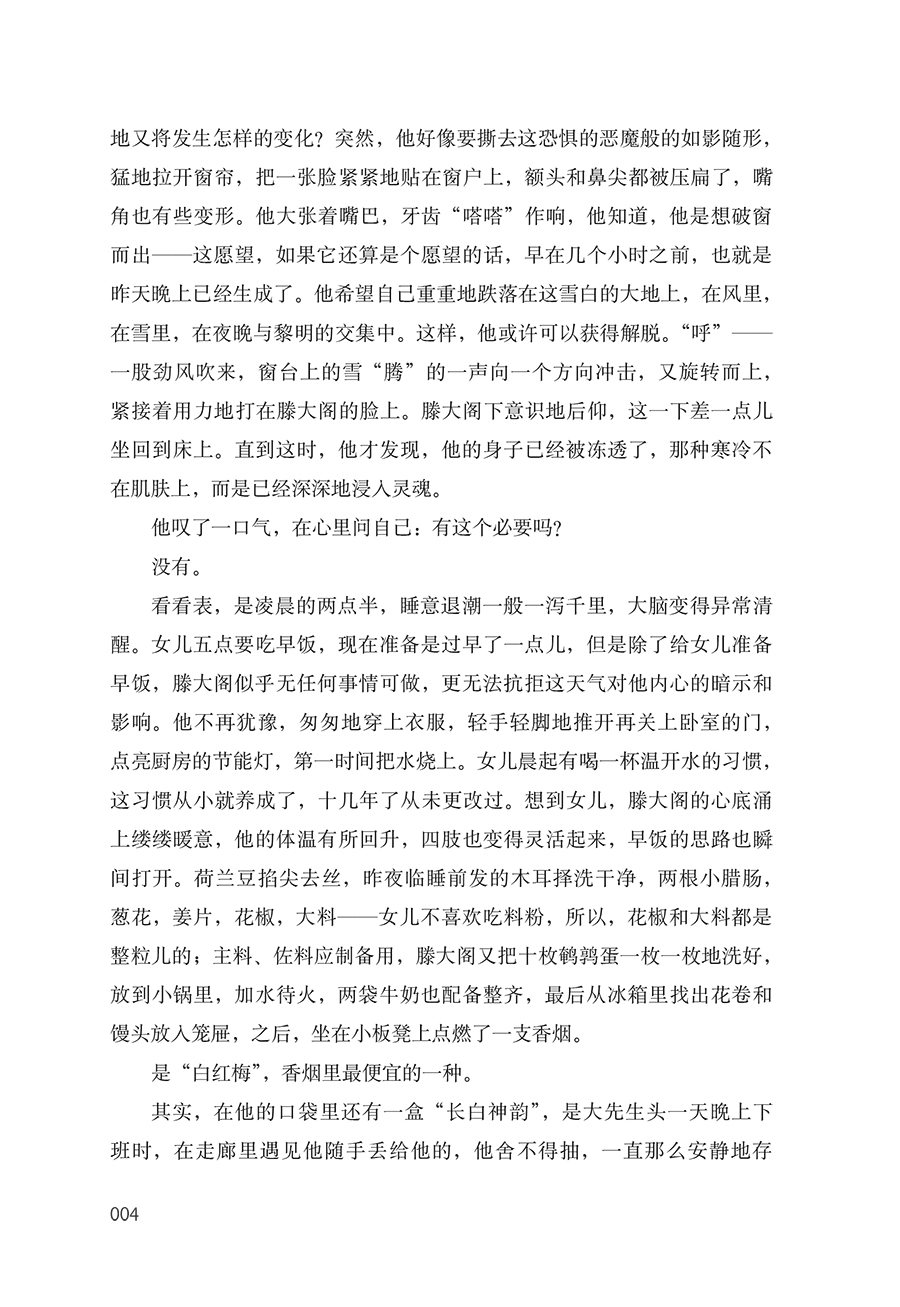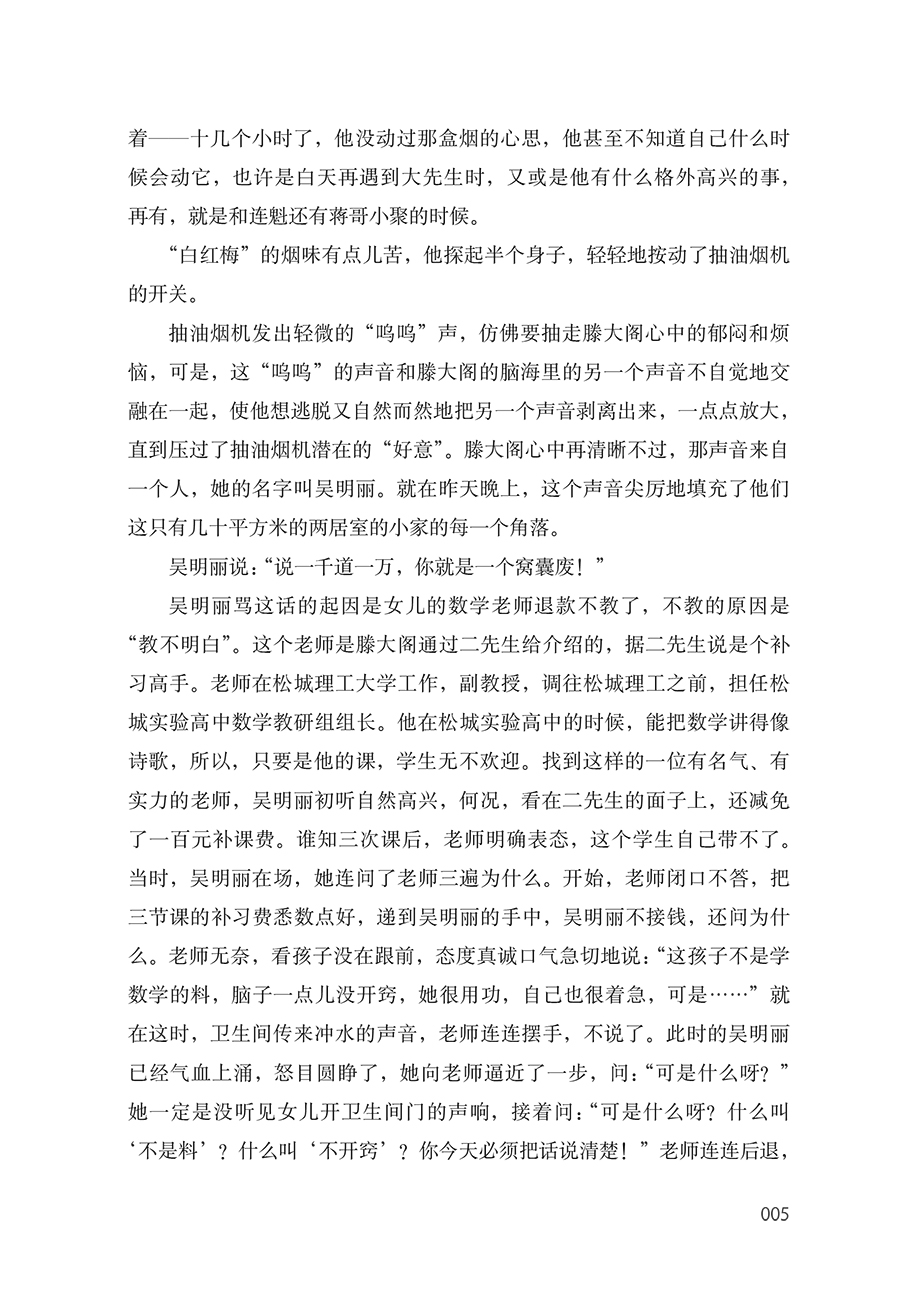出版社: 时代文艺
原售价: 56.00
折扣价: 33.10
折扣购买: 雪落天未寒
ISBN: 9787538763201

" 于德北,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吉林德惠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吉林省作协全委、小小说创作委员会主任,长春市作协副主席。迄今为止,在《作家》《小说选刊》《南方周末》《山花》《儿童文学》《小小说选刊》等国内外几百家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400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零点开始》、长篇随笔《我和端端》、散文集《自然笔记》、散文诗集《渡口集》、长篇少儿科幻小说《拯救海底城市》、长篇少儿侦探小说《失踪的妈妈》、长篇儿童小说《密林失踪者》、长篇童话《绿色和平城堡》、短篇小说集《少年菊花刀》、小小说集《青春比鸟自由》等六十余部。 2007年获第三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2009年《美丽的梦》获“冰心图书奖”,2018年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有作品被译介到日本、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
" 第一章 大风雪 这是松城十几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风雪。 从半夜开始,北风就不停呼啸,吹得窗户呼啦啦地直响,窗帘在动,隐约透入一点儿光亮——那是风雪迷离间的路灯的叹息和挣扎。雪花与灯光交错、纠缠、撕打、噬咬,最后无奈地混为一体,晕头转向地一并融入这个世界,向天、地、人、树、楼房、车辆、街道等等一切物体证明自己的存在。可是这存在又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暂时地封锁,不能畅通,更不能后退或抵达,前进无路,撤退无门,就这么冷冰冰地呈现着、凝结着,最后随着树枝的“咔咔”断裂而落地,静静地躺在雪地上,终于得到一丝丝喘息的机会。鹅毛般的雪片翻卷着,一会儿上扬,一会儿下坠,时而聚成一团,时而四下分散,这六角的精灵仿佛中了巫师的魔法,张牙舞爪,含肩拔背,沉臂坠肘,上下腾挪,是表演、是发泄、是狂笑、更是号叫,一眨眼的工夫就堆满窗台,用力地挤压着窗玻璃,如果不加制止,它们就会破窗而入。 可如何制止,制止又意味着什么? 一种势不可挡的恐惧突袭到滕大阁的胸口,让他透不过气来——他还只是拉开窗帘的一角,用半个眼眸向外窥视,那是怎样的一片天地,这天地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突然,他好像要撕去这恐惧的恶魔般的如影随形,猛地拉开窗帘,把一张脸紧紧地贴在窗户上,额头和鼻尖都被压扁了,嘴角也有些变形。他大张着嘴巴,牙齿“嗒嗒”作响,他知道,他是想破窗而出——这愿望,如果它还算是个愿望的话,早在几个小时之前,也就是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了。他希望自己重重地跌落在这雪白的大地上,在风里,在雪里,在夜晚与黎明的交集中。这样,他或许可以获得解脱。“呼”——一股劲风吹来,窗台上的雪“腾”的一声向一个方向冲击,又旋转而上,紧接着用力地打在滕大阁的脸上。滕大阁下意识地后仰,这一下差一点儿坐回到床上。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他的身子已经被冻透了,那种寒冷不在肌肤上,而是已经深深地浸入灵魂。 他叹了一口气,在心里问自己:有这个必要吗? 没有。 看看表,是凌晨的两点半,睡意退潮一般一泻千里,大脑变得异常清醒。女儿五点要吃早饭,现在准备是过早了一点儿,但是除了给女儿准备早饭,滕大阁似乎无任何事情可做,更无法抗拒这天气对他内心的暗示和影响。他不再犹豫,匆匆地穿上衣服,轻手轻脚地推开再关上卧室的门,点亮厨房的节能灯,第一时间把水烧上。女儿晨起有喝一杯温开水的习惯,这习惯从小就养成了,十几年了从未更改过。想到女儿,滕大阁的心底涌上缕缕暖意,他的体温有所回升,四肢也变得灵活起来,早饭的思路也瞬间打开。荷兰豆掐尖去丝,昨夜临睡前发的木耳择洗干净,两根小腊肠,葱花,姜片,花椒,大料——女儿不喜欢吃料粉,所以,花椒和大料都是整粒儿的;主料、佐料应制备用,滕大阁又把十枚鹌鹑蛋一枚一枚地洗好,放到小锅里,加水待火,两袋牛奶也配备整齐,最后从冰箱里找出花卷和馒头放入笼屉,之后,坐在小板凳上点燃了一支香烟。 是“白红梅”,香烟里最便宜的一种。 其实,在他的口袋里还有一盒“长白神韵”,是大先生头一天晚上下班时,在走廊里遇见他随手丢给他的,他舍不得抽,一直那么安静地存着——十几个小时了,他没动过那盒烟的心思,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动它,也许是白天再遇到大先生时,又或是他有什么格外高兴的事,再有,就是和连魁还有蒋哥小聚的时候。 “白红梅”的烟味有点儿苦,他探起半个身子,轻轻地按动了抽油烟机的开关。 抽油烟机发出轻微的“呜呜”声,仿佛要抽走滕大阁心中的郁闷和烦恼,可是,这“呜呜”的声音和滕大阁的脑海里的另一个声音不自觉地交融在一起,使他想逃脱又自然而然地把另一个声音剥离出来,一点点放大,直到压过了抽油烟机潜在的“好意”。滕大阁心中再清晰不过,那声音来自一个人,她的名字叫吴明丽。就在昨天晚上,这个声音尖厉地填充了他们这只有几十平方米的两居室的小家的每一个角落。 吴明丽说:“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是一个窝囊废!” 吴明丽骂这话的起因是女儿的数学老师退款不教了,不教的原因是“教不明白”。这个老师是滕大阁通过二先生给介绍的,据二先生说是个补习高手。老师在松城理工大学工作,副教授,调往松城理工之前,担任松城实验高中数学教研组组长。他在松城实验高中的时候,能把数学讲得像诗歌,所以,只要是他的课,学生无不欢迎。找到这样的一位有名气、有实力的老师,吴明丽初听自然高兴,何况,看在二先生的面子上,还减免了一百元补课费。谁知三次课后,老师明确表态,这个学生自己带不了。当时,吴明丽在场,她连问了老师三遍为什么。开始,老师闭口不答,把三节课的补习费悉数点好,递到吴明丽的手中,吴明丽不接钱,还问为什么。老师无奈,看孩子没在跟前,态度真诚口气急切地说:“这孩子不是学数学的料,脑子一点儿没开窍,她很用功,自己也很着急,可是……”就在这时,卫生间传来冲水的声音,老师连连摆手,不说了。此时的吴明丽已经气血上涌,怒目圆睁了,她向老师逼近了一步,问:“可是什么呀?”她一定是没听见女儿开卫生间门的声响,接着问:“可是什么呀?什么叫‘不是料’?什么叫‘不开窍’?你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老师连连后退,脸上是无奈的苦笑。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她听到了妈妈的问话,但一时间弄不明白其中的含意,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下意识地拉着妈妈的胳膊,一个劲儿地向后拽,“妈妈,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吴明丽用力地打开女儿的手,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女儿的存在,她使劲儿地吞咽着唾沫,眼泪已经急速地向眼眶奔涌。她的胸口连续地起伏,又一次伏下去的时候,出现了片刻的间断,趁着这当口,她上前一步,劈手夺下老师手中的一沓钱,数也不数,拉着女儿撞出了老师家的门。 那门本是半掩着的,给她这么一撞,早已和走廊的墙壁极不情愿地接了一个吻,发出一声压抑人心的巨大的声响。 老师家在四楼,吴明丽拉着女儿下到三楼半的时候,恰好又一个家长领着孩子上楼——显然,是按点来找老师补习的,她见到吴明丽客气地笑了一下,似乎还要和她交流两句,可是,吴明丽回过头,用尽全身力气一般,大喊了一声:“什么补习高手,自己都弄不明白!趁早别教!”她没看见,也不知道,此时,女儿的脸上已经全都是泪水。刚来的那位家长不明就里,但还是礼貌地又笑了一下,带着孩子快步上楼去了。 来到大门外,走出一百米,吴明丽才长吁了一口气,回头看女儿,发现她在哭,不由得波涛再起,“哭什么哭?你还有脸哭!你如果能学明白点儿,我何苦给你花钱遭这罪!”说完,自己也哭了起来。 回到家里,见滕大阁炒菜忘了开油烟机,吴明丽气不打一处来,把兜子撇到沙发上,径直进厨房,单指用力把抽油烟机的开关捅开。滕大阁炒菜注意力太过集中,根本没注意到吴明丽的表情和态度,一边表演似的翻了一下勺,一边笑盈盈地问了一句:“回来了?” “回来,不回来还死外面!” 只这一句话,滕大阁的心里就一下子全明白了,暗叫一声:完了。脸上的笑迅速抽紧,悄悄地平复下去,换上一副谦卑和小心的模样。谦卑是表面,小心是本质。在近二十年的夫妻生活里,滕大阁已经习惯了这谦卑和小心,他也万分地为这份谦卑和小心感到委屈和别扭,常常在喝闷酒的时候骂自己是个窝囊废——就像吴明丽常骂的那样。吴明丽骂是解气,而他自己骂,实实在在是有一分顾影自怜。 知道吴明丽在生气,而且大约猜到吴明丽为什么生气,所以他不能像每日那样往补习班上讲,只能侧开半个身子,虚拟似的冲着房厅喊:“闺女,洗手吃饭!” 女儿应了一声,小跑着去卫生间,因为卫生间和厨房比邻,所以,她能看见爸爸和妈妈的身影。她夸张地撒娇似的问了一声:“爸爸,做了什么好吃的?” 滕大阁也高声回答:“圆葱炒牛肉,芹菜炒香干。” 如此气氛下,吴明丽也不好再发作,默默地收拾上碗筷,把三碗红豆白米饭盛好。 其实,早在今天中午的时候,老师就给滕大阁发了一条微信,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决定。当时,滕大阁正在食堂吃饭,老师的微信让他有点儿不知所措。大先生不在身边,不然,他可以向大先生讨个主意。大先生和大学同学出去吃饭了,临出门时还喊了他一声,问他要不要一同去,他犹豫了一下,拒绝了。他和大先生的那几个同学一同吃过几次饭,大家对他也客气,只是,他们在一起吃饭,他根本搭不上言,觉得自己像个木偶似的,坐在那里除了尴尬就是尴尬,人家递烟他接烟,人家布菜他吃菜,人家敬酒他喝酒,仅此,再无别的“功用”。渐渐地,他就自觉地很少参加了。虽然,他和大先生的感情很近。另外,今天不去,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更主要一点儿,他要去桂林路市场,买一斤牛肉,顺带买几棵芹菜,四块香干——女儿今天有补习,提前就告诉,想吃炒牛肉,想吃香干。女儿的要求对他来说是最大的事,甚至比天大,所以,当大先生喊他时,他微笑着摇摇头。那大先生也不多言,随意地挥挥手,大步流星地走了。至于晚上下班丢给他的那盒“长白神韵”,应该就是中午饭局的“遗物”。大先生就是这样,干什么都有点儿“随意”,这“随意”是他骨子里更改不了的特性,放在滕大阁这里,就是百分之二百的温暖。 他知道,大先生的“随意”是一种对生活本质的隐藏,他不喜欢别人感激甚至感恩他对别人的好。 当然,他更不希望给别人造成任何心理负担。 吃完饭,滕大阁去桂林路市场买菜。他没有骑电动车,而是选择步行。前段时间,单位组织体检,他被查出来血糖有点儿超标,虽不能定性为糖尿病,但大夫再三嘱咐要控制酒,注意饮食,平时加强锻炼——最好的锻炼方式就是走路,饭后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尽量户外匀速步行半个小时,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控制血糖,同时,对身体的其他器官也能起到保健作用。桂林路市场离单位并不是很远,加之滕大阁走路速度快,十几分钟,他人已经进入市场了。桂林路是松城的商业圈,许多松城的大买卖人家都是在这里起步的,市场初建时,条件有限,房子没有精心装修,摊位也是杂七杂八,人们都称这里为大棚,但生意就是好,好得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大便宜。这“桂林路大棚”几个字,叫起来也不生疏,门槛儿低,价钱也好争讲,卖货的全都赔着笑脸,买货的更是理直气壮,半真半假地吵闹半天,最后是皆大欢喜。就冲这一点,滕大阁愿意来这里买菜,他从心理上接受这个大市场,觉得自己适合这样的场合。 买完菜,滕大阁给二先生打了一个电话,不知为什么,二先生没有接,这种情况在二先生身上时有发生,不只是滕大阁的电话,有时候大先生打也是一样。他不接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在喝酒,一是在睡觉。二先生喝酒有意思,不热闹的店不去,哪怕是大食堂,只要热闹,他就能坐安稳,二两白酒,两瓶啤酒,喝完就走,绝不多耽搁一分钟。喝完酒就睡觉,这一觉睡到什么时候,他自己不知道,别人就更难以替他计算。睡醒了,如果天色还早,便又找个热闹的地方——最常去的是街边摊,卖酱骨头、毛豆、豆腐串的那种,二两白酒,两瓶啤酒,有人搭讪,就说笑一番,无人说话,便一个人看风景。有时,他也会给大先生打电话,问他在干什么,如果大先生能出来,他就再多加两瓶啤酒,大先生出不来,他起身结账,付钱回家,一歪一歪地行走,任路灯把身影缩短再拉长。 滕大阁愿意和二先生在一起喝酒,就像他愿意来桂林路大棚一样——当然,现在名字叫得规范,是桂林路市场。叫大棚也好,叫市场也罢,恰似他爱交往的这位二先生,你是叫他葛明海还是叫他二先生,这在滕大阁心里,是最无所谓的。二先生不接电话,他就在微信上留了言,想约数学老师一起吃个饭,看看事情还有无商量的余地。二先生看到微信一定会回复的,这一点他有足够的信心。正是这份自信让他陷入了意料之中同时也是意料之外的烦恼,他后悔不已,自己的单位离二先生的家也不算远,在桂林路买完菜,为什么不去一趟二先生家呢?如果去了,如果见面了,如果把事情说开了,办妥了,又何必受眼前这份没深没浅的抢白。 事后,滕大阁想,和数学老师交流不及时,他还有话可以解释,毕竟给二先生发过微信。这个积极的态度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他心里更明白,女儿表面上乖巧的背后,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和痛苦。作为父亲,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尤其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吴明丽是绝对不允许他及他的家人插手的。上什么学校,找什么老师,补什么功课,学什么乐器,跳什么舞蹈,一切均由吴明丽说了算。吴明丽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滕大阁所提议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是欠考虑的,是有缺憾的,有时更是一派酒后胡言。如果滕大阁争执多了,吴明丽一定会有一句话在等着他:“你又喝高了?”滕大阁无话可说,更无计可施,他只能在女儿的身体健康上尽心尽力,饭菜尽量及时可口,接送绝不误点,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他像一个忠诚的厨师和司机,在自己应尽的能尽的父职上,堪称模范。 昨天晚上,因为女儿的努力,因为自己的三缄其口,吴明丽已经按下了心头的怒火,他们可以共度一个相对平静的夜晚,至少可以在冷战状态下,为女儿争取一点儿安安静静做功课的时间。自己为什么就这么没脸呢?为什么非要喝那一口酒呢?本来,吴明丽已经把饭盛上桌了,消消停停地坐下来不行吗?吃完饭收拾厨房,如果吴明丽愿意和他交流,那便洗耳恭听,如果不愿意交流,自己一个人在房厅里看书玩玩手机,如是,这场风暴就过去了。 滕大阁是没有脸。 他泡酒的玻璃罐子放在厨房的窗台上,就在他的身侧。那酒是用人参、鹿茸、灵芝、不老草泡的,色泽淡绿,观之诱人,甘洌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苦香。滕大阁没有经得住诱惑,他探起半个身子——他总是探起半个身子——一手拿杯,一手去取提溜,提溜碰到玻璃罐子上,发出一声脆响,正是这一声脆响,引出了吴明丽的燎原之火。她一巴掌打掉了滕大阁手中的杯子——那杯子也真是争气,落到吴明丽的脚背上没有碎,翻身滚到地板上去了,杯口碰到橱柜打一个转儿,杯底碰到桌腿打了一个旋儿,竟稳稳地停在原地一动不动。女儿见状,弯腰去捡,不想吴明丽早抬起一脚,将杯子踢飞到房厅里去。这一回,杯子没有那么幸运,一头撞向鞋架,不待发出一点儿响动,就已经粉身碎骨了。杯子碎了,鞋架这才闷闷地“哼”了一声,紧了紧身子,复贴到墙壁上去。 吴明丽开口骂道:“喝!喝!一天到晚你就知道喝!除了喝酒你还能干点儿什么?这个家你管过什么?管过我吗?管过滕雅维吗?你看看这个家,有什么?有房吗?有车吗?有……”她骂不下去了,把筷子一丢,回房间哭去了。女儿跟过去劝她,她也不理,再劝,引来的也是一顿数落:“滕雅维,你能不能让我省省心,我拼死拼活挣点儿钱,吃没吃上,喝没喝上,穿没穿上,全都交给补课老师了。补一次课,二百、三百、四百,我认,可你也得给我长长脸,争口气呀。” 女儿也哭了,口中喃喃道:“妈,我会好好学的,你放心,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的。” 女儿滕雅维,已经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了。 娘俩在屋子里流泪,全不知滕大阁的脸上也滑下了一行清冷的泪水。 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 "·中国当代长篇现实小说,书写东北城市中的百态人生,展现新时代善良朴素真诚的普通人群像,折射冰冷北方大地上的炽热人心 ·“但凡有爱的人,总会忘记自己。”小说中亲情、友情、爱情复杂交织,刻画生活真实的酸甜苦辣,剖析人性,反映时代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