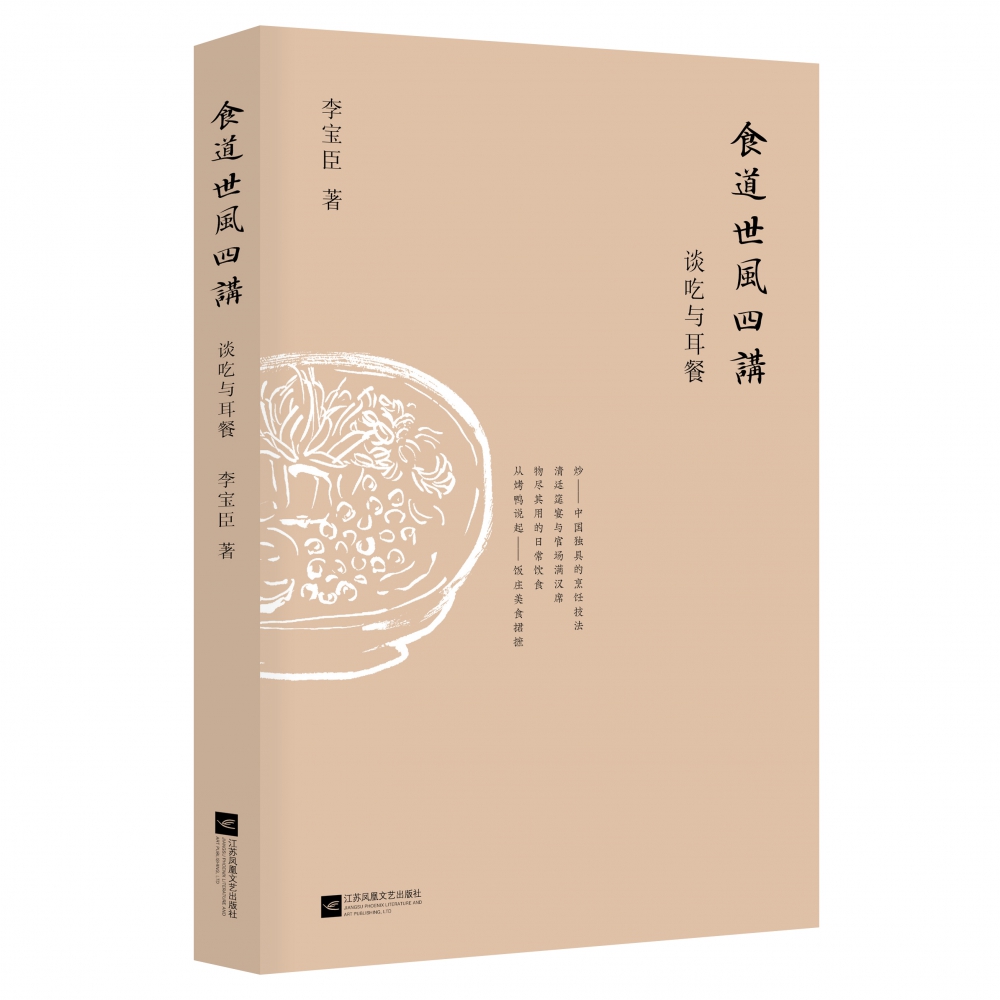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8.40
折扣购买: 食道世风四讲(谈吃与耳餐)
ISBN: 9787559431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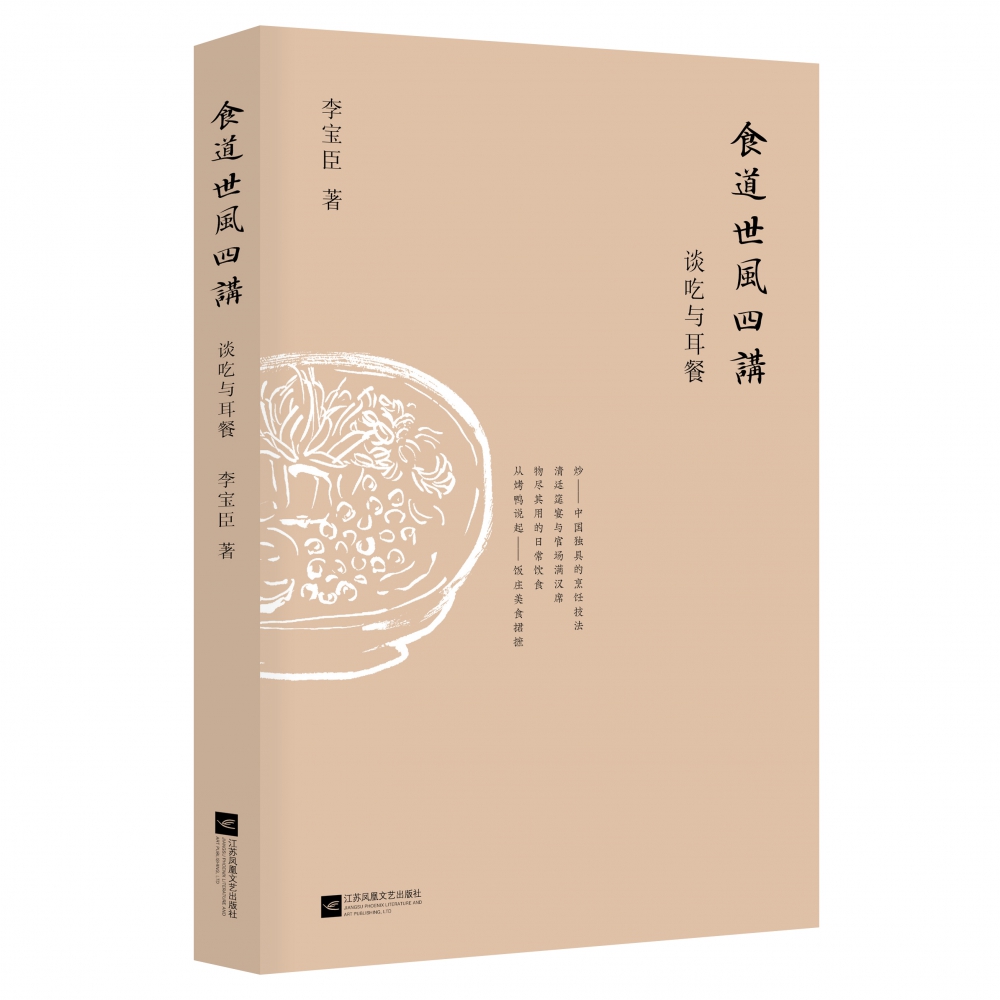
李宝臣,北京文史馆馆员、北京社科院研究员。有《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礼不远人》《明北京》等专著八部,以及《大顺用兵北京试论》《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制度比皇帝*重要》等论文六十余篇。
谈吃与耳餐 **聊的话题是“吃”,聊吃说吃,话题广泛,东拉西扯,即使说得口滑,听得过瘾,也不过是“耳餐”盛宴而已。袁枚《随园食单》反复强调饮食一定要“戒耳餐”。对于缺少美食经验又渴求美味珍馐的人,进行美食欺骗是很容易的。个人品尝经历简单,身心沉积不了太多的视觉与味觉记忆,自然唯耳是用,以耳代餐。现在新兴一个职业就叫说吃、谈吃,报刊也好,电视也好,大都设置“谈吃”、美食栏目,收视率与影响力长年不衰。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向往美食的、希望拓展美食认知空间的大有人在。 大家知道,一个人的味觉记忆是从幼儿味蕾*丰富时开始的。我常说,如果要成为一个吃主,得有个好爸爸。一般讲到好爸爸,不是有权就是有钱,但还得加上一条:好吃。你有好爸爸但他不好吃,也难以练就所谓的美食家。一个人如果在幼时味蕾*丰富的年纪,能够吃上各式各样的菜品,那么待到成年也就积累了足够多的视觉与味觉记忆。味蕾随年纪增长而衰减,成年之后,基本上下降50%,因此,一个人若在成长发育期缺乏美食经历,那么长大以后美味记忆同样是缺乏的。 个人对美食的视觉与味觉记忆积累如何,乃是自幼成长环境铸就的,包括地域、阶层、家庭、饮食态度等。吃喝寡淡乏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外在条件的限制,但这不等于就限制住对美食的**。越是吃得差,期待美味佳肴的心情可能越炽烈,一旦有机会实现,究竟味道如何,是满足?是失望?是不过如此?搜索味觉记忆,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会因人、因时令、因菜品质量而大不相同。 菜品一向存在名实之分。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走出饥饿也不过三十几年,这三十几年当中的前二十年,可以说是全民胡吃海塞。这是对多年饥饿历史的报复。在大吃大喝浪潮中,一些缺乏美食经验的人,往往愿意听信“美食家”的说辞与指引。毋庸讳言,这些年“美食家”真的是如鱼得水大展身手。 我向来主张“说吃”贵在经验体悟,而非道听途说、添枝加叶甚至编造糊弄他人。“美食家”称谓极其无聊荒诞。世间学问类别甚多,做学问可以成家,但自幼成长过程中,因享*资源比较充分而铸就的吃喝经验优势,*不是本事。称“家”实在恭维得让人害臊,一个人要真的吃过见过,说好听的是个吃主,*直白地说就是个吃货,或是饕餮之徒。 不管怎么说,天生本能,加上家庭饮食丰富多样的文化背景,养就好吃、讲吃、讲品位的习惯,个人的口感口味也断不能成为品尝美味的一般标准,尽管个人吃史辉煌令人称羡,也不过芸芸众生中的一张嘴。说实在话,说吃话题,因脱离饭局实景,融入了许多想象、夸张、故事与神话。 说到底,吃喝口感乃身内之物,谁也替代不了谁。吃喝是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建构,说得再天花乱坠,听得再如醉如痴,未能实践同样枉然。就像文玩鉴定一样,听人说得再多,书读得再广,未经实物反复把玩,遇到假货赝品,照样上当*骗。世间没有哪一个菜能够通吃天下,人皆赞不*口。凡是流传已久的成熟菜品一定是经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非“美食家”推介或专家评奖造就的。况且菜品名实之间相合相离,全在厨师手中,从来是具体的、一次性的。食材、技法达标则相合,否则相离。吃的是物,而非名。慕其名而丧其实,花了大价钱吃佳肴名菜,*悲哀的莫过于厨艺错乱,让美味荡然无存。 人们渴求美食美味,常常越出品尝本身,而*在意附于佳肴之上的名人、权势、财富等社会价值。因之,愈是扯上帝后、权贵、名人的复杂稀奇的美食解读,愈能欺世蒙人。就此准备了三个例证,逐一讲述。 举证一:活烧鹅鸭 唐代有位张鷟,所著《朝野佥载》卷二记载: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取起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即回,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拦驴于小室内,起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 张易之、昌宗、昌仪三兄弟皆是武则天的面首,面首就是男*。张易之为控鹤监。古人常称仙人骑鹤上天,因此以“控鹤”称皇帝的近幸或亲随。武则天时代的控鹤监是男*集中的地方,由张易之与张昌宗掌管;张昌宗又掌管秘书监,秘书监负责藏书与编校书籍;小弟张昌仪任洛阳令。兄弟三人权势熏天,无所不为。人到了这种“自由”境地,突发奇想,即可以马上实施。 深入考察这一美食故事,立即疑窦丛生。大铁笼中间放火盆,旁边设五味汁盆,让活禽自己不断喝味汁增香而后烧熟。如果从表现张氏兄弟残忍、任性、自以为是与权势风光上讲,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如果从美食意义上探究,不过是一种揶揄与讽刺。如此烹饪的结果肯定与美味无缘。 五味汁配方本书未做说明,只说把鹅或鸭关在这个笼子里面,让它一*热就喝盆里的汁,再走再喝,直至被烧熟。 举此例证,是我曾去西安时*到的启发。西安现在讲恢复汉唐雄风,我当时就跟朋友说,这真是有点想入非非。当今各地无不希望借重本地历史文化造势扬名,但要凭借文化厚度拉高经济与城市知名度,也要扬长避短。陕西本有地下雄风,何必再搞地上汉唐雄风。比如西安城墙修好了,那是明清的,钟鼓楼也是明清的。真正地面上的汉唐古遗存很少,况且汉唐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大得多。现在尚存古代雄风的城市首推北京,北京元明清三朝地上遗存大量存在。 到西安去,朋友免不了饭局招待,席间聊天,谈起烤鸭,有位陪客说烤鸭如今已是中华美食名片,其起源应在西安。当代各地争名人、争**蔚然成风,各地不乏高人引经据典,哄抬本地的文化高度。 持论烤鸭源自西安、起于唐代的历史根据就是上述张鷟的记载。我当时一听就乐了。我说这条史料实际上是在讽刺张氏三兄弟。首先,如果与烤鸭挂上关系,只是明火烧制的都是**,其余烹饪细节看不出有什么关联。明火烧制肉类食材,*非唐代才有,老祖宗从抛弃生食那一刻,用的就是明火烧物。其次,这则笔记并未记录味道,倘若以为鹅鸭喝了五味汁,烧熟后必有五味汁味道,那就是想当然了。其实活体动物遇大火只能在开始极短时间内喝香料汁,很快便被烧晕动弹不得,些许香汁尚停留在肠胃怎能化作肌肉香味?第三,鹅鸭活体烧死后,开膛拆解散发的一定是腥臭,让人倒胃,遑论垂涎。所以这条记载与其说在宣扬一种美食,倒不如说在讽刺张氏兄弟的无知任性与权势下的病态**。把它与烤鸭起源扯在一起,**是风马牛不相及。假如张氏兄弟创制的火烧鹅鸭是美食,那么以中国人从不放过美食机会的传统,它应该能流传至今。因为铁笼、炭火、鹅鸭皆为寻常之物,且制法简单,投入成本甚低。 这是**个例子。 举证二:茄鲞 《红楼梦》大家都读过,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又作“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讲刘姥姥在大观园家宴上吃了一道叫“茄鲞”的菜,大为赞许: 刘姥姥细嚼了半*,笑道:“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茄子。告诉我是个什么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凤姐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剥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油炸了,再用*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钉子,用*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瓜子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 俞平伯认为“茄鲞”只不过是曹氏开的一个美食玩笑,他曾经讲过:“小说上的食品不必真能吃,针线也不必真做,亦只点缀家常,捃摭豪华耳。”*此说启发,在此添些佐料,铺开讲讲“茄鲞”为什么是个玩笑。 首先,看其制法。中国饮食之道,历来讲究一菜一味。尝尽百味而非百味一尝。相比之下,成熟的什锦类菜品比较少,也难成为宴席上佳品。茄鲞用料过于复杂,以至分不清什么是主料什么是配料,这不符合国人美食追求与美食品尝的习惯。 袁枚《随园食单?变换须知》讲:“一物有一物之味,不可混而同之。犹如圣人设教,因才乐育,不拘一律。所谓君子成人之美也。今见俗厨,动以*、鸭、猪、鹅,一汤同滚,遂令千**同,味同嚼蜡。吾恐*、猪、鹅、鸭有灵,必到枉死城中告状矣。善治菜者,须多设锅、灶、盂、钵之类,使一物各献一性,一碗各成一味。嗜者舌本应接不暇,自觉心花顿开。”*脯肉、香菌、新笋、蘑菇、五香*干、各色干果等配料与茄子的口感硬度相差甚远。 诸位也许有这样的烹饪经验:炸制食品,除非为了追求嫩白效果而使用动物油之外,一定要用植物油。动物油炸制食品的颜色永远是淡白的,而且表皮不如植物油炸的那样牢固焦脆。四五月的鲜嫩茄子切成碎丁,经过*油炸,表皮本来不牢,再经*汤慢火煨干,再用香油收汤,糟油搅拌,估计茄丁早已变成茄泥了。鲜嫩茄子实在禁不住长时间烹制与反复翻炒,况且还是碎丁,在配置干果的坚硬环境中,茄丁怎能保持身形完整? 凡是名菜,主、配料混搭一定分明得当。中国的菜品烹制,历来讲究软硬搭配适中。菜名决定菜品的主要内容,既谓之茄鲞,而茄子并未当家,倒变成了大杂烩中的一味辅料,可以想见,在入口之前,茄丁差不多已是混在干果、*丁之中的茄泥,不是筷子轻易就能夹起的。 “香油收汤,糟油搅拌”。香油大家都知道,是芝麻油,而糟油知道的人相对少些。糟油至少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清顾仲《养小录》所记,用香糟十斤 、香油五斤、盐二斤半、花椒一两拌匀,然后把四样混合物料倒入缸里,大缸底下放一个瓶子,瓶口蒙上纱布。放置九个月到一年,渗进瓶子里的油汁就是糟油。 另一种是用甜糟加上酒曲、酱油以及香料,封到一个坛子里头。封存大约也需九个月到一年,到时将清汤滗出。乾隆以后太仓糟油比较有名,《太仓州志》谓之“色味佳胜,他邑所无”。至于王熙凤所说的糟油是哪一种,则不得而知。 其次,看其存放。茄鲞集中大量制作,分期食用,明显存在着食品保质问题。在物流与食品保鲜技术贫乏的时代,罕见鲜活食材异地交流和反季节蔬菜。在北方,鲜嫩茄子上市时是夏初,天气已热,再用瓷罐密封保存,恐不能长久。况且开封后不是一次用完,而是随吃随取出一些,与炒*瓜子相拌。其中干果倒还罢了,香干、*肉与茄丁无论如何也难保不*败变质。 追溯先民饮食习惯,由于*到保鲜保质技术制约,只在冬季过年前夕才集中制作大量荤素熟食,其余三季鲜见集中制作。曹氏故意将冬令菜肴移植到初夏,季节之间的巨大反差,恰恰留下了破解迷雾的玄机。 何为*瓜子?这些年也参加过一些烹饪方面的会议,说到*瓜子,有田*腿之说,亦有*腱子肉之说。我非厨行中人,也不做中国饮食烹饪史研究,只不过有些好吃而已。我常想,茄鲞既然是曹雪芹的创作,那么一定要了解当时的饮食文化背景,谈吃喝一定要结合当时人的生活情趣与生活习惯。如果脱离了小说创作的时代、地域场景,则变成纯粹的“物种之争”。倘若对历**曾经流行的菜肴和旗人的饮食习惯有所了解,就很容易知道炒*瓜子是野*丁炒酱瓜,又称山*炒酱瓜。炒*瓜子是一种北京旗人喜爱的冬令佳肴。比如说快过年了,旗人家庭预备的过年菜品,基本上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芥末堆、*鱼冻、豆酱等,其中有一项是**的,就是山*炒酱瓜。这些预制的小菜大都储存于坛罐之中,以备正月节*期间食用。 “瓜”有两重含义,一是指酱瓜,二是指去皮骨撕下的野*肉形似瓜条。山*系指产自东北的野*,满洲人迁居北京后,野*不大好找了,渐渐地改用里脊肉替代,或里脊丝炒酱瓜丝或里脊丁炒酱瓜丁,很少见用*肉炒制。讲究的酱瓜一定要选用六必居的,上乘的是大兴产的“五道眉”,瓜短粗、身有五棱;稍差的用大兴产的“八道棱”,瓜个头较大。两者相比,“八道棱”做出的酱瓜不如“五道眉”的脆。为什么要在年前把这些菜都做好?我们中国过年的传统禁忌是初一到初五之间不动刀,以免伤害祥和,因之,主食也好,副食也好,都要在年前预备好。来了客人留饭,将预备的芥末堆也好、豆酱也好、炒酱瓜也好一并上桌,先喝酒。然后热炖肉之类的肉食,以及馒头豆包之类的主食,酒后吃饭,主客尽欢。所以谈先民饮食,还是要了解当时人的习惯。《红楼梦》描写的贾府,生活习俗基本上是旗人的,仅从人物称谓上就足以展现旗人风范。比如宁府的贾珍不称贾大爷,而称珍大爷;王熙凤乃贾琏之妻,不称贾**奶,而称琏**奶,这是典型的旗人略姓以名行世的称谓习惯。至于饮食方面的描写,亦显露旗人偏好,譬如烧鹿肉。 《红楼梦》出现炒*瓜子并非仅有一次。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脂粉香娃割腥啖羶”描写雪后李纨、宝玉等人约请亲眷客人邢岫烟、薛宝琴、李纹、李绮到芦雪庵聚会作诗,当*一早,宝玉因性子急,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瓜子”忙忙地吃完,就赶去了。曹家从龙入关,隶属内务府旗籍。旗人饮食喜爱野味,清《调鼎集》载其烹饪之法:野*瓜,野*去皮骨切丁,配酱瓜、冬笋、瓜仁、生姜各丁、菜油、甜酱或加大椒炒。 其三,看其流传。《红楼梦》在刊行前就以钞本流传。从**可知的乾隆十九年(1754年)脂砚斋评钞本算起,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二百三十年。退而论之,即便说钞本流行不广,不足以引人关注,那么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经程伟元、高鹗整理排印,《红楼梦》步入印刷传播时代,以此为起点到20世纪80年代也将近二百年。为什么二百年间,经过这么多的红学迷恋者,这么多饕餮之徒,这么多达官显贵,这么多文人雅士,这么多身怀*技的厨师,都没能如法*制出这道茄鲞,将其送上餐桌,怎么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普遍拒*美食、批判美食的时代刚刚过去后,这道菜竟然堂而皇之出现,成为叫响的美食?真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众所周知,国人一向不会放过制造美食的机会,倘若此菜真的好吃又**,说句实在话,用等二百多年,应该是紧随《红楼梦》问世就能出现。我生得晚,吃过的馆子也少,在“**”之前从未听过这道菜,*谈不上品尝。这道菜之所以被推上餐桌,1987年的《红楼梦》电视剧功不可没。不过也只是响亮一时,如今基本销声匿迹了。 茄鲞问世后,曾吃过三次,一次在大观园红楼宴;一次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还有一次在南城的致美斋。这三家的炒法大同小异,够不上美味,也谈不上特色,*关键的是没有一家能**忠实凤姐菜谱。不外乎茄丁、笋丁、*丁与几味松仁之类干果炒制,取其名义而已。说白了就是个炒杂拌。也许厨师*明白其中奥妙,食材芜杂,程序错乱,不但难 从美食体验,到掌故传说,再到佳肴品鉴,信手拈来妙趣横生; 从*常饮食,到食摊名馆,再到清宫御膳,娓娓道来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