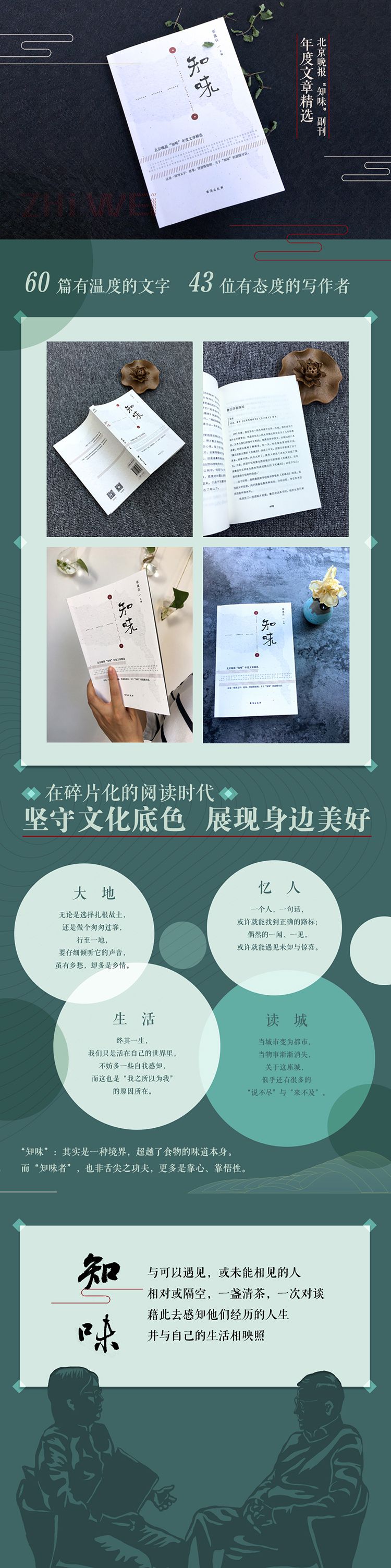出版社: 台海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知味
ISBN: 9787516812839

张逸良,媒体人。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毕业,现供职于《北京晚报》副刊编辑部。业余热衷于中国历史影像的收藏与研究,出版有《另一种表达——西方图像中的中国记忆》一书。
Ⅰ 地名如同人名,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又一代人息息相关。那里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接续着千百年来的情感传承,也是永不磨灭的心灵印迹。 无论是选择扎根故土,还是做个匆匆过客,行至一地,要仔细倾听它的声音,虽然有乡愁,*多是乡情。 成都小河,汇入激流 李辉 传记作家,记者,原《人民*报》**编辑。 走进汉中,必到勉县(旧称沔县)武侯祠和诸葛亮墓。 史载*早的这座武侯祠,偌大庭院,千年古树,一片浓荫,掩映着一条古道。据说这条古道修建于汉代,自东向西,穿越秦岭,蜿蜒千里,一直抵达成都中心。两千年悠久古道,如今只有短短几十米遗迹与我们相伴。青石板凹凸不平,站在上面,颇有历史穿越之感。遥想当年,虽然相隔崇山峻岭,却因为这条古道,汉中与成都遥相呼应,四川盆地与汉水流域从此不再陌生。 距古道百米开外,便是汉江的上游沔水。沔水东去,流经襄阳,汇入长江,浩浩荡荡奔涌千里,归于大海。站在武侯祠古道之上,首先想到的当是诸葛亮。自小生活在汉水之滨,若到襄阳,总是要去隆中走一走。儿时记忆里,远在千里之外的成都,与《三国演义》的蜀国在一起,与历史传奇中的诸葛亮在一起。 开始熟悉成都,却是因为巴金。“**”结束后,参加高考,我进入复旦大学,1978年底,同窗陈思和建议我们开始合作研究巴金,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巴金,以“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以他的故乡回忆,使我仿佛嗅到成都大街小巷的气息,人未到,已有亲切感。 1985年,我**次走进成都,参加巴金、阳翰笙、艾芜、沙汀这四位文坛老人的研讨会。他们都是四川人。还有一位成都作家李劼人,可惜已经故去,无缘相见。他的《死水微澜》《大波》等作品,以熟稔的四川方言,叙述袍哥故事,叙述近代四川护路运动,被誉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他与巴金一样,让读者熟悉了这片土地。 来到成都,当然要去武侯祠。伫立其间,想到杜甫名句“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同时,也很自然地想到另一名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汉中古道以陆路将四川盆地与汉水流域打通,而蔓延数千里的长江,是四川千百年来连接外部世界的大通道。 有的历史,永远不会忘记。抗战期间,长江天堑成为*后一道防线,四川乃至长江上游的大西南民众,以坚韧、忍辱负重精神,撑起中国*后一片天空。他们慷慨接纳各地流亡者,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大学,异地重开,延续教育与文化之脉。从而,民族不亡,祖国不亡。每念及于此,仿佛看到成都诗人流沙河,当年参与修建盟**用机场的瘦小身影。80高龄的他,为我书写的“宁静致远”,正是对四川深厚文化的*好诠释。我后来曾多次到成都,不时会想到一些前辈的斑驳身影,如熟悉的丁聪、郁风、黄苗子、吴祖光、杨宪益……他们在这里写作、绘画、教书,只把他乡当故乡,历史场景中,所有漂泊者那一时刻,都已融于其中。 巴金之后,在我眼里,流沙河就是成都*好的一张文化名片。 喜欢听流沙河先生讲话。从来都听他讲地道四川话——本地人大概还能分清是标准成都腔。他讲话语速不快,一板一眼,舒缓有致。他讲究语调,强弱相济,长短搭配,起伏之间形成乐感,如舞台道白一般,听起来,悦耳,舒服,且有趣之极。 回味他的说话语调,是一种快乐。 一年,我随一个摄制组到成都拍摄关于巴金“回家”的专题片,请流沙河出镜对谈,他带我们走进寓所对面的大慈寺。他瘦得出奇,轻得出奇,走路快而飘逸,让人担心一阵风会将他刮走。我们找到一处楼阁,他坐在游廊旁的石凳上,阳光把树枝碎影撒落满满一身,与清癯面孔相映衬,煞是好看。摄影师审视镜头,不由赞叹,对我说:“你来看,太有镜头感了!” 那天,流沙河与主持人对话时,我站在一旁,一边听,一边欣赏。阳光碎影下,听地道方言,看清癯面庞,他坐在那里,俨然就是一幅成都风情画:从容淡定,风趣幽默,*有少见的飘逸。 面对我们,流沙河娓娓道来。他不只是谈巴金,还有老成都遗韵的星星点点。80年代巴金回到成都,流沙河与周克芹一起前去看望: 巴金住在西门外金牛坝宾馆,我们去看他,弄一个椅子让他在中间坐。那个时候说话**洪亮,大得很,身体很好。 我记得一件事情,一个人对他说:你的脸色**好……他回答四个字:虚火上冲。巴老说这句话,是表明不爱听别人当面吹捧他。我们大家都笑了。 我和周克芹两人去的,周克芹现在都不在了。我们单独去见过他。推个车子,轮椅车。看到巴老,我想到一件事,中学我读的**部旧小说是《水浒》,**部新小说是《家》,读《水浒》是反抗社会,《家》读了就反抗家庭。 《家》的印象**深,《家》里很多细节记得**清楚。《家》写到成都人在家中晚上加热用五**,我感到**亲切。五**是用一个油灯,竹丝编一个罩子,把一碗要吃的东西放在里面烤……《家》里写到高觉慧、高觉民、琴表姐到华阳书报流通处看上海、北京新的报纸和刊物,我的印象很深。华阳书报流通处,上海、北京新的报刊全部集中在那里,巴金《家》里写觉民、觉慧到华阳书报流通处……我去找,窄得很的巷子,我就想那个地方。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是五四运动过了十二年才出生,这些细节都只说明当时巴老的《家》影响之深。 还有他家正通顺街后门在东珠市(街),我念中学时从后门过,门口还挂着巴金《家》中写的那个对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距他离开家已经十**年了。 ……像巴金这样的人,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中间影响之大,除了鲁迅之外,可能就是巴金。 这一次,也是巴金*后一次回故乡。之后,故乡再也无法返回,只留在他的记忆中,出现在梦中。 故乡遥远,时光悠长。 将近百年之前,*“五四运动”影响,向往外面世界的巴金,1923年执意离开家庭,离开成都,独自前往上海。成都城外有条河,他坐上小船,沿河而行,前往重庆。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巴金乘上轮船告别故乡。如杜甫诗句所说,过夔门,穿巫峡,走向上海,一个无比宽阔的天地,在巴金面前渐次展开。 这条小河,从成都流出,曲折蜿蜒,*终汇入长江,奔向大海。 年轻巴金曾以河流来描述生命流动: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或许,乘坐小船离开故乡时,巴金已经开始感悟着生命的这种流动状态。 成都那条河不知如今尚在否? 河水仍在流淌吗? 丰子恺的石门湾 钟桂松 浙江省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 一代艺术大家丰子恺先生故里石门湾的地名,已存续了2500多年。相传这一带原来是诸侯小国交战的地方,常常铁马金戈,硝烟四起。周敬王二十二年至周元王三年,即公元前498年至前473年,吴越争霸,战争不断,越王在此地“垒石为门”,作为吴越两国的疆界,从此有了“石门”这个地名。至今,石门镇上还有“垒石弄”的弄堂名称。隋大业六年,即公元601年,江南开凿大运河,规划时,大运河要从嘉兴经过石门、崇福、塘栖后到达杭州,而从杭州回来经过石门时,正好南来东去,从崇福北上石门,一个转弯,径直东去,所以石门又被人们称为“石门湾”。 一千多年以来,石门湾的先人们一直守护着石门湾这个古老而又有历史文化意味的地名,守护着世世代代石门人的乡愁,千年不改的石门湾,千年不*地传诵着石门的故事。这些饱含历史、文化和乡愁的故事,在丰子恺先生心里,也是美丽温馨,情深隽永的。 抗战时期,丰子恺带着全家老小逃难到广西、四川、重庆等地,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做得*温馨的夜梦,就是在故乡石门湾的生活。1939年9月6*,丰子恺写就一篇长文《辞缘缘堂》,其中一句“走了五省,经过大小百数十个码头,才知道我的故乡石门湾,真是一个好地方”,感动了无数乡亲。他还担心外省人看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特地介绍了“石门湾”的来历:“它位在浙江北部的大平原中,杭州和嘉兴的中间,而离开沪杭铁路三十里。这三十里有小轮船可通。每天早晨从石门湾搭轮船,溯运河走两小时,便到了沪杭铁路上的长安车站。由此搭车,南行一小时到杭州;北行一小时到嘉兴。三小时到上海。到嘉兴或杭州的人,倘有余闲与逸兴,可屏除这些近代式的交通工具,而雇客船走运河,这条运河南达杭州,北通嘉兴、上海、苏州、南京,直到河北。经过我们石门湾的时候,转一个大弯。石门湾由此得名。”字里行间,都饱含着浓浓的乡情。 00“石门湾”这三个字在外省人看来稀松平常,但在丰子恺先生那里,却是温馨而深刻的,这是他所有感观神经中*为敏感的焦点。他说过,抗战逃难“流亡以后,我每逢在报纸上看了关于石门湾的消息,晚上就梦见故国平居时的旧事,而梦的背景,大都是这百年老屋”。丰先生看到“石门湾”的消息就做梦,梦见石门湾老屋惇德堂,就梦见故乡故土故人,“梦见孩提时的光景”“梦见父亲中乡试时的光景”,这是对故乡何等的情怀?有时逃难途中住在酷热少雨的地方,丰先生便立刻怀念起石门湾来:“石门湾到处有河水调剂,即使天热,也热得缓和而气爽,不致闷人。”他恨不得立刻奔到运河边的石门湾,去享*那份温润和清凉。 石门湾不仅历史悠久,还是涵养丰子恺先生艺术的地方,他的漫画里,以故乡石门湾的社会世情为题材的漫画比比皆是,比如《巷口》《云霓》《话桑麻》《三眠》《南亩》等,流传甚广且耳熟能详;还有丰子恺先生回忆石门湾往事的大量散文随笔,如《歪鲈婆阿三》《四轩柱》《阿庆》《五囡囡》《五爹爹》《癞六伯》等,算得上是丰先生为故乡石门湾作的一部乡亲人物传。他们都生活在石门湾,讲着石门湾的土白,言行举止留有太多石门湾的元素。因此,无论是漫画还是散文,林林总总,终构成一部有滋有味的丰子恺版“石门湾艺术交响曲”。 丰子恺先生的生命里、漫画里、散文里,都散发着石门湾的韵味,石门湾无处不在,与他是鱼水乃至血肉一般的关系。千年不改的石门湾,在以后的千年里,地名也不应改,因为地名是历史形成祖宗传下来的文化,后人应该敬畏才是。 去安徽,寻访桐城派 韦力 爱书人,酷爱古籍,曾写过数本关于藏书之书。 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关于他在桐城派的地位,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有如下说法:“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大的散文派别。”关于他的写作特色,沈廷芳在《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录下方苞自己的说法:“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脸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看来方苞反对在散文内掺杂进语录体,故而他所写之文,被后世赞之为“雅洁”。可是这样的文章确实朴实,想从中选出一句隽永之语,颇为不易,故本篇的题目我想选他诗文中的两句话,来概括他的特色,这使得这个简单的要求颇难达到,故而只好从他反对的骈文中选出了这样一句话。 “躔分两度,天各一方;会稀别远,意满情长。”这句话,出自方苞所作的《七夕赋》,如此说来,他也作过这类韵文,从整篇《七夕赋》来看,方苞在这方面也颇具才能,我摘选该赋中的首段如下: 岁云秋矣,夜如何其?天澄澄其若拭。漏隐隐以方移。试一望兮长河之韬映,若有人兮永夜而因依。彼其躔分两度,天各一方;会稀别远,意满情长。欲渡河兮羌无梁,空鸣机兮不成章。叩角余哀,停梭积恨,四序逴以平分,寸心抚而不定。悲冬夜之幽沉,迷春朝之霁润,睹夏*之方长,盼秋期而难近。 即此可知,方苞确实是文章高手,即便他不擅长的韵文,依然写得如此漂亮。 方苞故居位于安徽省桐城市寺巷内。我的此趟行程是先到庐江,而后转往桐城。从地图上看,庐江到桐城并不遥远,看样子也就50公里的路程,然而在乘车方面却很不方便,这仍然是因为地域的管辖:庐江在行政上归合肥管辖,桐城归安庆管辖,虽然仅是短短的50公里,却每*仅两班车互通两地,我在庐江寻访完何晏后,已经错过了这两班车,只好打的前往桐城,谈好的价格是100元,对这个地区来说,100元的价格颇为公道。 进入桐城市区后,因为旅途顺利,天色并没有暗下来,我不想浪费这大好的时光,于是换上一辆当地的出租车,直接奔寺巷前往探看。这条小巷不长,没多长时间就能走一个来回,然而我在寺巷内转了几个来回,都未曾找到自己的寻访目标,然连问几个人却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正在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位大妈,旁边有人认识她,马上跟我讲:“你去问她,因为她是老师。” 这位大妈从穿着到面色都有着一种隐隐的书卷气,我觉得称呼她大妈有些不恭,于是我也随着那些人的称呼,向她叫了一句老师,显然这句称呼赢得了她的好感。她问我有什么事情,我递上了自己的寻访名单,她说自己眼力不好,让我念给她听,于是我告诉她自己准备到这里是要找方苞、方以智和姚莹的故居,老师听完后,告诉我说,这些故居确实在本巷之中,她看了我一眼,而后跟我说:“这样吧,你跟我走,反正我也是散步,我把你带到那里去看看。” 老师带我看的**个故居就是当年姚莹的居所,这个故居的门牌号为寺巷8号,走入院内,迎面看到了几栋老房子,老师指着一栋告诉我说:“这个就是。”果真,我看到了墙上的文保牌。我拍照之后,老师又带着我继续前行,又穿入了另一个院落,在这个地方,终于得见了方以智的故居。我当然*关心方苞的故居在哪里,等我拍完方以智的故居之后,向这位老师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想到她却跟我讲,自己不知道方苞的故居在哪里,这个说法让我有些意外。但老师又跟我讲,前方不远是左光斗祠,这让我想起方苞所写的《左忠毅公逸事》,难怪他跟左光斗的事情记录得那样的声情并茂,原来他的祖居旁就有左光斗的祠,只是不知道这个祠堂建于何时。 前来此地之前,我事先做过功课,网上有一篇文章称方苞的故居位于寺巷与新巷之间,老师闻我所言后,把我带到了新巷的巷口,原来新巷与寺巷是平行的两条巷子。进入此巷前行,看到了有一处老房子的后墙,细想刚才的方位,这堵墙应该就是刚才进去所拍的方以智故居后墙,原来两条巷子夹住的,就是方以智故居。如此说来,方以智的故居一直处在这一带,恐怕难有一个大地方容得下方苞的故居,那方苞的故居跟方以智的故居有什么关系呢?而方以智和方苞同属“桂林方”,且网上有文称方以智是长房的,又叫“中一房”,方苞是小房的,又叫“中六房”,如此说来,方以智跟方苞关系较近,那方以智的故居是不是就是方苞的祖居呢?我还未找到相应的佐证材料。 但显然,这位老师因为没能帮我找到方苞的故居而觉得遗憾,于是她就走入了一个房内,找出了一位年岁很大的老太太,她向那位老太太询问方苞故居在哪里,老太太也称不知,面对此况,只能存疑于此了。到此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我即便找到可以拍摄之处,也无法继续拍摄了,但是在桐城一地我还有多位寻访对象,于是准备找个酒店住下来,再筹划下一步的行程。我向这位老师感谢了她给我的指点和带路,老师很关心地问我准备住在哪里,我告诉她自己还未定酒店,接下来准备去寻找一家。 ★年度精选、去粗取精,凝结作者与编辑的共同努力。 《知味》精选自北京晚报“知味”副刊刊登的文章,全书分“大地”、“忆人”、“生活”、 “知味”和“读城”五个部分,在作者们的笔下,丰子恺、徐志摩、老舍、流沙河、范用、启功、冯亦代、*婴等学者大家,老成都、芙蓉镇、京西香山等那些熟悉的地名与故事,带着温度缓缓而来。 ★43位有态度的写作者,60篇有温度的文字。 这是一场由李辉、赵大年、陈子善、肖复兴、韦力、李小可、李燕、杨葵等43位新老作家,用60篇充满情感与温度的文字,展开的关于“知味”的温暖对话。在文字式微,碎片化阅读正兴的时代,那些曾经熟悉的文学形式正渐行渐远。这本书不仅能唤起人们对过去的回忆,*能给人以深刻而久长的回味。 ★文字隽永,短小耐读,无穷回味。 如同品茶时总说的“回甘”一样,苦尽甘来,说的是味道,*是味道背后的省略号。《知味》一书所做的,只不过是将这个省略号延展开来,以人、故事、情感的叙述形式,让它变得形象而有触感。文章不长,却很适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 ★读百家文,知百家味,识百家情。 《知味》所记录的,*多的是一些个体生活的边角料,以及当时心中琐碎的感知,不仅有大家写的小故事,也有平凡人写的平凡事。平凡其实并不平凡,做得平凡事,才是不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