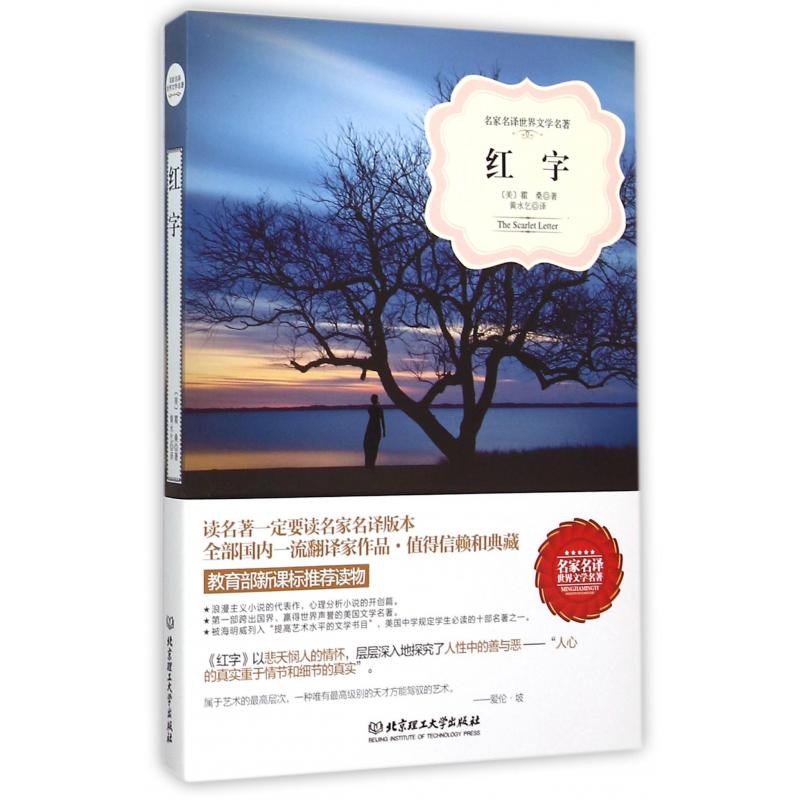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理工大学
原售价: 30.00
折扣价: 11.10
折扣购买: 红字/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
ISBN: 9787568210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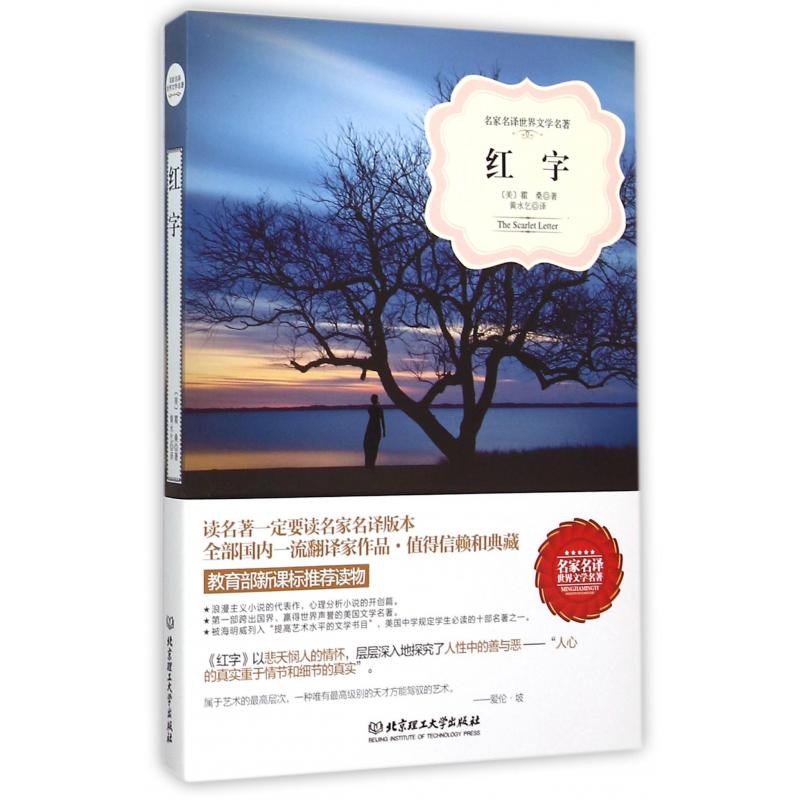
霍桑(1804—1864),19世纪美国文学作家,实践并发展了罗曼司体裁,擅长象征主义手法和心理分析,其艺术之花得益于新英格兰历史和清教主义的滋养,一直被视为美国本土文学的代表,亨利·詹姆斯甚至以“地方性”来形容他的创作。然而,他的作品既是本土的,也是国际性的,融合了欧洲多元文化传统,他的作品,因其深邃的思想与精湛的艺术技巧,散发出持久的艺术魅力,是当之无愧的美国文学的典范。 他的主要著作有《七个尖角阁的老宅》《神奇故事集》《杂林别墅里的希腊神话》《追求至美的艺术家》等。 黄水乞,福建南安人,1963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主修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晋升教授。曾于1982—1984年先后赴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美国加州大学访问,从事英美长短篇小说研究。1994年获福建省第二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主要译著有《红字》《罗曼斯和幻想故事》《雾都孤儿》《呼啸山庄》《皮兰德娄短篇小说选》等。
海关 ——《红字》导言 虽然,我历来不愿意在炉火旁向我个人的朋友过 多地谈论自己或自己的事,但是在和读者交谈时,我 一生中竟有过两次写自传的冲动,这实在有点不可思 议。第一次发生在三四年前,那时,我正给读者描述 自己在一幢极其幽静的古屋里的生活情景——对此, 无论是宽容的读者还是冒昧的作者都想象得出,这是 不可原谅的,也是毫无道理的。这一次实在是造化, 由于我非常荣幸地在上述场合找到了一两位听众,因 此我再次拖住读者大众,谈起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 并且忠实地仿效著名的“教区牧师——本教区执事” 的榜样。然而,事实似乎是:当作者将自己的整部作 品抛向人间时,作者并不是对会将书扔到一边或将之 束之高阁的多数人叙述,而是对能理解他的少数读者 讲述——这些人比作者大多数的同窗学友和终生的伴 侣都更了解作者。确实,有些作者远不只是叙述而已 。他们随心所欲地揭示内心深处的隐秘,甚至可以适 当地专门向完全富有同情心的人讲述;仿佛随意问世 的这部出版物一定可以找出作者自己天性的各个分离 的部分,同时将他与这些分离的部分彼此沟通,而使 他的生活范围完整无缺。然而,即使我们不针对个人 地将一切都抖出来,那也有失礼仪。但是,由于思想 僵化,表达迟钝,除非讲述者与他的听众的关系确实 非同一般——想象那是一位仁慈谦和、善解人意的朋 友(虽然不是最亲密的朋友)正在恭听我们的谈话, 这也许是可以被原谅的;这时,由于天生的缄默为这 一友好的意识所缓和,我们可以就我们周围的情况, 甚至就我们自身的情况进行畅谈,但是我们仍然会把 内心最深处的自己隐藏于面纱之后。我认为,这种谈 话在这种程度上和在这些范围内可以是自传式的,不 至于侵犯读者的权利和自己的权利。 同样地,人们可以看出,海关导言具有文学上向 来公认的某种行为规范:它说明了我如何拥有下列大 部分材料,并为此中所叙述的故事的真实性提供了证 据。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愿望,一种使我自己处于 编者的真正的地位的愿望,或仅仅是构成此书的故事 之中最冗长那部分的编者的真正地位的愿望——这一 愿望,没有别的,正是我认定与读者大众有着私人交 情的真正理由。为了达到这一主要目的,我假如通过 额外地添加几笔,轻描淡写地描述迄今尚未描述过的 一种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中生活的一些人物——作者 又恰好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看来这是被容许的。 半个世纪以前,也即年迈的德比王年代,在我的 塞勒姆老家有一个繁忙的码头——不过如今码头被颓 败的木头仓库充塞着,也许,除了死气沉沉的码头中 央正在卸兽皮的一条三桅帆船或方帆双桅船;或者较 近处一条新斯科舍的纵帆船正在卸木柴外,它有很少 或几乎没有商业生活的气息——我是说,这座现已破 烂不堪的码头的最前面,常常被涨满的潮水所淹没, 沿着码头,在那排建筑物的基底和背后,在路边不繁 茂的草丛中,可以见到漫长的怠倦岁月留下的踪迹。 这儿坐落着一幢宽敞的砖砌大厦。从建筑物前面的窗 口可以望见眼前一派不太有生机的景象,以及对面的 港湾大厦。每天上午整整三个半小时,挂在大厦屋顶 最高点的共和国的国旗,或在微风中飘扬,或在风平 浪静中低垂着,但是旗帜上的十三个条纹已不是横的 而是垂直的了。这表明这儿已建立起一个文职的,而 不是军人的山姆大叔政权。大厦的正面是装饰着六根 木柱的门廊。这些木柱子支撑着一个阳台,阳台下面 是一段宽阔的花岗岩台阶,向下斜伸,直通街上。一 个巨大的美国老鹰标本盘旋在大厦入口处。它展开着 双翅,胸前护着盾牌,而且,倘若我没有记错的话, 每一个鹰爪都抓着一把交叉的雷电和带刺的箭。由于 它具有代表这一不祥的飞禽的特征——通常坏脾气的 弱点,凭着它的凶神恶煞的鹰嘴和眼睛,以及好斗的 姿态,它似乎在向与世无争的公众预示灾祸的来临, 尤其警告所有的居民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不要贸然闯 入它以双翼庇护的这座大厦。然而,尽管它看上去很 凶猛,但是眼下许多人正在这只联邦老鹰的羽翼下寻 求庇护。我想,他们满以为它的胸脯如鸭绒枕头那样 柔软、舒适,殊不知即便在它心情最佳的时候,它也 并不温柔;而且,迟早,通常只早不迟,还可能会用 它的利爪一抓,用钩状嘴一啄,将它的巢中的雏鸟甩 掉,或者用带刺的箭给人造成疼痛不已的创伤。 上述这座大厦周围的人行道——我们还是马上把 这幢大厦称为港口的海关为好——旁边的裂缝野草丛 生。这表明近年来众多商人并没有在这条人行道上行 走。然而,在一年中的某些月份,人们也常常碰到一 个商务进展得较顺利的上午。这种场面可以使上了年 纪的居民回想起与英国最后一仗之前塞勒姆独自是个 港口的那个时期,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备受自己的商人 和船主所蔑视。这些商人和船主让自己的码头化为废 墟,但他们的企业却继续发展——使大量的生意不必 要地和不知不觉地涌入纽约和波士顿。在这样的上午 ,每当三四条船碰巧同时驶进港口时——它们通常来 自非洲和南美洲——或者船正要驶往那些地方时,人 们便会听见频繁的脚步声轻快地、来来回回地从花岗 岩台阶上传来。这里,在船长的妻子前来迎接他之前 ,你可以向刚进港口、腋下挟着装有船舶单证的已失 去光泽的洋铁皮盒的船长打招呼。他的脸因海风的吹 打而变得通红。他的船主也会在这里出现。他或兴高 采烈,或愁眉苦脸,或谦和有礼,或怒气冲冲,这要 视现在完成的航海计划是带来了很快能转手变成金币 的商品,还是带来了没人光顾的滞销品而使他陷入无 穷无尽的麻烦之类的情况而定。同样地,在这儿我们 还会见到个精明年轻的职员——一个将来也会额角爬 满皱纹、胡子灰白、饱经忧患的商人。他正尝到了买 卖的甜头,犹如狼崽尝到鲜血的滋味似的。他已经把 商业投机送到船长的船上,其实这时他最好在水磨用 的贮水池里驾驶模型船。现场中出现的另一个人物是 那位走外轮,企图寻求他国护照的水手,或者那位刚 抵达的、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正寻找进医院的途径 的水手。我们也不再忘掉从英国乡下为我们运来柴火 的那些锈迹斑斑的小纵帆船的船长们;也不该忘记那 伙相貌粗鲁的水手,他们没有美国佬机灵的外表,但 他们却为我们衰退的贸易提供了一件举足轻重的商品 。 将所有这些人与其他杂乱的各色人种汇集在一起 ——正如他们有时候那样,于是,一时间海关便出现 了一个人声鼎沸的场面。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一登 上海关的台阶,你就会看到——如果在夏天则在入门 处;如果在冬天或恶劣的天气,则在他们各自的房间 里——一排德高望重的人物坐在老式的椅子里,这些 椅子的斜倚着的后椅腿紧靠在墙上。他们常常睡着了 ,但偶尔可以听到他们一块交谈的声音,其嗓门介于 讲话声和鼾声之间,看那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仿佛 是济贫院的居住者,及其他一切靠救济、靠垄断劳动 过日子的人,或是那些根本不靠自己独自的努力谋生 的人。而这些老先生就是海关的关务员——他们像马 太一样端坐在收税所里,却不会像马太那样,动不动 为了使徒的差事而从那儿被唤走。 此外,当你走进大门时,靠左边是一间大约十五 平方英尺的极高的房间或办公室;其中的两扇拱形的 窗俯瞰着上述那个破旧不堪的码头,第三扇窗子面朝 一条狭窄的小巷,并可以看到德比街的一部分。从所 有三扇窗子都瞧得到杂货商、滑车制造商、卖廉价成 衣的商人和船具商人等开的店铺。在这些店门口,通 常可以看见一群群谈笑风生的老练的水手,以及老是 出没在海港码头一带的一些盗贼。这房间本身布满了 蜘蛛网,并因陈年的油漆而失去了光泽;地板上撒满 灰暗的沙子——这在其他地方早已不再风行。总之从 这个地方的邋遢劲,人们不难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连 女性,以及她手中富于魔力的工具——扫帚和拖把— —都很少光顾的圣堂。至于家具,里面有一只带着大 烟囱的炉子;一张陈旧的松木书桌,旁边有一张三只 腿的凳子;两三张破旧不堪、摇摇晃晃的带木坐垫的 椅子;还有,别忘了那个藏书室,在一些书架上放着 三四十卷的《国会法案》和一部大部头的《税务法汇 编》。一根锡管直穿天花板,构成了这房间与大厦其 他部分口头传话的媒介。就在这里,大约六个月前— —曾有一个人或者从这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或者 一只肘部撑在书桌上,身子懒洋洋地靠坐在那条长腿 的板凳上,眼睛上上下下地浏览晨报的专栏——尊敬 的读者,你也许会认得欢迎你到他欢快的小书房的这 个人。在这里,阳光透过古屋西边的柳枝,发出微弱 的怡人的光。而如今,倘若你再到那儿去找他,要找 到这位身为民主党党员的检查员,那简直枉然!改良 的铁扫帚已经将他扫地出门;一位更可敬的继任者摆 出他的威严,正将薪水装进自己的腰包。 尽管在我的童年和长大成人的岁月里,我常常远 居他乡,但塞勒姆这座古镇,我的家乡,现在支配着 或者过去也确实支配着我的情感。然而在我实际在此 居住期间,我从未认识到这种情感的力量。不错,就 它的物质方面而论,家乡的地面是平坦的、千篇一律 的,其上主要盖着一些木头房子,能称得上建筑上的 美的房屋寥若晨星——参差不一,错落不齐,既不别 致,也不古雅,只有平淡乏味——死气沉沉的长街萎 靡不振地穿过整个半岛。街的一端是加罗斯山和纽吉 尼镇,在街的另一端可以看到济贫院——这就是我的 家乡的地理特征。它就像一副混乱不堪的棋盘,要说 你对这副棋盘怀有深厚的情感,那也在情理之中。然 而,虽然我在其他地方总是最快乐的,可是我内心深 处对古老的塞勒姆却怀有一种感受力。在缺乏恰切的 词汇来表达的情况下,我倒愿意称它为“爱”。这种 情感很可能归因于我的家庭在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的 老根。自从我的姓氏最早的移民——原先的英国人— —出现在这荒无人烟的、森林环绕的村落以来,已经 将近二百二十五年了。村落后来已经发展成了这座城 镇。在这块土地上,他的后代就在这儿降生、死亡, 并且已将他们世俗的物质与这块土地交融在一起;一 直到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肯定其与人类的身躯有了血肉 关系,我也短暂地以这身躯走在这些街上。因此,在 某种程度上,我所提及的情感,只是尘土对尘土的感 觉上的共鸣。我的同胞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这种情感 为何物。由于频繁的移植也许对血统的发展有利,因 此他们也不必知道这种情感究竟是什么东西。 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