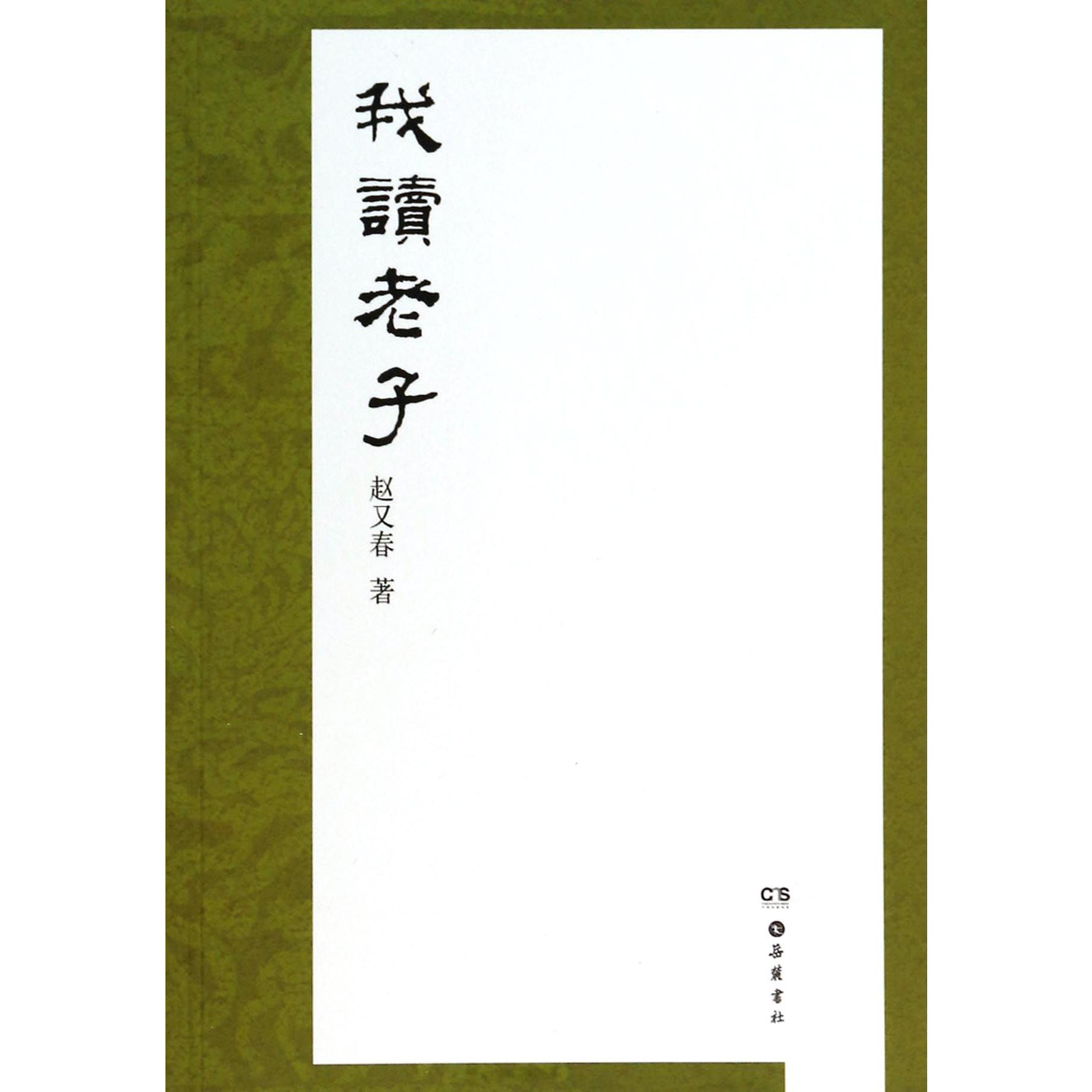
出版社: 岳麓
原售价: 25.00
折扣价: 18.70
折扣购买: 我读老子
ISBN: 97875538018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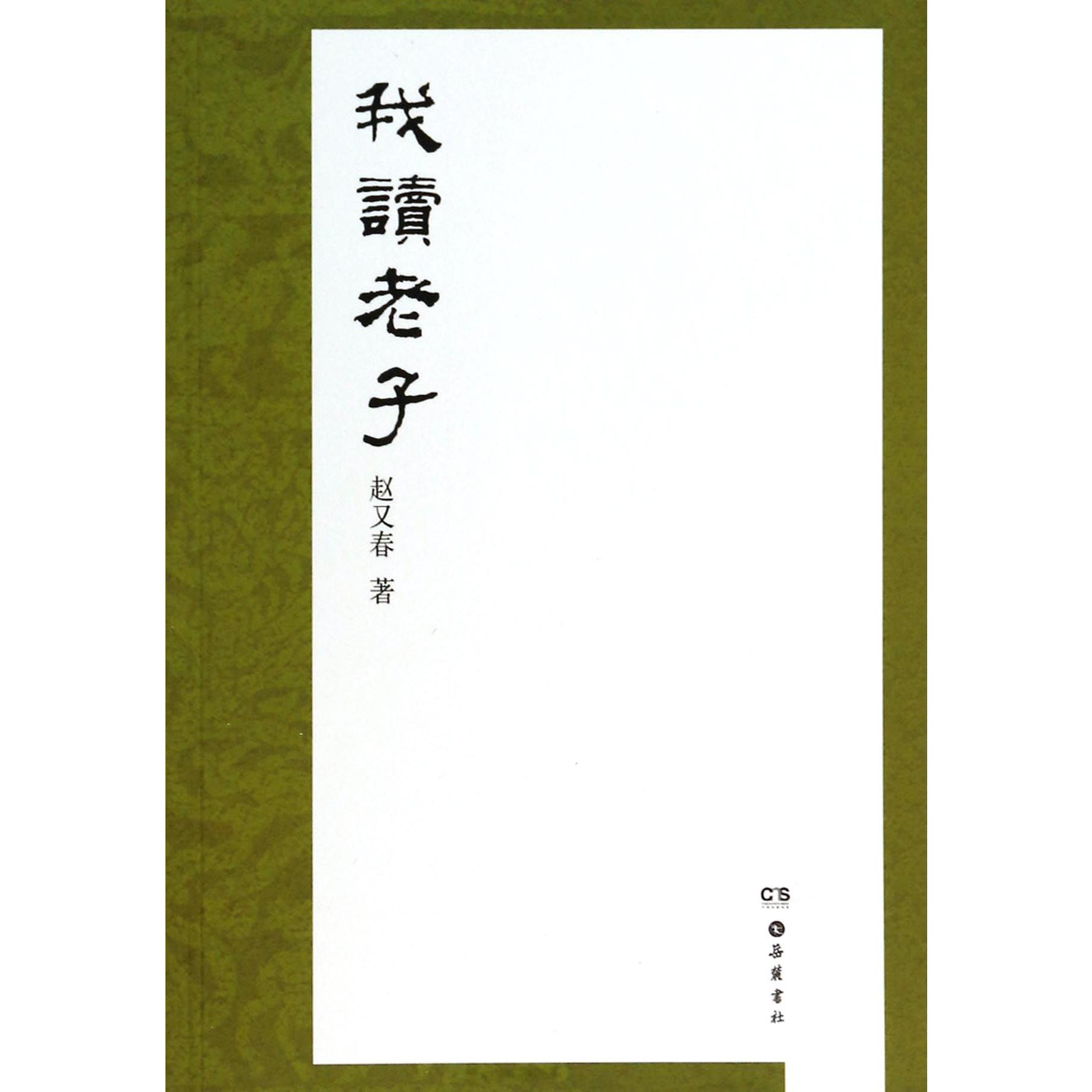
赵又春,男,1935年生,湖南邵东人,1957年从留苏预备部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60年底被开除学籍:1961—1979年,从事体力劳动和担任民办中学教师,1980年起在高校任哲学教员,1985年评为副教授,1986—1990年任湖南师大马列部副主任、主任,1996年初退休。曾发表过几十篇哲学原理方面的文章,主编过一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同人合译过两本书,73岁起开始写《我读论语》等著作。一生最喜欢的事,是和“可以对话的人”聊天,他说,他若印制名片,上面将写一句:同我打交道唯一有效的方式是讲真话。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 。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 之门。 这是《老子》开宗明义第一章,按说应该带有序 论或导言的性质,对于读懂以后各章,具有指导作用 。可这一章正是《老子》一书全部八十一章中最难懂 ,注家分歧最大的一章。因此,我对这一章的解说不 能不长一点。 一、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 。这两句王本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 名。”一般认为后人是为了避讳汉孝文帝刘恒的“恒 ”字,就将老子原文的“恒”替换成同义词“常”了 。这对文义没有影响,因为“恒”、“常”义同。多 了两个“也”字,意义就不相同了:没有“也”字, 前一句不管怎样句读,都可以作两种解释:①道是可 道的,但都非常道;②一个道,如果可道,则非常道 。加了“也”字,全句则只能看作是由两个判断句构 成的并列句(后句承前省去了主语“道”),只能作 前一种理解了。第二句也如此。两个“也”字大概不 是帛书抄写者任意加上的,所以帛书本可靠些。由此 可知,一直以来,《老子》研究者毫无例外地说这两 句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言说的不是永恒不变的道。 可以称谓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名”(见冯友兰著《中国 哲学史新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 页。本书以后凡引冯友兰先生的话,均出自此书第25 ~60页,不再一一作注),可说是“一开头”就误解 了《老子》。这个误解影响有多深远,读者可想而知 。不知为什么,冯友兰、陈鼓应、任继愈诸先生(本 书将多次提到陈鼓应先生和任继愈先生,以后一律简 称陈先生、任先生)等见到了帛书后还是这样作解释 。 不仅对这两句话的语法结构有以上误解,对“道 ”字的含义也有误解。头一个“道”是名词,作主语 ,是本章讨论的“话题”,这不成问题。第二个“道 ”放在“可”字后面,无疑是作动词,冯、陈、任等 先生以及至今绝大多数注家,都以为是“言说”的意 思。陈先生就说:“第二个‘道’字,是指言说的意 思。”任先生将“可道”译为“说得出的”。但“道 ”作动词时也是多义的,凭什么认定此处必是“言说 ”的意思?当然只有在证明采用其他任何一个义项都 说不通了以后,才可以这样肯定的。又不知为什么, 竞没有人想到必须作出这个证明。因此,沈善增先生 (以后提到沈善增先生时,同样只称沈先生)在其《 还吾老子》一书中证明这“可道”的“道”字并非“ 言说”义,我认为是一个极大的贡献,对于解读《老 子》真正具有“颠覆性意义”。他的理由之一是:“ 据我考证,‘道’在先秦时没有‘言说’的义项。” 他在书中介绍了他的考证,我以为是很有说服力的, 所以尽管沈先生说这个考证结论还只能作为《老子》 中“可道”之“道”并非“言说”义的佐证,我却认 为已经是“充足理由”了。因为既然直到秦朝灭亡时 “道”都不作“言说”讲,怎么能够设想两三百年前 的老子会独自发明出一个“言说”义项来,并且以后 两百多年中都没有得到一个作者的附和呢? “可道”的“道”究竟是什么意思?按说,①这 “可道”是作头一个“道”的谓语,因此首先要弄清 作主语的“道”的一般含义,然后从作动词的“道” 的各个义项中,选择可以同这个主语搭配的义项;② 如果可以搭配的义项不止一个,则要联系下文、全章 甚至全书,再作选择,力求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既能使 上下文义贯通,又同全章乃至全书他处的有关说法不 相抵触。考虑到在老子时代,作名词的“道”一般都 是指规律,或者说道理,而且用这个意思去解释《老 子》书中其他各章中的“道”字,又至少大部分都说 得通,所以我认同沈先生的理解,肯定“可道”的“ 道”是“指导”的意思,从而,“道可道也,非恒道 也”是说:任何道理(规律)都是可以用来指导行动 的。但都非恒道。下一句同这一句的语法结构和修辞 手法完全一样,所以也应是说:任何名字(名称、称 谓)都是可以用来指称某个对象的,但都非恒名。由 于“名”作动词时是单义的,所以对这一句第二个“ 名”的理解历来都没有分歧。 我还要指出,道,作为规律,特别是作为道理, 应该都是可以言说的,即使暂时下不出严格的定义, 只能通过各种描述或比喻来使人存想、领悟到它,也 是对它的“言说”,否则,怎能把它教给别人?老子 又怎么会写这本书来传他自己的道?所以,认为头一 句是老子声明他将教诲的乃是不可言说的道。在事理 上是讲不通的。 但这两句更难理解的是“恒道”。历来注家由于 把第二个“道”字解释为“言说”,自然把这第三个 “道”字理解为名词,一律将“恒道”看作名词性偏 正词组,或不作翻译,或译为“永恒的道”。沈先生 更正了第二个“道”字的含义后,又别出心裁,认定 “恒道”乃是前正后偏的领属性偏正词组,指“恒” 的“道”,即“‘道’是‘恒’的一个方面,而‘恒 ’则类于哲学上的‘实在’范畴,为世界的本原与本 体”。对他的这个“颠覆”,我就不敢苟同了。沈先 生举出了五条理由,但论证中采用的前提本身多只是 他个人的观点,并非学界的共识,如果一一进行辨析 ,就太烦琐了,所以我都不予介绍,只指出一点:如 果“恒道”是指“恒”的“道”,而第二个“道”字 又确是沈先生认定了的“指导”的意思,那么,这章 头一句就正是宣告“恒”的“道”是不能用来指导行 动的了,这怎么可能?按沈先生的意见,“恒”是世 界的本原与本体,“恒道”则是“恒”的行为法则, 既如此,“恒道”应该不但也可以指导行动,而且还 应是行动的最高指导。 根据以上分析,我的意见是: 1.这两句话,每一句的后一分句都是承接着前 一分句的谓语动词说下来的,所以“非恒道也”的“ 道”,“非恒名也”的“名”,也都是动词,并且同 第二个“道”和“名”的意思一样。 2.因此,两个“恒”都是它后面的动词的修饰 语,从而都是副词,“经常”、“总是”的意思。 3.所以这两句话是说:(人们通常说的)道理 都能够用来指导行动,但都不能用来指导一切行动; (人们通常使用的)名字都能够用来称谓事物,但都 不能称谓一切事物。 4.这样两个意思放到一起说,是因为“道”总 是关于某类对象、事物的道,因而与“名”有必然的 联系;前一意思虽然是本章的重点、主题,但不够显 豁,正有待于解说,后一意思的正确性却十分明显, 几乎像是公理,于是放到一起讲,让后句起着申述前 句理由的作用。因此,翻译时在第二句前句前加个“ 正如”之类的词点明一下,能够更好地表达老子的原 意。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