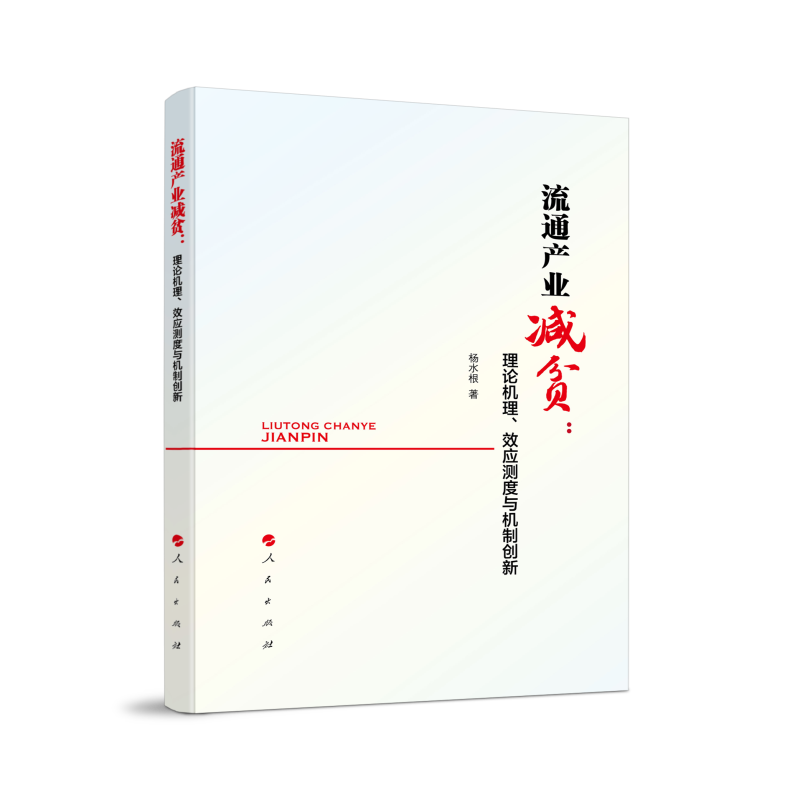
出版社: 九州
原售价: 138.00
折扣价: 89.70
折扣购买: 南北风味
ISBN: 97875225154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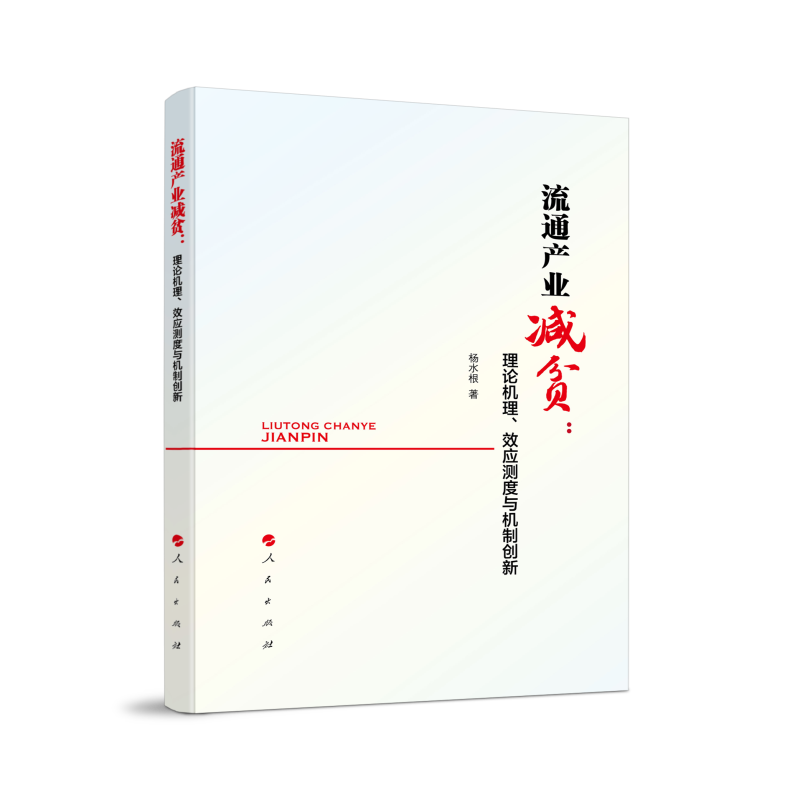
王稼句,苏州人,作家,学者,藏书家。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并在乡邦文献和文化整理中用功颇深。著述百余种,以文化随笔为多,有《谈书小笺》《秋水夜读》《看书琐记》《看书琐记二集》《看云小集》《听橹小集》《苏州山水》《姑苏食话》《吴门四家》《吴门烟花》等。
北京菜 金受申 以前《正报》上的“北京通”,大部分谈吃,谈起吃来,北京真是完备得很,西餐有英法大菜、俄式小吃,中餐有广东馆、福建馆、四川馆、贵州馆、山西馆、河南馆,江苏馆又分上海苏州帮、淮安扬州帮,至于号称北京菜的,却又是山东馆,近年又有介于南北菜之间的,是济南馆,纯粹北京菜,是没有这种馆子的。有人认为白肉馆是北京菜,这也不尽然,试想砂锅居的白肉烧碟,家庭中能否做出?不过白肉馆是北京馆子中独有特制,旁处是没有的。其实白肉原是满洲吃法,北京旗族家庭喜吃煮白肉,遂有人认为是北京馆就是白肉馆,这话是不周延的。还有人认为烧鸭是北京特有食物, 这是不错,不过老便宜坊仍写金陵移此,可见烧鸭也不是地道北京产物,因为北京填鸭得法,烧得得法,遂驾一切地方烧鸭之上了。 本文所谈北京菜,是北京家庭中家常菜,饭馆中是没有的,近年来旧家式微,一切老做法失传,又传入许多新菜蔬,遂使一般家庭竞仿新样,例如龙须菜、荠菜、盖蓝菜、苋菜、瓮菜、瓢儿菜, 都是从先北京没有的菜,虽然龙须菜是北京特产,也没见有人吃过。至于炒蕉白、烧菜花、炒洋芹菜,北京三四十年前谁吃过?于非厂先生最欣赏北京家常菜,实在是有特殊风味,而且经济的。今天谈几种地道北京老家常菜,诸位能仿制一下,也是不错的,闲来命山妻做一两种,请一请知音的尝尝,也未为不可。 北京菜分小吃、日常菜、年节或犒劳菜三种,先谈日常菜—— 再及其他。(一)“大萝卜丝汤”,这菜最富养料,最有特别味道,现在正是吃这菜的时候,做法是把红胡萝卜、大萝卜(红扁而辣的萝卜)擦成丝,先把胡萝卜丝入锅煎,煎出红油为止,然后用羊肉丝煸锅,放入这两种萝卜丝(胡萝卜十分之九),故汤不可太多太少,妙在拨入面鱼,洒以葱丝、香菜、椒面、生醋,味美绝伦。(二)“炒胡萝卜酱”,将胡萝卜切丁,加羊肉丁、豆嘴炒之,必须酱大,也是秋末冬初果腹的食品。(三)“大豆芽炒大腌白菜”,白菜虽在南北朝时已有,但近代已成了北京特产,江南地方以北京白菜价在鱼翅以上,白菜一物,可咸可甜,可荤可素,可以任意做菜吃。切白菜成方块,以盐微腌,加大豆芽、猪肉片炒之,最能下饭,久成北京菜中佳品了。(四)“熬白菜”,北京熬白菜分两种,一、羊肉熬加酱,味不太好;二、猪肉熬不加酱,味道深长,如再加炉肉、海米、猪肉丸子,将白菜熬成烂泥,汤肥似加乳汁,冬日得此,真可大快朵颐了。北京以前喜以“把钴子”熬白菜,真有几十年老钴子的,佐以玉色白米,又何斤斤于吃粉条鱼翅,脚鸡眼似的鱼唇呢!(五)“炒王瓜丁”,炒王瓜丁是夏日绝妙的食品,将鲜王瓜、水芥切丁,加豆嘴(或鲜豌豆、鲜毛豆均可),以猪肉炒之,有肉则加酱,素炒不加酱,食绿豆水饭、素炒王瓜丁,顿觉暑退凉生,不必仿膳社去吃窝头了。(六)“炒三香菜”,切胡萝卜、芹菜、白菜为条,用羊肉酱炒,也是深秋美食。如生食,只用盐一腌,再加上一些醋,可以代小菜吃。(七)“炒雪里红”,用腌雪里红或芥菜缨,加大豆芽,以羊肉酱炒,最能下饭。(八)“闷雷震芥头片”,北京老家庭,春必做酱,秋必腌菜,不是为省钱,实在为得味。腌菜是腌芥菜、雪里红,顺便还可以放入白菜,一冬一春的咸菜,可以无忧了。大雪初晴,日黄入户,捧着一碗热粥,醋泡芥缨加辣椒, 肚饱身暖,真是南面王不易啊!比那持着请帖赶嘴的,绝保不能风拍食的。雷震芥菜是芥菜带叶下缸,七日取出,阴八成干,揉以五香料,放入坛中,不许透气,明年雷鸣后出坛,切片加猪肉焖食, 算家常中高等菜的。水芥可以生切细丝,加花椒油、生醋,名“春菜丝”,另有一种特别滋味。水芥到初春时候,切丝加黄豆芽肉炒,吃时临时加入生葱丝,也是佐饭的佳品。我以为芥类东西,除佛手 芥外,自制总比外买的味美,现在家庭,是谈不到这点的。(九) “炒麻豆腐”,炒麻豆腐为北京特别产物,谁也不能否认的,因为炒时用羊油、羊肉,所以羊肉馆多半以此算敬菜,其实讲究一点家 庭做的,比羊肉馆还要好一些,用真四眼井做麻豆腐,以浮油、香油、肢油炒(不加肢油不算讲究),加上一点老黑酱油,加入韭菜 段、大豆芽,炒熟后,洒上羊肉焦丁,拌上一些辣椒油,自然味美 了。不过火候作料,不容易做得恰当,厨师傅有时不如女人会做, 所以就不太可口了。以外茄子、冬瓜、倭瓜、饹醮、豆腐,各种菜 蔬,做法很多,一样韭菜,有十几种做法,不能一一的说清了。 北京菜的小吃,也是很有滋味,不过北京家庭,平常不注意小菜,到年节才特别做些,预待年节食用,尤其是旧历年,因为天 气寒冷,食物不易腐坏,所以家家做菜,名为“年菜”。先谈小吃, 生食的有拌葈菜、拌王瓜干、拌海蜇皮等类。熟吃的有,一、“炒咸什锦”,把面筋、水芥、胡萝卜、豆腐干,切成极细丝,用香油、酱油炒熟,洒上香菜,最好是凉吃。二、“炒酱瓜丁”、“炒酱瓜丝”、“炒酱王瓜丁丝”,酱瓜系酱渍老菸瓜,最好的是酱甜瓜,甜瓜非夏日香瓜,为另一种小瓜,较老菸瓜短小,酱渍以后与老菸瓜同称“酱瓜”,但比老菸瓜所制之酱瓜甜嫩,非大“京酱园”没有。切丝切丁加生葱炒之,用猪里几或精致猪肉伴炒,如能用山鸡肉,就更 好了。主要条件要用香油,肉须先用滚水焯过,葱须炒熟后再加。更有一点足能增加美味,而为人少知的,即炒时加些白糖或冰糖, 自能别具一种风味,可以下粥,可以渗酒。又有“酱猪排骨”、“粉 肠”、“卤口条”、“卤肝”等,以及“酥鱼”、“酥鸡”、“鸡冻”、“鱼 冻”。讲究的家庭,多半在年关前做成。除夕家宴,元宵聚饮,拥红泥小火炉,燃百烛电灯,儿童点放爆竹,欢呼畅谈,或叙天伦乐事,或约一二契友作竟夜谈,一坛瓮头春,足洗一年心绪,又何必 侈谈闷炉挂炉、燕窝鱼翅呢?年菜小吃中最清适的,要算凉甜菜, 如“芥末墩”,又名芥末白菜,将白菜去外皮,只取内心,切成寸厚小段,用马蓝叶或钱串拴牢,放锅内煮熟,取出带汤放置盘中, 洒上高芥末面和白糖,凉食最好,但食时应加一些高醋才好。又有“糖素白菜”,系将白菜切成斜方块,佐以胡萝卜,入锅煮熟后加白糖,凉食但不必加醋。再有北京特有的“辣菜”,入冬即有担售的,系用芥菜头(千万不可用蔓菁)切片,及大萝卜切丝,煮熟后,连 汤倾入坛中,不可透气,食时加香油、生醋,虽辣味钻鼻,人皆嗜 食。新年大肉后,这三种实在是一服清凉剂啊! 年节及犒劳菜,以肉菜为主,讲究一点的,也有鸡、鱼、鸭等品,但不是家庭中习做的。第一大菜即“炖猪羊肉”,以小门姜店 好黄酒,加花椒大料炖之,以老黑酱油提色。至于炖牛肉,加五香 料及酱油红烧,皆入民国后才有(北京老家庭多不食牛肉)。次为“炖蘑菇肉”,以猪肉切成大片,加东蘑黄酱炖成。又有“炖铞子”,炖猪大肠加肝,如饭馆熘肝肠,但不勾汁。至于猪下水,近年城内才有吃的人。最美的要算“炖羊肚心肺丝汤”,即《六月雪》中羊 肚汤,以羊肚全份,羊肺、头、心、肝煮熟切丝,或加海带菜丝, 炖成后,加葱丝、香菜、麻酱、醋、椒面作料食之,实在是肉类中 逸品,不过难得肚板厚丝细罢了。 以上所举,皆北京旧家庭的菜肴,不能尽其十分之一二,北京家庭大半是主妇下厨房,这本是“主中馈”的遗意,近来中馈已转到大司务身上,女人只专任爱人的责任,真是堕落的现象。曾国藩位列三台,还督促家中腌菜,要知道俭德是由家庭养成的,是一点不错啊! (《立言画刊》1938 年第 6 期) 故乡的山梨 李辉英 一个人谁没有一个故乡呢。对于故乡的留恋,或是说一些回忆,恐怕也全是人人少不了的。 故乡使你留恋的地方太多了,一座山,一丛林,一条小溪,甚而是一些荒坟,都会给你留下清切的影子。故乡使你回忆的事物也太多了,某个乡绅怎样抽大烟,迈方步,或是团总讨小老婆的故事, 还有张家长李家短妇人家往还的言谈,以及少妇思奔,大姑娘突起大肚皮,疯狗咬了善人一些碎事,也全是叫人偶一回忆起来,就像些活动影片似的给你轮演一回。说到故乡的特产,那就更叫你关怀了,愈是久离故乡的人,愈是关心不忘故乡的特产,有时管叫你渴想得口水直流,为了思念特产得不到手的原故。 但这种特产,却并非都是名贵的东西,即以食品一类来说,肉包子也许就是特产之一,五香豆腐干也可以算是故乡的一种特产。此种食品,全在于地方风味的宝贵,而且更可以进而以某种特产物品或食品传名外方,叫别人一听到某种物品时,不自觉地就会联想起那出产物品的地方来,譬如南翔的包子、南京鸭肾、福建肉松、莱阳梨等全是。 说到梨,故乡也出产一种梨,因为不是种在人家园子里而自己生长在山上的,所以叫作山梨。这些山梨虽然并不出名,外人很少知的,在当地却是家喻户晓的了。由于这种山梨的生长,很可以推想到故乡偏僻落后的社会情形来,若在繁华的省份,人烟稠密的地方,那是无论如何不会让这些山梨自由生长的,大概不等结到七成熟时,早被别人打光了,留待成熟后再摘下来吃的事情,怕是不会有的。 说起故乡的山梨,并不像一般梨子那样甜蜜可口,皮嫩如膏, 反之,它倒是一身酸味,皮厚得像一层老布。你们也许很以为怪了, 这样的山梨,有什么值得不忘的呢。不,我觉得故乡的山梨特别叫我不忘的地方,就是它的酸和粗厚的皮!因为它是和一般梨子迥乎不同的。如果让植物学家来解释的话,山梨的酸味和粗厚的外皮, 正可以说是为保护自己的身体安全才长着的,因为山丛之中,杂虫甚多,如果它生得又嫩又甜,怕不待成熟早让虫子们蛆光了。果然, 山梨里面很少有生虫子的。 山梨的外皮虽然粗糙异常,但它的内中肉瓤却又嫩又甜,比起本地生梨和天津雅梨要细致多,而且又富有水分,剥了皮,一口就全吃净吮干了。 山梨的酸味是特别值人不忘的,正像你吃了它的酸味后一样, 口中久久不散,而留在你的记忆里的酸味尤其是难得的。普通一般人对于甜的感觉得之容易,忘之更快,不比酸的味道,虽不能使人愉快,却足可叫人轻易忘记不掉。在事务方面,我觉得也是这样, 得意的事情容易忘记,酸辛的事情倒是时常留在头脑之中不能忘去。 我爱故乡的山梨,特别爱吃它的酸味,因为我每每从它的酸味中,来比拟自身寒酸的境遇;是的,我的生活永远是在酸味中过着的,我没有过一日属于甜味的生活!也许,我此后的日子还是要在酸味中过着的呢。所以,对于故乡的山梨,就因此更给我不能忘记的深深的印象了。 故乡的山梨又是上市的时候了,村妇们定又一群一群的提着筐,肩着担子,还有背着口袋的,到人家里去作交易。她们不要钱,只是换些得用的东西,像棉花、布头、绒线一类的物品。这种交易,倒很和上古时代“日中为市”的“以己之有,易己之无”的情形有些相像,不同的就是没有固定的交易时间罢了。我爱故乡的山梨,但我更忘不掉比山梨还要酸上万倍的故乡人们诉苦无处的非人生活。 (《再生集》,李辉英著,上海新钟书局 1936 年 5 月初版) 苏味道 范烟桥 唐伯虎的《姑苏杂咏》,有句云“小巷十家三酒店”,见得苏州人喜吃酒的多,但是他写的明末的苏州,或许诗人习尚惯于夸张。现在却并不如此,只有几条大街,酒店确是不少。 酒店和菜馆不同,酒店只卖酒,不卖菜,至多备些小碟子,大概是素的如发芽豆之类,其他是应时节的,春天有马兰头、拌笋, 夏天有黄瓜,秋天有毛豆、雪里红,冬天有辣白菜。至于荤的,由小贩挽着篮来供给的。到酒店吃酒的,都是内家,要辨别酒的好坏, 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最经济的,吃“戤柜台”酒,没有座位, 立在柜台的外面,讲讲山海经,说说笑话,看看野景,也可以下酒, 和俄罗斯的“吧”有相似的作风。所不同的苏州是静的,他们是动的,所以吃柜台酒的决不会打起来的。 相传有一个吃“板酒”的,从来没有买过小菜,他见有小贩过来,伸手去拣食品,这样不好,那样不好,始终没有成交,可是手指上已染了许多油脂,他就用嘴吮着,吃完了他的“例酒”。虽然是讥讽,可是他们俭约的习惯,确乎可惊。酒不可不吃,却不肯多费钱,总是用最经济的方法,去尽他们一夕之兴的。 在小巷里,固然也有酒店,每天的座上客,都是经常的主顾, 而且坐的地方,也不会更换的,时间更有一定,今天某人不到,大家要牵记了,不是家里有事,便是本人有病,或者出门去了。倘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全体向他注目,所以各走各店,决不变动。那些酒店里的酒,不是十分高贵的,因为酒人以普通阶级的多。有的家里饭米都没有,他还是要来吃酒的,不过吃起来有限度的,至多一斤,少则八两,还有所谓“免四”,是出十二两的酒钱,吃一斤的酒。当然未尽其量,不过杖头钱不多,适可而止,只杀一杀酒瘾, 就心安理得了。 (《国光》1946年第1期,署名含凉) 碗底有沧桑 张恨水 “上夫子庙吃茶”(读作错平声),这是南京人趣味之一。谈起真正的吃茶趣味,要早,真要夫子庙畔,还要指定是奇芳阁、六朝居这四五家茶楼。你若是个要睡早觉的人,被朋友们拉上夫子庙去吃回茶,你真会感到得不偿失。可是有人去惯了,每早不去吃二三十分钟茶,这一天也不会舒服,这就是我上篇《风檐尝烤肉》的话,这就是趣味吗! 这里单说奇芳阁吧,那是我常去的地方,我也只有这里最熟。这一家茶楼,面对了秦淮河(不管秦淮碧或黑,反正字面是美的),隔壁是夫子庙前广场,是个热闹中心点。无论你去得多么早,这茶楼上下,已是声哄哄,高朋满座。我大概到的时候,是八点钟前, 七点钟后,那一二班吃茶的人,已经过瘾走了。这里面有公务员与商人,并未因此而误他的工作,这是南京人吃茶的可取点。我去时当然不止一个人踏着那涂满了“脚底下泥”的大板梯,上那片敞楼。在桌子缝里转个弯,奔上西角楼的突出处,面对楼下的夫子庙坐下, 始而因朋友关系,无所谓来这里,去过三次,就硬是非这里不坐。四方一张桌子,漆是剥落了,甚至中间还有一条缝呢。桌子有的是茶碗碟子、瓜子壳、花生皮、烟卷头、茶叶渣,那没关系,过来一位茶博士,风卷残云,把这些东西搬了走,肩上抽下一条抹布,立刻将桌面扫荡干净。他左手抱了一叠茶碗,还连盖带茶托,右手提了把大锡壶来。碗分散在各人前,开水冲下碗去,一阵热气,送进一阵茶香,立刻将碗盖上,这是趣味的开始。桌子周围有的是长板凳、方几子,随便拖了来坐,就是很少靠背椅,躺椅是绝对没有。这是老板整你,让你不能太舒服而忘返了。你若是个老主顾,茶博士把你每天所喝的那把壶送过来,另找一个杯子,这壶完全是你所有。不论是素的,彩花的,瓜式的,马蹄式的,甚至缺了口用铜包着的,绝对不卖给第二人。随着是瓜子盐花生,糖果纸烟篮,水果篮,有人纷纷地提着来揽生意,卖酱牛肉的,背着玻璃格子,还带了精致的小菜刀与小砧板,“来六个铜板的”,座上有人说。他把小砧板放在桌上,和你切了若干片,用纸片托着,撒上些花椒盐。此外,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报贩子,自会送来几份报。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眼镜贩或带子贩、钢笔贩,他们冷眼地擦身过去,于是桌上放满了花生、瓜子、纸烟等类了,这是趣味的继续。这里有点心牛肉锅贴、菜包子、各种汤面,茶博士一批批送来,然而说起价钱, 你会不相信,每大碗面,七分而已,还有小干丝,只五分钱。熟的茶房,肯跑一趟路,替你买两角钱的烧鸭,用小锅再煮一煮。这是什么天堂生活! 我不能再写了,多写只是添我伤感。我们每次可以在这里会到所要会的朋友,并可以在这里商决许多事业问题,所耗费的时间是半小时上下,金钱一元上下,这比万元请客一次,其情况怎样呢? 在后方遇到南京朋友,也会拉上小茶馆吃那毫无陪衬的沱茶,可是一谈起夫子庙,看着茶碗,大家就黯然了。 听说奇芳阁烧掉之后,又重建了。老朋友说:“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就在那里会面吧!”“好的!”可是分散日子太久,有些老朋友已经永远不能见面了。 (重庆《新民报》1945 年 11 月 14 日) 1. 一部民国版“舌尖上的中国”,饮食、文学、历史调和成的盛宴。 2. 至今可用寻访各地美食的宝典,资料性、趣味性兼备。 3. 饮食文化的精品之作,从饮食透视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元与历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