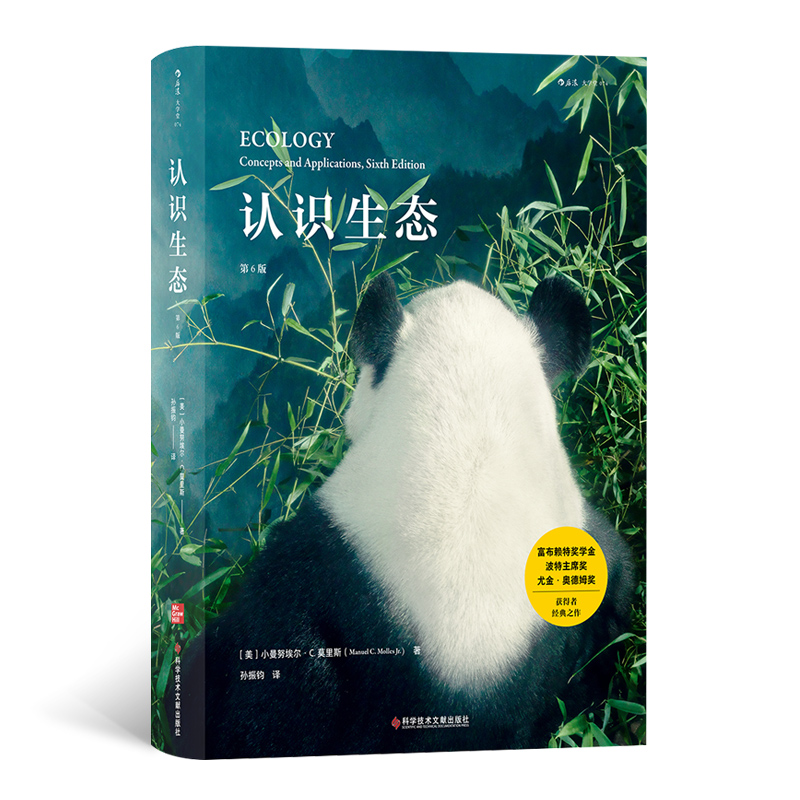
出版社: 科技文献
原售价: 268.00
折扣价: 168.90
折扣购买: 认识生态(第6版)(精)
ISBN: 97875189554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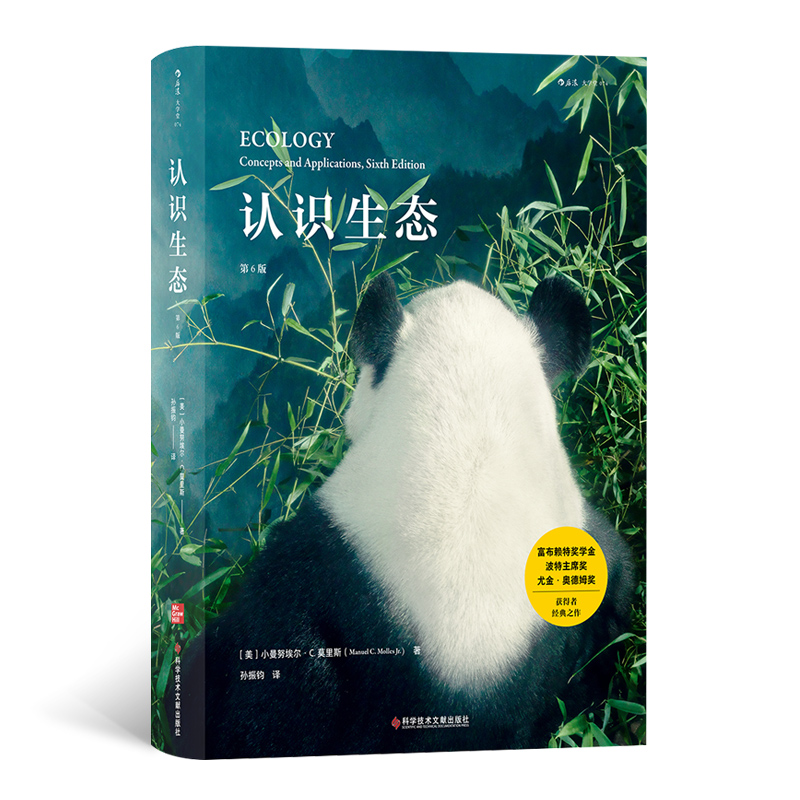
小曼努埃尔·C. 莫里斯(Manuel C. Molles Jr.)是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生物学名誉教授。自1975年以来,他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书并担任西南生物博物馆的馆长,一直从事有关生态学的写作与研究。他在洪堡州立大学获得科学学士学位,并于亚利桑那大学生态与演化生物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为了扩大地理视角,他曾在拉丁美洲、欧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教学,进行生态研究,并持富布赖特研究奖学金赴葡萄牙进行河流生态研究。他还曾在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动物学系、西班牙马德里理工大学水文实验室和蒙大拿大学弗拉特黑德湖生物实验站担任客座教授。1995—1996年,小曼努埃尔·C. 莫里斯博士荣获新墨西哥大学“**教师”称号;2000年,获得植物生态学的波特**奖;2014年,获得美国生态学会授予的尤金·奥德姆奖。 译者简介 孙振钧,现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生态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研究员、客座教授;美国生态学会会员;**生态工程学会会员;欧洲环境毒理与化学学会会员;美国《应用土壤生态学》编委。
**章 何谓生态学?生态学(ecology)可以定义为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以来,就开始学习生态学了。人类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善于观察环境的变化以及预测生物对环境变化的响应。*早的猎人与采集者必须熟知兽类的习性,也必须清楚食物的分布地点及植物可采收的时期;后来的农民与牧民必须知道气候与土壤的变化,以及这两者如何影响农作物与家畜。 时至**,地球上的人类大部分居住于城市中,很少直接接触自然。然而,与过去相比,人类这个物种的未来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好地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必须学习这些关系,因为人类正在快速地改变地球的环境,却不**知道这些改变会造成何种后果。例如,人类活动已经增加了生物圈内的氮循环量,改变了**的土地覆盖,并增加了大气二氧化碳(CO2)的浓度。这类改变已经威胁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也将人类的生命维持系统置于危脸之中。由于21世纪初环境变化的步伐在加快,我们必须继续积极学习生态学。 在简单的定义背后,生态学实际是一个涉及面很宽的科学领域。生态学家研究生物个体、森林或湖泊,甚至整个地球。他们测量的项目包括生物个体的数量、繁殖率,或光合作用与分解作用等生态过程的速率。生态学家研究环境的非生物部分(温度和土壤化学)的时间与研究生物的时间一样长。同时,在某些生态研究中,生物的“环境”可能是指另一种物种。你可能认为生态学家都在野外做研究,然而实际上许多重要生态学概念的发展都来自生态学家建立的理论模型或实验室的研究。很明显,生态学的简单定义并不能涵盖该科学领域的范围或各种各样的专业研究者。为了对生态学有*好的了解,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生态学的范畴。 1.1 生态学概览 生态学家研究环境中的各种关系,从个体之间的关系到影响整个生物圈过程的因素。在如此广泛的内涵下,本书将生态组织的层次分成各个不同的等级,图1.1就显示了生态学组织的不同等级。 历**,个体生态学位于图1.1的*底层,是生理生态学和行为生态学的主要研究范畴。生理生态学总是强调解决生物因环境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引起的生理与结构的演化(evolution,种群随时间变化的过程),而行为生态学则着重于动物应对环境变化的生存行为和繁殖行为的演化。生理生态学与行为生态学这两个领域都以演化理论为指导。 个体生态学与种群生态学密切相关,在演化过程中*是如此。种群生态学的研究重点是影响种群结构与生态过程的各种因素,种群是某物种栖息于特定区域内的全部个体的集合。种群生态学研究的生态过程包括物种的适应、灭*、分布与多度、增长与调节,以及物种繁殖生态的各种变化。种群生态学家尤其感兴趣生态过程如何*环境中的非生物组成与生物组成影响。 谈到环境的生物组成时,我们看图1.1中的第三个组织层次,即捕食、寄生与竞争等交互作用生态学。研究物种间交互作用的生态学家往往强调交互作用对物种的演化影响,以及交互作用对种群结构或生态群落特征的影响。 生态群落(ecological community)是指交互作用的物种的集合,这些物种将群落生态学与交互作用生态学联系在一起。群落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之间的相同之处甚多,均涉及控制多物种系统的因素,但两者的研究目的略有差别,群落生态学的研究焦点为栖息于某区域的生物,而生态系统生态学不但研究影响群落的所有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还侧重研究能量流动和分解等生态过程。 为了研究便利,生态学长久以来均尝试确定和研究独立的群落与生态系统,然而地球上 图1.1 生态组织的不同层次及生态学家对各层次提出的问题举例,这些生态层次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详述 所有的群落与生态系统均是开放式的系统,每个群落与生态系统内的物质、能量及生物均会与其他群落和生态系统发生交换。这类(尤其是生态系统之间)交换是景观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但所有的景观并非独立的系统,而是构成地理区域(geographical region)的一部分,进行着大规模、长期的区域性生态过程。区域性过程(regional process)是地理生态学(geographic ecology)的课题,而地理生态学引导我们了解空间尺度*大、层次*高的生态组织—生物圈(biosphere)。生物圈是地球的一部分,孕育着地球生命,包括陆域、水域和大气层的生命。 上述这些有关生态学的描述是对本书内容的简要说明,是本书的粗略框架和高度总结。要**图1.1的摘要,我们要将它们与创建生态学的科学家的工作联系起来。为此,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生态学家的研究,他们在研究内涵广泛的生态学各层次的工作中,强调历史基础和某些发展前沿之间的联系(图1.2)。 图1.2 生态学中两个快速发展的前沿 (a)大气生态学(aeroecology):研究地球-大气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新的研究工具促进了这个生态学前沿的出现。例如,靛蓝梅林热成像摄像机可拍摄飞行中的巴西犬吻蝠(Tadarida brasiliensis)的热红外图像,描绘蝙蝠的体表温度变化。热红外技术不仅能够检测和记录到自由觅食的夜行生物的存在,也可以无创的方式观测生物的生理学和生态学特征(第5章)。 (b)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把城市作为复杂的、变化的生态学系统进行研究。城市*到紧密相关的生物、物理和社会组成的影响。随着生态学家研究大部分人类居住的环境(如巴尔的摩市),他们获得了有关城市生态学的意外发现(**9章,457页)。 概念讨论1.1 1. 生态学组织的层次划分和生态学家的研究如何影响生态学家提出的问题? 2. 当生态学家研究图1.1的某一生态学组织层次时,其他生态学层次是否与之有关系?例如,当生态学家研究限制斑马种群数量的因素时,是否要思考斑马种群与其他物种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或食物对个体生存的影响? 1.2 生态学研究实例 生态学家根据他们研究的问题、时空尺度和可用的研究工具设计研究。由于生态学学科**宽广,生态学研究与所有的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相关。下面,我们介绍一个关于生态学问题和研究方法的简单例子。 森林鸟类生态学:老法与新法 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凝视着他的双筒望远镜,他正在观察一种名叫林莺的小鸟,它们正在云杉顶部寻找昆虫。在一般赏鸟者的眼中,麦克阿瑟似乎只是一个**赏鸟人。当然,他确实在集中精神观察那群鸟,只不过他感兴趣的是验证生态学理论罢了。 1955年,麦克阿瑟研究共栖在北美洲北部云杉林中的5种林莺—栗颊林莺(Dendroica tigrina)、黄腰白喉林莺(D. coronata)、黑喉绿林莺(D. virens)、橙胸林莺(D. fusca)及栗胸林莺(D. castanea)。它们是体形大小与外形长相都**相近且皆以昆虫为食的鸟类。理论上,凡是生态需求相同的物种必会相互竞争,以至于它们*终不能生活在同一环境中。因此,麦克阿瑟想要知道这些生态需求相近的林莺如何共存于同一座森林中。 这些林莺主要觅食树皮与树叶上的昆虫。麦克阿瑟推测,如果每种林莺觅食树林内不同区域的昆虫,就不会发生竞争,便可在同一座森林共存。为了绘制各林莺群的觅食范围,他将树林划分成不同的垂直区域与水平区域,然后仔细地记录各种林莺在各区域的觅食时间。 事实证明,麦克阿瑟的推测正确无误。他的观察显示,这5种林莺在云杉林的不同区域觅食。如图1.3所示,栗颊林莺的觅食区主要是树顶的新生针叶区与嫩芽区;橙胸林莺与栗颊林莺的觅食范围虽然有相当大的重叠,但前者的范围延伸到树林*靠下的区域;黑喉绿林莺的觅食区是树林的中上部;栗胸林莺则*集中于树林的中部;*后,黄腰白喉林莺则主要在地面及树的下部觅食。麦克阿瑟的观察表明这些林莺虽然栖息于相同的森林,但它们觅食的区域却是森林内的不同区域。他的结论为:这种觅食行为是林莺在云杉林内竞争较少的原因。 麦克阿瑟(MacArthur,1958)的林莺觅食行为研究的确是生态学研究**的经典案例。但是和大部分研究一样,它引发的问题与解答的疑问一样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于:科学不但可以直接告诉我们自然的奥妙,而且可以激发其他研究,从而增进我们对科学的了解。麦克阿瑟的研究激发了无数关于生物群体(包括林莺)间竞争现象的研究。其中,一些研究验证了麦克阿瑟的实验结果,一些研究产生不同的结果。但无论如何,这些研究增进了人们对物种间的竞争及林莺生态学的了解。 在罗伯特·麦克阿瑟利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林莺觅食生态学的半个世纪之后,阮·农里斯(Norris et al.,2005)率领一个由加拿大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小组,开发了一种新工具。它能够观测远距离迁徙鸟类的广阔觅食栖息地。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林莺科的另一成员—橙尾鸲莺(Setophoga ruticilla)。橙尾鸲莺和麦克阿瑟研究的鸟相似,是一种远距离迁徙鸟类,在温带的北美洲筑巢繁殖,在热带的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和加勒比海岛度过冬天。 历**,对橙尾鸲莺这种远距离迁徙鸟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它们的温带繁殖地。但已有证据表明,这种迁徙鸟类个体的繁殖成功取决于它们的热带越冬栖息地的环境条件。例如,早到达繁殖地的雄鸟通常比晚到的雄鸟具有较好的身体条件,能够*好地构筑繁殖区,所以它们的繁殖成功率也比较高。 鸟类到达时间和身体状况的变化促使生态学家思考越冬栖息地和鸟类在繁殖栖息地的繁殖成功率之间的联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大量信息,包括鸟类个体的越冬栖息地在哪里、在迁徙过程中越冬栖息地环境如何影响林莺身体状况、越冬栖息地如何影响鸟类到达繁殖地的时间。但鸟类的越冬栖息地和繁殖栖息地之间相距几千千米(图1.4),这超过了一个人或一个大研究团队通过双筒望远镜观察到的范围。 随着研究问题越来越复杂,生态学家逐渐开发了一些*强大的研究工具。生态学家研究迁徙鸟类的工具是稳定同位素分析(sta**e isotope analysis,第6章,150页)。化学元素的同位素因中子数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原子质量。例如,碳有3个不同的同位素(按原子质量由小到大顺序排列):12C、13C、14C。其中,12C和13C是稳定同位素,因为它们不发生放射性衰变,而14C易发生放射性衰变,因此是不稳定的。稳定同位素已被证明是生态学中**有用的研究工具。例如,稳定同位素可以确定食物来源,因为不同环境中各种同位素的比例是不同的。 稳定同位素分析为生态学家提供了一个新的“镜头”,使他们能够揭示存在但看不见的生态关系。例如,生态学家可以利用稳定性同位素分析追踪橙尾鸲莺的越冬栖息地。在牙买加,年长的雄橙尾鸲莺和雌橙尾鸲莺一起在生产力较高的红树林栖息地过冬,它们经常迫使大多数雌鸟和年轻雄鸟到较差的矮树丛中过冬。这两种环境中的优势植物和昆虫含有不同比例的碳同位素12C和13C。因此,在红树林(低13C)越冬的鸟类和在矮树丛(高13C)越冬的鸟类的化学组成被标上了有效标签。当它们到达温带繁殖地,生态学家就可以通过分析橙尾鸲莺的极少量血液标本,知道它们在哪里过冬。阮·农里斯和他的研究小组做了这些测试之后,发现在高产红树林中越冬的雄橙尾鸲莺通常较早到达繁殖地,而且它们可以繁殖*多可存活到羽毛丰满阶段的幼鸟。 图1.4 橙尾鸲莺的繁殖栖息地与越冬栖息地 稳定同位素分析以及它在生物多样性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将贯穿这本书。新方法创造了新的研究前沿,这在科学上**普遍,另外一个前沿出现在森林树冠层的研究中。 森林树冠层研究:一个物理科学前沿 关于林莺的研究揭示了生态学家研究一个或几个物种的方法,而其他生态学家关注的是森林、湖泊和*地的生态学,并视它们为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指的是一个区域的全部生物以及这些生物交互作用的物理环境。许多有关生态系统的研究侧重于养分(nutrient),即一个生物为了生存而必须从环境中获得的原始物质。 对生态学家而言,研究养分(如氮、磷或钙等)收支时,**步便是查清这些养分在生态系统内的分布。纳里尼·纳德卡尔尼的研究改变了我们对热带及温带雨林的结构与运转的看法(Nadkarni,l981,1984a,1984b)。纳德卡尔尼利用登山设备攀爬至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n)雨林的树冠层,成为**少数(包括她)开发该领域的先驱者。她站在雨林的地面上,想知道头顶上的树冠层隐藏的生命多样性及生态关系。她的好奇心在不久之后变成了决心。她不但登上树冠层,而且成为**位探究这个陌生世界的生态学家。 由于遭到暴雨的淋溶作用(leaching),许多雨林土壤的养分(如氮、磷)含量都很低。这么多雨林的土壤养分有效性都如此之低,生态学家不禁提出疑问:贫瘠的土壤如何维系雨林内惊人的生命?事实上,的确有许多因素共同维系雨林生物的密切活动。纳德卡尔尼的树冠层研究揭示了其中的一个因素,即雨林树冠层能储备大量养分。 雨林树冠层的养分储存与树冠层上的附生植物(epiphyte)有关。附生植物(如许多兰科植物与蕨类植物)是指附生在其他植物上的植物。它们不依靠附生植物的养分为生,因此它们并非寄生生物。 附生植物附生在枝干上时,开始囤积有机物,*后形成一层厚达30 cm的厚垫。该厚垫形成了另一个复杂的结构,可维系多种动植物群落。 附生植物厚垫含有大量养分。纳德卡尔尼发现,一些热带雨林中的养分只是树冠层枝叶养分含量的一半。在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克半岛(Olympic Peninsula)的温带雨林中,附生植物的养分含量是其附生的树木枝叶量的4倍。 纳德卡尔尼的研究显示,在温带雨林与热带雨林中,乔木的枝干在高处长出根群,深入附生植物的厚垫中吸取养分。基于这个研究结果,若要了解雨林的养分经济学,生态学家必须冒险到达树顶。 由于使雨林树冠层研究*为便捷的设备不断*新,现在此类研究并非只有敢于冒险或身手敏捷的人才能开展了。抵达树冠层的新式设备有热气球、空中缆车、大型起重机等。在美国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谷(Columbia River Gorge)附近的2.3 hm2针叶林中,科学家利用风河树冠层吊车(Wind River Canopy Crane)抵达70 m高的森林顶部(图1.5)。这种吊车设备大大推进了科学家的研究,包括树冠层的候鸟生态学、附生植物在树冠层不同高度的光合作用、蝙蝠和甲虫的栖境的垂直分层现象(Ozanne et al.,2003)。截至2006年,**共有12 辆树冠层吊车装置在温带森林和热带森林工作(Stork,2007)。纳德卡尔尼指出,由于这些设备的发展,人们可以接触到树冠层这一新物理领域,但对这一***领域的探索却刚刚开始,尤其是当我们试图预测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结果时。 图1.5 风河树冠层吊车提供了到达树冠层的方法,拓宽了生态学和生态学研究的范围 气候与生态变化:过去与将来 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总是在变化中,但是许多变化的形成时间**长,或发生的空间尺度**大,所以要研究它们**困难。在有关湖底沉泥中的植物划分和生物演化的研究中,有两种方法增进了我们对长期过程和大尺度过程的了解。 玛格丽特·戴维斯(D**is,1983,19**)仔细地钻研了湖泊沉积样品中的花粉。该沉积样品来自阿帕拉契山脉(Appalachian Mountains)的一个湖泊。通过研究其中的花粉,她可以了解过去数千年来湖泊附近的植物的变迁。戴维斯是一位古生态学家,专门研究大空间与长时间的生态过程。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她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第四纪植物的分布,尤其是*近2万年发生的变化。 湖泊附近植物的花粉有些落入湖中,然后下沉,并埋入湖底沉泥内。数百年之后,湖泊沉积层形成,花粉被保存下来,成为湖旁植物种类的历史记录。当湖旁的植被发生变迁时,湖底沉泥内的花粉亦随之变化。在图1.6的例子中,*早出现的是云杉(Picea spp.)的花粉,埋在距今12,000年前的湖泥内;美洲山毛榉(Fagus grandifolia)的花粉在8,000年前开始出现;栗树(chestnut)花粉约在2,000年前才出现。这3种树木的花粉一直出现在湖泥中,直到1920年,湖旁的大部分栗树因栗黄枯病(chestnut **ight)死亡。因此,保存在湖泊沉积中的各类花粉可用来重建该地区的植被史。玛格丽特·B. 戴维斯、路斯·G. 邵和朱莉·R. 爱特森讨论了大量植物在气候变化中演化和分布的证据(D**is and Shaw,2001;D**is,Shaw and Etterson,2005)。随着气候变化,植物种群的地理分布发生变化,经历了适应(adaptation)演化过程,这增强了它们在新气候区的生存能力,同时表明气候变化的演化证据开始在各种动物群的研究中积累。威廉姆·布拉德肖和克里斯蒂娜·豪尔扎普费尔(Bradshaw and Holzapfei,2006)总结了几个记录北方动物演化变化的研究。这些动物包括从小型哺乳动物、鸟类到昆虫(图1.7)。面对**变暖(第23章,546页),它们的生长季变长了。戴维斯和她的同事们进行的这类研究对于预测和理解**气候变化的生态反应**重要。 本章提出了生态学的框架,具体内容将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介绍。这个简单的框架仅仅提示了生态学研究的概念基础。在本书中,我们将强调生态学的基本概念,每一章都会集中讨论几个生态学概念,我们还将拓展一些与概念相关的应用实例。当然,生态学家用到的*重要概念工具是科学方法,这将在第9页介绍。 在**篇“自然史与演化”中,我们继续探索生态学。自然史(natural history)是生态学家建立当代生态学的基础,而演化提供了概念框架。本书基于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自然史和演化促进了我们对生态关系的了解。 1.揭示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规律,掌握不可不知的生态常识。以深入浅出、循序渐进的科学论述风格总结每个自然事件背后隐藏的自然规律,有助于增进读者对生态、自然的理解,掌握在实际生态建设、环境治理及环境保护中应该遵循的法则。 2.再现经典研究案例,追踪学科前沿进展与热点探讨。通过引入大量具体案例,如怎样恢复河流的勃勃生机、细菌怎样解决环境问题、城市化对物种多样性有何影响,紧扣时下人们关注的热门生态问题和生态学科前沿发展,让读者切实掌握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和理论,并学会以辩证思维思考现实问题。 3.生态学的经典标杆之作。本书凝聚了作者20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引用了海量数据和文献,将生态学的各个分支整合在一起,全面涵盖了当代生态学的内容,形成系统的综合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