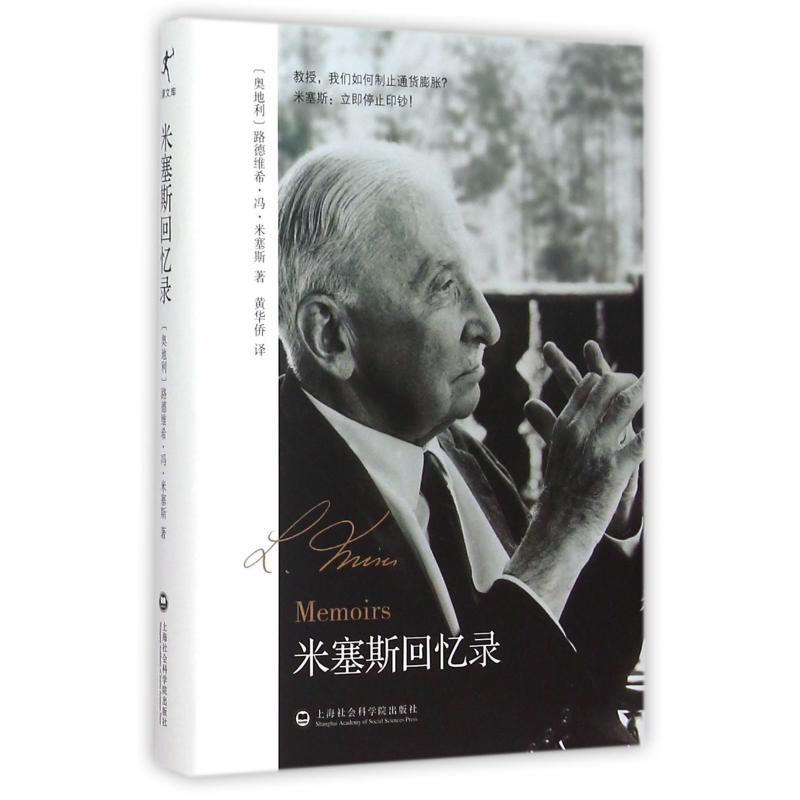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社科院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3.94
折扣购买: 米塞斯回忆录(精)
ISBN: 9787552008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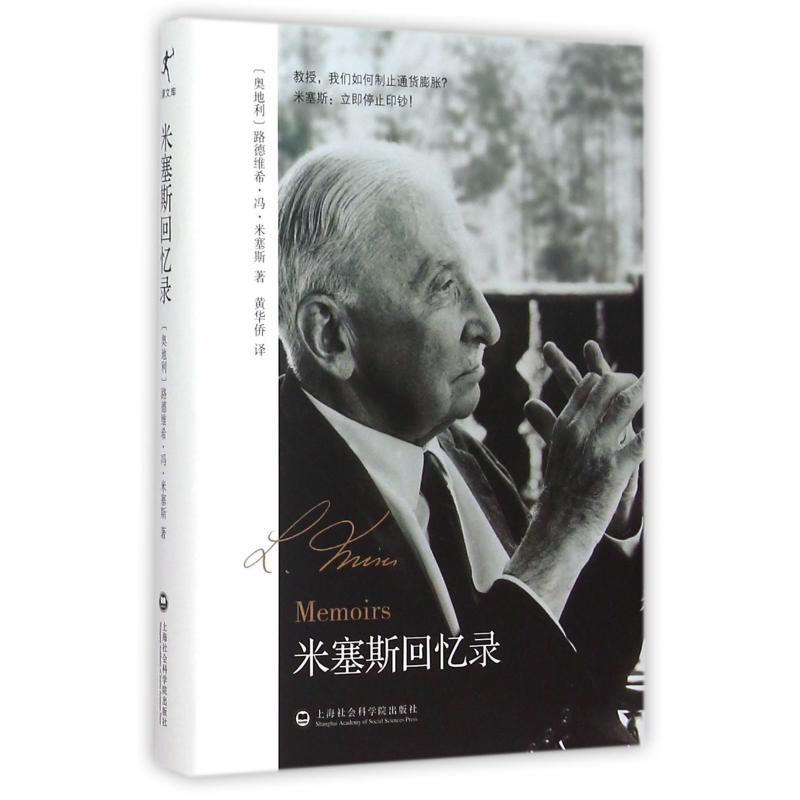
黄华侨,1978年出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现为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学术助理,长期从事艺术理论和米塞斯思想研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大师,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的领导人之一,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代表者,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其思想对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穆瑞罗斯巴德等学者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对美国自由主义运动具有深远的影响。2000年他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
这个学派的相对主义同样引起我的反感,在许多 忠实信徒的推波助澜之下,这种相对主义已经堕落成 了对过去和过去体制的盲目崇拜。一些进步迷们 (fanatics for progress)曾经断定所有古老事物都 是糟糕和恶劣的,而这些伪历史学家 (pseudohistorians)则缅怀过去,排斥一切新生的 事物。那时我还没有领会自由主义的真意,但是在我 看来,虽然自由主义思想付诸实践并不早于18世纪, 这一事实本身却不构成反对它的充分理由。我无法理 解人们怎么可以依靠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为暴政、迷 信和不容异说提供辩护。维护从前的性道德并当作今 天的模范,我认为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历史扭曲。不过 ,最极端的过激行为发生在教会史和宗教史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不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在力图 压制一切他们发觉不合自己心意的事物。 奥地利的法律史家的著述是真诚的。至少在这一 点上,他们截然不同于普鲁士历史学家的著作表现出 来的偏见。西格蒙德·阿德勒教授在他关于奥地利历 史的五小时课程中——这是所有第一学期的法律学生 必修的课——讨论了创始人鲁道夫公爵(Duke Rudolf the Founder)伪造大许可状的历史,他全面透彻地分 析这一问题,可以经得起最严厉的批评。直到数十年 后,恩斯特·卡尔·温特才鼓起勇气试图为这一章奥 地利历史辩解,他的办法是给这位已故公爵贴上社会 主义的标签,其社会主义成分甚至超过了德国社会主 义者的偶像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皇帝(Kaiser Friedrich Wilhelm I)。 从前土地曾被视为共有财产,这是一个事实,令 我不解的是,我们怎么可以从这个事实推出反对私有 财产的论证;我也不懂,为何仅仅因为过去某个时候 存在男女乱交的现象,就应该废除一夫一妻和家庭制 度。在这些论辩中,我所见的全是一派胡言。 同样,我也无法理解相反的观点——持有这些观 点的常常是同一批人。根据这种观点,随着时间推移 而产生的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一个进步,都是一个更高 的发展阶段,因而,这种发展在道义上是合理的。 真正深思好问的历史主义者秉持一种真诚的相对 主义,与这个学派错误的相对主义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不过理论上说,它的基础也并不更加牢靠。按照它 的信条,合适的政策与不合时宜的政策之间没有什么 区别。它所处理的是一个给定的事实的领域,因此, 贤明的历史主义者所要做的不是评判,而是观察和接 受,就像自然科学家之讨论自然现象那样。 为了表明这种观点的谬误,我们无需花费太多笔 墨,虽然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在许多经济学家中间 引起争论。价值判断不是科学的职责和任务。不过, 告诉我们某些手段是否适于达到特定的目的,却是科 学的两个任务之一,在有些人看来,甚至是科学的唯 一任务。自然科学不作价值判断,但会告诉人们,为 了达到特定的目的,哪些手段对他来说是有效的。人 类行为科学的责任则在于审查这些为了达到行为的目 的而采纳的手段和方法是否恰当,而不是判断行为的 终极目的本身。 我经常和卢多·哈特曼讨论这些问题,后来的一 些年里,也曾和马克斯·韦伯,以及阿尔弗雷德·弗 朗西丝·普里布拉姆进行交流。可是他们三人完全沉 湎于历史主义之中,因此很难认清我的中肯的立场。 在哈特曼和韦伯身上,热烈的性情最终战胜了哲学上 的焦虑,促使他们投入到了政治活动的领域。普里布 拉姆缺乏这种付诸行动的欲望,因此仍然坚守着他的 清静无为和不可知论。歌德关于斯芬克斯曾经说过的 那番话,可以用在他的身上: Sitzen vor den Pvramiden Zu der Volker Hochgericht,Ubershwemmungen,Krieg and Frieden Und verziehen kein Gesicht 至于小德意志的历史主义者,我厌恶他们在权力 问题上的粗暴的唯物主义立场。在他们眼里,权力意 味着刺刀和大炮,而权术政治(Realpolitik)必然要 以军国主义为前提。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幻想、理想主 义和乌托邦主义。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休谟的至理名言 ——民意是统治的基础。 在这方面,他们的主要论敌海因里希·弗里德永 和他们想法一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数月, 他告诉我: 我听到人们议论俄罗斯民众的情绪,议论那些煽 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潮。我不太明白我们为什 么要关心这些。这些说法让人如坠云里雾里。相反, 决定性的因素是那些身居要职的政治家们的意志和他 们敲定的计划。 这和约翰·朔贝尔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一 名下级巡警,后来成为奥地利总理。1915年年末,他 向他的上级报告说,他不相信俄罗斯的局势会导致一 场革命。 “谁会领导这场革命?当然不会是托洛茨 基先生,他只会坐在中央咖啡馆(Cafe Central)里看 报纸。” 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