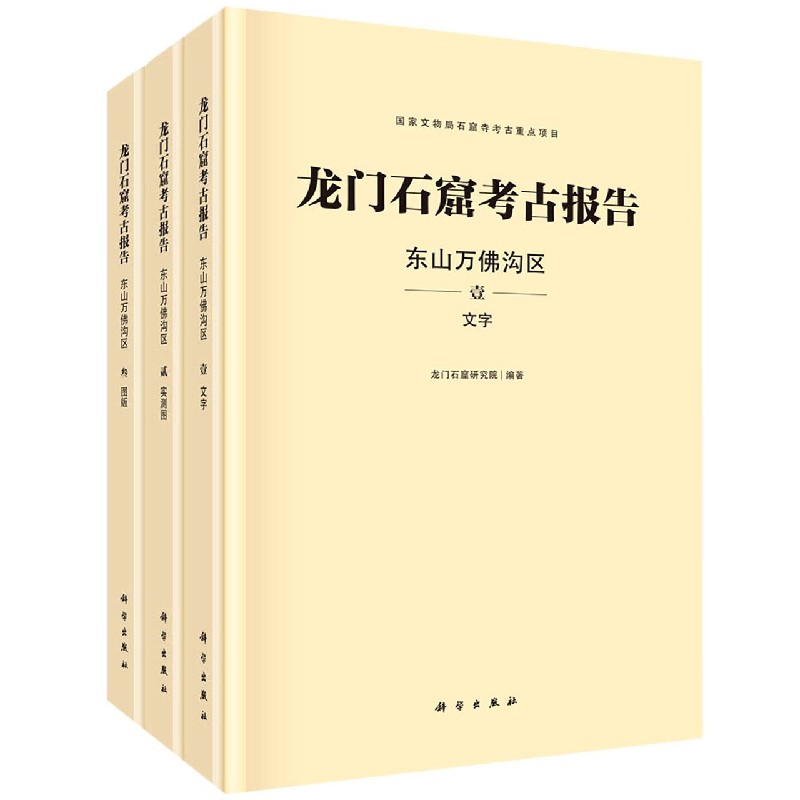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2580.00
折扣价: 2038.20
折扣购买: 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万佛沟区共3册)(精)
ISBN: 97870306940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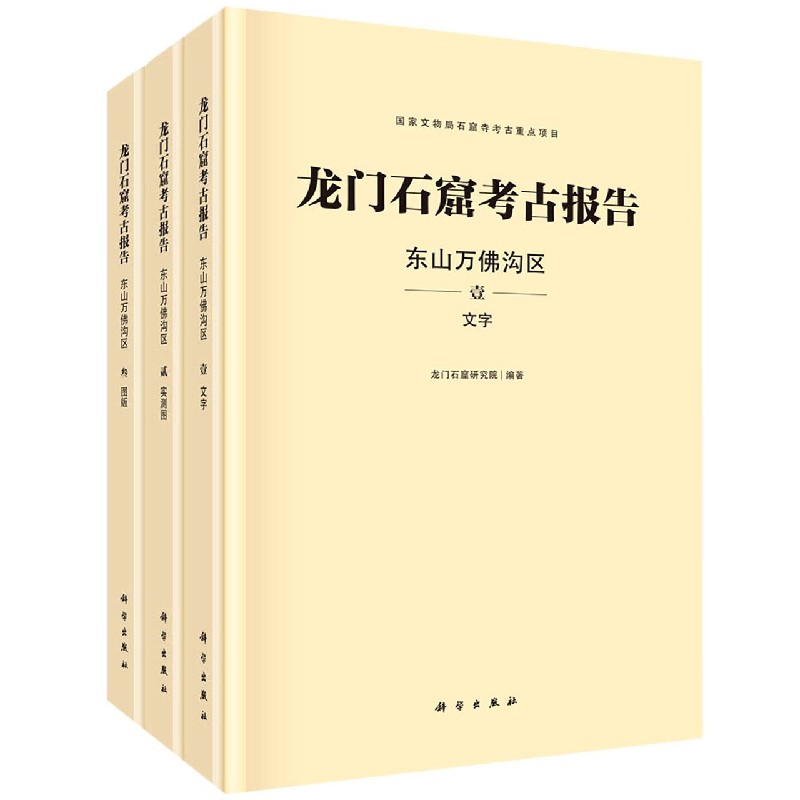
绪言
龙门东山南段形成三条横对伊河河谷的大型冲沟,自南向北依次为一道桥沟、万佛沟和老君坝沟,东山的石窟寺遗存大多分布在三沟之间,尤以居中的万佛沟内及沟口外南北两侧临河崖壁最为集中,大致呈以万佛沟为中心的南北对称分布格局。三沟之中,南部的一道桥沟和北部的老君坝沟内仅有零星的窟龛造像;居中的万佛沟内则窟龛造像遗存分布集中、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因万佛沟内窟龛造像相对集中,较附近其他区域相对独立,且在东山窟龛造像分布格局中位置特殊,故将这一区域石窟群划为“万佛沟区”单独编制考古报告,其南侧紧邻者即为龙门石窟首卷考古报告的工作对象“擂鼓台区”。万佛沟区的窟龛造像是龙门唐代佛教石窟寺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报告即为调查整理相关资料的成果(图1;图版1、图版2)。
图1 万佛沟区在龙门石窟的位置卫星图
第一节 万佛沟区概况
万佛沟区所在,包括民间通称的万佛沟沟口、万佛沟沟底及沟两侧的南北崖壁。该区与西山南端的极南洞一带窟龛隔河相对,窟龛造像高低错落俱分布于沟内北崖,窟龛朝向因崖壁自然条件而大致呈坐北朝南;南崖除近沟口处的采石痕迹外未见窟龛造像的雕凿遗迹(图版2~图版6;附录1:附图1~附图3)。
一、万佛沟概况
万佛沟古名乾元沟,因沿沟可达乾元寺而得名。万佛沟之名未见于清代以前文献记载。沟内虽窟龛密集、造像数量较多,但与两山其他区域相比并无明显数量优势,远不及“万佛”之数,故其得名或与近邻擂鼓台区第4窟窟门上方题额“大万五仟佛”有关。抑或沟内曾有数量众多的窟龛造像因后世采石烧灰、修路而破坏不存(附录1:附图4),由于历史记载和图像资料的缺失暂不得而知。
万佛沟为自然形成的大型沟壑,东西绵延约650m,高空俯视呈“丫”字形,内侧二沟较窄,在距沟内端约350m处斜向交叉,合二为一后沟谷变宽,整体呈东高西低、东窄西宽态势,切割深度10~60m,相对高差60m。沟内北崖陡峭,岩体裸露;南崖呈缓坡状,近沟口处岩体出露,余部则表面覆土少现岩石。沟口地势最低,直抵伊河。沟内常年无水,地表水由东及南北两侧向沟底排泄基准面渗流,至迟于清末已在沟口外垒砌有石构涵洞,以便其中渗流汇入伊河(图2;图版3~图版6;附录1:附图5、附图6)。
万佛沟崖壁岩层为中寒武纪碳酸盐岩体,岩性为微-细晶灰岩,岩体上覆盖第四纪土层。石质因含有泥质条带夹层,抗风化能力弱,造成保存状况较差。卸荷裂隙、构造裂隙和层面裂隙等交错分布,形成网状通道,所过之处岩石或分离、脱落,或有明显的渗漏水现象。岩溶也非常发育,常以溶孔的形态出现。沟区内窟龛在北崖壁上分别选依不同岩层走势雕凿,分布因而呈现高低错落。
1991~1992年,于沟内南、北崖上贴壁顺筑栈道,连通部分东西窟龛,在沟中间的第6窟(俗称“高平郡王洞”)下方凌空横搭拱桥,互通南北两崖,部分洞窟前凿砌出台阶以供登临(如第6窟、第9窟)。这些设施虽方便了参观考察窟龛造像,但也因此改变了万佛沟的原始风貌(附录1:附图7、附图8),影响到部分窟龛(如第6窟、第9窟、第18窟)外崖面营凿痕迹的观察与识别。据20世纪初照片资料,当时万佛沟沟口外原有坡道连通南北,后被20世纪30年代修筑的东山道路和80年代修筑的洛汝公路覆盖,2003年龙门景区封闭,将洛汝公路改造为景区内部游览道路时,重新对其进行清理揭示,始知这段坡道为略经加工、不甚规则的大块青石铺就,从而予以保留展示,古道外侧为当时改造而成的景区游览道路(图版3;附录1:附图1、附图2)。
二、万佛沟区洞窟概况
万佛沟区洞窟即分布于万佛沟内北崖壁的60个大小窟龛,包括《龙门石窟窟龛编号图册》(以下简称《编号图册》)中的第2129~2179号及其附龛53个、未予编号的小龛4个,以及2015~2017年清理发掘的窟龛3个。本报告按照自沟内到沟口、从东至西的顺序,以窟带附龛的原则重新编号,共计24窟36龛(测1;图3;附表1、附表2)。
根据万佛沟的天然形状和窟龛的位置分布,万佛沟区的窟龛以沟内分叉处为界,分为东、西两段,两段相距100m,两段之间的崖壁上未见雕凿窟龛痕迹(测1)。
东段位于分叉右支的北崖,距分叉处75m。此段窟龛稀少,仅有1窟1龛,即第1窟及其附龛第1-1号龛,左侧紧邻东山窟区保护围墙。该处窟龛为万佛沟内延伸最深的窟龛遗存,窟外上下崖体均见明显人工刻凿痕迹,大部被窟前覆土形成斜坡及其上草木所掩盖,窟龛整体风貌难以辨识。经过考古清理,窟前发现大量建筑遗迹、遗物,窟龛营造及使用状况得以展现(图版7)。
西段位于合二为一后的沟谷北崖,距分叉处36m。此段是万佛沟区窟龛造像分布集中区域,数量众多,计23窟35龛,即第2~24窟及附龛。窟龛随所属不同岩层走势分布而高低错落明显,彼此落差较大。大部分窟龛雕凿于远离沟底的崖壁半腰以上乃至近巅处,临近沟口位置的窟龛地势相对较低。其中第6窟及附龛的地势最高,视野开阔;其次为第7、9窟和近沟口崖壁顶端的第15窟,三窟水平方向大体对应;位于端口的第24窟最低,已近沟底,其间高差近60m。沟口处窟龛分布密集。第6窟是万佛沟区规模最大的洞窟,第9窟次之,其他窟龛规模比较小,体量多为中小型(图版8~图版11)。
西段北崖修筑的栈道随底层窟龛位置及岩体走势修筑,多有上下起伏。栈道直抵第3窟前,未延及第2窟及附龛处;第5、6、8、9、10五窟的部分附龛,第7、14、15三窟及附龛也因所在崖壁过于陡峭而未及外,区段内其余编号窟龛前均有栈道途经。栈道与第6、9窟间存在巨大落差,凿出陡直的台阶予以连通(图版8~图版11)。
三、调查研究简史
龙门石窟的著录,始于北朝末期《魏书》的编撰,唐代佛教史籍中也有少量记载,此后唐宋诗人作品中也偶有关涉龙门窟龛或造像的只言片语。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数量众多,其中不乏名人佳作,故北宋以来的金石著作中多有收录。清代乾、嘉时期金石之学大兴,龙门题刻遂倍受重视,万佛沟区相关资料的著录,即始于金石学者的关注,但被收录者为数甚少,仅有第18窟(俗称“卢征龛”)的造像发愿文一则(详见附录2)。这些出于政治讽谏、宗教劝化、金石鉴赏、文学赏析目的而予龙门造像行为和碑刻题记的记载、著录,显然不同于现代学术意义的石窟记录。
龙门石窟学术考察与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日本学者从雕塑、美术、建筑、考古等角度开展的中国佛教石窟寺踏察活动,其学术成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相继公开出版发行,其中部分较为全面的田野调查、较为系统的资料结集影响较大,从而将龙门石窟推向了当时的东西方学术舞台。受其影响,中国学人随即也自主展开了窟龛造像、碑刻题记调查统计、整理结集等工作,其成果也有零散刊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学者开始成为龙门石窟学术研究的主力,龙门石窟开始设置专门的保护管理研究机构,学术目的明确、规划设计有序的全局性、基础性工作逐渐列入日程并接续实施,主要有洞窟编号、碑刻题记的棰拓与整理、内容总录的编纂等。基础资料得到全面系统的整理刊布,专题学术研究随之逐渐展开,学术著作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呈现出与20世纪上半叶显著不同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初东西两山崖壁栈道的修筑,极大地提高了窟龛考察的覆盖率,为工作开展提供了便利,特别是这一时期龙门石窟管理机构的工作重心在原有文物保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为以研究为主,使龙门石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工作步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学术成果产出开始加快,数量日益增多,质量不断提升,学术研究实现了质的跨越。万佛沟区石窟寺遗迹的学术研究正与龙门石窟这一学术历程相伴同行。因此我们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把万佛沟区石窟寺遗迹的学术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学术研究
1910年10月29日至11月12日,美国著名艺术鉴藏家、实业家弗利尔到龙门考察,通过书写日记、手绘草图、拍摄照片和棰拓碑文记录龙门之行。日记显示弗利尔曾三次渡河到东山参观,惜无万佛沟的任何具体描述,其拍摄照片中幸有沟口远眺一帧,留存了此区形象资料的第一次记录(附录1:附图1)。
1914年,针对龙门驻兵毁坏佛龛一事,北洋政府内务部致河南民政长训令,要求河南委派专员会同地方官到龙门石窟调查,将龙门石窟所有佛像石刻登记在册,并责成附近寺庙僧侣管理,酌情给予津贴。洛阳县知事曾炳章随即奉命组织人手,对龙门两山洞窟进行了有计划的调查:统计佛像的规格、保存状况以及数量,并借机棰拓造像题记,形成《龙门山等处造象数目表》咨复到内务部。《龙门山等处造象数目表》将龙门一带32处寺庙、洞窟的石佛数目做了统计,总计大石佛476座,损坏180座;小石佛88633座,损坏7250座;石佛之在门外者6座,其他石佛742座。这次调查未有正式报告刊布,仅顾燮光在其金石著作《梦碧簃石言》中曾言及此事。尽管这一政府行为并非出于学术目的,却是中国人全面调查龙门窟龛造像的开始。作为此次调查的组成部分,万佛沟内共统计出完整大佛17尊、破损大佛11尊,完整小佛57尊。
20世纪初至3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和长广敏雄、水野清一等人先后考察龙门石窟,万佛沟在其考察成果中多少有所涉及。1939年出版的《支那文化史迹》中对万佛沟内的窟龛无一提及,仅有一帧名为“东山香山寺附近远景”的照片可见万佛沟(附录1:附图2)。1941年出版的《龙门石窟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顾氏关于曾炳章调查龙门的记录;涉及个别万佛沟窟龛,其记述甚为简略,文图共约一页篇幅,简单描述了沟内今第5、6、9窟的形制,对造像题材和年代进行了推测,认为三洞开凿于盛唐,第5、6窟表现的是阿弥陀净土变,第9窟为三佛窟;较为重要的是刊布的东山全景和第5、6窟局部等六帧照片(附录1:附图2、附图9),正面显示了万佛沟全景图像,记录了第6窟主室内堆积的大量造像残件,成为今天辨识万佛沟及相关窟龛原始遗迹的重要参考。
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关百益对龙门石窟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于1935年出版了《伊阙石刻图表》,保留了大量龙门石窟的图像和拓片资料,这一反映龙门石窟原貌的较早成果,受到大约同期考察龙门的日本学者的注意。书中有对万佛沟的简单文字介绍,并附题记目录一则、图版2帧(附录1:附图5~附图7),其中1帧图版留存了第24窟外右侧上下两龛被毁前的珍贵影像(附录1:附图6)。1936年,中国学者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人考察龙门石窟,分“伊水西岸”和“伊水东岸”对两山洞窟进行编号记录,并绘制各窟平面图,伊水东岸仅记录了万佛沟沟口外两侧的擂鼓台三洞和看经寺,未涉万佛沟区窟龛。1940年7~10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赴洛阳调查龙门石窟,其间注意到了万佛沟及其内雕刻:“在东岸七窟的背后,有一处大的峡谷,其中还有不少的唐代洞窟,有的高不可登。就能看到的雕像来评价,有的高于上述各窟,堪称为龙门唐代佛像雕刻艺术之精华作品”。
20世纪上半叶,万佛沟区第一期的学术考察与研究较为薄弱,中外学者对龙门石窟的考察较少涉及这一区域,沙畹、梁思成等学者的考察成果中甚至全然无涉。或有万佛沟区窟龛较为分散且所处位置多陡峭险峻难以攀临的客观因素,致使当时基础资料的欠缺影响到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知。尽管如此,由于万佛沟区部分洞窟已损毁、部分洞窟外崖面遭封护凿砌和部分洞窟内部造像被挪动移出,当时留存的少数万佛沟及该区个别窟龛20世纪初期面貌的图像资料显得弥足珍贵。
(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学术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龙门石窟管理机构随之设立,开始有计划地开展石窟的保护管理和宣传工作。1960年,龙门文物保管所挑选精品造像结集出版了《龙门石窟》图册)。其后的60~90年代,洞窟分区编号、碑刻题记的棰拓与整理、内容总录的编纂等重大基础性工作相继实施,洞窟文化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成效显著,成果陆续出版发行,有力地推动了龙门石窟学术研究的蓬勃开展。作为这些系统工作的有机组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