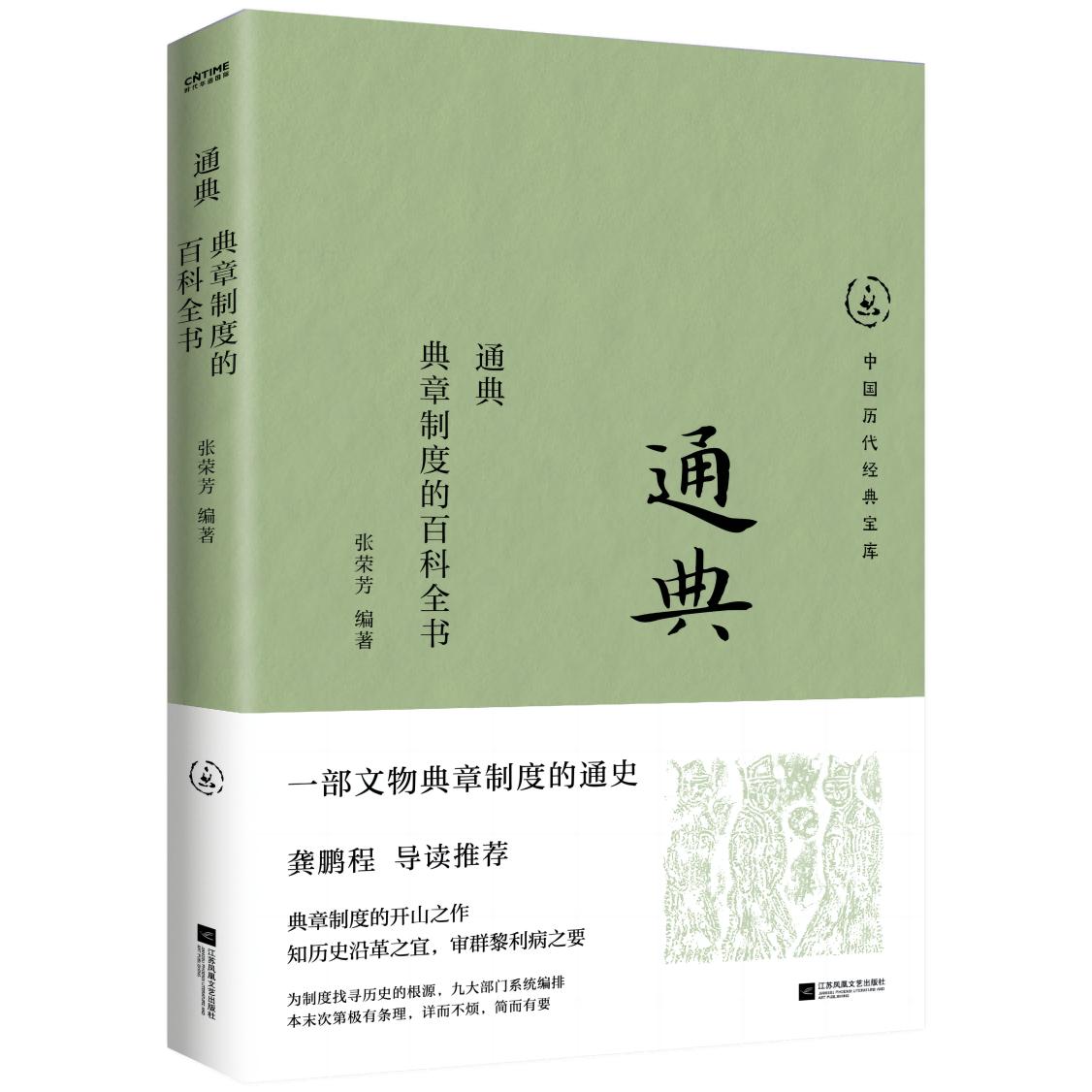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4.80
折扣购买: 通典: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
ISBN: 9787559487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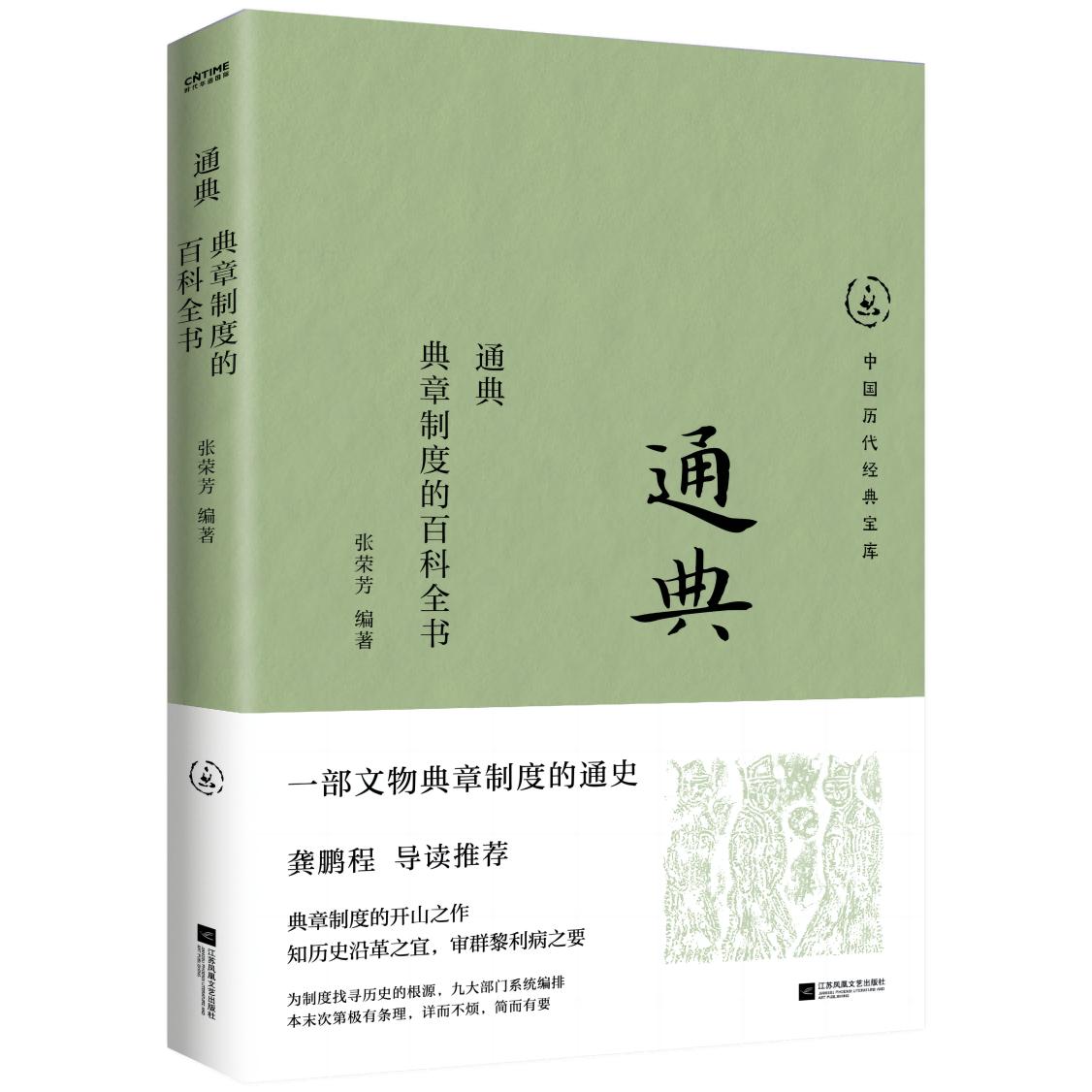
张荣芳,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访问学人、电视历史报导节目制作与策划人,东海大学历史系主任。现为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中国政治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国历史文献学。
第一章.杜佑与《通典》 一 中国历史上以百科全书式体裁出现的史书,最著名的首推汉朝大史学家司马迁所撰的《史记》。但是,从《史记》以降,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中叶,编纂巨大篇帙的百科全书式史书不复再现。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环境的变幻无常,朝易夕改,在动乱的世局之下,很难定下心来专心一意地从事长期编纂的工作;另一方面,时代愈后,累积保存下来的史料也愈多,加以学术的分工愈细,庞大编纂工作已经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单独负担,个人费尽心力皓首穷经,也很难突破这一限制,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工作的艰难。 大唐帝国统一海内之后,在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前,处于长期的繁荣富庶,政府也大力推动各项学术工作的发展,奖掖学术。科举的设立,更使得天下士子竞相投诸其流,形成了相当深厚的文化素养与良好的学术环境。后来,虽然唐室迭遭大难,东方藩镇势力兴起,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危,但李唐的国祚命脉却也能不绝如缕,继续维持了一百多年。中央政府的各项施政措施也尚能大致施行,不致因种种变乱而告停顿,表面上犹可维持一个大一统帝国的形象。 时代的动荡,世事的变幻,最容易使人产生各式各样的思想。有人感叹世事无常,醉心释氏;有人目睹世局不安,遁入山林,归于老庄;也有人眼见国家兴亡,危如累卵,亟思力挽狂澜,拯救生民疾苦。 就史学来说,将近千年的孕育累积,顿时之间遭遇大变,常使有心以历代兴亡为鉴,思古幽情,希望借着学习既往历史教训而有所惕厉振扬。中国史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以唐代刘知几为一分水岭,刘知几总结了以往的历史著作成绩,汇成一部《史通》,而杜佑则以《通典》开创出史学的新领域。 二 唐玄宗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安史之乱以前,大唐帝国声威远播,达到前所未有的富庶强大。此后,国势如江河日下,再加上朝廷内有宦官跋扈,朋党相争,外有藩镇肆虐,外患频仍,交相进逼之下,中晚唐的政局并不算稳定。 杜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长的人物,也是这一时代的见证者。他虽然在宦海中浮沉升降了六十年之久,也曾历仕六朝,位极人臣,但是,他对唐代中叶的紊乱政局,并未产生丝毫振衰起弊的作用,更谈不上有拨乱反正之功。宋代欧阳修、宋祁等人所修撰的《新唐书》上,对他的评语是: 淳儒,大衣高冠,雍容庙堂,道古今,处成务,可也;以大节责之,盖 中而玉表欤! 意思是指杜佑为一地道的读书人,如果在升平治世的时代,还可望有一番作为,但是碰到中唐这种混乱的环境,就欠缺大魄力与大担当了。 然而,历代之所以赞美《通典》,并不是因为杜佑在政治上位居高位的缘故,而是因为他编撰的这部《通典》,罗列古今历代典章制度的因革损易,内容详赡,脉络分明,可说是典制史上一座蕴藏丰富的史料大宝库。以下就分别说明杜佑为什么编撰《通典》,如何编撰,具备哪些特点,对中国史学的贡献何在。 三 古人说:“泰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唐代的史学,也正表现出这一种蓬勃的气象,一方面纳川汇海,总结魏晋以来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创造唐宋以后的契机。当时史学家中较著名的有专门注重名物训诂研究的颜师古等人,有侧重研究史书体例的刘知几,也有意在典章制度的赵仁本、蒋乂等人,称得上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群说毕出、蔚为大观。 以典章制度为主的史书,在中国正史之中,就是所谓的“志”与“书”一类,如《史记》有《平准书》《封禅书》;《汉书》有《食货志》《礼仪志》等。除了这两部书外,其余的大都专记一朝一代的典制,很少有贯通古今的记载。 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典制史撰述的风气逐渐形成时尚,而且从正史里面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唐朝初期,以著述一代典章制度而单独成书的有李延寿的《太宗政典》,中唐有苏冕的《唐会要》、刘秩的《政典》,晚唐还有王彦威的《唐典》等,都是同一类的著作,说明在杜佑的《通典》问世的前后,撰述典制史已经形成一股学术风气,不断冲击着史学界。 四 《旧唐书·杜佑传》上记载,唐玄宗开元末年时,史官刘知几的儿子刘秩挑选中国经、史、百家的记载,依照《周礼》所描述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的职制,撰写一部三十五卷的《政典》,极享盛名,大为当时著名学者专家的赞誉。而杜佑自从看到了刘秩的《政典》以后,潜心探索其中蕴含的精义、主旨,他认为《政典》的条目、内容都还不够完备,因而加以扩大增广,并且补录了玄宗时代的《开元礼》和《开元乐》,撰述完成《通典》一书,共二百卷。 宋朝著名的文学家苏东坡也曾经记载说:当代叙述兵制,全都取材于《通典》,而《通典》虽然是杜佑所收集编纂,但它的源流乃是出自刘秩。 宋朝距离唐世尚不远,这两种记载都直接指明《通典》本于刘秩的《政典》,应当是不错的。然而,除此之外,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宰相张九龄、李林甫等人曾编修一部名为《六典》的书,有三十卷。它的内容是以周代官制的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与十二卫为纲要,罗列了每一个职官的职掌,记载了每一个职官的品级,而整部书也是模仿《周礼》。由此,可以知道《六典》和《政典》都是以《周礼》一书为蓝本,性质相类似的著述,并且均是杜佑撰写《通典》的主要依据。 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书以外,《通典》另一个重要的史源是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颁行的《大唐开元礼》。杜佑曾经赞美这部书是:“百代之损易,三变而著名,酌乎文质,悬诸日月,可为盛矣。” 在总数达二百卷的《通典》里,关于礼的部分有一百卷之多,占全书一半的篇幅。杜佑对礼的次序,排列为吉礼、宾礼、军礼、嘉礼与凶礼。这种排列,并不是杜佑首创,早在唐初所修撰的《贞观礼》已经开始采用这种次序,而《开元礼》沿用《贞观礼》《显庆礼》,《通典》又加以承袭罢了。但是,《通典》将原为一百五十卷的《开元礼》删节为三十五卷,这种取材方式,疏漏自然在所难免,所以清朝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特别称誉《开元礼》的赅洽完赡,凡是朝廷礼仪有疑问时,稽考《开元礼》就可以得到解答,若是国家有盛大的举动仪式,依照《开元礼》记载就可以实行,推崇它是一部研究“礼”制的圭臬。相对地,对《通典》就颇有微词了。 关于乐的方面,中国从先秦以降,《乐经》失传,虽然学者常常拿礼乐并称,实际上却很少有人专门去研究乐。唐朝建国以后,高祖、太宗采用隋朝的乐,命令祖孝孙、张文收二人研究制定,但是并无完整的规章流传下来,史书上的记载也仅仅是聊备一格,因此,杜佑在撰写《通典》乐门的时候,也感到资料非常贫乏,极为困扰,最后只好收集了开元年间制定、通行的乐,加上历代沿革经过的大概而定。 在礼、乐与政制之外,唐朝还有一批学者专心致力于州郡、边疆地理以及外藩诸夷民族的研究,成绩斐然,颇有可观之处。这种风气的盛行,最主要的因素是政府的提倡、监督,如政府规定地方州府必须三年一造地图,对唐帝国域外的国家由中央政府的鸿胪寺派官,负责讯问各国的使臣、侨民,记录每一个国家的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报告给朝廷。最有名的地理书籍,稍早有唐高宗时代,许敬宗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详细记载西域各国的风俗物产。武则天时也曾经下令尚献甫召集学者修撰《方域图》。这些记载到了玄宗天宝年间,与实际情形不相符合,改变甚大,因而时时下令加以修改。 唐玄宗以后,最著名的地理书籍首推德宗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撰的《海内华夷图》,以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称得上是巨细靡遗,莫不备载。贾耽经常到出使夷狄的使臣那里,询问风俗,深明当时天下地土、区产、山川与夷岨,《新唐书》即极为赞美他的著作。 贾耽的书,今天虽然多已失传,但作为和杜佑同时代的人物,他的著作也是在德宗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并献于德宗,我们并没有直接的史料证明《通典》本于贾耽的著作,但推测杜佑曾参考他的著作,或者采用相同来源的资料,应是极为可能的事情。况且杜佑的父亲杜希望曾经担任过和亲判官这一职务,出使吐蕃,又出任鸿胪卿,主管外国事务,他和贾耽应当也有过交往才是。换句话说,杜佑就在这种种风气与家学的交互影响之下,从事《通典》的撰述工作。 五 说明了唐代的史学环境与《通典》选述的时代背景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介绍杜佑的生平。 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人。他的家世在唐代甚为显赫,杜氏一族仕宦至宰相的人多达十余位。杜氏这一系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共分为杜陵、京兆、襄阳、恒水与濮阳五个分支,杜佑自认出自杜陵这一支,但也有历史学家考证他是出于襄阳一支的。 杜佑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唐朝边境虽经常有契丹、奚、突骑施、吐蕃等骚扰,但是唐朝的殷富丰饶已经达到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巅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描述开元末年的富庶说: 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杜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富庶繁荣、人文荟萃的首都长安度过。但他自小读书,就不喜欢那些专讲对偶章句、华丽辞藻的文章,终于未能与流俗一样,自时下盛行的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而是以他父亲的官位荫任补官。 杜佑正式踏入官场,大约在玄宗天宝末年到肃宗至德初年期间。这时候唐帝国国势颓危不振,历史上的所谓“安史之乱”“建中之变”“永贞内禅”等事变都是在杜佑的生平期间发生。当时杜佑或是在朝廷任职,或是出镇担任节度使,终其一生,都没有卷入各种政治风潮,也没有参与阉宦、朋党的冲突之中。 总计他一生,宦途生涯几乎达一甲子之久,直到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3年)十月壬辰病逝,享年七十八岁。政治生命的长远,也是国史上极为罕见的。他曾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与宪宗六任皇帝,担任过德宗、顺宗与宪宗三朝的宰相,位至三公,可说是国之大佬。他一生的著作也很多,除了最著名的《通典》之外,还有《宾佐记》一卷、《管氏指略》二卷与《理道要诀》十卷,这些作品直到宋代仍然十分盛行,流传很广,但今天除了《通典》外,其余都已经散佚无存了。 六 今日我们所见的《通典》,分门情形是: 食货 十二卷 卷一至十二 选举 六卷 卷十三至十八 职官 二十二卷 卷十九至四十 礼 一百卷 卷四十一至一百四十(其中历代沿革有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 乐 七卷 卷一百四十一至一百四十七 兵 十五卷 卷一百四十八至一百六十二 刑 八卷 卷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 州郡 十四卷 卷一百七十一至一百八十四 边防 十六卷 卷一百八十五至二百 杜佑在《通典》序中曾说明全书共分为八门,也就是现今通行本的兵、刑合为一门,他认为二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他说:“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意思就是兵与刑是一体的两面,差距极微,只是有轻重的分别罢了。 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李翰为《通典》写序时也说是八门。到了宋朝,几部目录书籍如《直斋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等都说《通典》的编类为八门,但《直斋书录解题》是把礼与乐合而为一。另外,杜佑在他呈给唐皇帝的《进〈通典〉表》却又说成九门。对这种分目上的歧异,清朝史学家王鸣盛的解释是:李翰的序在《通典》定稿前早已写毕,因为门类未定,后来杜佑自己还有所更动。王鸣盛的解释颇为合理,因为《通典》撰述的时间长达三十余年,杜佑在撰述期间更动原先拟定的篇目是相当可能的。 于《通典》撰述年代的问题,由于李翰序中提到杜佑从代宗大历初年开始纂写,杜佑自己也说长达三纪。因此,后代的史学家便在“大历之始”和“三纪”这两个字眼上大做文章,出现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到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一说大历三年(公元767年)到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另一说认为大历元年到贞元十七年完成,而贞元十九年所完成的是杜佑根据《通典》删节完成的《理道要诀》一书。也有认为杜佑的编撰时间不止三十六年。大致其撰写的时间确实很长,至少有三十多年,可能在贞元十七年前已经完成,等到这年,他已经是位高名巨,这时候献上《通典》,既可以增加自己的声望,也可以提高《通典》的地位。 七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杜佑在撰写《通典》时所显现的史学方法。大要有三:第一,会通古今;第二,章法严谨;第三,剪裁允当。 早在唐代以前,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就指出中国史家撰述的弊病,他说: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旁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 这段话实在是史家必须遵循不渝的原则,但时代风气多“贱近而贵远,昧微而睹著”,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一直到《通典》问世以后,才一扫唐世的弊风恶习。 《通典》中凡是叙述一项制度时,必上溯于上古三代,下及唐朝,罗举史实,详详细细说明经过原委,而且对唐代的制度尤其精详。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特别指出《通典》,正是可以通天下的不通,上达三王,下及当代,贯通古今,当之无愧。梁启超更称赞说“有《通典》而政制通”,就是指会通古今这一点。 典章制度史的撰述,最忌讳的是杂庞无归,漫无所依,如果编撰者不能匠心独运,妥善分门别类,很容易陷入数据庞杂、毫无头绪的泥淖当中,无法探究每一制度的缘由始末,这样就失去会通的意义了。更甚者往往又是搜罗无度,把一切讨论制度的史料,通通纳入书中,章法不严,取舍不一,又无标准可为凭恃,如此一来,便形成史料的大杂烩。 有唐一代学者的毛病正是如此,李翰在《通典》序中很明白地说明这种现象。而杜佑的《通典》,分为九门,每一门再分以细目,列举史实与历代的议论、批评,逐一返本探原,将礼乐政刑的始末、千载制度的变迁,都纳入二百卷之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这是相当独特的贡献。 另外,我们再从杜佑仕宦的经历来看,总计他一生之中,曾担任过数十个职官。假如从大历元年开始撰写《通典》算起,到贞元十七年呈献给皇帝为止,三十六年里,杜佑的简历大致是:司法参军、主客员外郎、工部郎中、青苗使、抚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金部郎中、江淮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判度支、苏州刺史、饶州刺史、御史大夫、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尚书右丞、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礼部尚书兼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刑部尚书、检校右仆射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节度使。 将上述杜佑的经历与《通典》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兵、州郡、边防做一对比,很清楚可以明白这三十六年的阅历与政治生涯,对《通典》的写作有多大的帮助。如杜佑以他所曾参与经济财政决策,以及负责实际执行工作后,在撰写食货门时,必能产生休戚与共的感触。在食货门中,他分别叙述田制、赋税、户口、钱币、盐铁、榷酤、平准、轻重等制度,而且他曾任工部诸司郎中、青苗使、转运使、度支郎中与和籴使等职务,这种实务经验,配合独具的历史眼光,一定比其他足不出户的学者仅就史料排比更为精辟,也更能体会制度的利弊所在。其他如礼、乐等也是和上述情形一样,读者略加比较,自能明白,不必多说了。 杜佑仕宦既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每能观察各地风土,同时他受到父亲杜希望影响很大,对外蕃诸夷必有一番心得。 在《通典》中,我们屡屡看到杜佑的“说曰”“议曰”“评曰”“论曰”等文字,这些都是就一代制度或前世后代相悖相契的地方,发表议论,比较古今得失的所在,并不与叙述历代制度之处相混杂,他的精审由此可见一斑。所以章学诚称誉《通典》,我们赞扬他“章法严谨”,并不是过誉之词。 《通典》一书,体例不可谓之不大,类目不可谓之不细。如何将庞杂的史料系统地纳入二百卷之中,这就全靠杜佑的剪裁之功了。正因为体大博洽,纲目巨全,包罗古今,涵贯精粗,唐宋时代的人甚至视之为“类书”,而《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它“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清朝乾隆皇帝说它“网罗百代,兼总而条贯之”,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说“包括宏富,义例严整,繁不至冗,简不至漏”,都说明《通典》的取材、剪裁,乃是别创一体,既近于纪事本末体,又可以补纪传体、编年体的不足,实为开创唐代史学新途径的第一人。 八 史学的目的,并不仅是为史学而史学,更包含有更远大、更恢宏的理想。在杜佑看来,他服膺古人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盼望能通过《通典》的撰写,达到立功与立言的目的,企求他的理想,能用《通典》表达出来,能实施于当代,有补于时政。 杜佑借着《通典》来表达他“将施有政,用乂邦家”的计划,以挽回大唐帝国江河日下的颓势。同时他也对当时学者蝇营狗苟,专务于辞章之学现象感到十分痛心。因此,在《通典·自序》中提出他的一番政治理想: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礼乐兴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可见整部《通典》的内容息息相关,每一门类有如一环,环环相扣。这也说明杜佑不仅仅是从事典制史的编纂,而且企望将他的政治蓝图借着二百卷的《通典》表达出来,影响人心,裨益世局。 这种以写史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政治思想的蓝图,由来久远,与中国传统儒家的表现方式并没有什么两样。孔子就曾借《春秋》企图拨乱反正,达到“乱臣贼子惧”的理想政治,可说传统史学的最高理想,是为“经世史学”。换句话说,乃是寓政治思想于史学之中,杜佑充分地表达了这一努力,无怪乎乾隆皇帝称誉《通典》是一部“经国之良谋”。 九 杜佑经世思想中首重民生经济,由于他曾经多次担任主管经济措施方面的大员,也出任过地方长官,与百姓时有接触,相当能够体会一般百姓的需要。他认为政治上的一切措施应该以民生为主,如果居上位的人不能够满足百姓的基本需求──衣食温饱,还谈什么教化理道呢?诚如管子所说的:“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如此才能看清政治问题的症结所在,而所谓“政治”,应是政府施政以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让人民能达到富、足、均的境界。要达到这一点,首先执政者必须以仁德爱民,培养人民对政府的信心,使百姓对政府产生深切凝厚的向心力,也就是政府与百姓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庙堂与江湖之间没有隔阂闭塞,上与下能够密切沟通,国本自然深厚,国基自然屹立不摇。 但是政府的一切支出,都是来自人民,因此必须以公平的赋税向百姓征收。他特别向往三代的授田给人民,因为如此一来,政府与人民之间就产生相对的给予关系,而不仅仅是政府单方面的敛之于民。 杜佑赞美古代的井田制度是富国富民的良法,虽然时代、环境转变,后世再也无法恢复,但是井田的精神──乡党互相扶助救济,应该继续推行。能授田给人民,足以杜塞争端,防范不足,百姓淳然,亲和团结,百姓富庶则国本自然雄厚,可谓两全其美,臻于理想国家的境界。 自从秦汉以降,井田制度破坏,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形成富者占山连城,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形,因此应当防制权豪之家兼并土地。初唐所实施的均田制,还能达到这一理想,然而,安史之乱后的帝国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光荣,均田制既没有办法维持,与授田法相伴的租庸调制也颓然不行,而改行两税法,甚至有各种名目的赋税增加,这一切都形成政府单方面的敛取人民。 衰乱时代的苛捐杂税,重敛暴赋,最足以导致人民的反感,加以冗官冗员充斥在僵化的政府当中,使得各职司往往不得其人而任。上焉者伴食君主,下焉者贪墨侵渔,无所不为,上下不得相通与闻。杜佑认为这就是法隳纪乱的时代,但如何从根本上改革弊端呢? 他首先指出文士和胥吏是不足为政的,胥吏政治是最坏的政治形态。因为如果政事由胥吏操纵把持,则人民对政府就会丧失信心,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培养主管经济的专门人才,亲自主持实际事务,从而使胥吏无法上下其手、欺瞒长官、压榨百姓。 在改革政府财政困窘方面,杜佑认为政府对人民如果横征暴敛,那无异是杀鸡取卵的不智之举。他主张从两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方面应“省用”,国君先从自身做起,到裁汰冗员都在范围之内;其次为“轻税”,杜佑自客观环境分析,认为轻税、省用实际上是一体两面,如果轻税则人民安定,不致逃亡他乡,免于流离转徙之苦,也益加勤劳于农耕种植,再用乡党互助的民间组织为辅助,则人民富而强,国家也才能强盛。最后,他从节用轻税,论说安民的办法,主张采用汉代晁错的“贵粟”之方,也就是重农重谷政策,才能建立教化的基础。 十 政治乃是因于人事、人才的消长,往往可以决定一代的治乱与否。简拔真才实学之人,分配职司当是政治清明进步的首要之务。 杜佑认为,一个政治结构中,必然会产生尊卑君臣的关系,而人的欲望没有穷尽,如果没有国君治理必定天下大乱,而君主也无法以一个人的力量来治理天下,所以分别设立许多职官帮助他处理政事。因此,有君主然后职官设,这才是论才选士的本原。而国君必须尚德尚贤,以德治天下,选举贤能辅佐,充任职官,也就是将政权普遍开放给人民,而非仅限于少数公卿巨室。 由于上等人才较少,一般人民大都是中等之资,因此应该教化百姓,然后观察、选择才学识兼备的人充当官吏。杜佑特别推崇“两汉号为多士”,就是能从乡举里选,万中擢一,选拔言行、才能俱备的真才。 唐帝国自盛世以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在士多官少的情况下,甄拔选用相当困难,再加上其他种种政治因素,于是只好官外加官,员外增员,伤多且滥的弊病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武则天时已有“车载斗量”的歌谣,“腕脱把推”的谚语,用来讽刺官吏满街的景象。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造成士子日日竞逐于升官求官之途,最后甚至形成“一州无三数千户,置五六十官员,十羊九牧”的局面。杜佑认为解决的办法,唯有省等级、鼓励人民从事工商业,才可以避免人才集中、人才过剩的病根。 唐政府取士任官的步骤,除通过礼部考试外,还要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甄选,所谓身言书判,即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良。杜佑认为四者之中,举措可观,词说合理,都属于才干能力,要观察一个人是否具有才干,观其判就能了解,至于书法字体,只要不至乖劣就可以了。他认为最好的措施是恢复古代乡举里选的办法。 十一 杜佑在《通典·自序》里说:“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确然,在三代之世,礼乐是宗法社会的维系力量,天下一体。但三代以后,礼乐已经失去了它们本有的理想与精神所在。 唐代的环境也是如此,有关礼乐的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俛伏兴等细节,成为专门官员负责的事情,斤斤计较于礼乐的枝节末叶,早已丧失教化成俗的精神。 杜佑在《通典》中,以一半的篇幅,采纂抄录礼乐的本制。首先对每一制度都详细说明古今不同的地方,阐释其精神的所在;其次考证原意,从诸家庞杂的解释注疏中,发挥“从宜之旨”,希望合于当时所用,这点可以说明他对三代“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的向往。 十二 上面所说的民生经济、选才设职、礼乐教化,还要用安内攘外为辅。就是用刑罚、列州郡以安内,置边防、遏戎狄以攘外,属于“教化隳”后的解决方法。 所谓五刑是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杜佑认为用刑应该本于先王爱人求理的原意,而不是害人作威、钳制百姓的工具,所以实施时必须分辨本末次序,不能滥用无度,让人民动辄触犯刑章,生活于恐惧之中。对于唐代中叶政治社会混乱的弊病,他认为矫正之途不是在用重刑、轻刑的争论之上可以解决,治乱隆污的关键是在于“无私绝滥”,而不是在法的宽松与否,这真可称得上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之论。 杜佑认为列置州郡地方行政单位,防范戎狄部族的袭扰,才能让教化行之于全国,所以大刑用甲兵,甲兵就是行教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但是用甲兵必须谨慎而谋,如果措置得当,自然国治民安,否则就会国乱民危。因此,他特别取《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义旨,配合历朝历代行军部署、统军御兵相类似的例证,分成十五卷叙述。例如唐太宗、高宗时,所以能强盛,乃是政府制度、处置得宜,使兵为国有,事毕将还朝廷,兵归于本业,没有将帅专擅、危害国家的事情发生。 他认为穷兵黩武易肇败亡,如唐玄宗所以亡命奔四川,唐帝国国基动摇,危如累卵,即是由于边将骄矜邀功,于是兵集于边境而京师空虚,造成朝廷中央势衰力薄的局面,因此,政府想用兵命将,应该做到汉代贾谊所说的“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操纵自如,控制将帅士兵的调动指挥,使将士全为国家所有,就不会发生将领图拥重兵、干纪作乱的事情了。 他以为国君治理天下,对四夷的教化,要从道德去感召;治理本国,须让人民休养生息,使国家安宁而天下绥服,达到天下一家的理想。 总之,杜佑的主张是国君修仁务德,则四夷从化,外患自然无由而生,使才智之士管理州郡,杜绝私滥,与民休息,百姓宁谧,则内清而外平,纵然礼乐教化稍隳,国家还不至陷于危殆之局。 十三 唐朝权德舆在杜佑的《墓志铭序》里称美杜佑说: 若公都将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论道,两朝总己,缙绅瞻仰者凡六十年。 六十年的漫长宦途中一半以上的时间,杜佑也从事《通典》的撰写,因此,我们可以说杜佑一生之中,史学与政治是紧紧契合着,也是他一生精力之所萃。 杜佑撰成《通典》以后,典制史纂述的风气更加兴盛,元稹就以人文豪的身份撰成一部《古今刑政书》三百卷。唐宣宗大中年间,姚康也撰成《统史》三百卷,时间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内容包括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乃至僧道是非,无所不包,无不备载。最著名的是宋代郑樵的《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与《通典》合称为“三通”,到清代更形成有所谓“十通”。凡此,都说明《通典》继往开来的卓越贡献,后世赞誉为开山之作,实在不是虚诬之言。 当然,《通典》也不免有缺点存在,马端临、《四库总目》、清人王鸣盛等都曾批评它阙失简略的地方,但这些都属于小瑕疵,终究瑕不掩瑜,无损于《通典》的价值与贡献。 典章制度的开山之作 数百万读者奉其为经典入门的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