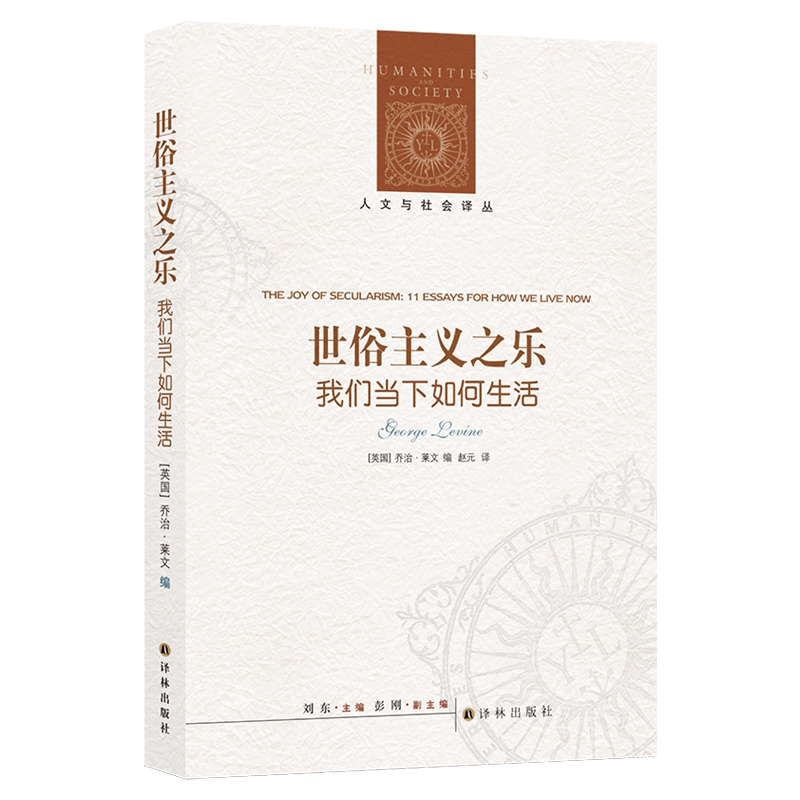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6.00
折扣购买: 世俗主义之乐:我们当下如何生活/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76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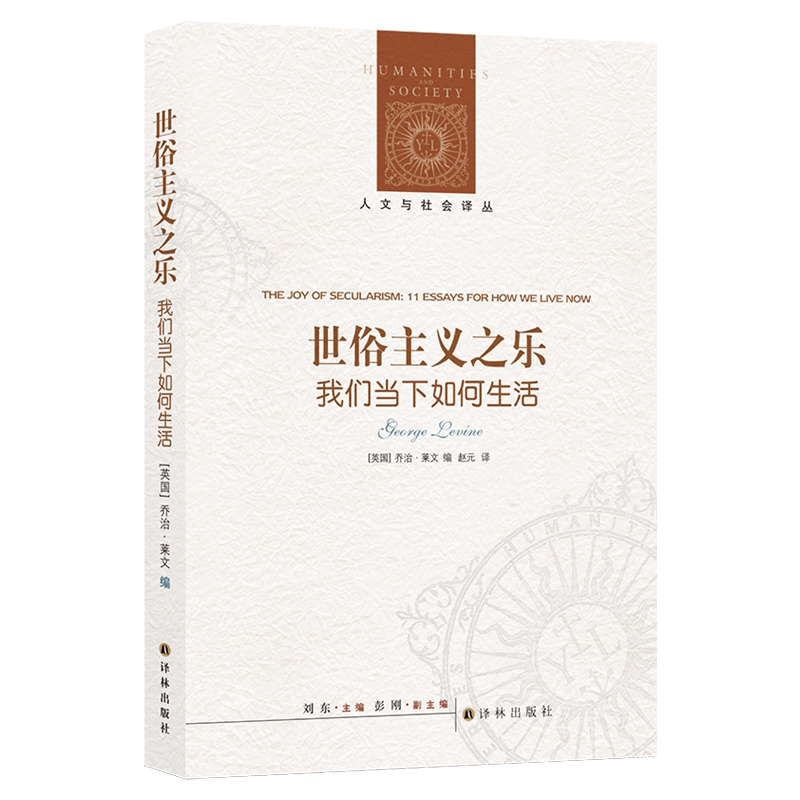
【作者简介】 乔治·莱文,罗格斯大学荣休教授,有多部论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以及文学与科学关系的著作,其中包括《达尔文与小说家》(1988)和《达尔文爱你》(2006)。专著《现实主义、伦理学与世俗主义》(2008)被英国文学与科学协会授予2008年度文学和科学类最佳图书奖。
二 祛魅——返魅 查尔斯·泰勒 一 这两个术语常常一起使用:前者指我们所谓的世俗化过程的一个主要特征;后者指一种对前者的假定取消,根据个人观点的不同,它可以是令人期待的,也可以是令人担忧的。 但是两者关系的复杂程度远甚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祛魅的过程是不可逆的。对返魅的向往(或返魅有可能造成的令人担忧的危险)指向一个不同的过程,它也许真的可以再现类似于被施了魅的世界的特征,但并不是对那个世界的简单复原。 让我们用“被施了魅的世界”来指称祛魅所去除的那些特征。主要有两点。 那个世界的第一个特征,是其中充满了精灵和道德力量,而且这些力量对人类有影响;也就是说,自我和这些力量之间的界限是具有一定渗透性的。这里有树林的精灵或者旷野的精灵。这里有具有招致好运或厄运的力量的物体,例如圣物(好的)和爱情魔剂(不一定好)。我用“道德”力量一词是为了表明某些物体被用于或善或恶的目的。因此,来自坎特伯雷的一小瓶水(其中必然包含殉道者托马斯·贝克特的一点血)具有治疗任何疾病的力量。在这方面,它和现代的药完全不同,后者因其化学构造而“瞄准”特定的疾病和状况。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魔法”的世界。这一点暗含在我们的术语“祛魅”之中,因为它可以被视为祛除魔法的一个过程。这在德语原词里看得更加清楚:韦伯的Entzauberung就包含Zauber(魔法)一词。但是它实际上并不那么能说明问题。祛魅的过程最初是因为宗教原因而实施的,它的内容是使所有与精灵和力量有关的习俗丧失其合法性,因为据说它们不是忽视了上帝的力量,就是干脆与之对抗。这类仪式据信具有本身的力量,因此是亵渎上帝的。所有此类仪式都被归为“魔法”一类。这种归类是由于排斥而形成的,它并未明确指出排斥的理由是什么。此后它便在西方文化中一直延续下来,即使信仰衰落之后仍然如此,例如弗雷泽对魔法和宗教的区分。只是到了西方人试图对非西方社会进行人种学研究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种归类是多么不恰当和不稳定。 刚才我谈到不可逆。但是我们的许多同时代人确乎已经“回到了”那个世界。他们相信并实践某些仪式,以便恢复健康或取得成功。这种心态留存了下来,即使以不为人所知的方式。这是实情;很多事物从更早的年代留存了下来。但是大的变化(这是很难取消的),是往昔的能渗透的自我被我所谓的“缓冲的”自我所取代。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被施了魅的世界,我们的先人所公认的精灵、魔鬼和道德力量的世界。祛魅的过程就是那个世界逐渐消失,以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取而代之——在这个世界里,思想、感情、精神活力的唯一所在是我们所谓的心智;宇宙间唯一的心智是人类的心智(大体如此,或许还有火星人或其他外星人);心智是有界限的,因此那些思想、感情等位于心智“之内”。我说“思想、感情等”是什么意思呢?我当然是指我们的感知,以及我们对世界和自身所怀有的信念或见解。不过我还指我们的反应,我们在事物中发现的意义和重要性。我想用类属名词“意义”来指称它们,尽管从原则上来说,这有可能会与语言学上的意义相混淆。在本文中,我用的是谈论“生命的意义”时的那层含义,或者是谈论对我们“意义”重大的一种关系时的那层含义。 一旦我们审视这层含义的意义,以心智为中心的观点与被施了魅的世界的关键区别就显现出来了。根据前者的观点,意义“在心智中”,也就是说,事物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唤醒了我们的某种反应,这与我们的生物本性有关,因为我们具备这样的反应,也就是说,我们是具有感情、欲望、厌恶的生物,换言之,我们是具有(最广义的)心智的生命。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种理解事物的方式先于不同哲学理论(唯物论、唯心论、一元论、二元论)的解释。我们可以采用严格的唯物论观点,认为我们的反应要用事物对作为生物体的我们而言所具有的功能以及因感知事物而引起的神经生理反应的种类来解释。我们仍是用我们的反应来解释事物的意义,这些反应在我们“之内”,因为它们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编程”或“硬接线”方式。 根据唯物论,我们说不定是一个大桶里的大脑,受到某个疯狂科学家的控制;这个幻想有没有道理取决于以下观点,即各种思想的物质充分条件在头盖骨之内。因此,关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的令人信服的想法可以随着正确的大脑状态的出现而产生。对于心智观至关重要的内外之分以及两者之间的界限在这种唯物论的解释中得以再现。 但是在被施了魅的世界中,意义不仅仅存在于这种意义上的心智之中,显然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的心智之中。如果我们观察在五百年前普通人的生活(精英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发现这一点。首先,正如我在上文所述,他们生活在一个精灵(既有善的也有恶的)的世界里。恶的精灵自然包括撒旦,但是除了他之外,这个世界充斥着从四面八方逼来的魔鬼:森林和旷野的魔鬼和精灵,以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造成威胁的那些恶灵。 善的精灵也有很多。除了上帝,还有他的圣徒,人们向他们祈祷,并在特定情况下,如希望疾病得愈,或因疾病得愈而还愿,或祈求从极度危险(例如出海)中得到拯救时,参访他们的圣地。 这些非人的作用者对我们而言恐怕并不陌生。它们违反了上文提到的现代观点的第二点,即(我们通常相信)宇宙间唯一具有心智的是人类,但是它们似乎提供了一幅心智的图景,多少与我们的心智相类似,意义(以善意或恶意的形式)可以在其中存在。 但是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未能充分反映被施了魅的世界的陌生感。因此,正是在对圣徒的崇拜中,我们可以发现,此处的力量并不都是可以决定是否要施以援手的作用者或主体。力量也存在于事物之中。因为圣徒的治愈力量常常与他们的遗物所在地有关:或者是他们(被信以为真的)遗体的一部分,或者是与他们生前有关的某件物品,比如钉死耶稣的那个十字架上的木片,或者圣梅洛尼加用来给耶稣擦脸的汗巾,这块汗巾曾几度在罗马展出。我们还可以列举出其他被赋予神圣力量的物品,例如圣饼或圣烛节被祝福过的蜡烛之类。这些物品是精神力量之所在,因此需要谨慎对待,使用不当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事实上,在被施了魅的世界里,个人的使然作用和非个人力量之间的界限并未做清晰的划分。这一点又可以从圣物上看出来。圣物产生的治疗作用,或者施加在偷盗它们或对它们处理不当的人头上的诅咒,被认为既源自它们(作为力量的所在),又来自它们所属的圣徒的善意或愤怒。甚至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里有着一整套大小不同的力量,(暂时只举恶的一端)从高级作用者,比如那个始终企图让我们堕入万劫不复境地的撒旦,到小魔鬼,例如树林的精灵(它们几乎无法与它们所栖息的环境分别开来),最后是导致疾病或死亡的魔剂。这说明了我在这里想要提出的一个观点,不久我将重提这个观点,即与我们那有着缓冲的自我和“心智”的宇宙不同,被施了魅的世界令人费解地缺乏某些对我们而言必不可少的界限。 因此,在前现代世界里,意义不仅属于心智,也可以存在于事物之中或人类之外、宇宙之内的各种主体之中。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通过观察这些事物/主体所拥有的两种力量,来展现其与现在的差别。 第一种是把某种意义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现在一直在发生,因为某些反应是由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知不觉间在我们心中触发的。我们遭逢不幸而伤心难过;我们遇到大事而充满喜悦。但是在被施了魅的世界里,具有力量的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方式在我们今天的理解当中没有可比之物。 对我们而言,世上的事物,那些既不是人类也不是人类所表达的东西,处于心智“之外”。它们可能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心智,实际上有两种可能的方式。 我们可以因为观察这些事物而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或者以平时办不到的方式受到激发。由于我们本身是与这些外物相连的肉体,并与它们时刻进行着交换,由于我们的心理状况以种种方式对我们的身体状况做出因果反应(我们意识到这个东西,但不拥护任何一种具体的、有关什么引起什么的理论),我们的体力、情绪、动机之类会受到,并正在不断受到外界所发生事情的影响。 但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这些反应从我们心中产生而事物获得这些意义这一点,是作为心智,或作为分泌心智的生物的我们如何运作的一个功能。相比之下,在被施了魅的世界里,意义已然存在于物体/作用者之中:完全独立于我们而存在;即使我们不存在它也会在那里。这意味着物体/作用者能够将这种意义传达给我们,把它强加于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可以说是把我们带入它的力场之中。用这种方式,它甚至可以把格格不入的意义,即鉴于我们的本性,那些我们通常不会有的意义强加给我们;此外,在积极的情况下,它可以加强我们内生的好的反应。 换言之,世界不仅仅通过向我们展示事情的某些状态(我们出于本性对其做出反应),或者通过在我们体内制造某种化学—有机环境(它根据我们的运作方式而产生,比如说,欣快或抑郁)来影响我们。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只有当世界对心智/生物产生影响时,意义才出现。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内生的。但是在被施了魅的世界里,意义已然存在于我们之外,两者并未发生接触:它可以把我们带过去;我们可以落入它的力场。它从外部与我们不期而遇。 被祛魅逼出局外的那个早期世界的第二个特征,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特征。它通过另一种方式将意义置于宇宙之内。只不过这是精英文化的一个特征。我并不是在论述通俗的“魔法”和能渗透的自我的感觉力,而是在论述高深的理论。宇宙反映并展现伟大的存在之链。存在本身存在于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宇宙的整体结构和它的各个不同领域都反映了这种等级制度。灵魂相较于肉体所体现的尊贵和统治同样体现在国王之于一个国家、狮子之于动物世界、鹰和海豚之于鸟类和海洋生物所处的优越地位。这些特征在不同领域中彼此“对应”。整体是由互补的等级关系构建起来的,这一点应该在一个管理有序的国家里得到再现。 为了再次强调与我们的世界之不同,我们可以说,在被施了魅的世界里,充满的事物具有引起结果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事物所包含的意义相匹配。虽然文艺复兴鼎盛期的对应理论与其说是一种通俗信仰不如说是一种精英信仰,但是它具有相同的施魅逻辑,充满着由意义居间促成的因果链。为什么水银能治愈性病?因为这种疾病是在市场上感染的,而赫尔墨斯是市场之神。这种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后伽利略时代、以心智为中心的祛魅。如果思想和意义只存在于心智之中,那么就不可能有“充满的”物体,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可能取决于它们的意义,因为意义必然是从我们的心智投射到它们之中的。换言之,心智之外的物理世界必然按照因果法则运行,这些法则绝不会依赖事物对我们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我们可以发现精英理论和民众的感觉力是如何互相渗透和互相强化的。在一个被施了魅的感觉力的世界里更容易相信高深的理论。该理论本身可以汲取民间学问的一些特征,从而赋予这些特征一种新的理论依据和系统形式。 我们更容易想象的是在我们的世界里恢复这第二个特征。显然,许多人持有“稀奇古怪”的理论。但是把这种观念视为具有霸权地位而加以全盘接受的想法在后伽利略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二 那么寻求“返魅”的人的意图何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追求的是同一个基本特征,但看法不同。换言之,他们不满于我们身处的宇宙完全没有人类意义。当然,工具意义可以被归因于我们自然环境的各种特征(就其满足或妨碍我们的生物需求而言),但是任何人类意义必然只是主观的投射。我所谓的“人类意义”是指当我们辨认出生命的目的时试图通过诸如以下这些判断来解释的东西:这确实是一种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或者这种生活确实值得拥有;或者这种存在形式确实令人满意,或者是一种更高的存在方式,诸如此类。再推导一步,鉴于我们周围的事物在这些目的和目标中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可以把人类意义赋予它们。梭罗的话“世界保存于荒野之中”就是一个赋予意义的例子。这正是返魅的支持者们经常想做的陈述。 这种失落感在浪漫主义时期频频得到表达。以席勒的《希腊的群神》一诗为例。 那时,还有诗歌的迷人的外衣 裹住一切真实,显得美好, 那时,万物都注满充沛的生气, 从来没有感觉的,也有了感觉, 人们把自然拥抱在爱的怀中, 给自然赋予一种高贵的意义, 万物在方家们的慧眼之中, 都显示出神的痕迹。 但是这种情感交融现已遭到摧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剥夺了神道的自然”: 被剥夺了神道的这个大自然, 不复知道她所赐与的欢欣, 不再沉迷于自己的妙相庄严, 不再认识支配自己的精神, 对我们的幸福不感到高兴, 甚至不关心艺术家的荣誉, 就像滴答的摆钟,死气沉沉, 屈从铁一般的规律。 那么彻底的祛魅错在何处呢?是什么驱使人们寻求返魅呢?在我笼统地称为后“浪漫主义”的时期中,我们一再发现这种抱怨,它针对的是对我们现代处境的一种解读,根据这种解读,一切人类意义都只是投射而已。也就是说,人类意义被认为是由人类主体随意赋予的。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义。对于这些意义的普遍认同将源自我们投射的实际存在的交点。梭罗关于荒野的话只能被理解为这样一种主观投射,而并非对所有人类有效。 但是这种投射主义的世界观并不是从上文概述的双重意义上的祛魅中得出的。诚然,人类意义不再被视为存在于物体之中,甚至不是独立于人类作用者的。这些意义因作为世界作用者的我们而产生。但是从中并不能推导出它们是被随意赋予的。 这里的推理有一个严重错误,它常常伴随着这一主题的现代转向而出现。在认识论领域,这一转向(笛卡尔、洛克)首先产生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将知识视为存在于头脑之中的对外部现实的正确描述。但是全面展开之后,这种返回自身对我们的经验进行检视的方式最终消除了这个错觉。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并不仅仅是我们内心的一个表征。事实上,它存在于我们与现实的互动之中。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海德格尔的Inderweltsein),或者面向世界存在(梅洛—庞蒂的être au monde)。 在人类意义的这一领域中必须进行一些类似的探究,否则,我们将一直活在对自身的扭曲观点之中。 简单说一下这个辩论与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之间的辩论的关系。显然,前者不会同意以下观点,即抽离人类作用者的现实当中不存在意义;我本人也不接受这个观点。不过这丝毫不影响我饶有兴致地探求我们该如何在人类经验中发掘那些必须承认是放之四海而皆能成立的意义。一旦我们确立这些意义是什么,那么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之间的辩论就可以更好地展开了。如果我们不跨出这第一步,就将以人类境况的一种扭曲形式生活下去,而其中的工具主义偏差将会使整个地球面临生死攸关的局面。 因此,返魅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一旦我们离开了“施了魅”的精灵世界,不再相信伟大的生存之链,我们该如何理解以下观念,即自然或者我们身处的宇宙是人类意义之所在,这些意义是“客观的”,因为它们并不仅仅是选择或偶然欲望的随意投射? 换言之,这些意义的属性对我们而言属于强评价。我在此处提及的强评价与弱评价的区别在于,弱评价取决于我们可能无法做出的选择,或者取决于我们对可能并不接受的目标的拥护。由此,对于声称某事物应该于我们有价值的观点,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另一个目标或者否定这一价值所依赖的那个目标来推翻它。就强评价而言,我们无法那样解放自己,我们一旦试图那样做将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道德领域的这一区分可以用康德的绝对命令和假言命令之间的对比来说明。如果有人说:投资房地产吧(在今天看来显然不是一个好点子,不过通常是明智的意见)。你可以这样说来挫败这个命令:我已经够富有的了;或者,我甘于过贫穷的生活。但是假如有人说:采取行动以减少不必要的痛苦吧,你就无法通过辩称你还有其他生活目标来解放自己。你需要的是以下这样的论点:减少痛苦是不好的,因为(比方说)这会导致一个“最后的人”的世界,或者会阻碍“超人”的产生。 但是,当然也可以在道德领域之外做出强评价,例如在美学中。某个作品或场景是美的这一判断将是强的,假如它暗示那些无法认同的人是审美有缺陷而不只是对这类东西不感兴趣。 把人类意义归于宇宙(中的事物)作为一个强评价跨越伦理和审美的界限。它涉及的也许是广义的道德,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对什么样才是一个真正好的或体面的人类生活做出判断。 以这些思考作为背景,让我们对有关祛魅和返魅的诸多争辩审视一番。我在此处跟随的是乔治·莱文在近著中的出色讨论。这一争论始于许多人(包括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以及一些居于两者之间的人)的论调,即韦伯的理性化和后伽利略时代的科学,伴随着宗教的式微,使我们面临一个失去意义的世界,而且没有提供任何慰藉。在这方面,一般认为现代人的处境与此前所有时代和文化中的人的处境都极为不同。于是就有可能爆发有关我们可以或者应该如何应对这个处境的争论:以大无畏精神面对空虚的世界,抑或对否定宗教提出质疑,抑或寻找一些新的意义来源。 但是我们还可以审视这幅“韦伯式”图景。这真的是我们的困境吗?有些人对此已经表示质疑。我们现在不是正对浩渺而复杂的宇宙、多样化的生命形式,以及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进化奇迹惊叹不已吗?难道我们从中没有发现美吗?这样看来,被认为使世界祛魅的那个变化的一部分,此处指现代科学中我们称之为进化理论的那部分,事实上让我们有更多、更深刻的理由对宇宙感到惊奇。正如莱文所说,世界尚未失去意义:“它惊艳、美丽、可怕、迷人、危险、性感、真实。”前四个修饰词也许可以被认为是审美的而非伦理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主张,即这种伟大感和美感可以培养对世界的热爱,这是宽宏大量的源泉之一。正如康德所见,我们从“头顶的星空”得到的灵感近似于我们在“心中的道德律”面前所感受到的东西。 事实上,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种对宇宙和对我们人类从宇宙中诞生的敬畏感。我们可以从卢克莱修那儿发现这一点,不过这种感觉在18世纪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和稳固而得以强化和发展。这一看法站稳了脚跟,但同时也得以深化。 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这让我们感到害怕;不过这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孤独中有一定的喜悦,尤其对缓冲的身份而言。因为孤独而产生的激动一部分是自由感,一部分是对这个易逝时刻的深刻感触,你必须抓住(carpere)这日子(dies)。一切意义尽在其中,就在这个小小的斑点之中。帕斯卡把人比作会思考的芦苇,这差不多说到了点子上。 新的宇宙图景在它之上又增加了一个层面。由于我们意识到宇宙在时空上是多么地浩瀚,它的微观构造是多么地接近无限小,因此我们感到自身的渺小和脆弱,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从这个浩瀚无垠、了无目的的机器中竟然产生了生命,继而有了感情、想象和思想。 一个信教的人看到这里很容易表露一种神秘感。唯物主义者常常希望批驳这种认识;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承认有任何神秘事物,只有暂时的未解之谜。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感到生命将它的根扎入一个深度如此令人难以想象的系统之中,以至于能从中产生意识,这种感觉也让唯物主义者惊叹不已。 对于我们来历不明的疑问,以及我们能感受到的围绕这一疑问的争执,被一个当代作家很好地捕捉到了。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发现,某些人 对于“通过解释消除”灵魂有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有此恐惧,而另一些人,比如我,在简化论中找到了终极的宗教。也许是我毕生的物理学和一般科学的训练使我看到最坚固、最熟悉的物体或经验在趋近无限小时逐渐消散,最终成为奇特的非实体以太,成为无数瞬间生灭、有着几乎无法理解的数学活动的旋涡,此时会产生深深的敬畏感。这在我心中引起无尽的敬畏。对我而言,简化论不是“通过解释消除”神秘,而是增加了神秘感。 但是这种惊叹为一种亲属感、一种归属于这些深度的感觉所调节和加强。这使得我们得以重拾18世纪时由于我们感到我们来历不明而产生的与万物的联系感和一致感,不过现在我们对于它的广度和深度有着无法比拟的认识。 因此,唯物主义变得更为深刻,更为丰富,此外,其形式也变得更为多样,因为倡导者们对于我刚才试图说明的若干复杂方面采取的立场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选择无信仰,不仅是因为我们对宗教的评判以及所谓的“科学”的拯救。其他原因还包括我们现在在宇宙中发现的道德意义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起源。现在唯物主义壮大起来了,这一方面是由我们的宇宙图景之中的某些生活方式以及对这个宇宙图景的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改变我们对这个浩瀚宇宙的无目的感的某些方式以及我们对宇宙的惊叹和亲属感造成的。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不前。充满敌意的批评家会反对说,这些只是感情而已。我们感受到深度和伟大,但是这是否与现实相应?如果我们抛开一切宗教和形而上学,是否还存在一个与这些感情相对应的现实?对此我们可以回应道,仅仅发现对事物的一个新的、(据信)更正确的解释根本不会改变我们在这些事物面前所感受到的惊叹或钦佩。因此,我们在解释宇宙的形状或者生命的起源时,完全可以把以下两者一分为二:我们对事物起源的解释;我们对它们所具有的意义的感受。 这个回答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事情实际上要更加复杂。当我们言及我们面对宇宙之宏伟和复杂时的惊奇感时,或者言及世界在我们心中激起的爱时,这就是我上文所说的强评价。它们隐含的意思是,惊奇是我们应该感受到的;无法产生惊奇感的人缺失了某种东西,他们由于某种原因对于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对象感觉迟钝。在这方面,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偏好,例如对冰淇淋口味的偏好(举一个无足轻重因而反差显著的例子)。我喜欢草莓味,你喜欢香草味。互相指责对方没有看到某些东西是荒唐的。 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对比。强评价背后的认识是,它们追踪到某种真实。可以提出一个问题:那个物体真的值得尊重或感到惊奇吗?那个物体可能会激发起你心中的爱,但是它值得爱吗?显然,这些争论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是的,我们应该大胆行事,但是那(盲目对敌人发起进攻)是真正的勇气吗?我们应该慷慨一点,但是那(花费公共关系预算来提升公司形象)是真正的慷慨吗?再举一个(令人相当吃惊的)对比:我们对某些事物感到恶心;我们说这些事物“令人恶心”。争论真正令人恶心的是什么是否有意义?我想到的是字面意义,即某些物质的外观或气味令人无法忍受;此外当然还有道德含义,例如当我说一个政府决策令人恶心。显然,在直白的、字面意义的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令我们感到恶心的是一个无情的事实(brute fact);某些事物恰好引发这种反应,其他事物则不会。如果存在人际差别的话,它们也属于无情事实的范畴。无法对它们做出公断。 这些对比表明以下事实,即强评价背后隐含着事情的某种真实性。这无法与有关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反应的事实分隔开来。简言之,我们的道德反应认为,它们是对某种现实的回应,如果误解了这种现实可能会遭到批评。但是说到恶心,就不能这样论述;现实与否的问题无立足之地。 如果我们记住这个区别,也许就会赞同以下观点,即没有理由认为从有神论的现实观转变为唯物主义的现实观就会削弱我们对宇宙的惊奇感,尽管关于是什么引起了惊奇感的看法将会不同,而且对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而言将会与不同的事物相联系。 但是让我们看一下社会生物学的观点,它宣称能够证明人类行为和所有的动物行为一样,是受到“自私”基因的驱使。确实存在“利他”的行为模式,在这种行为模式中,一个行为者损己利他;但是其背后的动机并无区别。这必然会破坏那些欣赏利他主义的人的一部分关键性背景理解。为什么?因为欣赏利他主义不仅意味着他们发现这种行为模式有用,还意味着他们认为为利他主义提供动力的那个动机在某些方面更高、更高尚、更令人钦佩。这种主张只有基于以下背景观点才有意义,即人类动机可以转化,从而越来越受到更高事物的吸引,最终让我们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这一背景也比单一的动机等级划分来得丰富;必然会有某种解释,说明为什么某一种动机更加高尚:因为它通过各种方式带来真正的和谐,与我们的真实自我相应,促成我们梦寐已久的人类之间的统一与和谐。正是由于以下主张,即我们从根本上来说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才使得这整个背景观点遭到否定且无法成立。 我们可以从尼采对基督教的攻击中看到类似的情况。基督徒谈论“仁爱”、“爱”,以及转过另一边脸。但事实上这是谎言。因为我们其实都受到权力意志的驱使。基督徒的行为事实上是受到一种欲望的驱使,他们想要报复甚或支配那些在权力斗争中胜过他们的人。再从基督教角度来看,付出额外的努力、进一步推行无私的爱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我们朝着更像耶稣和上帝的转化之路上的一步。如果这整个前景都是错觉,如果我们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同样的权力意志的驱使,那么这种期盼将徒劳无功;整个人生观将崩溃。这仅仅是尼采观点中惯常出现的又一个反讽,他告诉我们,这里的“爱”其实是受到它的对立面,即愤懑和仇恨的驱使。 因此,一方面当然可以说,以上双重意义的祛魅,以及去除宗教,本身并无法削弱非常强大的人类意义,例如一种惊奇感、对世界和对他者的爱,诸如此类;另一方面,某些有关人类生活和行为的还原论解释却将它们排除在外。我们不能只说,关于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些意义的解释与它们是否正确无关;或者,它们言之成理,因为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了它们。我们只有弄清这些意义的属性才能使我们的主张更加令人信服。需要认识到它们的本质是强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声称它们具有真理、现实性,或客观正确性。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我在上文描述的对现实产生过惊奇感的人觉得有必要解释它和明确表达它。我们在上文看到,一个完整的背景理解构成不同的利他主义伦理学的基础。对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而言,这种背景是不同的,但是两者都不能仅仅建立在单纯的反应之上。一个人可以认为,在人类生活中这样的反应是第一位的,所有构想哲学和宗教理论的尝试都源自表述那些反应的需要。但是这些表述并不是派生的和次要的。每一种表达类似反应的方式都在修改它、发展它,给它一种不同的趋势。因此,我们在今天的人道主义工作中看到,各种信仰的人,无论是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在并肩合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受到同一种冲动的驱使,但是在共同的奉献背后有着一些非常不同的伦理观:关于人类生活、关于转化的种种可能性、关于采取何种精神或心智准则模式等的不同观点。 但是这些阐述并不完整。它们留下了可供神秘性闯入的缺口,对真理的断言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貌似有理的反驳犹抱琵琶半遮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必须要有某种程度的信仰才能从原则上克服这些困难。无论是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困难,还是“基于信仰的”困难,这一点都适用。事实上,尽管缺口和不确定性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个条件可以运用于一切人道主义的努力中,无论其动机是什么。 有些人也许会惊讶于在伦理道德领域居然能够做出真理的断言。我们如何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转化的某种方向,成为圣徒,或成佛,或者成为一个纯粹的康德的意志,真的可以实现,而这一路上并没有关键的障碍?事实上,古典的“科学”方法无法表明,我们能够找到某种实相,它与希望相对应,而且能够证实这种希望。一些人(佛陀的常随众、耶稣的门徒)相信他们看见了这样一种实相,但是他们无法向没有见过实相的人显示它。事实上,我们对自己信仰所具有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另一条路径获得的,即撕下我们幻觉的假面具,使得我们能够抛弃早先更值得怀疑的观点。当然,这个过程永远也不会完成,但是能够从这种去伪存真的步骤中留存下来的观点总要比不能留存下来的观点可信一些。 三 以上讨论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以下问题:一个对于世界的科学描述怎样令它彻底“祛魅”,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们所说的返魅?显然,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物种是如何进化的这个简单事实(无论这个过程被认为有多么机械论),并不能减少我们对于这个最终系统的广度和复杂程度的惊奇感。我们面临以下事实(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它),即我们可以带着惊奇感来回应;我们还想补充一点,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知识、训练和意识,都能够感受到这种惊奇。 那么,潜在的冲突在哪里?在于这种惊奇感是我们作为强评价加以体验的;它在某些方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崇高,一个人缺乏惊奇感表明其人缺失了某种东西,从而对这些奇迹无动于衷。就像一切我们借来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的强评价,这将与某种还原论解释相龃龉,不是关于太平洋群岛上鸟类进化的解释,而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心理和行为的解释。 这种冲突存在于何处?一个我们理解为强评价的反应以下列本体论为前提:(1)这个反应真正地激发我们,它不只是一个伪装、一种理性化,或者是其他某种欲望的幌子;(2)它在某些情况或某些人身上不会发生,但是这表明那些情况或那些人的局限性、愚昧或感觉迟钝;(3)换言之,这种反应具有某种客观的正确性;(4)我们能够也应该培养这种反应,提高我们对它的专属对象的感知能力。这四点是一个整体,表明这种评价是有基础的。用伯纳德·威廉斯的话来说,我们在道德和其他方面的强评价是“基于世界的”。 用盲目的、机械论的观点来描述鸟类的进化对我的惊奇感不构成重要威胁——尽管在这里有可能产生冲突,假如我的惊奇感与一种对主观意图的信仰紧密相连的话。但是,对我的心理和行动的只允许存在“盲目的”直接原因的描述,因此也就是某些场合下产生这种反应的描述,的确制造出一种冲突,正如我们在上文中利他主义动机的例子里所看到的。在这里,还原论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当我们拥有针对貌似相同的现象的两种描述时(“相同”可以用时空坐标或者用其他识别相同物体的没有争议的方式来注解),还原论解释的问题就产生了。基于后伽利略时代的科学的描述显然有意避免目的论或意向性、目的或评价,认为这些不是构成原因的因素,而承认强评价的、针对我们正在做的事的描述则必然涉及这些因素。关于还原论解释的问题如下所述:我们用“上层”语言(例如人们用惊奇感对宇宙做出反应)描述的现象能否用“下层”语言(后伽利略时代的科学)进行充分的解释?这将尤其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下层语言为所有用上层语言描述的状态提供必要和充分条件。但是,基于“上层”现象所做出的断言,即它们的运作原则与用下层语言充分解释的原则完全不同这个观点,将会被宣告无效。 当然,一些哲学家试图否认人类与机器在本体论上的差别。人类与貌似表现出有目的行为的机器(例如导弹和电脑)的唯一差别,除了复杂性的差异之外,在于我们所赋予它们的立场不同。作为观察者,我们可以对人类和导弹都采取“意向性”立场,也可以把它们视为机械,后者是解释它们所作所为的更有成效的语言,但是两者都用了相同的原则来解释。那么,我们能否认为更为复杂的机器人具有意识和自我情感呢?为什么不能?丹尼尔·丹尼特争辩道。也许机器人觉得它正在努力地、勤勤恳恳地完成任务。但是除了很难把意识和感情归于由塑料和硅酮制造的存在物之外,这种内在知觉对机器人而言只可能是副现象,也许它本身就是借助工程学的大手笔植入的,而不是描述它正在做什么的必要因素。 但是我们整个的道德—评价生命有赖于相反的理解。评价提供动机,它们反映的是对它们的对象的一种感知,这种感知大致是充分的。 一些哲学家欣喜地谈论还原论解释,把它视为几乎确凿无疑的前景,这事实上是非同寻常的,考虑到我们对人类生活和进化的所有了解。对人类意识行为的神经生理学描述,即我们是如何“接通”的,主要在个体有机体的层面上运作,它用这类有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社会组但是人类文化事实上是在社会当中发展起来的。正如默林·唐纳德所指出的,语言不是由哪个人独立发明的,更不用说人类文化了。遭人遗弃的孩子,或者像海伦·凯勒那样的残疾人,仅靠自己永远都无法习得语言,也无法在意识层面把握事物,这只有靠语言才能做到。此外,婴儿大脑的“接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早期抚养过程中所学到的事物,这些事物因文化不同而不同。没有人能够先验地否认,所有这一切可以用对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形成和运作的单线逻辑的、具有直接因果性的描述来捕捉到,但是看清如何做到这一点不是容易的事。 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文化的进化带来了新的强评价,例如我们今天赖以生活的那些强评价(如民主和普遍的人权),而且我们给任何一个希望能够更加充分地描述人类进化的人准备了相当详细的议程表。这是一个极为有价值的目标,但是我们该如何来实现它并不是非常明朗。 从上文可以推知,祛魅和返魅的问题至少在两个层面上出现。首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在文章开头所描述的祛魅(被施了魅的世界的瓦解、对伟大的生存之链的否认,以及对西方有神论的普遍排斥)是否使具有任何人类意义的宇宙变得无效。尤其是我还提出,对宇宙的惊奇感没有进一步的基础,这种惊奇感继而可以激发人类对他们所处的更伟大的整体的爱甚至是感激。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无疑问,以某种方式表述的一些惊奇感的模式将遭到决定性的削弱。但是,基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亲身经验的其他形式能否被恢复,这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我觉得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以这种方式,“科学”的陈述可能会削弱肯定的回答,我指的是某种形式的还原论解释,它不是针对宇宙,而是针对人类生活的。这也许是现代文化中极其严重的一个思想问题。 当然,回到第一个问题,还存在着以下这个问题,即纯粹的人类中心论调是否能够公平对待我们的惊奇感以及其他相关评价。这个问题将继续成为持不同立场(宗教的、世俗的、心灵的,不一而足)的人之间的争论焦点。我们之间的讨论有望结出成果;这里有几乎无限的洞见,没有哪一个观点能够独占鳌头。但是所有这些观点都必须建立在反对针对人类生活的还原论解释之上。 【编辑推荐】 在这个被祛了魅的、世俗的世界中,我们可以过上有意义且丰足的生活吗? 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心理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生物学问题。 本书特别以跨学科的视野,重新审视这个关乎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不同领域的专家观点相互碰撞、交织。你不一定能得到答案,但是也许可以受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