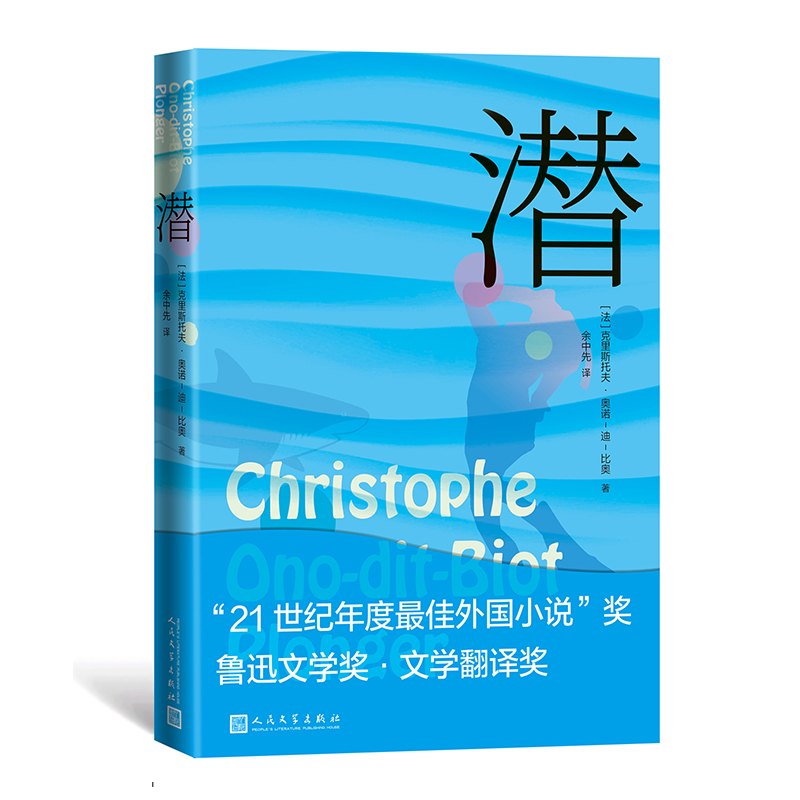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5.60
折扣购买: 潜
ISBN: 9787020129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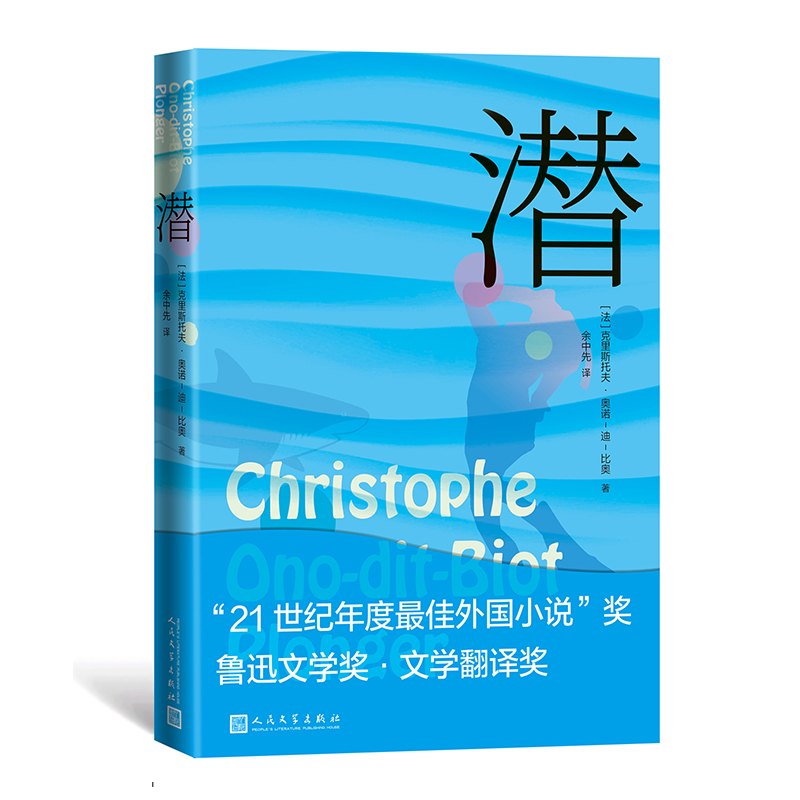
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生于1975年,法国《观点》周刊副主编、记者,已经发表四部小说:《剥蚀》(2000)、《一切女人和雌性禁止入内》(2002)、《直接的一代》(2004)、《缅甸》(2007)。本书获得2013年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和勒诺陀中学生文学奖。
欧洲在死去,塞萨。欧洲在死去,因为它死死地包裹在了往昔中,恰如一瓶莫斯卡。我不愿活在钟罩底下,我不愿活在对往昔的崇拜中。正因如此,我离开了西班牙,历史遗产,往昔的荣光,征服…… 我吓了一跳。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他应该有五十来岁,肤色略略发红,蓝蓝的眼睛,目光锐利,头发很短。他双拳叉腰,穿一件黑色的体恤,我的目光立即就停在了那体恤衫上:众所周知的人类进化的图标——用五幅图画来表示,一只猴子渐渐地站立起来,最后成为一个人——只不过这里多出来一个阶段,多出来一幅图画,在这里,直立人,然后是智人,不是垂直方向,而是水平方向行进的,头戴着棕榈树的叶冠,嘴里吐着泡泡。他成为了潜水者,按照体恤衫图案设计者的意思,这就是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而这当然也是我那对话者的想法了。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后,我发现了一个世界,描述它的时候我将试图不那么过于平庸。在书中,在电影中,我们全都见过水下的生命。但是有一点截然不同,即,在这里,我们自身也属于电影,属于书。短短几秒钟内,我就从大海的表面,从它单色画面的光亮,过渡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运动和惊喜的世界,过渡到了一个如此纷繁复杂的地理环境,它似乎直接出于一个走火入魔的建筑师的头脑,在一种新毒品的影响和推动下,相信一切皆有可能。就让我们付诸实践吧…… 在我的脚下耸立起一座岩礁和珊瑚的真正城市,一座座高塔拔海而起,挑战万有引力定律,托举起镶嵌有蓝色、绿色和黄色花边的,仿佛悬在那里的宽阔平台。一把把巨型的扇子,鲜红鲜红的,恰如在放出火光,波动在看不见的潜流中。一个个强健的大烛台淡泊而显紫红,由其枝杈自由伸展出无穷的分叉,其尖端最终交织成千奇百怪的玫瑰花窗。 我听到我在呼吸。很乱,很不自然,令人焦虑,一颠一颠的。我越是格外注意,它就越是一颠一颠的。我摆动双腿,像是要停靠到一把并不存在的梯子的横档上。马林摁了一下我胳膊上的肌肉,用食指和中指比画出一个“v”字来,然后用这两个指头指定他的面罩,让我瞧着他的眼睛:玻璃镜板后面透出一道专注而又柔和的目光。我试图平静下来,不再踩脚蹼。 我听到我始终在呼吸。更有规律了。 我们沿着暗礁逐渐下降。一些体积庞大的玫瑰色圆拱,像是一个个乳房,勾勒出一条条复杂的盘绕之道,像是巨人的脑回,而在这些脑回上,另一个脑子,大胆无畏的,将会建立起一座座大教堂,带有尖利的钟楼尖顶,以及镂刻有三叶草形状图案的杂乱无章的阳台。哥特式的海底圣殿,一些唇瓣形如波涛、蓝中透着浅紫的双壳类软体动物则把它们当做了圣水缸。更何况这也正是它们的名称。为的是什么崇拜呢?天使鱼成群结队地游过,一条苦行僧般的海鳝从洞穴中悄悄探出身来,伸出它那张可怕的脸,像是要亲吻一个看不见的神。一些独自行动的笨重的石斑鱼,下唇特别厚,带有金色的条纹,似乎准备去开教皇会议。小丑鱼的大军享受着一个海葵抚摩式的敷圣油,因为海葵以其精美的怀抱,如处女手指头一般温柔的纤纤触手,为它们提供了温暖的庇护所。 我听到我在呼吸。越发更有规律了。 兴许因为我忘了,因为我忘了我自己。加在我肌肉上,加在我整个身体上的压力很是舒服,我感觉到一种力量在我体内聚集,让我告别痛苦,告别散乱。 我的眼睛睁开来。四面八方的一切都在涌动,各种各样的色彩与形状在爆炸。在中毒的建筑师之后,现在则是疯狂的神:他的造物拥有极不规则的形状,令人咋舌的色彩,有时候,同一个动物身上就有各种各样的色彩,蓝色的嘴唇,橙黄色的眼睛,绿色的脸,黑色的肚皮,还带有白色的大斑点。有些鱼像是一根笛子,长长的,半透明的,极易受伤的,另一些则像是很灵活的羊皮袋,外表竖满了尖尖的刺。有一些像是赶去舞厅,化妆得如同迷娘,臃肿的嘴唇烘托出粉红,下垂的眼皮粉饰了淡紫;另一些则前往围猎场,如同那三个带鳍的猛兽,披戴了褐白相间的条纹,其展开了的鳞片显得如同一个大酋长头饰上绚丽的羽毛。我们还在继续下降,一直到我们的脚蹼碰到沙地为止。马林跪了下来,我也想那样,但我做不到,我上浮,他抓住我,给我来了一个手势,我相信我看明白了,我应该把我的肺清空。我依法操作。我又下降了,我做到了。我感到沙粒在我套了氯丁橡胶的膝盖的压力下沙沙作响。我俯下身子看景。我们处在最佳观察点,恰如看戏坐在了头等包厢。只见一条灰色的鳐鱼,浑身都带紫色的圆点,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最末端就是一个箭头,悄无声息地从我们身边滑过,裙边在波动。马林拿掉嘴上的呼吸调节含口,抬起头,缓缓地吐气:气泡便朝天升腾。从水下看上去的波浪成了一团动荡不已的云彩,偶尔有辉煌的阳光穿透,就像快要下雨时的诺曼底天空。 我迷醉。被征服。被战胜。 我听到我在呼吸。已经极端地稳定了。 马林竖起大拇指向我示意。得上浮了。时间已到。缓缓地,他示意我。静默的、流动的、和谐的话语。我信任他,我把我的性命交到他手中。一个惊慌的动作,我摆脱了他,这超出了我的限度,我的肺要爆炸,他对我说过。但我为什么要摆脱他呢?他抓住我的胳膊,我很平静。头顶上,一些人形聚合到了一起,两臂交叉在胸前,仿佛失了重。他们盘腿坐在水中,沿着一条看不见的线不被察觉地上升并下降。 我很喜爱写信。但它又不免让我有些羞涩。写信需要打开心扉,直接面对面,同时又得注重形式,因为书简的传统要求文雅。因此,这是一个危险的练习。尤其因为我们彼此还不熟悉,你和我,尽管如此,中国的读者,不久后,你就将读到我,潜入我的想象力,潜入让我幻想和思索的那一切,畏惧、愉悦、渴望,让我经历的那一切,很快地,你就将是我的一切…… 首先解释一下,我在此为何与你们直接以“你”相称:我希望这不至于冒犯你。在汉语中,也有与“您”不同的直接的“以你相称”吧?对我来说,这样称呼是一种信任的体现。我与你坦诚相见。很显然,由此我想到了波德莱尔,想到了他杰出的《恶之花》:“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你能不能接受,我为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而把你称为我的中国兄弟,我的中国姐妹? 要知道——而我本该从这里开始行文的——这个汉语译本让我万分开心。一想到,我的词语,我的句子,还有我在小说中提到的种种形象和种种景色将变为令人赞叹的和强有力的表意文字,一想到,我的那两位主人公——在汉语中“Paz”和“César”会是如何书写的?——将跟这一古老、美丽和坚实的语言,这一我那么渴望能说的语言融为一体,我就感到一种荣幸,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要知道,一想到,这两个穿越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欧洲情人的故事,将在这里,在你的伟大国家被人读到,一想到,他们终于来到了与他们的爱情领地万里之遥的地方,来到了他们本来连想都不敢想来的地方,就会让我从心灵深处激动不已。尽管——我敢肯定——他们本来也会在中国深深地相爱,也会喜欢跨越云南的崇山峻岭,或者航行在波涛滚滚的黄河上,让他们纷扬的思绪随波漂荡…… 我的中国兄弟,我的中国姐妹,这确确实实是一个爱情故事。它很罗曼蒂克,就是说,很绝对,也很悲剧,但它是不会吓坏你的:悲剧揭示出最令人难忘的美。它也是一个关于美,关于伟大的艺术品在人们心底激发起的强烈情感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欧洲这一被大大削弱了的古老文明,关于情感深度的故事,也是一个充满了阳光和海水的故事,一个关于海洋的故事,这海洋,它将让我们这两个情人结合到一起,然后又分开。 这段爱在一个叫帕兹的女人和一个叫塞萨的男人之间展开。小说采用了塞萨向他与帕兹所生的年幼的儿子讲故事的形式,以后,等到孩子大了,他就将翻开这本书来读,就会知道他的母亲是谁。因为,当这本书开始时,帕兹已经死了。有人在一个遥远国家的海滩上发现了她的尸体,赤裸的皮肤上满是晶亮的盐花。她在那里究竟都做了什么呢?出了什么事?当初,事业达到顶峰时,她为什么要匆匆离开欧洲,前往一个陌生的地点,把她爱的这个男子,还有他们共同孕育的这个孩子丢弃在巴黎?她到底要去寻找什么? 帕兹是个摄影家。极有才华。极为漂亮。也极为固执。因为要探寻真相,要把真相告诉儿子,塞萨就独自展开了调查,去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一边展开调查,一边为儿子追溯了他们爱情故事的线条,从他们俩的第一次邂逅,一直到帕兹的神秘离去,而这儿子恰恰正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他是想通过词语,让她栩栩如生地重新复活。 亲爱的中国读者兄弟,读者姐妹,这本书叫做《潜》,因为你也将,通过帕兹和塞萨,潜入到一对欧洲男女的内心中,潜入到他们所喜爱的地点、氛围和气味中,到他们的文学、艺术、遗产、神话、礼仪中,到被人们称作的一种“文化”中。跟他们一起,你将夜游卢浮宫的展厅,摸黑游荡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中间,你还将见识奥赛博物馆中《被蛇咬了的女人》的奥秘。跟他们一起,你将前往威尼斯,在那里的古老宫殿中,出席当代的艺术庆典。跟他们一起,你将在西班牙北方和意大利南方的一些秘密海滩上游泳,神圣地美餐,痛饮。然后,你还将追随他们去往东方,去往海洋的深处,在那里,人们会洗涤一切,在那里,人们将最终亲近本原。永恒? 中国的读者姐妹,中国的读者兄弟,最后,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时,恰逢我儿子诞生,他的诞生改变了我看待生活的方式,因而也改变了我经历生活的方式。我是在这样一个想法的引导下写下它的: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假如一切不得不停止下来,我渴望为他留下些什么?我渴望传承给他什么?答案很快就来到:一个爱情故事。一个在今天发生的爱情故事,有两个沉湎在这一复杂世界中的情人。一个爱情故事,好对我儿子说——同时也对你说,但是,这个,你一定已经知道了,我的中国姐妹,我的中国兄弟——再也没有任何什么比爱更基本、更珍贵、更强有力、更不朽、更普遍的了。它为我们复仇,为我们荡涤一切,重新创造我们,同时还让我们变得更有人性,也更神圣。 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 2014年7月,于马略卡,戴亚 《潜》中译本序言 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Christophe Ono-Dit-Biot)的小说《潜》(Plonger),2013年出版时就获得了当年的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次年,又获得了中国的“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本既好看,又内容深刻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选中它作为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法语卷,又委托我来翻译,确实是我的一个荣幸。而它的翻译过程,对于我也是一个十分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一,小说情节 《潜》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 《潜》探讨了潜入另一种文明的可能性。 初读之际,读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历险小说,或者是一部侦探小说,一部游历小说,一部疑谜小说…… 若是读得更细致一些,读者则会认为,这就是一部反映当代生活、尤其是艺术家生活的写实小说。 男主人公塞萨在巴黎的某家叫做“企业”的大型媒体工作,担任高管,是著名的记者。他对女摄影家帕兹一见钟情,并为她艺术上的成功摇旗呐喊。他想尽办法追踪帕兹,终于获得了她的爱,后来还小施阴谋诡计,偷走了帕兹的避孕药,让她避孕失败,从而有了儿子赫克托耳。后来,当帕兹离家出走后,他一个人苦苦地坚守家中,等待帕兹的消息。当帕兹溺毙海滩的噩耗传来,他迫不得已动身前往阿拉伯海岸,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逐渐地弄清楚了帕兹的死因,同时还弄明白了她离家出走的原因…… 女主人公帕兹是个天才的艺术家,一开始时专门从事沙滩摄影,获得成功后,多次举办个人摄影展。在塞萨的帮助下,她渐渐出了名,在媒体上大获好评。而在个人生活方面,她与塞萨相爱并有了孩子赫克托耳。后来,她一度转而做博物馆内的“人与艺术作品”的摄影,并获得惊人的成功,甚至在卢浮宫举办了个人展。帕兹觉得欧洲文明已是坟墓,不愿意生活在对欧洲辉煌往昔的崇拜和留恋中。就在个人的艺术生涯到达顶峰之际,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欧洲,离开了事业,放弃了摄影,也离开丈夫和孩子,一个人跑到阿拉伯的某海滩,住到一个小棚屋里,去下海潜水,去探索海底世界的奇妙,去关注鲨鱼的生存境地……最后,在一次潜水中不幸因缺氧而溺死。 二,小说人物 《潜》所写的,是塞萨和帕兹所熟悉、所经历的欧洲艺术家和记者的生活。由此,他们所经历的经济危机、恐怖袭击、天灾人祸,也就是一般欧洲人所遇到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奋斗经历,也就是一般欧洲人为生存、为艺术、为人生价值的实现而做出的追求。 塞萨和帕兹这两口子对当代欧洲文明的认识上的分歧,大概是整部小说故事情节发展的动因。探究这个原因,恐怕也是我们探索小说《潜》主题意义的最好方法。当然,我们在此也并不想用三言两语来总结小说的现实意义,更不想学究气十足地归纳出作品的社会学意指。 塞萨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他在巴黎的新闻界和艺术界闯荡多年,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对社会的种种弊病,他看得清清楚楚,但他同时更看到,欧洲尽管充满了危机、暮气沉沉,也还是尚可苟活着的唯一地方,世界的其他地方太乱,不是台风海啸等天灾,就是恐怖袭击类的人祸,那样的乱世景象,他见得多了。他曾经在泰国报道过2004年的海啸灾难,也曾在贝鲁特被伊斯兰抵抗组织逮捕和审问……在他看来,帕兹根本就不了解世界,而他是了解的,他比她要清醒。他知道,全世界都在恐怖袭击的威胁之下,因此,他干脆就不愿意离开欧洲一步,即便要陪帕兹去海滩,他也只想在欧洲的海滩转悠,尽管那里每年都会有一些“奇观”在不可挽回地永远消失。后来,当他不得不前往阿拉伯某地去辨认帕兹的尸体时,他简直就不想从机场的那道安检门越过一步去,仿佛那道门就是一个分隔开生与死、宁静与动乱、安全与危险的“鬼门关”: 我闭上眼睛,我穿过门。短短的十分之一秒,就像人们一口喝干一杯那样短,我度量我所离开的那一切,这个欧洲的美,我孩子的脸,还有那么像你母亲的这个里皮笔下的圣母的脸[……]。 而帕兹,她显然不那么世俗,比塞萨要“野”得多。作者故意把她写成是一个西班牙女子,或者不如说是一个阿斯图里亚斯地方的西班牙女人,经历了当代西班牙社会曲折多变的动乱历史,无疑要比法国男人塞萨更多一些内在的“叛逆”气质。她的艺术创作在构思上就与众不同。海滩能给她一种启发,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的观察视角,以至于当塞萨在报刊上撰文评论她的摄影作品时,会把她的艺术意图完全弄“相反”。夜游卢浮宫,能给她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无与伦比的灵感,启迪她创作出“人与艺术作品”的系列来。个人生活方面,她本来不想要孩子,避孕失败后,却坦然地迎接孩子的出生。当然,她最惊人的举动,乃是离家出走。而且,她很早就收养了一条鲨鱼,通过对小鲨鱼“努尔”的收养,她对欧洲当代文明逐渐形成了一种彻底否定的看法。在她看来,这一文明已经死亡:在她看来,“欧洲变成了一个大博物馆,一个旧时代的天文馆,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临时展览会”。她这样对丈夫塞萨说: “欧洲在死去,塞萨。欧洲在死去,因为它死死地包裹在了往昔中,恰如一瓶莫斯卡。我不愿活在钟罩底下,我不愿活在对往昔的崇拜中。正因如此,我离开了西班牙,历史遗产,往昔的荣光,征服……” 可以猜想,塞萨和帕兹对欧洲文明的不同看法,体现出了作者奥诺-迪-比奥矛盾的心声,这恐怕也是大多数当代欧洲人的内心矛盾。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欧洲文明,只是借人物的口,对这一文明提出了质疑,当然,小说也没有简单地否定非欧洲文明,更没有否定那里的美: 对那些地区堪与欧洲之美景媲美的美视若无睹,实在是太愚蠢了。 没错。我知道,很少有什么能比得上缅甸若开邦的偏僻小镇谬杭上空被太阳光穿透的精彩的薄雾,或者钦族姑娘脸上纹刺上的精美的蜘蛛网般的图案。 我还可以对你倾诉说,跃入到阿布-苏鲁夫温泉中实在是一种享福,是最有滋味的一种沐浴,它就在锡瓦绿洲的心脏,在利比亚的边境[……]。 小说用一些统计数字和小插曲故事,道出了这个地球各处皆不安宁,为塞萨的观点提供证据。而在小说第三部分的“论战者”这一章节,不同身份的人物对当今世界种种敏感问题(经济危机、欧洲衰落、核电站泄漏、生态主义、恐怖袭击、海洋保护)亮出了不同观点,展开尖锐交锋,实际上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塞萨和帕兹不同观点的论据和论点 三,小说主题 帕兹认为,只有在另一种文明中,即在海洋文明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宁静、和谐、生动。而鲨鱼(应该还有鲸鱼、海豚等其他深海动物)的生活价值更应该被看重,尤其因为鲨鱼它们正在遭到人类无节制的捕猎杀戮。 小说借帕兹、潜水教练马林等人物的言行,把人与鲨鱼的关系看得非常重要,甚至超过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鲨鱼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和谐的,人不应该怕鲨鱼,因为鲨鱼并不咬人;人更不应该只为获得一点点有经济价值的鱼鳍而去猎杀鲨鱼。从马林的嘴里,我们甚至还得知:“在某些文明中,鲨鱼不被人看作一个敌人,必须消灭,而是被当做一个神。在汤加群岛,它甚至是一个女神。在斐济,你要想成为一个男子汉,就必须亲吻一条鲨鱼的嘴,如此,它将赋予你它强大的力量。”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关系才是和谐的,理想的。当然,也是野蛮的。但野蛮的,就不一定不好。 这种海洋文明,在小说中被写成为“蓝色”,用西班牙语来说是“azul”,用帕兹的法国式读法则为“assoul”。小说对海洋的描写体现在很多精彩的段落中,包括塞萨本人后来参加的两次潜水,那些细致描写的段落无疑是小说《潜》最好看的部分。但在,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帕兹后来住在海边小屋中所从事的绘画,更具象征性地体现出一种对大海文明的追求和向往。在调查中,塞萨走进了帕兹生前住过的小房子,看到里面都是她创作的题为《蓝色》的绘画,整整一个系列。而这画塞萨不久前才刚刚看到过: 白布上用蓝色颜料画了一幅很精彩的素描。线条粗犷,用力遒劲,是一个躺着的女人,仰卧,赤裸,头发披散着,两腿分开,两脚撑着地面,两手放在身体底下,像是试图要解开束缚住她的看不见的绳子——底下,则是大大的一团黑影。 我在翻译这一段时,十分强烈地感到,那是海洋的一个形象,或者说这蓝颜色的女人就是海洋的象征。帕兹爱上了大海,为了大海,她宁可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抛弃她的摄影艺术。 读者一定会问(其实男主人公塞萨就已经替读者们问过了),帕兹这样背井离乡,抛弃家庭,抛弃丈夫儿子,抛弃艺术生涯,抛弃已有的功名,难道她就不爱他们了吗。小说始终就没有从帕兹的角度回答过这一疑问,但在小说的末尾,有这样一句用西班牙语写的话:“No dije que no te quería. Dije que no podía querer”,小说还用法语重复写了一遍这句话的意思:“我没说过我不爱你。我说我无法爱”。这一反复的强调,应该就是帕兹何以要不惜代价地主动寻求历险和流亡生活的答案。 小说中,塞萨自始至终就一直无法理解帕兹对所谓“野蛮”(也可以读作“海洋”、“孤独”)的需要,读者(在这方面,塞萨应该是读者的代言人)恐怕也无法理解,而直到读者读到这句话时,他们恐怕才真正找到了男女主人公之间内心的差距。无论如何,这一差距是可以看到的,可以找到的,也是可以消除的。只是,在小说中,一切都太晚了。 另外,《潜》中有专门的一章,写到贝尔尼尼创作的“雌雄同体人”赫尔玛佛洛狄忒的雕像。帕兹对这个融希腊男神赫尔墨斯和女神阿佛洛狄忒(维纳斯)的性别特征为一体的的赫尔玛佛洛狄忒十分地欣赏。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帕兹离开丈夫和儿子,独自一人跑到天涯海角去过苦行僧那样清心寡欲的生活,应该是看上了赫尔玛佛洛狄忒的“榜样”。 这个雌雄同体人无疑是一种自身完美的象征。就“性”本身来说,赫尔玛佛洛狄忒是完美的,自身和谐的,而抛夫弃子的帕兹也是完美的,大海更是完美的。在小说,我们甚至还看到,一条叫西庇太的雌鲨鱼竟实现了孤雌生殖,由此联想到,帕兹已经收养了角鲨幼崽努尔,已经欣赏到了赫尔玛佛洛狄忒,从性爱和生殖的意义上,她可以完全不需要男人和儿子了,她已经完成了自我生成,或曰“复生”(reproduire)。而大海,以其包罗万象的繁复性,保障了她的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也体现了以帕兹为代表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小说题目 小说的题目是“Plonger”。“Plonger”这个词,在法语中作“浸入”(faire entrer quelque chose entièrement ou en partie dans une liquide)、“扎入”(enfoncer vivement)、“潜水”(s’enfoncer entièrement dans l’eau)、“跳水”(sauter dans l’eau)来讲,也可以引申为“远眺”(regarder du haut en bas ou de fa?on insistante)、“专心致志于……”(mettre brusquement ou complètement dans un certain état physique ou moral)等意思 。应该说,小说选取这个词作为题目,涵义是十分丰富的。 Plonger在小说《潜》中有时指“浸入”或“专心致志地沉浸于”。在常人看来,女主人公帕兹的艺术活动和平常生活就处于一种“沉浸”状态:她总是特别地专注于摄影(后来则是绘画、刺绣),工作中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漠然傲视的态势。 后来,出现了“扎入”:帕兹一个人赶去阿拉伯海滩,属于某种从高到下的“扎入”,离开大都市的高楼那个“高”地方,迅速跃入到平展的海滩,以及海洋的水下那个“低”地方。 小说中还有很多的“扎入”:读者读到,塞萨和帕兹夫妇俩的第一次性爱是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煤矿博物馆的旧矿井中,是一次真正意思上对“大地深层”的“扎入”。后来在威尼斯,孕育了未来儿子赫克托耳的那一次做爱是在“鲸鱼”的“深腹”中完成的。 连后来那一次在卢浮宫的夜游参观,也可以被看作是女主人公于“黑暗中”对艺术珍品的一种心醉神迷的“沉湎”。因为,在她身上,明显地有“一股热流潜入到皮肤底下”。 Plonger也指“远眺”,帕兹离开了家庭和事业,同时也离开了过于喧嚣、过于危机重重、过于垂暮的欧洲文明,去远眺蓝色的海洋。甚至在离开之前,她就已经在更专注地关心海洋动物的保护事业,关心鲨鱼的收养,她已经从电脑中通过互联网来远眺大海;而来到海边后,她更是在远眺,远眺一种野蛮,一种非现代文明的“文明”。这一点,我们在对主题的分析已经说过了。 Plonger当然还指“潜水”,帕兹最终死于潜水,塞萨最后也在潜水实践中解谜。整篇小说以“潜水”来贯穿始终,而且小说本身也有整整五章(“马林”、“海底”、“水人”、“最长的夜”、“强直静止”)充满细节地讲述到主人公在海洋中的潜水。而且,潜水者的形象,甚至还被描写成了人类进化的最高象征。我们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的“中心”那一章中看到潜水中心的一个教练,穿着这样一件黑色的体恤: 我的目光立即就停在了那体恤衫上:众所周知的人类进化的图标——用五幅图画来表示,一只猴子渐渐地站立起来,最后成为一个人——只不过这里多出来一个阶段,多出来一幅图画,在这里,直立人,然后是智人,不是垂直方向,而是水平方向行进的,头戴着棕榈树的叶冠,嘴里吐着泡泡。他成为了潜水者,按照体恤衫图案设计者的意思,这就是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 这里的指涉影射不言而喻。 小说满篇都谈到了Plonger。在第一部分的“找到帕兹”这一章中,当了父亲的塞萨告诫年幼的儿子:“绝不要忽视你的肉体[……] 加工它,让它变得漂亮、光明、矫健,让它到处潜入,抚摩一切可能的皮肤,浸泡在所有的水中。” “在山上”这一章中,塞萨与帕兹做爱时,想到的是:“我知道我潜入,再潜入,进入到她无限源泉的肉体那最细微的空隙中”。 例子太多,不胜枚举。 我最初把题目译为《潜水》,大致上不算有错,但是,在对“Plonger”的译法绞尽脑汁地费了一番考虑之后,我最终还是把它改译成了最简单、最广义的“潜”。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在此费一些笔墨,如上所述,把Plonger的种种涵义说个大致清楚。 五,小说写作 《潜》的写作特色不少,但我认为值得在此特别一说的,却只有寥寥一二。 小说的语言十分生动,用词讲究。全书的叙述用第一人称进行,也即男主人公塞萨的视角和说话口气。 从结构来看,小说是塞萨对儿子赫克托耳的讲述:除了讲述塞萨和帕兹的相爱、同居、生育、分离、孤独、寻找的主线故事之外,还描绘了巴黎(乃至法国和欧洲)的摄影、绘画等时尚艺术的日常活动和未来倾向,同时也涉及到了当代的国际形势、环境保护、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重大现象,内容可谓包罗万象。 帕兹和塞萨所熟识的艺术界和新闻界在《潜》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这无疑得益于作者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的记者身份,以及他对艺术界的关注。 小说对艺术家众形象的描写采取了虚构和纪实相结合的手法,书中提到的不少艺术家都是史有其人,尤其是,通过帕兹在塞萨的陪同下参加威尼斯双年艺术展的详细描写,小说写出了一些世界顶级艺术名人的实践活动和作品面貌。例如洛里斯·格雷奥及其作品《盖佩托馆》(即搁浅的鲸鱼),查尔斯·雷及其作品《孩子与青蛙》,等等,都有细节上的描写。而略略提及的艺术名人就更多了,如弗朗切斯科·韦佐里、托马斯·豪斯阿戈、胡安娜·瓦斯贡采罗等人。另外,小说中许多真人真事(如法国影后卡特琳娜·德纳芙在巴以前线的遭遇)都可以从奥诺-迪-比奥对黎巴嫩和缅甸的报道中得到佐证。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奥诺-迪-比奥的儿子就叫赫克托耳,而这部小说就是献给他的。这也就让人更容易猜测到小说中的自传因素。 这种把历史名人和当代名人写入虚构小说的做法,是当今小说家很时髦的手段之一,有人把这一类小说称作“vrai-faux roman”。记得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地图与疆域》(2010年)中就有类似的描写。这部龚古尔奖获奖作品,就把小说家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和维勒贝克自己写入了小说,甚至还让作为小说人物的“自己”被人杀死。维勒贝克还让他的主人公杰德·马丁(也是一位画家和造型艺术家)为世界IT领袖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为全球艺术大亨达米恩·赫斯特和杰夫·昆绘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小说《潜》的叙述顺序大致按照历时性纪事方式进行。但也有一些小小的倒叙和插叙。例如,小说一开始,塞萨以一个年轻父亲的语气,回忆了儿子赫克托耳的出生。然后,时间一跳跃,塞萨就叙述起了自己如何接到法国使馆的报丧电话,坐飞机去阿拉伯某地辨认帕兹的尸体。 随后,故事的时间流逝和情节发展就很正常了,从塞萨第一次认识帕兹的物证“除尘喷雾器”谈起,讲到在小店铺中与帕兹的第一次见面,后来又如何买她的照片,为她的作品写评论,为追求她而特地跑去西班牙,在阿斯图里亚斯的旅行和求爱……然后就是在巴黎的艺术家生涯他当他的记者,她拍她的照片。帕兹成名后,两口子不断出席各种展览会的开幕式,她也逐渐走向艺术生涯的顶峰…… 但小说中的一些段落,作者特地用异体字体现,表示故事叙述状态的停顿,转入离题话,或是塞萨对在远方的儿子的谆谆教诲,或是他内心中的祈祷,或是对正在叙述的故事情节作事后的评论与回忆,总之,读起来一目了然,似乎也不必在此赘言评说。 还有一点,小说中,很多的句子不用主语,直接由动词开始,说明动作和行为与上一个句子是由同一人完成的,其间并没有主语的更换。因此,我的译文也保留同样的处理法,句子中不加主语。 其他方面,小说的写作就似乎没有太多的艺术特点了。 六,小说作者 小说作者克里斯托夫·奥诺-迪-比奥1975年生于海滨城市勒阿弗尔,现为法国《观点》周刊的副主编、记者,负责该刊的“文化”版面。已发表小说四部:是为《剥蚀》(2000)、《一切女人和雌性禁止入内》(2002)、《直接的一代》(2004)、《缅甸》(2007)。 其中《剥蚀》获得了拉罗什富科奖,《直接的一代》获得圣召奖和夜航奖,《缅甸》获得了联合文学奖。 2013年的这一部《潜》不仅获得了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同时还获得了勒诺陀中学生奖。 有评论认为,《潜》是对生命和爱情的一种高调颂扬,同时也是对现实社会表象的一种深入,作品中透出了作者对古典文学的爱,对历史,对大海的爱。有评论还用两个词简述了这部阳光和黑暗的美丽作品:活生生地死去。而在写作风格上,《观点》杂志的评论家弗朗茨-奥利维埃·吉斯贝尔(本身也是小说家)认为,小说《潜》明显地受到菲茨杰拉德、端木松、萨冈、贝格伯德等前辈的影响 。 七,小说的翻译 关于《潜》这一小说的翻译,除了书名(上文已有论述),倒是还有几句话可说。 翻译的时间比较短,有些仓促,译文也不甚理想。从3月中旬到7月下旬,整整四个多月,包括了翻译和两遍校改。 初稿完成后,我就在博客上晒了一下翻译初稿的两个相对独立成章的段落:“第一次潜水”与“夜游卢浮宫” 。目的是听取网友的意见。 反馈的意见虽不多,还是很管用。例如,有人提出,小说人物之一潜水教练Marin的名字译成“马兰”不好,有些女人味。于是我接受,就改为“马林”。 对小说原文的理解,我曾有三两处难点,始终查不到答案,需要直接问作者。于是,我电子邮件发去巴黎的伽利马出版社,结果被出版社的编辑挡驾,说是作者很忙,无空回答那么多译者的问题。好在,那位女编辑倒是耐心地解答了我的提问。我倒无所谓,只要疑问得到了解答,谁回答不是回答! 另外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小说的最后几章重点描写了在海中潜水的故事。我在翻译时感觉很亲切,其原因很简单,去年,我下海潜了一回水。那当然还是在翻译《潜》这部小说之前,当时,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旅游,有自费的潜水项目,不知道我脑子里哪一根筋搭错了,全旅游团就我一个报名下了水。那一段潜水的经历,几乎与主人公塞萨的第一次下水一模一样,连细节都一模一样。于是在翻译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如鱼得水的感觉。在此录一段译文: 当我重新睁开眼睛后,我发现了一个世界[……]短短几秒钟内,我就从大海的表面,从它单色画面的光亮,过渡到了一个充满了生命、运动和惊喜的世界,过渡到了一个如此纷繁复杂的地理环境[……] 在我的脚下耸立起一座岩礁和珊瑚的真正城市,一座座高塔拔海而起,挑战万有引力定律,托举起镶嵌有蓝色、绿色和黄色花边的,仿佛悬在那里的宽阔平台。一把把巨型的扇子,鲜红鲜红的,恰如在放出火光,波动在看不见的潜流中。一个个强健的大烛台淡泊而显紫红,由其枝杈自由伸展出无穷的分叉,其尖端最终交织成千奇百怪的玫瑰花窗。[……]我迷醉。被征服。被战胜。 翻译这个段落的时候,我自己当真觉得仿佛又潜了一次水。 至于潜水的装备,我则询问了比我资格老很多的爱潜水的出版人吴文娟女士,得到了她令人可信的解释。 《潜》写了一个最终死在阿拉伯的西班牙女人的故事,这使得小说作者有意地在法语原文中用了不少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的句子和单词。不懂西语和阿语的我,在翻译时就不得不求助于方家。好在朋友中有专家可请教,林丰民、杨玲、宗笑飞的解答给了我一个明白,也给了我翻译时的自信。 由此,回想起当年我翻译《复仇女神》的情景,作品中有大量的德语、俄语,我就请教了同一单位的杜新华、苏玲等专家。翻译外国文学,光懂一门外语,似乎是远远不够的,但若是有很多懂得其他外语的人可请教、可信赖,翻译也就可做了。 余中先 2014年7月19日初稿于蒲黄榆寓中 7月24日修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