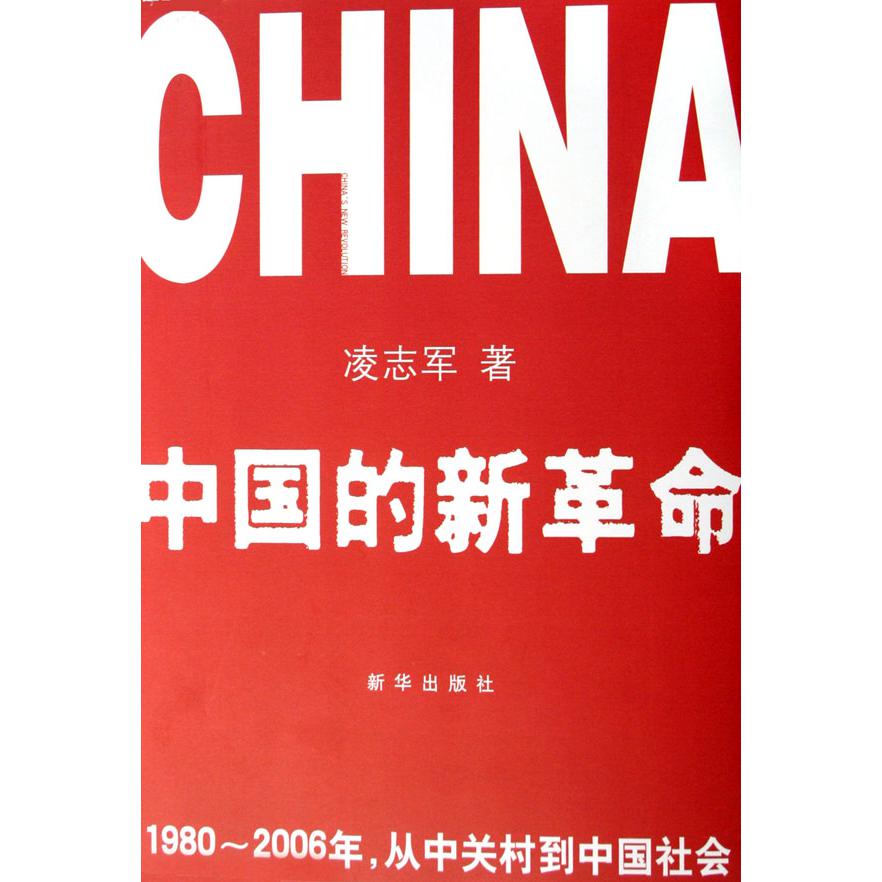
出版社: 新华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7.06
折扣购买: 中国的新革命(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ISBN: 97875011792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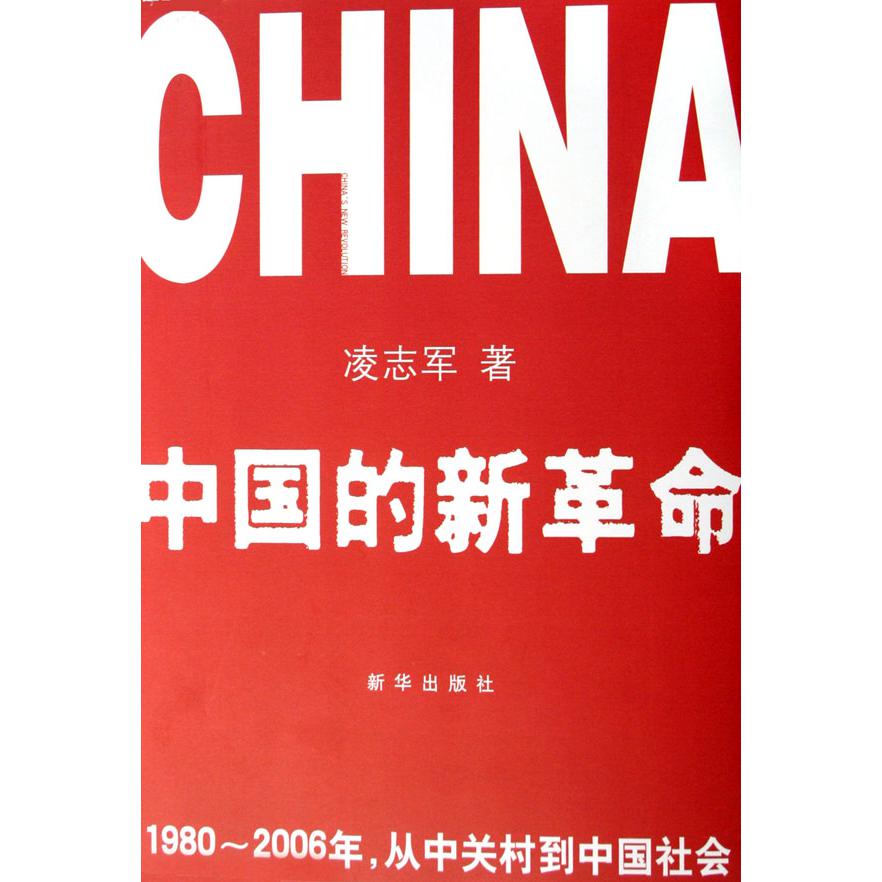
凌志军,祖籍广东,1953年生于上海,长在北京。十五岁到工厂做工,十六岁做农民,十九岁当兵,二十五岁成为新华社记者。三十岁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三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凌志军是当今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中国的威廉·曼彻斯特”、当代中国记者的“标杆”。2003年《南风窗》年度人物。他的每一本书都引起巨大反响。他拥有广泛的读者。他在过去十多年间连续出版九部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7年出版的《中国的新革命》,被境内外媒体和研究机构评为当年“值得记忆的好书”、“年度商业书”、“最佳商业图书”。 2005年出版的《联想风云》,入选当年“最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最佳版权输出图书奖”。 2003年出版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体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 2000年出版的《追随智慧》,被媒体评为当年“最佳纪实文学”。 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1996年出版的《历史不再徘徊》,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
最迟到1985年春天,中国人已注意到,出现在白颐路上的气氛与他们习 惯的那一套颇为不同,于是出现了“电子一条街”这个新名词。其实,我们 把它叫做“中关村的商业体系”更确切。因为直到这时,这个国家还没哪个 重要发明能够通过自由交易渠道成为老百姓手上的消费品,而这个历史,就 要被这条街上的散兵游勇们给改变了。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选择在白颐路落脚,显然是看中了这里的商业设施 和人来人往。这条马路如今已经改名为中关村大街,那时候它没有这么宽, 也没有这么长。来到这里的北京人能看到些什么呢?首先,他们能看到它的 繁华集中在北端的一片狭小地带,也就是今天四环路和中关村大街的十字路 口。这一点倒是和现在的情形差不多。但是除此之外,面目全非。那时候马 路两面没有那些外观张扬华丽的高楼,现在海龙大厦的所在地,当时是海淀 区的供销社。现在的图书城,当时是一片平房组成的小小的商业区,与海淀 区政府机关比邻而居。一条小路从东南到西北穿过去,当地人都叫它“斜街 ”。斜街上最辉煌的建筑就是80年代早期兴建的一个蔬菜自选商店,里面都 是新鲜货,任由顾客挑选。如今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可那时,它却是京城 第一家超市,所以接连好几天都是报刊上的一个新闻,让人惊喜。从这里向 东延伸,也就是现在“科贸电子商城”占据的那片土地上,当时有个宾馆叫 “宜宾楼”,灰砖绿瓦,坐东面西,是一座颇有皇家风格的建筑。它的一侧 是个五金店,每天兜售铁丝、钉子、钳子和门窗合页之类的东西;另一侧是 个洗澡堂。澡堂里的浴池由水泥砌成,长达6米。那年代百姓人家没有浴室 设备,所以大都选择工作单位里的公共浴室。如果这些浴室人满为患或者出 了故障,白颐路上的居民们就会跑到这个澡堂里来,有科学家、工程师、教 授、干部、工人、学生、商店店员,偶尔还会夹着几位农民。花两毛钱就能 在里面泡上一整天。 然而从1985年开始,来到这里的人们发现街头多了一些新招牌,都是陌 生名字,越来越多,迅速侵蚀着原来的一切。蔬菜店、杂货店、五金店、洗 澡堂,全都变了脸。人们只知道,这些新招牌后面的柜台,不是卖电脑,就 是卖电脑零件。沈仁道在海淀区区委副书记任上已16个月,所以成了这段变 迁的一个活的见证。他原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教师,而且从未改变自己的教 师习惯,总是在下班之后去买菜。他眼看着那些蔬菜日杂商店变了模样,怀 着一种好奇心走进去,就看见“门后面有一个玻璃柜,里面摆着乱七八糟的 什么电子产品”。柜台后面的那些人都是他熟悉的打扮和做派,说出来的话 也和他在北大校园里听到的差不多。“就是知识分子啊,从研究所出来,两 三个人聚在一起,搞个小公司”。他们满嘴“新技术”,其实只不过是在做 买卖。有些部件是从香港弄来的,那叫“进口”。当时京城有好多新名词, 用来形容这些新时代的劳动者。买进卖出赚取差价的,叫做“倒儿爷”;蹬 辆平板三轮车拉货载人的,叫做“板儿爷”。“这些人,”沈仁道说,“既 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啊!”这话是有一点根据的。后来那些有头 有脸的人物,比如联想的柳传志,还有华旗资讯的冯军,都曾推着平板车拉 电脑。 变化如此迅速。以至这段长度不过一公里的大街很快便不能容纳,向东 扩张。东边那片土地叫黄庄,这名字直到今天还没改变,在当时是条东西走 向的马路。它是白颐路的延伸段,所以很快便成了新公司的“殖民地”。连 接白颐路的交叉口上有个点心店,原本是那些家境稍好、好吃甜食的当地人 经常光顾的地方,这时首当其冲,最先“沦落”。“点心店变成了电子店。 ”谭左亭说。她是在白颐路西侧的民族学院里长大的,从小学直到大学一直 都走在这条马路上。如今她是中关村科技担保公司的总经理,满脑子都是贷 款、利率、保证金这些东西,可是童年的记忆里有个烙印永远不能磨灭,就 是这家点心店。“那时候它就好像是我们家的装满好吃东西的橱柜子。”但 是在1985年,“对,就是在1985年”,她肯定地说,“白颐路变了”。一天 早上,几个年轻人闯进来,摘去点心店的招牌,把一大堆电子打印机搬进来 ,连个营业执照还没有,政府也不知道,这就完成了商业史上的一次除旧布 新。 “电子一条街”出现在躁动、纷争、摈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又是 生长在这样一片沃土上。有谁料到,那些由旧世界的教条主义培养出来的人 们,一旦到达这片土地,却成了新世界的开拓者。以矢志不渝而闻名的红色 中国共产党人,竞一跃而为白颐路上机变百出的风云人物。随着夏天的到来 ,白颐路的气氛也更加热烈。以“发展新技术”自我标榜的早期创业者们, 力图把自己与旧式商场上的芸芸众生区别开来,依靠那个时代的混乱秩序、 政府的不知所措,以及整个社会的欲望和梦想,来获得利润。 新开张的商店已经连接起来,店后面还有店,从南端的白石桥开始,沿 白颐路向北,直达黄庄,再由两条平行的马路向东延伸,穿过中国科学院的 那些大院子,形成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F”。这是“电子一条街”的最初 形态。除了“两通两海”之外,还有41家公司,这是很多年以后官方公布的 数字,可是有些人的估计要超出很多。邵干坤说:“早已超过200家。”鲁 瑞清说:“进入统计数据的有148家”。后者当时是海淀区供销社主任,在 这条马路上多年从商、也掌管着几乎所有商店的动向。“新公司都是做买卖 的。”他说,“谁做呀,就是中科院的知识分子,把国外的产品拿进来卖。 ”他领导的供销社当时拥有一栋楼房,就在今天科贸电子商城的那块土地上 ,他把它租给四通和联想,一个在楼下,一个在楼上,很快就成了“最大卖 场”。 这样看来,“电子一条街”的早期历史在本质上并非技术革命,它是一 场地道的商业运动。这从新公司群体的早期交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1985 年夏天,陈春先领导的“华夏”成立已有12个月,尽管此人以“新技术开发 和转移”而扬名,可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唯一的大宗收入,却没有一点“技术 开发”的味道。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代理商”的角色,所以对于很快到来 的危险局面,也就完全不能掌控。 那是他与科学院北京器材供应站之间的一笔总额320万元的生意。按照 合同内容,华夏将“负责开发并提供100套有完整硬件、软件、外部设备配 套的微计算机系统”。陈春先如约拿到40万元定金。他向属下宣布,这一计 划能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华夏的生死存亡”。然而此项合约的令人难以置信 之处,是全部微机系统必须在130天内交付。我们已经知道,当时全中国只 有电子部六所拥有开发微机的能力,其第一台微机——“长城—0520”尚处 实验室的阶段而不能批量生产。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当华夏签署这桩合约时 ,他们心里想的只不过是一个贸易计划。 这一点在公司文件中得到证实。随后华夏所谓“开发”,只不过派出一 个名叫梁瑞森的员工,乘着飞机“往来于广州、北京之间”。梁瑞森在颠簸 往还104天之后拿到首批货物,总计66件,1133公斤,全部为计算机组件。 这时候交货期限已迫在眉睫,情势急迫,他竟租用一架飞机把货物空运至京 。15天后,又有第二批货物装入4个集装箱中,由广州经由铁路运达。根据 公司文件记载的情形,华夏当时无法应付如此紧迫的局面,所以立即召集电 子所、计算所和物理所的大批员工,加班加点,不分昼夜。于是“奇迹出现 了”:14天后,全部微机都被组装起来,调试完毕,通过鉴定。 公司就像过节一样。因为的确是个“奇迹”。不过,它肯定不是“新技 术开发的奇迹”,而是“新技术贸易的奇迹”。事实上,这是我们今天可以 查阅到的中关村大规模代理贸易的首次记录。根据有案可查的文件,这笔交 易到最后已达到1364万元,已经远远超过最初的合约。 “代理商”的概念直到1992年才在中关村立住脚,成熟的“分销制度, ,也是在那以后渐渐形成。然而早在1985年,陈春先就通过进口散件加以组 装转手倒卖的办法来兜售微型机。当然他的这宗交易后来并未成功,华夏不 仅没有获得利润,而且还导致一场致命的官司,终于一蹶不振。这一点我们 在后面还要详说。现在只须特别强调,这位“中关村第一人”,与其说是“ 科技第一人”,倒不如说是“科技贸易第一人”。 P6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