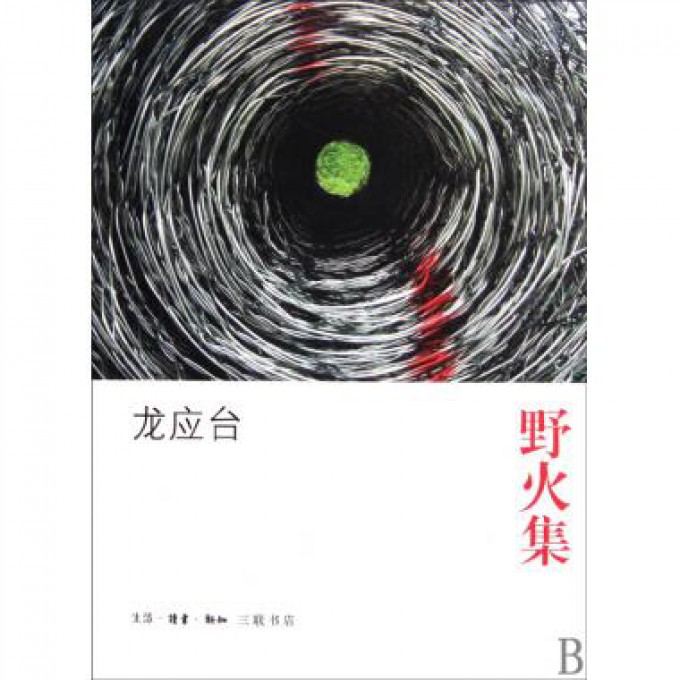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27.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野火集
ISBN: 97871080345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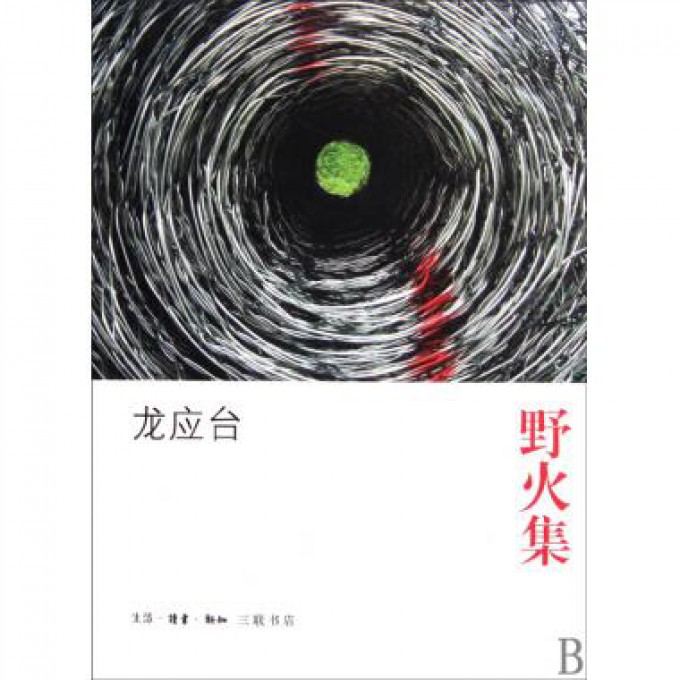
龙应台,近年来常驻三个地址:香港沙湾径二十五号滨于海,台北仰德大道白云山庄藏于山,金华街月涵堂隐于市。写作教书兼成立基金会推动全球意识之余,最流连爱做之事,就是怀着相机走山走水走大街小巷,上一个人的摄影课。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 ,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 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 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 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 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 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 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 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 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 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 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 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形。从小 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 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 育。 二十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 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 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 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 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做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 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 等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 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 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 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 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 ”(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 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 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 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 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 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 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 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 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 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 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 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 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 、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 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 ,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 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 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 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 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 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 听同一个人有系统地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 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 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 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 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 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 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 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 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 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 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 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 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 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 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 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 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 ,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 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 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 ,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 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 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惰,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 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人 ?这是不是又牵涉到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 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 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 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 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P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