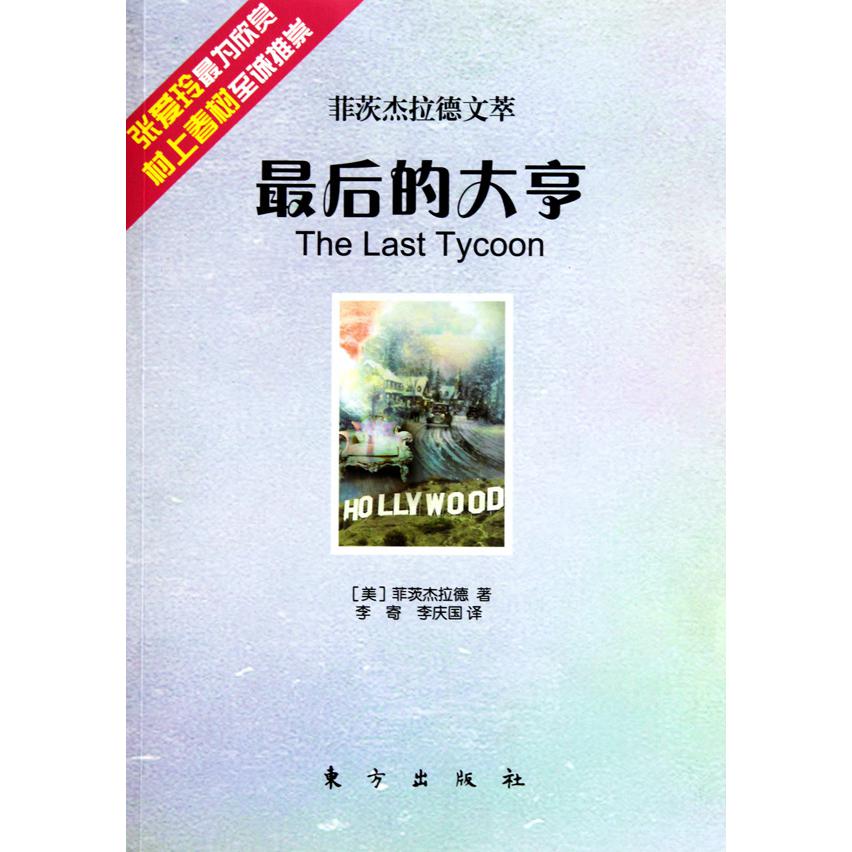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21.42
折扣购买: 最后的大亨(菲茨杰拉德文萃)
ISBN: 9787506039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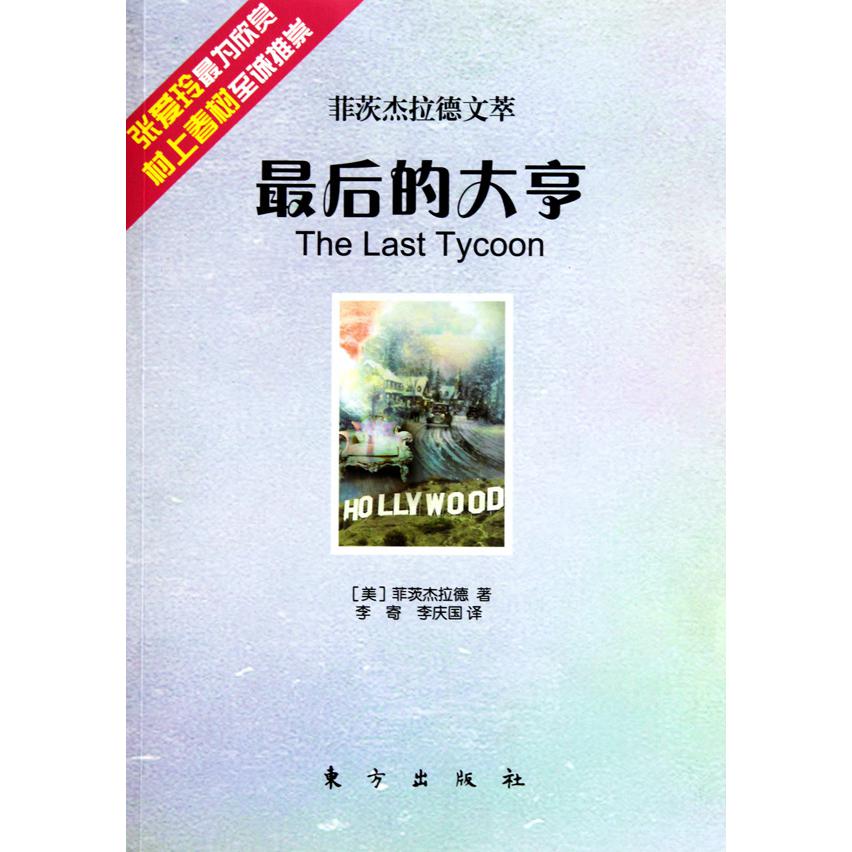
李寄,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外语教学。译著有《伍尔芙随笔全集》(第一卷)等。 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二十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以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为“爵士时代”吟唱华丽挽歌。短短四十四年的人生,他的遭际几经跌宕,在名利场中看尽世态炎凉。二十世纪末,美国学术界权威在百年英语文学长河中选出一百部最优秀的小说,凝聚了菲茨杰拉德过人才华的两部长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均榜上有名,前者更高居第二位。 菲茨杰拉德的另一大成就是他的多达一百六十部的短篇小说,本书选录的《返老还童》(直译作《本杰明·巴顿奇事》)和《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是其中富有奇幻特色的代表作,结构奇特,概念新颖,文字则如诗歌般行云流水。二○○八年,好莱坞斥资一点五亿,打造“大卫·芬奇(导演,代表作《七宗罪》、《搏击俱乐部》等)+埃里克·罗斯(编剧,代表作《阿甘正传》)+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的梦幻组合,将《返老还童》搬上银幕,使得这部小说“返老还童”,跻身当代经典行列。
7月的一个夜晚,九点。在制片厂对面的杂货店里还聚集着三三两两的 临时演员。当我停下车时,看得出他们在埋头玩着木柱戏。老约翰尼·斯 旺森身穿牛仔式服装,独处一隅,神情忧郁地凝望着月亮。他曾经像汤姆 ·米克斯和比尔·哈特一样,也是大牌明星;现在,我实在不忍心跟他打 招呼。我匆匆穿过街道,走进大门。 制片厂从来没有绝对安静的时候。总是有技术员在实验室和配音室值 夜班,维修部的工人到食堂吃夜宵。车胎减速的啸叫,马达空转的低鸣, 女高音歌手在扑面而来的夜色中对着麦克风无伴奏的歌声:各种声响交汇 在一起。在拐角处,我遇见一位穿着橡皮靴的人在奇妙的白光下冲洗汽车 ——这是死寂工业阴影下的喷泉。当我看到马库斯先生在行政楼前被扶上 汽车的时候,我放慢了脚步。他花了好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甚至是晚安 的问候。在我等待时,我听清楚女高音歌手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的是:“来 吧,来吧,我只爱你一个。”我记住了歌词,这是因为地震时她不停地唱 着这一句。五分钟之后地震发生了。 父亲的办公楼位于一座有着长长的阳台和铁栏杆的旧建筑物——让人 联想到不停地走钢丝。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斯塔尔的在一边,马库斯先生 的在另一边——今天晚上一溜都亮着灯。 在靠近斯塔尔的时候,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 。回来之后的一个月里我只见过他一次。 父亲的办公室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我简略地说几句。坐在外间的 是三个面无表情的秘书:伯迪·彼得斯,莫德·(姓不详)和罗斯曼莉·施 米勒。自从我记事开始,她们就像巫婆一样坐在那里。我不知道伯迪是不 是她的真名字,但不用说,她是三个的头儿。在她的办公桌下有制动装置 ,让你进入父亲的“王宫”。三个秘书都是激进的资本主义者。伯迪制定 过一条规则:打字员若被发现在一起聚餐,每周超过一次,就要受到严厉 训斥。那时候制片厂就怕暴民统治。 我继续朝里走。今天所有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有巨大的客厅,而在我父 亲时代他是第一个。他的客厅也是第一个在巨大的法国式窗户上装有单向 玻璃。我听过传言说地板上有个陷阱,可以把不受欢迎的来访者摔进地下 的土牢,但我相信这是捏造出来的。威尔·罗杰斯的巨幅油画醒目地挂在 墙上,我想这是为了显示父亲与好莱坞的圣弗朗西斯的亲密关系。另外, 墙上还挂着斯塔尔死去的妻子明娜·戴维斯的签名照片,其他电影厂名流 的照片以及一幅我和母亲在一起的巨大的粉笔画。今天晚上,单向玻璃的 法式窗户打开了,一轮巨大的金黄色的月亮四周笼着一圈雾霭,从其中的 一扇窗子无助地照了进来。父亲和雅克·拉博维茨、罗斯曼莉·施米勒正 端坐在客厅前部一张大圆桌旁。 父亲长得什么样呢?我无从描绘他。只有一次我在纽约不期然遇到他 。我注意到他是一个身材魁伟、步入中年、看上去有点羞怯的人。我希望 他再走近一点——这才看出这个人就是我父亲。过后我对这个印象感到震 惊。父亲原本是很有魅力的。他的下巴轮廓分明,带着爱尔兰式的微笑。 至于雅克·拉博维茨,我不想多加描述。只用告诉你他是制片助理, 有点像苏联的人民委员,仅此而已。斯塔尔是怎样挑选这些思想僵化的人 ,又是如何容忍他们硬安插在他身边,特别是如何使用他们的,总让我感 到震惊。每一个刚从东部到达的人,与他们一接触,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如果非得说有,雅克·拉博维茨当然也有其优点。那些在显微镜下边难以 观察的原生物也有,那些四处逡巡寻找交配的母狗和寻找骨头的公狗也有 ——哦,我的天哪! 从他们的表情,我肯定他们在谈论斯塔尔。我想大概是斯塔尔发出指 令做某事,或是禁止做某事,或是公然违抗父亲,或是让拉博维茨的一部 影片报废,或是发生了什么灾难性的事件。这一伙人在夜晚聚集在一起, 进行徒然无助的抗议。罗斯曼莉·施米勒手里拿着拍纸簿,似乎准备记下 他们的沮丧。 “好歹我要开车接你回家,”我对父亲说,“那些生日礼物放在包装 袋里都腐烂了!” “生日?”雅克赶忙道歉,“多大岁数?我怎么不知道!” “四十三岁。”父亲明明白白地说。 他实际上比这个年龄要大——大四岁——雅克知道。我看到他把这写 在记事本上以备未来之用。他手里拿着记事本翻开着,无须依赖唇读就可 以看清上面写的东西。罗斯曼莉·施米勒被迫仿效着在拍纸簿上记点什么 。当她试图擦掉记下的文字时,大地在我们脚下颤动了。 我们这儿的震情虽没有长滩那儿厉害——那儿,商业楼的上几层砸到 大街上,几家小旅馆被扔进大海里——但整整一分钟,我们的五脏六腑随 着大地的五脏六腑在翻腾,像是梦魇试图用脐带把我们重新拴起,再把我 们抛回孕育生命的子宫一样。 母亲的照片掉落地上,现出一只小保险箱。罗斯曼莉和我疯狂地相互 抓着对方,一边尖叫着一边跳着华尔兹似的滑到房间另一边。雅克晕倒了 ,至少是暂时消失了。父亲竭力抓住办公桌,喊道:“你们还好吗?”在 窗外,女高音歌手正唱到“我只爱你一个”高潮处,突然停了一会儿,然 后——我敢起誓——又重新开始唱起来。也许,有人在用录音机重放录音 。 晃动了一会儿,房间平稳下来,我们朝大门走去,包括突然又重新出 现的雅克。我们踉踉跄跄地穿过前厅来到装着铁栏杆的阳台。几乎所有的 灯光都熄灭了。到处是一片哭声和叫声。一瞬间,我们停住脚步,等待第 二次震动。然后,似乎是一种相同的冲动,我们穿过通道走进斯塔尔的办 公室。 办公室非常宽大,但没法跟父亲的相比。斯塔尔正坐在沙发一角用手 擦眼睛。地震发生时他正在睡觉,他还不能肯定他梦到了地震。当我们告 诉他怎么回事时,他觉得一切挺滑稽的。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了。我尽可能 不唐突地观察他的举止。他听着电话和对讲机,脸上显出疲惫的青灰色。 不过,听完汇报后,他的眼睛又有了神采。 “有两三根主供水管道爆裂了,”他对父亲说,“他们正赶往后摄影 棚。” “格雷正在‘法国村’拍片。”父亲说。 “‘车站’附近也淹了,还有‘丛林’和‘城市一角’。有什么办法 呢——好像没什么人受伤。”顺便,他神情严肃地握了握我的手,说: “最近去哪儿了,塞西莉亚?” “你打算去那儿看看吗,门罗?”父亲问。 “等所有的消息都送过来再说。另外,有一根输电线断了——我已派 人去找鲁滨逊了。” 他让我和他一道在沙发上坐下来,再次谈起地震。 “你看上去有点疲倦。”我做作又慈母般地说。 “是的,”他表示同意,“晚上我无处可去,所以干脆就工作。” “我来给你安排些晚间活动。” “结婚之前,我和一帮伙计打扑克。”他陷入沉思,“但他们酗酒致 死。” 他的秘书杜兰小姐走了进来,带来新的坏消息。 “鲁比一来什么都会收拾好的。”斯塔尔安慰父亲。又转过身对我说 :“有个人——就是那个鲁滨逊,他是个检修工,曾在明尼苏达的大风雪 中修过电话线——什么都难不倒他。他一会儿就来——你会喜欢鲁比的。 ” 他这么说,似乎让鲁比和我见面是他终生的意愿,似乎地震就是他安 排的——为了这个缘故。 “是的,你会喜欢鲁比的。”他再一次说,“你什么时候返校?” “我刚刚到家。” “整个暑假在家?” “不,我会尽快回去。”我说。 我如坠入云雾中。我并不是没有想到他可能会对我有所打算,但还处 于令人不快的初级阶段——我仅仅是“一个不坏的财产”。像嫁给一个医 生之类的想法在当时对我没有吸引力。他很少在十一点之前离开制片厂。 “她还有多久大学毕业?”斯塔尔问我父亲,“我一直想问这一点。 ” 我想我当时就要迫不及待地说我根本不需要回去,我已受过良好的教 育了。就在这时,那位被说得神乎其神的鲁滨逊走了进来。他很年轻,弓 形腿,红头发,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 “这位就是鲁比,塞西莉亚。”斯塔尔说,“来吧,鲁比。” 我就这样遇到了鲁比。很难说这是命定——但确实如此。因为后来鲁 比告诉我斯塔尔那天晚上是如何找到他的爱的。P1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