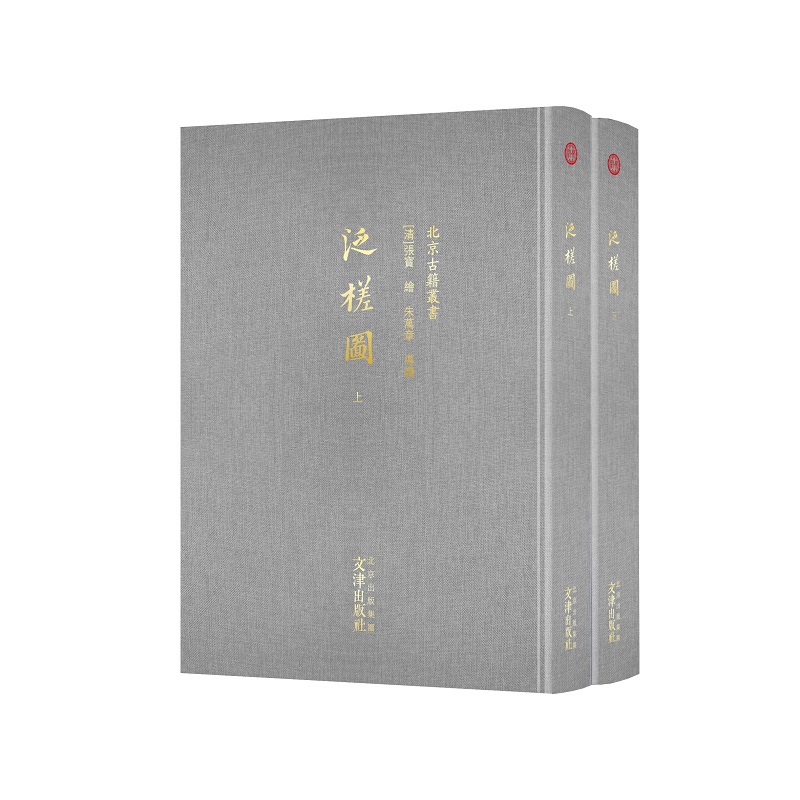
出版社: 文津
原售价: 198.00
折扣价: 116.90
折扣购买: 泛槎图(全二册)
ISBN: 97878055482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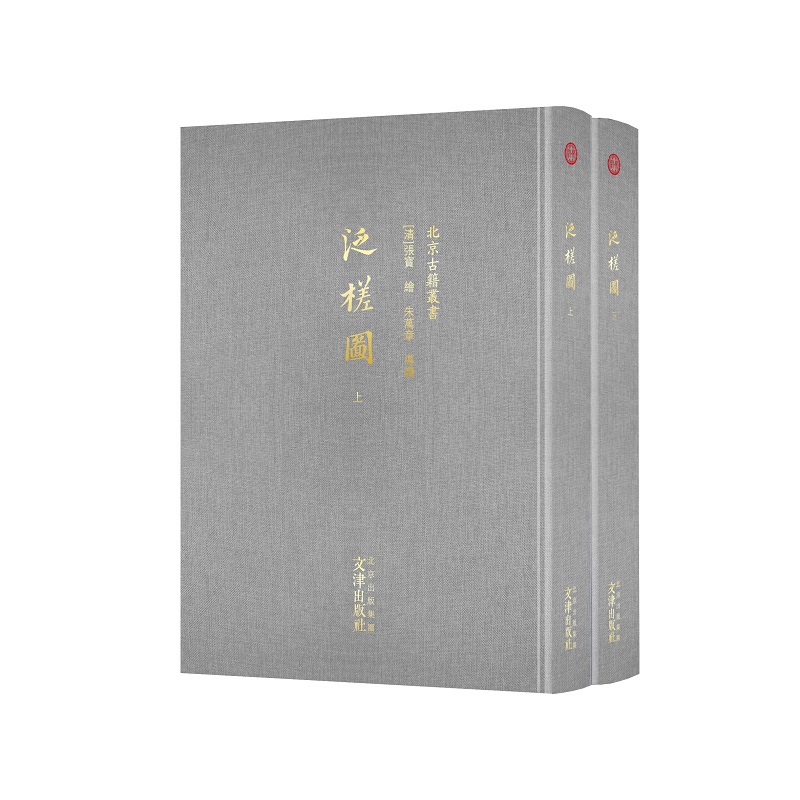
张宝(1763—1832),字仙槎,清江苏上元(今江苏南京)人,嘉庆、道光间著名画家,工山水,好游历,足迹历十数省,与当时贵戚、士人交往颇为密切。张宝随游历足迹所至,自绘所见名胜,系以诗词,累积百幅,共成《泛槎图》六集,于嘉、道两朝陆续刻印出版。朱万章(1968.12—),男,四川眉山人,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明清美术研究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北京画院齐白石艺术国际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书画鉴考与美术史研究》、《岭南近代画史丛稿》、《居巢居廉研究》、《书画的鉴藏与市场》、《髡残》、《陈师曾》等论著20余种,撰写美术史与书画鉴定论文近百篇。
张宝与《泛槎图》 朱万章 《泛槎图》又名《泛查图》、《仙槎图》,是清代画家张宝绘制的一套以山水纪游为主题的系列画册。张宝在绘成之后,延请时人,题咏殆遍。他将六集绘画连同诸家题咏,“手自钩勒,付之梓人”,因而成为现在所见的版刻绘画。张宝的《泛槎图》原画现在未见传世,其六集版画流播甚广,且大多来自写实山水,为我们了解清代嘉道时期的山川形貌、风土人情与文人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槎”的本意是木筏,“泛槎”又称“乘槎”、“浮槎”,即有乘坐木筏之意。晋人张华在《博物志》中记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忽忽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故后来便指乘坐木筏登天,并引申为畅游之意。张宝的《泛槎图》系列即多是以其足迹所至,大多写其眼中所见山水与人物,成为清代画坛上较为罕见的纪实山水画册。 一、张宝与《泛槎图》的生成 张宝,字仙槎、仙查,号梅痴,上元(今南京市)人,道光二十八年(1763年)生。关于其卒年,一直没有明确的纪年。现在一般以道光十二年(1832年),张宝年七十岁为其最晚的活动记载。其依据是在该年的四月十六日,张宝为其七十寿辰写了自寿诗七律八章。但现有的资料表明,在此年之后,张宝还有活动的相关记载。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九月既望,张宝到麟庆(1791—1846)的官署处,相与谈论园林及诗画。在同一年,汤贻汾(1778—1853)与其重晤于白下(今南京),集诸老饮于花下,汤贻汾有《白门重晤张仙槎宝山人》诗云:“七十张安世,悬河三箧书。千山销蜡屐,百卉拥精庐。解我辞乡剑,寻君踏雪驴。相携何处好,酒国是华胥。”在这一年的初春,张宝还绘有《山水册(十六开)》(天津博物馆藏)传世。因此,就现在所见文献与图像资料,张宝最晚的活动记录应该是在1834年的九月,时年七十二岁。 张宝少年时便喜作画,对山水情有独钟。在二十岁时,他便摈弃了一般学子常见的参加科考,进入仕途,建功立业等人生轨迹,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放浪山水,壮怀卧游,并笔之为画的生活。他从早年的壮游江右楚越间,遍历佳山水,直到年已古稀,仍然沉浸于山水冶游中,持续近五十年的时间,几乎占据其人生的全部。在当时的十八省中,张宝游历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辽宁、福建、广西、广东、陕西、浙江、山东和山西等十四个省,所以他有一方朱文葫芦印“十四省游人”,以记录其游历之富。在晚年,张宝归居白下,与张敦仁(1754—1834)、钱益斋、瞿曾辑(秩山)、孙尹圃、黄屿(友兰)参与耆英会,“每遇春花秋月,互相邀饮追欢,玩水游山,联吟宅句”,“或十日,或半月,互相邀饮敲诗,以娱晚景”,过着悠游林泉的惬意生活。 张宝擅诗画,其诗被辑为《仙槎游草》。在其《泛槎图》系列中,几乎每一幅画都有其题诗,诗和画相配,为画境增添文人意趣,如其在《洞庭烟櫂》中题诗曰:“五两帆轻过岳阳,高楼雄峙如墙傍。卷蓬目送君山髻,一棹烟青漾水光。”在其画中,洞庭湖中帆影绰绰,近岸高楼林立,在烟云中隐约可见远处之高墙,湖心沙渚中柳树参差。画中所渲染的意境与诗中所营造的画境融为一体。时人谢堃(1784—1844)在其《春草堂诗话》中也谈及此:“张仙槎宝,上元人,足迹半天下,以所涉之地绘图成册,名曰:《泛槎图》,一时公卿大夫题咏甚夥。余因驯象院僧恒照得读其诗,如《晓发野塘》云:野塘风系浪生花,帆饱舟轻一片斜。行尽清溪山欲转,白蘋红蓼两三家。真画境也。”谈到其诗中的“画境”,很显然,这是长期浸淫于山水林泉之间,烟云供养的结晶。 重要的是,张宝将游历所见,再加以艺术创造,先后绘制了《泛槎图》六集。这六集分别为《泛槎图》、《续泛槎图》、《续泛查图三集》、《舣槎图四集》、《漓江泛櫂图五集》和《续泛槎图六集》。其中,《泛槎图》(初集)有十三幅、《续泛槎图》有二十三幅、《续泛槎图三集》有二十七幅、《舣槎图四集》有十八幅、《漓江泛櫂图五集》有十二幅、《续泛槎图六集》有七幅,共计一百幅。 《泛槎图》的前五集,几乎都是张宝游历之后的写生之作。他自己曾说:“余落笔时闭目静思,宛然身至其境。所有亭台楼阁,寺观城池,位置各得其地。峰峦水石,各肖其形。桥梁舟车,随其地之情形,以点缀之图成,俱有八九分相似。”据此可知其画多来自其眼目所及,与实景有“八九分相似”。在其画中,一般以山川景物为主体,人物往往作为衬景而存在。画中之人,或驱车行进,或骑驴缓行,或翘首观景,或驻足流连,或倚栏远眺,或江中摇橹,或舟中赏月,或山中望月,或江岸留别,或松阴纳凉,或夏日赏荷,或松下听琴,或雨中望远,或扶杖登高,或湖中观鱼,或园中小饮,或湖畔评画,或临碑参禅,或采药探穴,或深山怀古,或他乡访友,或园中宴饮……囊括了作者在游历山水中的各种状态。也有的画幅仅有山水佳致,却无任何人物点缀,如《黄山云海》、《罗浮访梅》、《衡岳开云》、《岱峰观日》、《坝城泛月》、《盘山叠翠》、《清江候闸》等,都是如此。除了自然风景外,在《泛槎图》系列中,亦不乏人文景观和活动场景,前者如《瀛海留春》中描绘的风景即是今之北海公园。画中可见琼华岛上的白塔、永安桥上的游人及驴车、金海桥后若隐若现的御苑楼台和团城前熙熙攘攘的人流等,其名苑古迹远胜于秀丽山川。作者在画中题诗曰:“皇图春色渺无边,瀛海风光分外妍。玉虹夭桃红似锦,金鳌嫩柳翠含烟。”也突出了皇家园林的人文特色。后者如《家园宴乐》描绘的是张宝花甲生日时儿孙为其设家宴祝寿,但见在绿树掩映的堂屋中,张宝端坐于罗汉床上,右手持书,左手倚栏,怡然自得地尽享阖家欢聚之乐。园林中,儿童嬉戏,妇幼子婿齐来称贺。画中有“弟兄欢会天伦乐,更集良朋肆管弦”句,便是其张宝所谓“诸弟诸子归家为余称觞,备尽天伦之乐”的寿宴实景。但此类活动场景在《泛槎图》中并不多见,真正能代表其主流的还是行迹所至的写生佳构。 与前五集不同的是,《续泛槎图六集》并非亲历山水所绘。据张宝在六十九岁时所作《续泛槎图六集》的题记时说,他历经四十余年,已历十四省,但尚有甘肃、四川、云南和贵州四省“屐齿未到”,因而将四地的名山连同其他省份中未尝涉及的诸山合绘为七图,“虽未得庐山真面目,曾闻友人话其形势,约略抚其大概,使未了之缘,恍结于尺幅之中”,这就是现在所看到的张宝所绘的昆仑山、峨眉山、点苍山、叠翠山和五台山、武当山、五指山等七画。七幅画中的山景依据一是来自友人的描述,一是源自其想象,正如其在绘武当山时说:“名山胜迹任追求,箬笠芒鞋遍九州。咫尺武当山未到,依稀曾向梦中游”,是描绘梦中所见之武当山。 在完成六集《泛槎图》之后,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春天,张宝应陈印千司马之邀赴江苏通州游览狼山(一名紫琅),在山中逗留数日,陈氏嘱其绘狼山勒石补入《泛槎图》中。《泛槎图》百幅图虽然已经完成,但张宝考虑到“虞山、狼山又长江之大收束,江水由两山之中而入于海”,因而补绘了以狼山和虞山为主题的《虞阳海旭》、《紫琅香市》、《双山毓秀万水朝宗》三图,“亦《泛槎图》之余波也”。此三图附在《续泛槎图六集》之后,故六集《泛槎图》的绘图实际为一百零三幅。《续泛槎图六集》诸图均以山水景致为主题,并无任何人物衬景。 尤为难得的是,《泛槎图》不仅记录了清代嘉道时期的山川形貌、风土人情,更有时人题咏殆遍,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张宝自己说:“舟车到处,学士联吟。”因而往往当面即席挥毫留题。也有雅士,与其从未谋面,“寄以诗歌”。有的虽为旧雨,但天各一方,“乃题付邮筒”遥寄。正如张宝自己说:“王侯、公卿、学士,以至布衣、方外、闺秀,皆有题赠。”时人王政治也说:“一时名公巨卿、雅士文人,无不题咏唱酬,争先快睹。诗笺稠叠,车马纷纭,直不啻洛阳纸贵矣。”不仅如此,甚至还包括儿童题诗,如广东顺德十二龄童何梦书、十四龄女童何月卿就以小楷为《舣槎图四集》题咏。此外,外国使节也有题咏者,如朝鲜贡使李镇华就以行书为《续泛槎图三集》题诗。相关研究表明,全书题跋者除去张宝自题及一则满文题跋外,共计有三百七十七人,这在同类的书画题跋中,确乎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在数量上罕有其匹,在人员的构成上,也是出类拔萃的。这些题跋者,集中了其时文坛、政坛、学界和书画界的文化精英,如阮元、翁方纲、翁心存、梁章钜、包世臣、成亲王永瑆、孙星衍、法式善、赵慎畛、邓廷桢、屠倬、江藩、张敦仁、张维屏、陈希祖、英和、吴嵩梁、谢兰生、许乃普、张岳崧、钱泳、鲍桂星、程恩泽、陶澍、潘奕隽、刘华东、麟庆、姚元之等,故《泛槎图》既是一套反映清代嘉道时期图像叙事的版刻精品,又是一部其时文人交游、文坛活动的文献典籍。又因为这套版刻均以题跋者原迹勒石,不少作者书迹罕覩,故保存了很多濒临失传的书法原貌,因而又可称得上是一部透析其时书坛风貌的法书名帖。 在题材方面,张宝极大地拓宽了山水画创作的范围。历来山水画题材,大抵不离眼中山水与胸中山水两类,而眼中山水,因受画家足迹所限,往往并不丰富。而张宝遍历十四个省,所寓目的佳山水自非一般画家可比拟,故其笔下,出现很多前无古人的题材。正如焕明在题《续泛槎图三集》所说:“古人诗中所未吟,古人画中所未写。生面劈开宇宙奇,待须大笔如椽者”,这是《泛槎图》系列的又一特色。 二、《泛槎图》中的张宝画艺 在六集《泛槎图》中,前两集均注明师法对象,第一集十三幅,分别师法高其佩、仇英、董源、李唐、吴镇、郭忠恕、文徵明、倪瓒、蓝瑛、赵千里、米芾、王诜、展子虔。第二集二十三幅,分别师法李思训、李成、王维、郭熙、李公麟、关仝、王蒙、范宽、高克恭、范宽、唐寅、宋迪、巨然、李升、郑虔、李昭道、蓝瑛、赵孟頫、黄公望、沈周、荆浩、王振鹏、刘松年。张宝提及的前代名家,几乎囊括了隋唐以降直至明代的重要山水画家,且没有两幅画是相同的。这也印证了张宝在第一集《泛槎图》中自题所云:“所过名胜,遍访名人遗迹,以次临摹之,画学稍有进意。”时人邓守和在为其题《泛槎图》初集时也称:“自南而北所游历摹画者,雅咏翩翩。”很显然,在第一、二集《泛槎图》显示,张宝是在游历的过程中,同时搜访名家翰墨,传移模写,滋养其山水写生,以诸多名家笔法熔铸于画中。这反映其早期艺术生成的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其艺术溯源哪家,其画中表现出的风格还是大同小异的,究其实还是张宝自己的画风,可见其并非是对前人的忠实临摹,实则已融合己意。此类现象,在清代极为普遍,书画鉴定家苏庚春(1924—2001)就指出:“清代绘画中如‘四王’等画家题字多是‘仿××人’,这种风气沿袭到晚期。”张宝正是受到清代画坛摹古之风的影响,因而在前两集《泛槎图》中出现每一件作品都有不同师法名家的现象。但艺术的真谛在于推陈出新,独出机杼。在第三至第六集中就完全不再见其题写的模仿前贤的痕迹,或可见其师法造化而中得心源的艺术取向。时人叶世槐在题其《泛槎图》时说:“作画师古人,未能称了义。作画师天地,乃得真神气。”故在后续的《泛槎图》中几乎都是“作画师天地”。曾燠也在《<泛槎图>引赠张秀才宝(宝号仙槎,江南上元人,善画而好游,所历四方名胜,各写一纸,凡三十六幅,统题曰:泛槎图)》诗中谈到张宝遍历山水、以造化为师的艺术取向:“画师足不离乡里,胸次何曾有山水。章江昨夜虹贯月,一客乘槎游至此。自云浪迹十数年,但恨不到银河边。人间名胜颇周览,囊箧所贮皆云烟。披图应接殊不暇,令我须臾遍天下。才看晓日出东溟,又见明星照西华。乾坤造化巧设施,乃自董展荆关师。亲从真境悟其妙,焉用临摹古本为。仙槎画理晩逾进,吾侪眼界须恢奇。君不见史迁文与少陵诗,平生游迹自叙之。”这种模山范水的写生之道,使得张宝艺术精进,为人激赏。由此不难看出,在诸本《泛槎图》中,大抵可看出张宝艺术轨迹的嬗变历程。 在《泛槎图》诸家题咏中,亦可见时人眼中的张宝画艺。李芳荣在题其《续泛槎图》时谓“昔曾见先生白描《百美图》”,可知张宝兼擅白描仕女。而石谷成在题《续泛槎图三集》时称其“天下名山挥指下,宇中奇士列图中”,并谓“先生善作指画”,可知张宝兼擅指画,且在《泛槎图》中,应有不少作品来自其指画创作。只因现在所见《泛槎图》都是摹勒上石再印制的,已经无法看出其指画的痕迹。 在六集《泛槎图》之外,张宝也有其他作品传世。据不完全统计,张宝存世画作有作于道光二年(1822年)的《银杏图》卷(青岛市博物馆藏)、十四年(1834年)的《山水册(十六开)》(天津博物馆藏)和年代不详的《墨梅图》扇面(石家庄市博物馆藏)、《指画竹石图》轴(山西博物院藏)、《梅花轴》(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倚松听泉》扇面、《卢沟晓发》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等。此外,尚有与弘旿、钱楷、汪梅鼎和朱壬合作的《诗龛图》五段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从这些作品看出,张宝不仅长于山水,也擅长梅花、竹石。张宝别字梅痴,他有一方白文方印“仙槎一字梅痴”,可知其对梅花情有所系,因而在传世作品中,除了山水外,梅花便是最多的了。 关于张宝最为擅长的山水画风格,清人李玉棻称其“工山水,作《泛槎图》勒石,李伯雨戎部藏有设色《金焦图》立帧,笔意近梅道人”。“梅道人”即“元四家”之一的吴镇(1280—1354)。书画鉴定家杨仁恺(1915—2008)则称其晚年所作《山水册(十六开)》的画风“近如意馆”,即来自清代宫廷画家的院画风格。张宝曾数次到北京,和清代王公巨卿有过交游,也曾一度被礼亲王永恩之子昭槤聘入府邸,他虽未供奉宫廷作画,应有机会接触到清宫院画作品,故在耳濡目染中受到词臣画家的影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张宝自己并未有过功名,但在《舣槎图四集》引首却钤有一方朱文方印“臣宝之印”,可见其虽然“啸傲烟霞四十年”,但其入世之心尚有迹可循,故在其山水中潜移默化受如意馆画风熏染也就很正常了。 三、不一样的文人生活与“泛槎”的图像隐喻 张宝从二十岁开始,一直到七十岁左右,遍历十四个省。除去弱冠前的诗书学习,这些卧游山水的经历几乎占据其人生的全部。最为难得的是,张宝并非仅止于游山玩水,而是将眼中山水与胸中臆气融为一体,挥写于纸素,并配以即景诗,成为诗与画融合的山水纪游绘本。这在清代绘画史和文学史上,都是不多见的。 别出心裁的是,张宝一开始便选择了一种迥别于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他没有参加科考进入仕途,而是过着一种游历半天下的行旅生活。能达此目的者,除了强健的体魄和足够的余闲外,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作支撑,非一般人力所及。就相关文献梳理可知,张宝的游资主要来源于三个不同的渠道,一是张宝早年家境殷实。他自己曾说:“少小芸窗愤志向,叨享丰余”,时人亦有“仙槎先生家本富,挥手黄金不知数”之谓;二是张宝画画的润资。他自己曾说“五岳畅游,遂接交于仕宦,笔端润色,不乏游资”,又言“以笔墨为自食,语云: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看得出来,在游历的过程中,张宝是边鬻画边游历。各地的“仕宦”也就成了张宝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三是来自于各地官员的襄助。张宝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四十四岁初到北京后,经法式善(1753—1813)引荐于礼邸司理笔墨时,与成亲王、郑亲王、裕亲王、恒公、裕公及卿相学士等招饮聚谈,联吟作画。后离开北京时,“各大人赠以外省当仕荐函,乃得畅游三湘五岳,遍历海角天涯”。张宝亦有“数纸荐书成独往,伴身琴剑遍沧州”之谓。张宝凭借这些京城高官开具的推荐函,每到一处,均能得到资助或提供便利,如其到山东泰安时,拜谒了麟庆之父——泰安知府完颜廷璐,“荷蒙资具,一登泰岳”。正是因为具备这些主客观条件,才使得“半生作客寄天涯,万里归来两鬓华”的生活成为可能。 在张宝的用印中,有不少闲章,分别为白文扁方印“游遍天涯”、“天地间第一闲人”、朱文长方印“为山水写照”、“山灵爱我这痴人”、“烟霞散人”、白文方印“行万里路”、“独开生面”、朱文方印“造化为师”、白文长方印“啸傲烟霞四十年”、“人磨墨墨磨人”、“处处青山是故人”、“天阙仙人”、朱文方印“家住三山身游五岳”、朱文葫芦印“十四省游人”和白文随形印“不薄今人爱古人”等。这些印文,可谓是张宝一生的写照,亦可看出张宝对其游历生涯的自得之意。 张宝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记录和真实再现了清代的山川形貌与风土人情,以及文坛的交游实录。他代表了一种另类文人生活,所谓“烟云供画意,风月助豪吟”和“尽有深心托豪素,诗中画意画中诗”,正是传统士大夫所向往却又很难企及的林泉高致式的山水卧游。其友人杜堮在题其《续泛槎图三集》时说:“先生之行,或以舟,舟固槎也;或以车以马,车、马亦槎也;其诣极造险亦或杖与履,杖、履皆槎也。兴与景会,则聚唐宋以来之名迹而摹之以为图,仿元明以来之款识而题之以为诗,则笔与楮与墨莫非槎也。先生之槎,以意为帆樯,以情为篙橹,挟以跌宕豪逸、酣嬉淋漓之气,则浩浩乎御风而行矣。”张宝在“游遍天涯”中,不乏有形的“槎”,如舟、车、马、杖、履、笔、楮与墨,但更有无形的“槎”,如“意”和“情”等。借助这些“槎”,张宝“行万里路”,“家住三山身游五岳”,“啸傲烟霞四十年”,成为“烟霞散人”和“天阙仙人”,“为山水写照”,因而成就其一生的名山事业。江藩(1761—1831)在《题乘槎破浪图》诗中说:“乘槎贯月到罗浮,不为梅花不远游。琼管老仙骑鹤去,苍烟千叠向东流。是处青山可卜居,诗筒画具利名疏。平生踪迹半天下,五岳归来好著书。”这是对其一生业绩的概括。而丁仁静在题《泛槎图》诗中也说:“凌虚壮志托浮槎,海阔天空未有涯。到处烟云供画本,半生风月贮词华。”同样是对其行旅与笔墨生涯的揄扬。 张宝在自题四十五岁自画像《乘槎破浪图》时说:“破浪随风自在流,也无帆橹也非舟。吾家就有仙槎在,海阔天空任我游”,这是其一生的自况。诗中讲到的“吾家就有仙槎在”,指的是汉代张骞乘槎的典故。据宋人陈元靓转引《荆楚岁时记》时说:“汉武帝令张骞使大夏,寻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丈夫牵牛饮河。骞问曰: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搘机石与骞而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所得搘机石,为东朔所识。”该记载与前述《博物志》有相近之处,或有传播之误,但“张骞乘槎”的故事却是一直被广泛应用与传诵的。无论在诗歌还是画图方面,“张骞乘槎”都成为经久不衰的素材。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都在其诗歌中经常提及此典,南宋画家郑思肖(1239—1316)就有《张骞乘槎图》诗云:“牛女宫中事若何,亲身曽得上天河。逢人莫说支机石,漏泄苍苍意已多。”而晚清“海上画派”代表画家清任颐(1840—1895)则有《张骞乘槎图》扇面(南京市博物馆藏)传世。 因美丽的传说,且张骞被汉武帝封为博望侯,故在诸家题《泛槎图》系列中,多次将张宝与博望侯乘槎相提并论。郑德昌有“闻说当年博望侯,远从河汉遇牵牛。星槎本是君家物,传到先生任溯游。一路和风漾碧流,天津桥畔系仙舟。江南燕北三千里,眼底云山笔底留”,黄安涛有“迢迢博望槎,枯烂三千秋。横海发孙枝,精气冲斗牛”,富芳有“博望通侯汉世封,飞仙夜泊碧莲峰。梅关春早传花信,桂岭秋深写岸容”,章复文有“凿空真同博望侯,直从人海泛虚舟”,严骏生有“破浪乘查万里行,张骞端合是前身”和冯懋昭有“历遍天涯留翰墨,灵槎应不愧张骞”等题诗,将博望侯张骞乘槎与张宝泛槎遥遥相接,隔代相望。 除张骞和张宝为主角外,以“乘槎”为主题的绘画并不鲜见。一类是以“乘槎”本意出现,一般写画中人乘坐小舟出行,且题句中往往点明“乘槎”之意,如清初画家程邃(1607-1692)的《乘槎图》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画的是一人乘坐一叶轻舟飘荡在浩渺无垠的湖面。作者在画中题诗曰:“濯足人非濡足者,闭关何事写乘槎。钓鳌大手期君子,冰壶莹处有骊珠。”这是画中最为常见的“乘槎”主题。其他如晚清时期何澄波的《乘槎图》册(广东顺德博物馆藏)和翟岱的《湘月泛槎图》卷(福建博物院藏)也是如此。晚清学人皮锡瑞(1850—1908)有《题卢仁山(懋善)乘槎破浪图》:“破浪疑无地,乘槎直到天。扶桑攀赤日,独木跨苍烟。尺缩三壶小,瀛环一镜园。抟风九万里,应接斗牛躔。仙境常骑鲤,神游懒策鳌。随身一书剑,濯足几波涛。苇渡天风软,星浮水气高。十年沧海梦,消息问卢敖。”诗中提及的《乘槎破浪图》与前述张宝的自画像颇为相类,也是“乘槎”的本意所在。 一类是在本意之外,被赋予长寿的隐喻,因而这类《乘槎图》往往便成为祝寿的祥瑞题材,如清代中期“扬州画派”代表画家黄慎(1687—1770)的《乘槎寿星图》轴(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便是代表。图中所绘在波涛翻涌的海上,两仙人乘槎出行。年长者为常见的寿星形象,手持羽扇,秃顶,银须飘逸;年少者前侧放着花篮,手捧仙桃。这类《乘槎图》多寄寓长寿或仕途显达之喻,其他如清代画家程尧的《仙人乘槎图》(连云港市博物馆藏)也是如此。由于其雅俗共赏的吉祥之意,不仅在绘画中,而且在一些受众面较为普及的器物如陶瓷中也较为常见,如清道光年间景德镇窑粉彩仕女泛槎献寿图碗(上海博物馆藏)即是一例。明代诗人臧懋循(1550—1620)在《送谢在杭捧表北上分得夸字》诗中说:“徽号崇周姒,覃思溢汉家。万方俱献寿,仙使正乘槎。”这是将“献寿”与“乘槎”并论,是仙人“乘槎”作为献寿的重要表现。而在行乐图式的肖像画中,往往也有将画中主人公渲染为“泛槎图”范式的现象,如查慎行(1650—1727)有《题高江村先生泛槎图小影次韵》诗曰:“葛陂龙化杖如仙,欲卷银河泻作泉。除是先生能镇定,波涛人海正粘天。”从诗题及内容可知,这是描绘书画鉴藏家高士奇(1645—1703)的小像,以“乘槎图”为其渲染,是有寄托其介寿之意。 在张宝的《泛槎图》系列中,虽然都是以山水为描绘对象,并无仙人“献寿”之意,但却将“乘槎”和“泛槎”的本意发挥到极致。他为山水写照,为山川立言,过着“身似闲云心野鹤,却将踪迹寄浮槎”的闲适生活。心与境相融,天人合一,画无寿意而早已福寿绵延了。 四、《泛槎图》与《鸿雪因缘图记》之异同 在《泛槎图》刻书的同时,另有一部与此相类的书是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麟庆,字伯余,别字振祥,号见亭,满洲镶黄旗人,是恽寿平(1633—1690)族孙女恽冰(1771—1833)与泰安知府完颜廷璐所生之子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兵部主事、安徽徽州、颍州知府、河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湖北巡抚、江南河道兼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和两江总督等,是清代在位时间较长的江南河道总督,治河有方,著有《黄运河口古今图说》、《河工器具图说》、《鸿雪因缘图记》和《凝香室集》等。 《鸿雪因缘图记》是麟庆的宦迹图,是其在北京、安徽、河南、贵州、湖北、江苏、江西、湖南、浙江等地为官或游历时,倩人将所历经的山水风貌、人物行迹等绘制成图。该书共分三集,每集四册,凡十二册,每册二十幅,累计二百四十幅。初集绘麟庆自幼年至四十岁生活;二集绘四十五岁至五十岁生活;三集绘五十岁至五十五岁生活,均为彩绘,其原图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在每集首页,均有麟庆的画像,分别为汪英福、胡骏声(芑香)和贺世魁(焕文)所绘,笔者曾专文论及此像,此不赘述。《鸿雪因缘图记》是麟庆“自述一生游历之作”,“凡道里、山川、形胜、古迹、风土、民俗、河防、水利,靡不博考见闻,兼综条贯生平文章政绩”,是一套图像与叙事并重的清代纪实绘本。 《泛槎图》与《鸿雪因缘图记》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都是从绘本摹勒上石,再以版刻形式付梓,均记录了清代嘉道时期的山川形貌与风土人情。但二者的不同点也是明显的,其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作者不同。《泛槎图》的绘画作者是张宝本人,因而对所见所闻有切身之感,能将眼中山水与胸中逸气融为一体。与张宝不同的是,麟庆本身不擅绘事,故其《鸿雪因缘图记》都是延请不同画家绘制。据相关研究表明,《鸿雪因缘图记》第一集是汪英福(春泉)所绘,第二、三集为陈鉴(朗斋)、汪圻(惕斋)所绘。但实际参与绘制的画家远不止此,据晚清金石学家顾燮光(1875—1949)在其《梦碧簃石言》中记载:“《鸿雪因缘》三卷,系嘉庆、道光间麟见亭先生记宦辙所经流连山水之作,图画多出钱叔美、张仙槎二君之手,镂工又复精美,旧日图书中之美术品也。”“钱叔美”即钱杜(1764—1845),山水画家,兼擅人物。在《鸿雪因缘图记》中,有一幅《禹门激浪》,便是由张宝所绘的《龙门激浪》寄赠麟庆,故“特摹而存之”。在《泛槎图》中,有一件《龙门激浪》,是此画的母本。有论者认为:“《鸿雪因缘图记》之《金鳌归里》和《泛槎图》之《瀛海流春》,无论是选择景观内容、视角取向、构图方式、布局比例,甚至希望表现的意境,都极为类似。”这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前者极有可能就是张宝所绘——或者是以其所绘《瀛海流春》为母本的传移模写。此外,在《鸿雪因缘图记》中,还有一幅《清华品秋》,记录的是麟庆与张宝及其他友人在园林中坐而论道的情形。据此可知,张宝与比其小二十八岁的麟庆有过密切的交游,且直接或间接参与了《鸿雪因缘图记》的绘制。 二是记录内容不同。《泛槎图》多写山川景物,偶尔涉及人物活动。画中人物,多为虚拟的点缀,也有少量的衬景人物为作者本人。在画图之外,大多配以张宝的题诗,诗与画融为一体。《鸿雪因缘图记》是写麟庆的宦迹,所见所闻均在画中。画中出现的人物,多为麟庆本人。画中并无题识,在画图的对开,一般由麟庆本人撰文,描写画图的来龙去脉。由此之故,《泛槎图》更贴近文人意趣,而《鸿雪因缘图记》更侧重图画叙事。 三是题咏不同。《泛槎图》的每一集都有时人题咏,可见张宝的行迹与交游盛况,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鸿雪因缘图记》除潘世恩、许乃普、阮元、祁隽藻、郎葆辰、钟世耀、金安澜、龚自珍、赵廷熙、但明伦、阮亨、李肇增和毕克琦等人作序而外,并无时人题咏。 四是刊刻时间不同。《泛槎图》是张宝摹勒上石,延请梓人印制,而《鸿雪因缘图记》则是麟庆下世三年之后,由其子崇实、崇厚付梓。 五、结语 张宝的《泛槎图》系列在其时已经受到关注,一时名流耆宿都给予较高评价。清人刘瑗在其《国朝画征补录》中称其“足迹半天下,以所涉之地绘图成册,名曰《泛查图》,一时公卿大夫题咏甚夥。余曾见临本,读之如身亲游历,奇制也。诗亦佳”,而朱应坊则对其画中所寄予的山水奇趣作了肯定:“今读《泛槎图》,乃知仙槎志在山水之间,而不在朱门要路也。在务求山水之奇趣,而不在矜言快游,以耸动观听也。”今有学者则认为“《泛槎图》不仅是张宝的旅行人生的记载,更是明清文人画家在理论创新和观念认同方面的生动演绎。” 我们在解读《泛槎图》时,就会发现,从不同的角度,都可寻找到《泛槎图》的不同价值与文化涵义。从区域文化与地方盛景方面,可见其反映京畿地区、江南、淮南、闽浙、三湘、临桂及岭南等地的地域风貌;从绘画史角度,可看到其时山水写生与时代画风;从书法方面,可看出清代嘉道时期士人书风;从文学方面,可透析其时纪实性与酬和性诗歌的特色;从民风、民俗方面,可见出清代晚清社会风尚的特征与嬗变;从地理方面,可洞悉清代地形面貌的特色与演变轨迹;从政治、文化等方面,则可见清代文官之间、文人之间交游与活动的状态;从精神传承方面,可看出传统文人所向往的山水卧游的恬淡生活。当然,还可从版刻方面、社会生活甚至艺术市场与经济方面,都可挖掘出潜在的价值。由此不难看出,张宝的《泛槎图》系列,不仅反映了传统文人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清代嘉道时期地理形貌、风俗民情、地域文明、书画版刻、诗文唱酬等特色的窗户。 2022年11月7日于金水桥畔 ·五十年,十四省 从弱冠离乡,到古稀归老,近五十年间,本书作者张宝游历了我国的十四个省份,足迹遍及江南冀北,成为当世闻名的“旅行家”。 ·全六集,百余幅 张宝将足迹所至之处印象深刻的胜景绘制成高度写实的工笔图画,在二十余年间分六集刊印,充分展示了他对祖国山水的热爱。 ·三百家,四百篇 本书各集的题咏多达四百余篇,作者达三百余家之多,一时名流网罗殆遍,尤其收录了诸多旗籍作者的墨迹,为今人提供了大量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