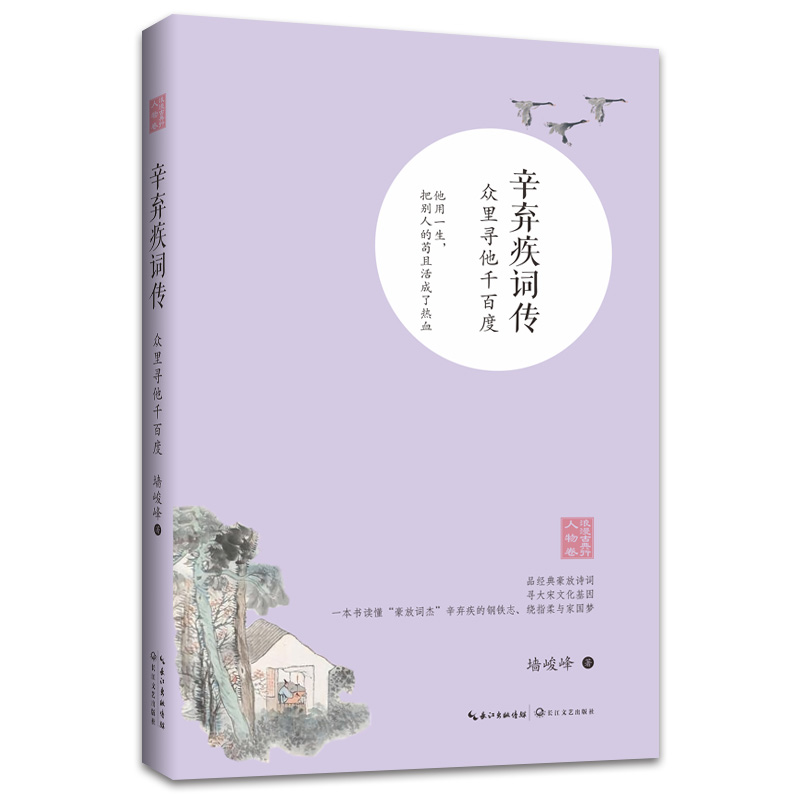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22.40
折扣购买: 辛弃疾词传(众里寻他千百度)/浪漫古典行
ISBN: 9787570209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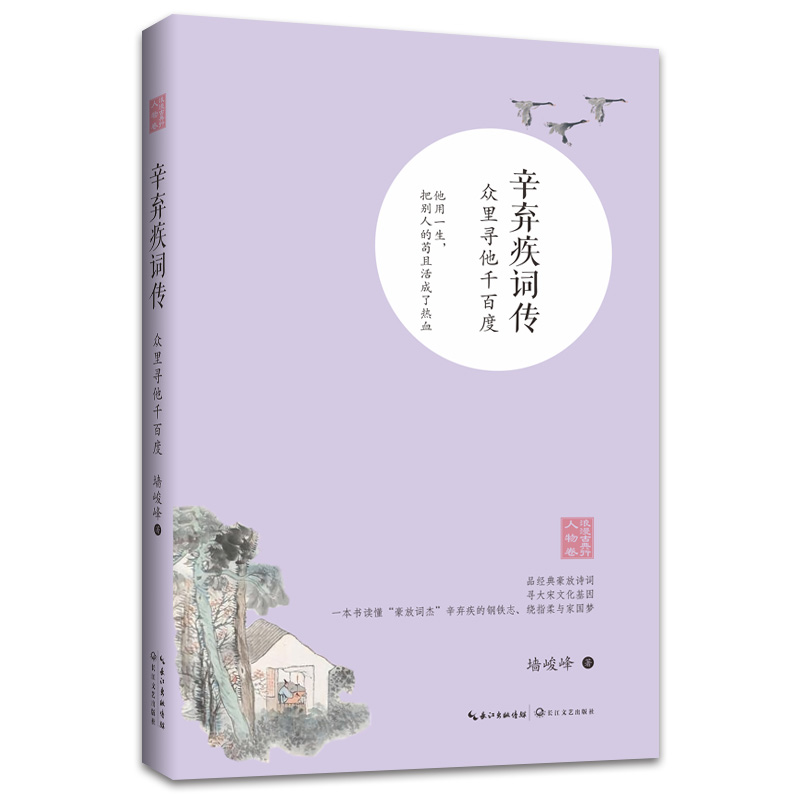
一困境:几人真是经纶手 “几人真是经纶手”,是辛弃疾写给北伐将领张浚的,他将一腔豪气寓于这首近乎恭维的词当中,只是想捧出自己的一颗热烈跳动而又赤诚的心,可惜,张浚受不起。 张浚不是能托载起他梦想的经纶手,南宋的君君臣臣都不是。他其实是在叹,也是在发问,在神州陆沉的时刻,到底有没有经纶天下的王者? 答案他自己知道:没有。 他的一生注定摆脱不了历史的困境,注定是一个悲剧。从他萌生收拾旧山河的初心时便已经注定。 有的人的初心惊心动魄地宏大,有的人的初心很平凡。平凡诚可贵,宏大则要颠沛一生。 只要看看他正在面临且必须克服的两个困境,便会明白其悲剧的必然性。一个困境是南宋以及整个宋朝“重文抑武”“轻外安内”的政治体制,一个是他无法摆脱的让人尴尬的“归正人”身份。 在自我麻醉中苟且偷安,仍奉行“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的政治策略。 两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达到极至,由此而影响了士人文化的空前繁盛,波及诗、词、文、书、画及市民文化各个领域。他们一方面高扬道德主体、内心情操,一方面大肆提倡士人的典雅趣味。 但这种繁盛,只是在学问、在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管理方面。宋代的儒生都很好,但这些人一辈子所受的训练都是为了道德文章,而不是为了管理政府,不是为了开拓一个新局面。士大夫在享受空前的待遇之时,并未对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反而满足于群体的利益,徘徊在历史的困境中,不断循环历史错误。士大夫的“仁厚”没有体现在治国为政上,却凭空造就了一个皇权与官僚为了追求共同利益而变得越来越狭隘的政治模式。 他们在钳制武人的信条中惊人地保持一致,并奉行着这个信条打算一直苟安下去。一有打破,便想方设法摁下去。他们以文人领兵,宋代著名的领兵之将几乎都是科举出身,韩琦、范仲淹、张浚莫不如此。那些真正有雄才大略的武将,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会因为功劳太甚,处处招来算计。 名将狄青惨死,英雄岳飞惨死。宗泽、李纲这些北伐名将,为了自保,大修庄园,安享晚年,以向君主昭示自己的忠心。就像五代的韩熙载,为敛雄心,日日开夜宴,以此消除君臣的戒备。 绍兴十一年岳飞惨死,表面上死于奸臣秦桧,实则是借秦桧之手,南宋君臣的一场合力围歼。他们太害怕这些真正的英雄,而岳飞的惨死,象征了一个历史困境中英雄的悲剧宿命。 凡事都有偶然的凑巧,结果却是宿命的必然。 殷鉴不远,辛弃疾不是看不到,也不是听不见。他对人性和人心还抱着一丝幻想,他对自己心中的执念难以割舍。而人活在世上,如果不奋力一搏,把自己的生命炼进自己的剑中,又怎么算得上轰轰烈烈地活过? 他在重复岳飞走过的路,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活过。 他在重复岳飞的悲剧,只是放不下心中的那个信仰。 正如死后的辛弃疾不知道的他的名爵一会儿被削、一会儿被夺一样,岳飞的名爵在需要的时候,被高高捧在天上,被树为世人的楷模,换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时候,又被狠狠地摔在地上,再狠狠地踏上几脚。 这两个军事天才,面对着微妙的政治,束手无策。不是每一个人都要理想地活着,而社会得以运转的原则是只看那些庸俗的取舍,所以英雄只和悲剧统一。 二际遇:谁念英雄江左老 他的另一个困境是“归正人”的身份。 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 他的这个摆脱不了的“归正人”身份,也影响了他一生的际遇。 “谁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这是他在为别人叹息,也是在为自己叹息。英雄空老,是他一生的命运写照。 “归正人”的身份不是他能选择的,是历史犯下的错,是国家的耻辱,但承担者却是他。 他可以选择不南归,就留在金国,他会和他的朋友党怀英一样有远大前程。但故国难忘,他选择了回归。故国并没有张开双臂欢迎这个赤子,却因他祖辈曾经降金而给了他一个特殊的身份——归正人。 归正人,意味着曾经背叛、曾经不忠。它已经在回归者和当权者之间划了一个鸿沟,时隐时现。当宋金关系吃紧,朝廷需要人才时,这个沟便隐去。当宋金关系和缓,朝廷觉得归正人的功劳太大让他们心存忌讳时,这个沟便凸显。 南宋建国初期,士大夫还发出了“问罪金人,迎还二圣”的呼喊,但这种呼声,随着宋高宗支持“和议”“退避”而减弱。孝宗虽欲励精图治,却因张浚北伐失败而意气萧瑟,时人强烈的抗金爱国激情一变而为愤懑压抑;到宁宗时,女真人与北方汉人之间渐渐融合,抗金的声音越来越弱,随着韩侂胄北伐失败,只变成几声悲凉的叹息。 他的一生中,有两次北伐的机会。当张浚北伐时,他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吏,越级呈供给张浚的平戎策只换来“某只能受一方之命,此事恐不能主之”的冷漠回答,战争打响时,他只能在江阴远远地看着。一个“归正人”,一个小吏,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取得肉食者的信任? 第二次北伐时,六十多岁的他从退归了近十年的瓢泉重新起复。而起复他的主战派韩侂胄,在北伐的光鲜之下,既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私欲,又缺少一个将领应有的韬略。六十多岁的辛弃疾,顶着晚节不保的风险,前来助阵,却在他们泛滥的猜忌中被当作一枚棋子,甚至再次被踢回家去。 两次离梦想最近的机会,就这样白白地流逝了。 余下的时间里,北伐的声音渐渐微弱甚至平息。当权者像鸵鸟一样把头深深埋在求和的沙砾中,虽然心中也有难过,也曾动摇过,但在金人的铁蹄下,他们那点阳刚之气瞬息即逝。此时此刻,那些主战、主北伐的声音,不是在提醒他们挽回自尊,而是在提醒他们何其懦弱。这种聒噪之音,让他们心烦。 你不是枕戈待旦,准备北伐,重拾旧山河吗?好吧,给你一个地方让你治理去。只是不是去攘外,而是去安内。平叛、治乱、救荒、缉盗,他样样干得有模有样,样样以雷厉手段收到别人做不到的效果。结果呢?因为你是一个归正人,能力太大了,不好管,也管不住。办法只有一个:频频调任,让你在一个地方无法打牢根基,刚有成效,便派往它处。 以为怀抱着一腔忠诚就一定能受待见吗?也许辛弃疾明白了,只是他不愿意相信。但现实如泥潭一般,消磨了英雄的意气,挫败了他的壮志。想腾飞,也只是扑棱了一下翅膀而已。 我们不能选择怎么生,也不能选择怎么死,却能选择怎么活。 依辛弃疾的能力,他真的可以选择活得很好,但那个北伐的魔咒迷住了他的心,他选择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活得很憋屈。 他有一双看透历史的巨眼,知道兴废成败转头即空,功名事业恍如一梦。但他没有一双看穿当下的巨眼,在当世的双重困境之下,徒耗心力,等待着早已注定的悲情结局。 同时,一个的人性格也会影响他的际遇,如果你坚持某种性格,你就无权拒绝某种际遇。 辛弃疾那种“成大事不拘小节”的刚毅果敢与霹雳手段与南宋士大夫集团的宽忍软懦的政风士风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这种个性和行事风格,也为他日后九次被弹劾,两次长达近十年的退隐埋下了祸根。“贪”与“酷”两大罪名,如影子般跟随着他,而且位越高、权越重,阴影也越来越大,越跟越紧。 平定茶商叛乱,落得了“酷”名;建飞虎军,落得了“用钱如泥沙”的“贪”名;缉盗赈灾,再得“酷”名;建备安库又摊上“贪名”。最可恨,六十多岁从瓢泉起复,又加上了一个“好色”之名。 辛弃疾知道自己的个性会给他带来什么结果,而且他还是一个身份敏感的“归正人”,言未出口而祸已及踵,他了然于胸。 他曾在《千年调》中借一个小酒杯,描摹南宋士大夫中那些无所作为、阿谀奉承者的众生相。他们一团和气,唯唯诺诺,万事称好;他们圆滑处世,就像寒热随人、调和众药效的甘国老;他们学人言语,巧舌如簧,就像惹人怜爱的秦吉了。而他偏偏“出口人嫌拗”,像辛辣之物一样刺激别人的神经,最终落得被“捣烂堪吐”的地步。 他知道,但他不屑于做,也做不到。 一段不为的气节,是撑天撑地的柱石。如果他没有保留这点“方”,这点气节,这点真,他最后也不会成为辛弃疾,而是无数个俯仰随人的乡愿中的一员而已。 三健笔:倚天万里须长剑 以南渡为界将辛弃疾的人生舞台分成明显不同的两个体系。 南渡前,他生活在属于齐鲁文化圈的山东,这二十多年是他个性气质和文化品格的奠基期;南渡后,他生活在江浙两湖福建安徽等江南文化圈,这四十多年对他的心灵和思想也有重要的雕塑作用。 北方的厚土深水、贞刚义气给了稼轩雄浑健朗的男儿铁骨。 南方的杏花春雨、诗意阴柔给了稼轩清丽婉约的柔软温情。 北方给了他崇尚实际、执着事功的英雄志气。 南方给了他超越功利、闲适诗意的审美气质。 两种文化的交汇融合,让他的词风丰富多彩,而内心也分外旖旎。步入他的世界里,忽而像闯入了一座庄严肃穆的庙堂,忽而像流连于明山秀水的诗意田园;时而是横扫六合、剑指八荒的古战场,时而是浅唱低吟、闲婉清丽的后花园。 凌云健笔,低回柔情,都是他。 只是在不同的形态当中,始终有一种主导的风格贯穿其中,那便是豪郁。 辛词的“健”,到底体现在何处?回顾他生活的一幕幕,回味他一首首的词作,我感觉像找到了通往他内心宫殿的那条路。 辛词的“健”,不只是在他的“豪”、他的“雄”、他的“狂”,这些别人早已说过。在我看来,他的健却在以下几方面很有意味——健在它呈现出来的崇高美学风貌,健在它变动不居的动态气势,健在它扑面而来烈酒之气。 辛词以豪郁为主,“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英雄豪杰的志意一再在现实中被抑制,使得他的词一方面呈现极豪雄开放的上升之势,一方面又呈现出极悲郁内敛的下沉之态,两者之间形成一种极强的矛盾和张力,这种张力使得他的词呈现出一种崇高的审美风貌。 崇高是一种对立和冲突的审美体验,它是弱与强、善与恶的抗争与对垒。辛弃疾一生在那个光复大梦的激励下壮志昂扬,却一生也没有挣脱来自对立面的压制与贬抑,他无法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困境,只能在孤独的抗争和坚守中彰显生命的力量和光辉。 他所写的那些英雄词,以其粗犷博大的形态,劲健强大的力量,雄伟宏壮的气势,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他要一把倚天万里的长剑,拨开西北的浮云;他准备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好补西天北;他叹息谁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他渴望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结果却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他登临意。英雄迟暮、廉颇已老,谁人问他尚能饭否?汗血宝马,空拉盐车,骈死槽枥,谁人来替他收埋凋于西风的骏骨? 黑格尔说:“人格的伟大和刚强只有借助矛盾对立的伟大和刚强才能衡量出来,环境的相互冲突越多、越艰巨,矛盾的破坏力越大,而心灵越能坚持自己的性格,也就越显示出主体性格的深厚和坚强,因为在否定中保持住自己,才足见出威力。”无论现实怎样灰暗,无论意绪多么沉郁,他始终抱持着梦想,在疲惫生活中将别人的苟且活成热血,而他人格的伟大和刚强,正在这种矛盾和对立的衬托中越发熠熠生光。 辛词之“健”,还在于它变动不居的动态气势。这与他的英雄词呈现出的崇高风貌有内在的一致性。崇高必须在矛盾对抗中才得以存在,矛盾对抗便是“动”,便是变动不居。 它的“动”是心理意识的流动。 它的“动”是自然造化的生生不息,他的笔下很少有静止的意象或意境,世间万象莫不在“动”中蕴含着勃勃生机。 辛词的“健”,还在那扑面而来的烈酒气息中。 酒自古以来就与英雄相伴,实在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你别忘了,这是在宋代。 宋代的审美趣味尚清、尚雅。茶之性淡与味长,十分贴合宋人清雅的审美趣味。品茶如参禅,茶禅本一体。品茶,是他们在尘俗凡世中一种优雅从容的姿态。 李清照与赵明诚曾“生香熏袖,活火分茶”,文同“唤人扫壁开吴画,留客文轩试越茶”,周紫芝“城居可似湖居好,诗味颇随茶味长”,就连与稼轩一样有着激烈的家国情怀的陆游,退居山阴后,也“每与同舍焚香煮茶于图书钟鼎之间”,这个老英雄,最终在茶的闲适中减轻了心中的隐痛。 可稼轩不。在他的诗词中,我很努力地嗅着茶的气息,却似有若无。而浓浓的酒气,让人中心如醉。 酒适宜烈性之人烈饮,茶适宜淡泊之人淡品。 酒浇的是胸中永不平息的块垒,茶润的是气定神闲的从容。 稼轩喝不了茶,他只能喝酒。 独饮是自欺,醺然中竟起了烈士的幻觉,震荡这胸腔节奏忐忑,依然是暮年的一片壮心。 对饮是自醉,深夜对饮,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他曾经戒过酒,我知道他戒不了。戒酒就是戒掉他的功名心,就是在心中杀死那个元气淋漓的曾经的自己。当他煞有介事地请来酒杯,郑重其事地与它约法三章时,我笑了。这是干吗呢?何苦自己为难自己? 四:柔情:心弥万里清如水 江北的秋风雕刻了他阳刚的线条,江南的春水滋润了他温柔的心灵。 给人以震撼的崇高与给人以安宁的优美,在他的生命中和谐共存,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使命。 优美是超然优雅的人生境界的呈现。此时人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平和、淡远、安定,内心温软,一片柔情。 这样的状态不是稼轩的主流,但作为一个分支,在他的世界里不可忽视。 稼轩的“柔”,又有怎样的表现形式? 他的柔,不是“柔软”得化不开的、瘫下去的“柔”,是摧刚为柔,刚柔并济。 他刚拙自信,孤危一身已久。倾国无媒,入宫见妒、恐遭排挤的心情时时都有。志在恢复又屡受排挤,这种矛盾痛苦郁积于心,时而发为裂竹之音,时而化为欲吐还吞的柔软的悲愁。此时的他不是那个英雄壮士,而是一个“惜花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的见花落泪、对月伤心的佳人,是“准拟佳期又误”“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的弃妇,一片幽情,满怀闲愁,他能做的只是独倚危栏,在斜阳烟柳深处黯然神伤。 登高临远,水天无际,秋高气爽的阔大有如他的胸襟清疏刚健,然他只能像个失意的游子,拍遍栏杆,孤愤孤独。刘郎才气、忧愁风雨的建功立业的信念忽而闪过,又瞬间消逝。刚健的英雄,此刻最想要的是“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英雄落下了泪,百炼刚最终化为绕指柔。 他的柔,是对爱的缠绵,情的珍重。 稼轩也写过一些爱情词,但他的“柔情”不只是在爱情词中。只是在爱情词中,他的秾丽纤绵,一点也不逊于秦观晏几道两个痴情种。 爱情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亲情和友情,也在他的世界里举足轻重。 他交游广,朋友多。对陈亮的惺惺相惜,他分外珍重。相聚十多日,离开以后,他心中难舍,竟骑马一路追去,直到雪深路滑实难行,才怅怅恋恋而返。 族弟辛茂嘉要远行,阴差阳错的命运造成的人生离恨,让他情难自已。在送给族弟的离别词《贺新郎》中,他写下了前无古人的“恨”。连用五个历史上著名的恨别典故,将他的离情铺叙无余。每一种恨,牵系着不同的场景和情感内核,沉郁苍凉,语语有境界。 亲情词中,有宦游在外,对家的依恋。层楼望,春山叠,家在遥远的那边。他恨蝴蝶不传千里梦,子规叫断三更月。每一声叫,都是声声枕上劝归人;体贴妻子的一片怜子意,他郑重其事地写下了戒酒令;儿子要他置办田产,他又像一个温厉的长者,送去规诫和叮咛;小儿子出生了,他又像一个慈父一样,祈祷小儿子无灾无难过一生。 在面对朋友和亲人时,他卸下了盔甲,做回了那个柔软的自己。 他的柔,还在乡村的山水田园和温朴人情中,心弥万里清如水,一川明月照冰雪。 他有时像个隐者。 或借助理性平息内心的痛苦。他友渊明,南山种豆,东篱访菊;效颜回,一瓢自乐,箪食豆饮;参禅悟道,以求心灵的清明安宁。 或借助静谧的农村生活、朴野的田园风光、淳朴的民风乡俗来疗救官场险恶带给他的心理疲惫和创痛。 万物静观皆自得。山水自然蕴藏的活泼生命和大化运行周流不息的神奇,让他的内心得到洗涤、净化和安宁。与白鸥订盟,与青山交心,与流云对话,与山鸟共情。万物莫不适性。 他有时又像个老爷子。 闲游在村头地脑,看采桑的女子归省探亲,看苍苍的老者说着今年的雨水匀,看田里正忙的人骑着秧马,看儿童在自家的园中偷了几颗枣。 有时还喝点酒,村里的人都认得他,没钱自可赊。在春社结束后,和村里的老头一起,喝着分回来的社酒,杂处其中,浑然忘己。有时喝醉了,找不着回家的路,或是被人扶着躺下,或是找人问回自己家的路。 那头力能杀人的青兕收去了他的利爪,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英雄敛藏了他的雄心,像个可爱的老爷子一样,感受着生活的点滴温馨。 这样也好,在被剥去了名利、权位种种外在的东西之后,人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人又如何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他用他的行动告诉了世人。 他一无所有,却又拥有一切。 心弥万里清如水,一川明月照冰雪。 在这样优美的天地间,我看见他满身散发着柔软的光辉。这样的光辉,不逼人,不耀目,却更让人觉得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的可爱可亲。 ◆品豪放词派的经典代表词作,寻大宋文化基因 ◆一本书读懂“豪放词杰”辛弃疾的钢铁志、绕指柔与家国梦。 ◆“浪漫古典行?人物卷”畅销书系新品之辛弃疾卷登场,套书附赠中国诗词大会飞花令通关宝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