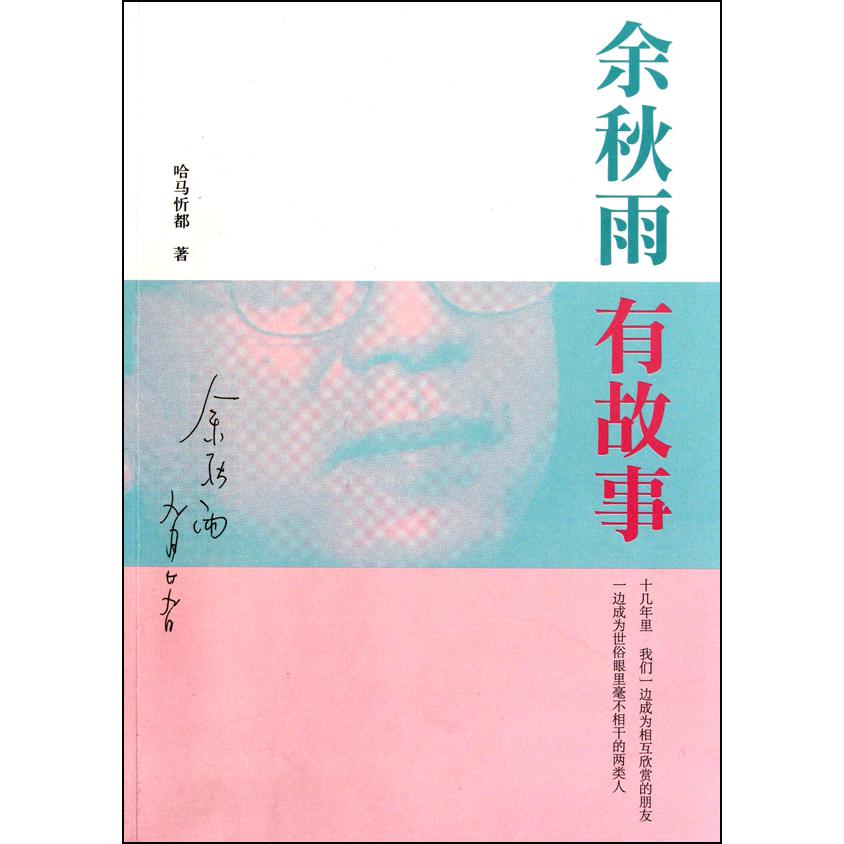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青年
原售价: 26.00
折扣价: 18.70
折扣购买: 余秋雨有故事
ISBN: 97875006948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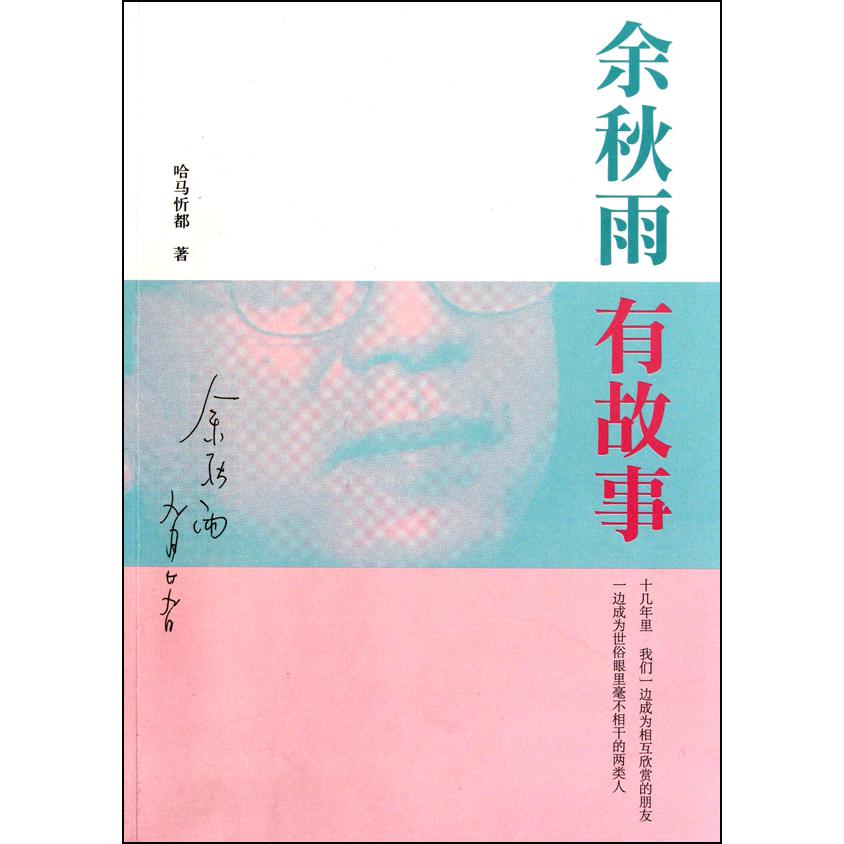
哈马忻都,本名马小娟,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攻读戏剧学硕士学位,师丛余秋雨。做过大学教师,写过小说(曾在《当代》等杂志发表《对烛成影》、《女孩儿》、《女审》等小说),搞过电影、电视(曾任电影《一样的天空》编剧),现为《人民公安报》编辑、记者。出版有作品《尾随者》、《藏着的中国》、《吾师余秋雨》。
那是一次偶遇,更是一次暗合 成为余秋雨的学生,肯定不是我撞上的。 多亏那次失意。人在穷途末路之时就想要远走他乡,二十四年前我决定 离开南京大学的教职岗位时,像不少人那样,选择了报考研究生。这是一条 轻松得多的捷径:不需要走关系,不需要办调动,不需要去求人,只需要参 加考试。 我站在南大图书馆书架前,不停地自问:我考什么?我考什么呢?这有 点可笑。读了四年大学中文,一直没能弄清楚自己究竟想要“搞”什么。这 在治学严谨的南大,是不可原谅的。个别老师和同学认定我有点才华,但没 有人认为我是个好学生。毕业时我被模模糊糊分来分去,最后分在写作教研 室,给学生讲写作课,可我却躲在心里反抗:写作是教出来的吗?我大概也 不是个好教师。 那是选择的开始,太过学究和专一的研究领域,会要我的命,我一直都 在拒绝。一辈子躲在书房里专攻一段或某人的一生,淹没在别人的生命与世 界里,定会叫我了无生趣。我开始往四处发信,骚扰我的一些同学,以及同 学的同学。我一个劲地打听:你们那儿有没有那种泛学科的、不那么确定研 究方向的“专业”?也许正好有那么一位老先生,一时“想不开”,愿意招 三两个我这样的人做研究生? 想要的回答真的来了!那是一封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信。我第一次知道 了余秋雨的名字,并且一下就从来信里感受到,这个余教授可能还挺欣赏我 的。 1986年上海戏剧学院的研究生招生科目别具一格,以余秋雨教授为主的 导师组联合招收“戏剧学”研究生,除了余先生的艺术、戏剧美学,导师组 里还包括戏曲学教授、欧美戏剧研究教授、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教授、戏剧 表演学教授、舞台美术学教授,他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学、研究领域独当 一面的精英,所以要联合招生,本意也正在于不急着框死学生的研究方向, 想要培养几位全方位的戏剧通才。 这样的方式,光是听上去就叫我喜不自禁。 上大学时我是中文系戏剧社的骨干分子(每次排练《雷雨》,扮四凤说 “已经四个月”时,会笑得蹲在地上起不来),系里的所有戏剧课程我都选 修过,曾历任各戏剧科目科代表,这也是我四年大学生涯唯一的“官衔”。 喜欢倒是真喜欢戏剧,但要把这样的爱好缩小至某一段戏剧史或某一位刷作 家的定向研究,从来没主动想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意思,既能满足我对戏剧 的热爱,又不至于一头扎进某一只牛角尖一辈子出不来,我喜欢。拜拜了南 京,我要去上海。 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告诉我,这是余秋雨的思路,这在上戏是第一次,在 全国也是首创。 余秋雨的名字,正是伴随着“独特、开放、宽容、自由”这些我爱用的 词进入印象当中的。当然,最重要的,余秋雨的方式,也仿佛与自己朦胧中 想要的方式暗合,这个名字头一次出现就让我有了亲切和认同感。 直到那时,我才开始读余秋雨的学术专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 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等,一下又掉了进去,简直相见恨晚。 对于一个不习惯在一个封闭体系里看字读书的年轻人,余秋雨学术专著 里那种大开的、放射状的思路提供与线索展示,让我的眼睛完全不能停住。 仿佛跟着他在跑步,拐过一道弯儿,眼前豁然会出现数道门,每道门里的情 形,又都是我急于要获知的。我一边跟着跑,一边会涌出许多的想法,一些 是突然想到的,一些是早巳沉淀在某一角落的,只是突然因这阵风的掠过, 飞扬升腾。那些书,应该是我那时为止读到的最过瘾的学术著作,是我四年 拉拉杂杂东翻西看大学学习的最终总结与升华。很难描述那种感觉,总是惊 喜,甚至有些扬眉吐气的意思。南大的教育是十分严谨和素有传统的,一切 都有条不紊地进展了几十年近百年。我天性散漫,很多时候觉得自己融不太 进去,或是不入流,成不了最好最优秀的学生。总是不太高兴上系里安排的 课程,只热衷于四处听讲座,南大校园里的听不够,还跑去南师、南艺听, 一些讲座能一下把我的眼界打开,新奇与新鲜的风迎面而来,让我莫名兴奋 ,还无比充实。当时读余秋雨的书,就仿佛听一个接一个的讲座,不再被日 间的课程打断,很过瘾,并且心里慢慢地还会升腾起隐隐的牛气,觉得自己 四年人学学习也似乎并不那么一无所获,至少让自己具备了领略新思维、新 思潮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领略过程当中为自己带来的无比快乐。同样是学 术著作,我不仅领略了余先生开放式的思维,还读出了满篇磅礴大气的文笔 ,对成为余秋雨的学生更多了神往和信心。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