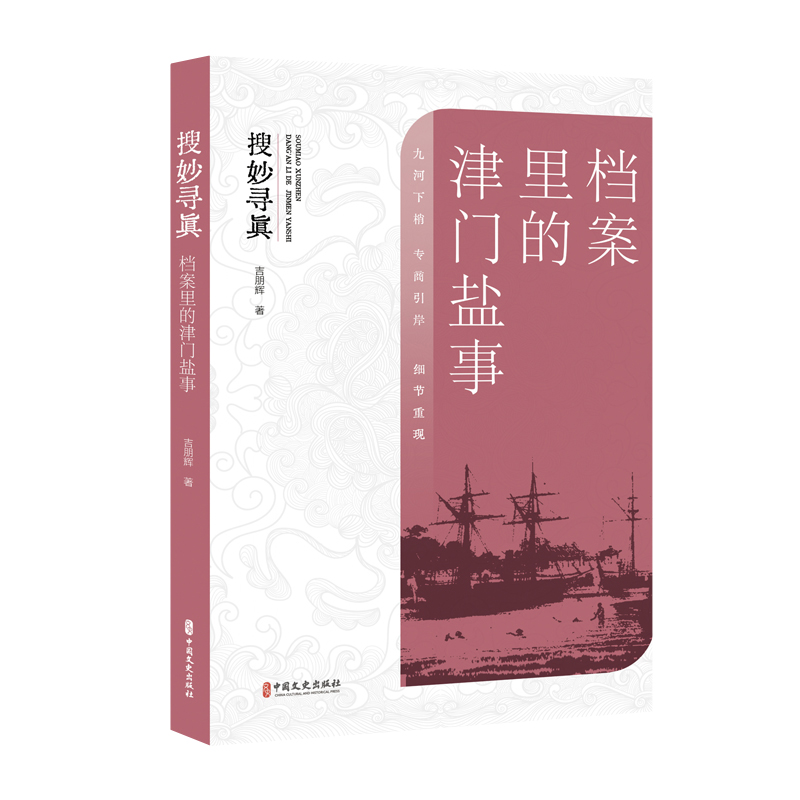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文史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6.00
折扣购买: 搜妙寻真(档案里的津门盐事)
ISBN: 9787520540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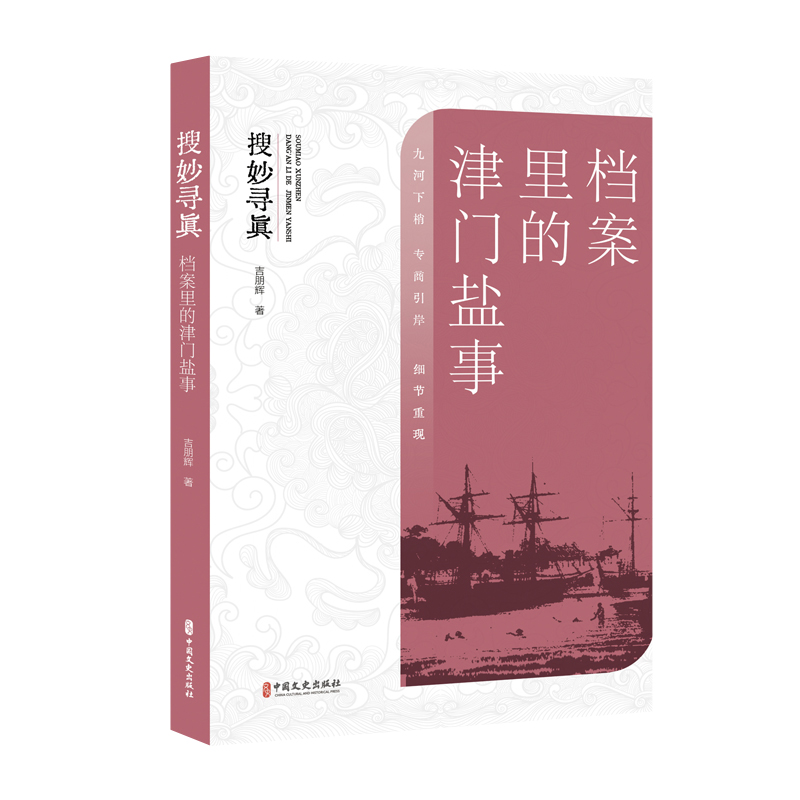
吉朋辉,天津市档案馆一级主任科员,从事档案史料编纂及天津地方史研究。主编“天津旧事丛书”之《天津运河故事》《长芦盐务档案史料丛编》,主编国家档案局重点档案保护与开发项目《天津近代工业档案选编》。著有《皇权的力场:清前中期天津大盐商的兴衰》。在《中国档案报》《天津日报》《今晚报》《城市快报》《湖南工人报》《天津文史》等报刊发表关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文章90余篇。
乾隆朝最“不靠谱”的长芦盐政 清初规定长芦盐政的任期为一年,但后来并不拘泥,比如雍正朝莽鹄立就连任三年。到了乾隆朝,大部分长芦盐政都能连任,其中连任年头最多的是西宁,达十一年之久。然而,他却堪称乾隆朝最“不靠谱”的长芦盐政。 上任伊始自摆乌龙 乾隆三十五年(1770)闰五月,杭州织造西宁被乾隆帝调任长芦盐政,开始了其长达十一年的任期。连续担任要职,可见乾隆帝对他的信任。然而上任伊始,他就交出了一份令乾隆帝颜面扫地的成绩单。按照规定,每年十一月份长芦盐商应将本年的盐运销完毕,交齐盐课。但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底,应该运销的一百万包盐才完成了六十余万包,而应缴纳的五十六万多两盐课才完成了三千七百多两,竟然不足百分之一。即便如此,西宁仍然应盐商们的要求,上了一道建议缓收长芦盐课的折子。这道奏折自然被户部驳回了,乾隆帝也下旨责备西宁任由盐商拖延,导致“课运两误”。 原来盐商运盐纳课,盐政有督催之责。西宁督催不力,以致出现了应纳盐课只完成不足百分之一的窘况。受到斥责后,西宁不敢怠慢,令盐运使福贵抓紧追征,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仅仅二十天之后,收上来的课银就达五十五万余两,只剩下一万多两未收了。乾隆帝对此十分不解,下旨让西宁解释为什么会如此“冒昧奏请展限”。 其实这不是西宁在长芦盐政任上唯一一次自摆乌龙。当时天津建有皇船坞,乾隆帝南巡所用安福舻等船只平时即存放其中,由长芦盐政负责管理修缮。乾隆三十五年(1770)九月,乾隆帝令西宁修缮安福舻、翔凤艇。本来只将船顶上层木板更换即可,西宁却自作主张,将两层木板及中间锡片全部揭起重加修整。乾隆帝很不以为然,认为西宁如此大费周章,乃是“攘为己能,希图见好”,实在是“不晓事体”,将其申斥了一番还不算完,又令他赔出了所耗费的银两。 稳坐要职的秘诀 西宁办事既然如此不靠谱,为什么还能稳坐要职呢?乾隆帝首先看中了他一点:人是老实的。有一个事例为证。乾隆中期以后,长芦盐政与盐商之间有一个“潜规则”:每年由商人购买贡品,再由盐政以自己的名义进献。乾隆三十五年九月,乾隆帝召见西宁问起此事,西宁不但承认了,而且将此事历任相沿,其前任高诚、李质颖都如此办理的实情和盘托出。其实乾隆帝早已就此事问过李质颖,李当时没有承认。于是乾隆帝认为西宁“人尚诚实,是以和盘托出,不敢隐瞒”,而李质颖则不老实。 西宁的另一个秘诀,就是绝对实心实意为皇帝办事。他在任的十年里,交给内务府的银两从来没有短少过,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三十八年两年就交了近六十万两。乾隆三十六年(1771),乾隆帝发起第二次攻打金川的战争,这场战争旷日持久,耗资巨大,西宁动员辖下的长芦盐商捐银九十万两作为军费。另外他颇能投乾隆帝所好,每年进贡的数量惊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令在承德建造一座罗汉堂,西宁不仅承担了全部一万六千两费用,而且与其子基厚共同经办此事。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他还曾给东巡山东的乾隆帝送去一个名叫张东官的苏州厨子,其做菜甚合乾隆帝的胃口。乾隆帝对西宁也恩赏有加,比如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曾赐给他一份珍贵的《淳化阁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西宁背景非凡,可以说是一门显贵:他的叔叔高斌、弟弟高晋都是大学士,高斌之女高佳氏即慧贤皇贵妃;他的儿子基厚曾任江宁织造,侄子书麟官至两江总督;他任长芦盐政时的同僚、直隶总督杨廷璋是他的儿女亲家。正如他在一份奏折里所说的:“奴才一门世受国恩”,的确如此。 乾隆帝的“回马枪” 乾隆四十六年(1781)闰五月,年逾八旬的西宁已任长芦盐政整整十一年,乾隆帝终于下旨让他离任回京,并且给了他一句评价:“办理一切事务尚无贻误。”似乎西宁可以从此安度晚年了。然而第二年八月,和珅忽然给西宁面传了这样一条谕旨:“西宁在长芦盐政多年,办理不善,以致商人拖欠甚多,着西宁自行议罪。” 其实乾隆帝以“商人拖欠甚多”为由惩罚西宁,是说不过去的。长芦盐课积欠的主要原因,是频繁的带征,也就是将某年的盐课分摊在其后数年内逐次交齐。西宁任职的十一年中,于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五次为盐商奏请带征,带征年份少则五年,多则十年。旧的带征未完,新的又叠加上来,使长芦盐课成为一笔糊涂账。但这十一年盐商们从来没有拖欠过交给内务府的帑利银,且报效频繁,光是捐助金川军饷就有九十多万两,再加上乾隆帝一次六旬万寿、一次南巡、一次东巡,太后一次八旬万寿,每次长芦盐商都要掏腰包。在报效上多掏了钱,就会在盐课上少掏钱,所谓拆东墙补西墙是也。这一点乾隆帝岂能不知?实际上每次带征都是经过他允许的,有时甚至是他一高兴,作为恩典赏给盐商的。西宁之所以能够平安卸任,原因即在于此。 然而乾隆帝却来了个“回马枪”,在西宁卸任后又追究起盐课积欠的事来,并且把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在他身上。这背后的原因,似乎并不像谕旨里说的那么光明正大。两年前的乾隆四十五年(1780),和珅想出了议罪银这么个“天才”的点子,允许犯罪的官员缴纳罚银,这样既可以让罪官得以从轻发落,又可以充实皇帝的小金库。当和珅向西宁转达了那条让他“自行议罪”的谕旨后,西宁心领神会,一下子给自己开出了八万两之多的议罪银,请限八年交完。按照西宁乾隆五十三年(1788)奏折中的描述,他拖着耄耋之年的衰朽之躯,卖房卖地凑了五万余两,剩下的实在拿不出来,只得求助于侄子书麟,让他从养廉银里每年拿出六千两来替自己交罚金。 在敲完西宁的竹杠之后,乾隆帝继续对他施以“恩泽”。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宁已是九十一岁高龄。正月,乾隆帝特意下旨:“基厚之父西宁年逾九十,基厚在外久缺定省,着仍回京,仍以内务府员外用,俾得就近侍养,以示体恤。”打一个巴掌给个甜枣,这就是乾隆帝对待自己名为大臣、实为奴才的臣子的方式。 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大部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奏折、谕旨为主。那泛黄的纸张、精工的书写,穿越几个世纪仍保持着本来的样貌,散发着悠远厚重的历史韵味。它们并不像后来的大多数公文那样,因形式和内容的制式化而冷却了人性的温度。其内容近似于臣子与皇帝的直接对话,在密折制度实行后尤其如此,某些密折、密旨甚至已经相当于书信了。那里记录着种种不便公开的事实,充满克制的情绪、隐秘的心机,有时甚至会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解读这些档案,犹如在一个曲径通幽的园林中搜妙寻真,能使一些幽远的史实再现,还能触碰到真实的人性,体会出别样的兴味。 这本小小的书,仅仅揭开了中国历史或天津历史小小的片段。我们怀着忐忑之情将它捧出,亦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既然不能百川之流汇成大海,那么只求萤萤之光照于一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