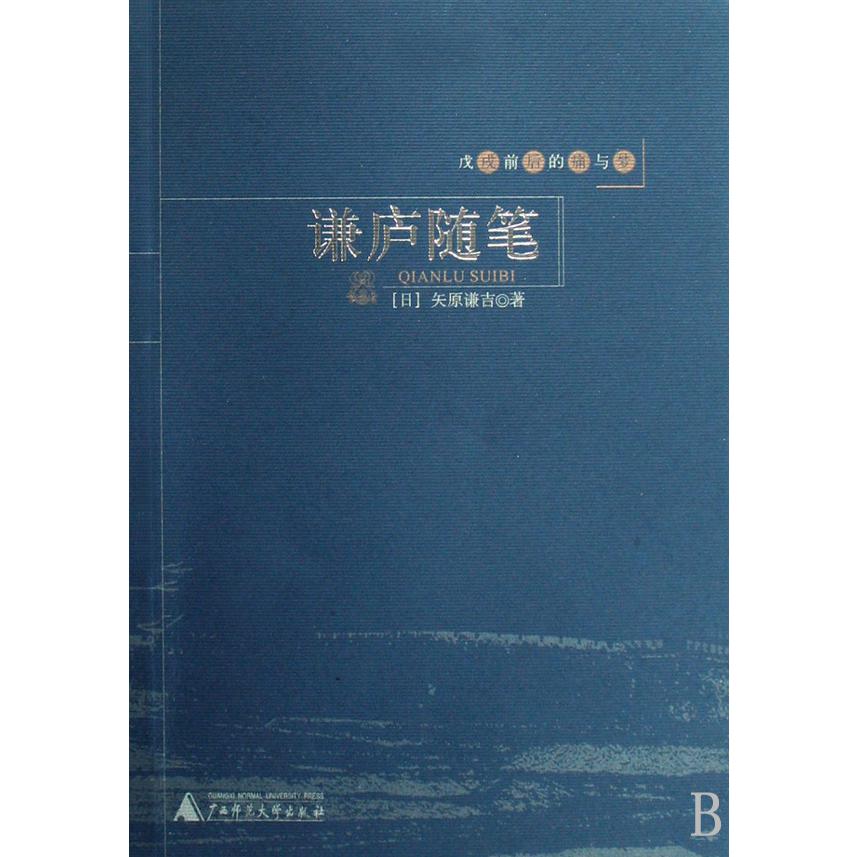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15.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谦庐随笔/戊戌前后的痛与梦
ISBN: 97875633777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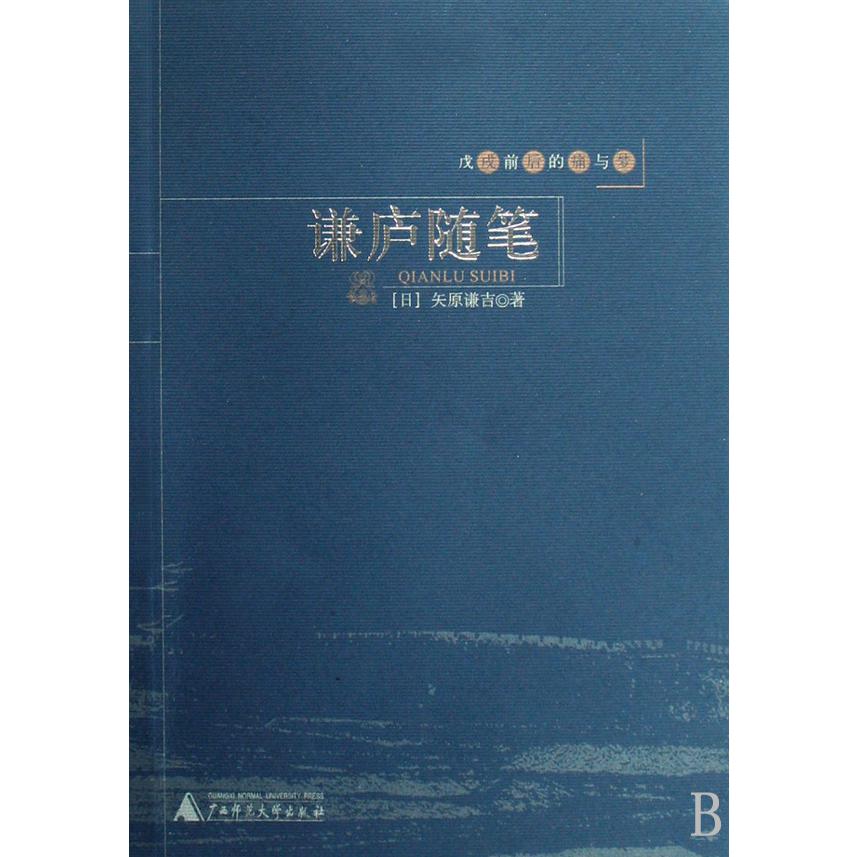
矢原谦吉(笔名谦庐)原籍日本,早年留德习医,学成之后即在中国北京悬壶济世。由于医术湛深,留居北京之达官贵人及其眷属有病皆求诊于矢原大夫,矢原因此遍识政海红员、失意官僚。其所见所闻,皆近代史料。本书所记即抗战前北京的军政界逸事,兼记民国年间种种杂事,饶有趣味。 迨中日大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后即逼矢原离开北京,不得在中国行医。但他个性坚强,不为世屈,移居德国,及希特勒上台后再迁美国,二次大战时病逝于美国。
“义贼”李三 是时也,古城中又有所谓“义贼”燕子李三者,四出活动,军警为之 束手。人谓李其人能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故有“燕子”之名。其人豪侠 疏财,每喜劫富济贫。后以醉卧娼寮时,为鸨儿所卖,遂为侦缉队捕去, 而竞引起公愤。侦缉队长马玉林,遂成唾骂之对象,卒至不得不招待记者 宣布:“燕子”李三,当受特别优待,绝无受刑上镣之事。为证明起见, 更于押赴监牢,公开起解,供人旁观,并为李三特置新衣一套,头插纸制 之小白燕一只,以示殊宠,民愤始平。 讵此一侦缉队长真小人也。为防李三再度越狱,彼竞秘密下令将李之 足胫斩断,使其无法行动。管翼贤语余时,李已残疾废逾半载矣。一日, 马以肠疾,来余处就医。余以不直其为人,且不欲取其诊金,玷污吾手, 乃托词不与相见,嘱护士转告渠“另请高明”。 “现世报”与“眼前报” 《塘沽协定》前后,何应钦、黄郛等相继抵古城,主持划地议和事。 此际,余于交际场合,与何晤面之机会颇繁。尤以何为其同乡贵州丁春膏 氏,邀至北京西城太平桥“砺园”中,赴所谓豆花宴时,同席几达五六小 时之久。观其辞色,察其举止,亦以此次最为直接,最为亲切。 丁为前四川总督丁宝桢之曾孙,时任中法储蓄会副理事长。中法储蓄 会者,南京中央政府进行金融改革前,尝与万国储蓄会并立争雄,改革后 始被南京改组为中央银行信托局。丁在任时,业务蒸蒸日上,绝无衰败之 征。迨后为当道排挤,问题日多。除理事长李思浩另被安排外,丁氏亦被 任为华北烟酒税总局局长,与余往还,较前更密。 丁宅“宫保家风”,颇异凡俗。每宴贵宾必以贵州最平民化之“豆花 ”为一席之主菜,然后佐以家传之“宫保鸡”。 丁宅花园,有亭台阁榭之美,假山曲径小桥流水之胜。每当百花盛开 ,喷水池畔绿草如茵,茅亭内石几石凳,古气盎然,置身其间,更增如人 画图之感。此园大于吾家二倍有馀,而林之幽雅,复远过之。是故,亦诗 人墨客集会吟哦之地也。 余尝谓:中国世家子弟,要可别之为三型。日恶少型,日报应型,日 书香型。吾友丁君,君子人也,“书香型”确可当之无愧。相识者中,几 亦人同此心。平居之日,丁宅“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诚非虚言。 而在座者,颇鲜铜臭之士,炙手可热之人,泰半属斯文一脉,问亦有玩世 不恭者。何遂、张恨水、陈元伯、福开森、方石珊、孔伯华与余,几均每 周必到。 犹忆一夕,丁府招宴。适张季鸾与管翼贤亦在座。张与张恨水,颇于 当时世家子弟不满,称之为“害群之马”,二张与丁君交素笃,乃笑而问 之日:“宫保后人,以为如何?” 丁君起而逊谢日:“舆论权威,一语破的。从来批评纨绔子弟,未有 痛快若是者,当浮一白。” 管翼贤君,时为《实报》社长,亦与丁甚稔,乃更以笑话一则,公诸 同好日:世家子弟既饱受社会攻击,嘲为绣花枕头,遂集议自办日报,专 为纨绔子弟鼓吹。 款既齐矣,社址已得矣,而报名仍付阙如。有世家子弟言于众日:新 闻迅速,为报纸成功之关键。我报之名,必标榜“新闻迅速之程度”不可 。众皆日诺。 旋有纨绔子建议日:我报曷以“现世报”为名,以兆其新闻报道之速 乎? 另一世家子弟忽大呼日:我已寻得更恰当之报名矣。曷即名之为“眼 前报”乎? 语甫尽,满座喷饭。 何应钦惧内成癖 丁君宴何应钦之夕,曾应何君之请,简邀何之妻舅王伯群,以及滞留 古城之三大名旦:程艳秋、尚小云、荀慧生与之同席。何以如此?则非我 所知。外人中,除余外,尚有美人福开森,协和医院名德医克利大夫等。 客人之成分既如一“拌冷盘”,席间自无人一语片言涉及政治。 何君为一雍容之军人,颇有大将风度,人亦和蔼。或谓其素有季常癖 ,家中事事无大小,悉赖夫人一言决之。久而成性,于公事亦然。万事只 秉承上峰决定而已。据新闻界友人语余:何在南京外号之一,为“全国怕 老婆会会长”。关于其“内阃森严”之传说,几可与明将戚继光相媲美。 犹忆席间,何君曾频频以循环系统与妇科症,下问克利大夫与余。并 慨叹南京之大,而颇乏为人信赖之外籍医生。每有疑难之病,必须赴沪求 诊。即在中医方面,古城之大名医有孔伯华、施今墨、萧龙友,而南京只 有一张简斋而已。言次颇致惋惜。且戏语克利大夫日:“先生日后退休, 盍不于返国之前,先往南京悬壶数年,济世救人?目前之南京,贵国专家 学者,颇不乏人,当不致感客中孤寂也。” 克利大夫医术极精,而人属木讷之流,白发苍然,为座中春秋最高者 。闻何言,未仰视逊谢,亦未停箸寒暄,仅答日:“且看将来,一切都视 上帝如何安排耳。”P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