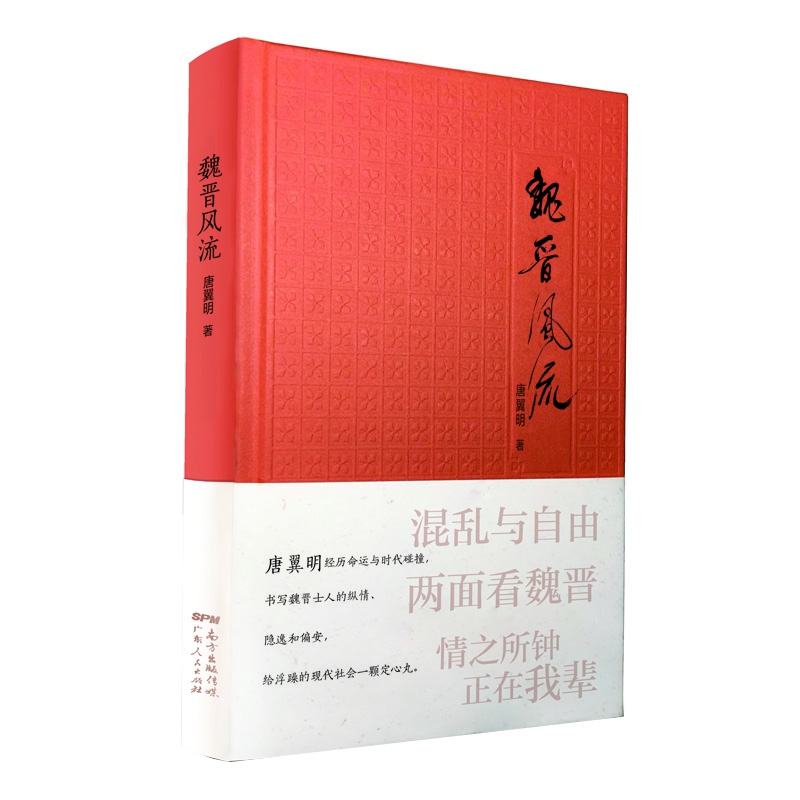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49.00
折扣价: 29.40
折扣购买: 魏晋风流
ISBN: 97872181375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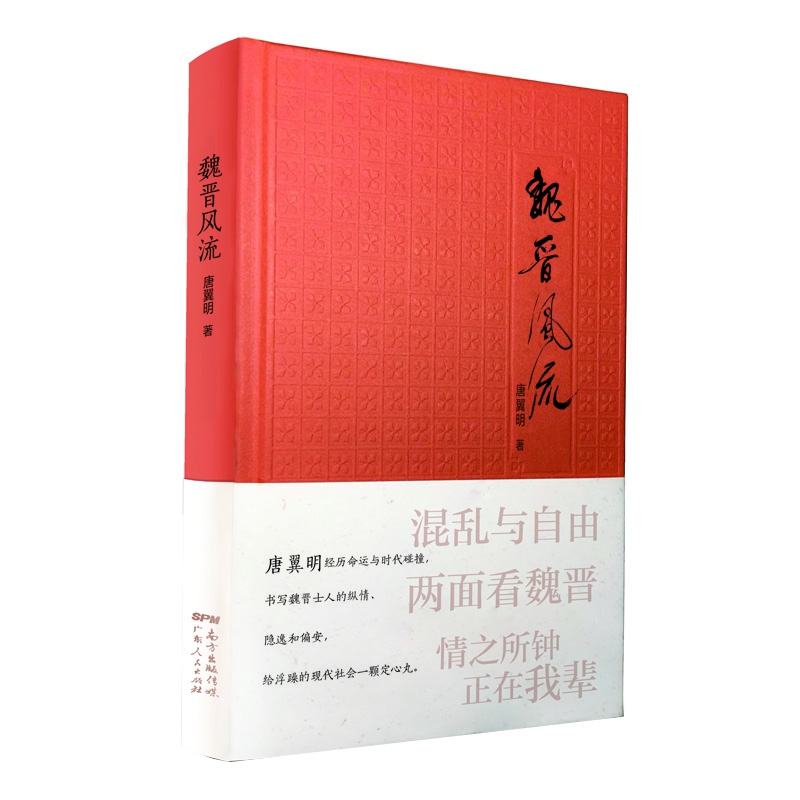
唐翼明,**知名学者,作家,书法家。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硕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曾任**文化大学、政治大学教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兼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著有《古典今论》《魏晋清谈》《魏晋文学与玄学》《魏晋风流》《<颜氏家训>解读》《<论语>诠解》,散文集《宁作我》《时代与命运》《江海平生》《江海清谈》等。
第六章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魏晋士人对情的执着 圣人有情还是无情? 王戎爱子,荀粲爱妻,王徽之爱弟,郗超爱父 魏晋南北朝时,在士族精英分子也就是所谓名士当中,流行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叫作“清谈”。 魏晋清谈探讨了许多哲理,这些哲理构成一股思潮,叫作“玄学”。魏晋玄学与清谈中有一个**的命题,就是:圣人到底有情还是无情?在中国古人的观念里,圣人是***的人,是所有人的典范,在圣人身上体现着天的意志和道的**。天不可攀,道不可见,所以天道是不能直接学习的。人要接近至高无上的天道,只有通过圣人,因为圣人是可以学习模仿的。所以圣人是沟通天道与人的桥梁,一个人通过向圣人学习而接近天道,因而一个人修养的**就是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古人把这叫“内圣”。那么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弄清这个问题,凡人才好学习修炼。尤其在情这方面,圣人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情感问题往往是困扰一生的大问题,人和人之间许多争斗乃至互相残杀的悲剧,常常因情而起。如果说圣人也是有情的,那圣人是不是也会受到情的困扰呢?如果圣人真的很**,似乎应该无情才对,那么“内圣”的*高境界岂非也要做到无情吗?人有没有可能做到无情呢?这些问题在魏晋时代被一些思想家、知识精英提出来反复辩论,这些辩论被后世称为“圣人有情无情之辩”。 “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后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倾向于接受王弼的说法,就是:圣人也是有情的,只是他的情很正,不偏激,不离开人的本性,因而他就不会为情所困扰。说得简洁一点,就是“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 来了解一下王弼。王弼真是人类历**少见的天才,史书上说他死的时候二十四岁,实际上按**的算法顶多二十三岁,如果他生在冬天,说不定还没满二十三岁,因为他是秋天得流行病(古时叫“疾疫”或“时疫”)去世的。但是他在哲学上的成就很了不起,在中国历**没有几个人可以相比,如果我们遴选中国有史以来十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是**名列前茅的。 既然圣人都有情,凡人有情就是很自然的事。这样“有情”不仅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言下之意还是应该提倡的。凡人应该做的只是努力让自己不为情所累,这样就接近圣人了。来听几个有关的故事。 先来看一个父亲爱儿子的例子,主角是王戎,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他生了一个孩子,不幸几个月就死掉了,山涛的儿子山简去慰问他(王戎是竹林七贤中*小的一个,比山涛要小二十九岁,所以跟山涛的儿子山简年龄差不多),看他悲痛得不得了,就对他说:“不过是个几个月的小孩罢了,还不懂什么,用得着这么悲痛吗?”王戎却回答说:“圣人忘情,*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的白话就是:*上等的人,也就是圣人,会忽略情;而下等的人呢,根本就不知情是什么东西,情这种东西就是集中表现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王戎这句话很有名,其实就是“圣人有情无情之辩”在当时名士身上发生的效果。*有趣的是“圣人忘情”这几个字,他不说圣人无情,也不正面说圣人有情,而说圣人忘情,“忘”在这里不是忘记,而是忽略的意思。这其实是王弼“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的另一种说法。“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说的并不是惭愧,而是骄傲。因为前面说了,下等人根本不知道情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辈”也即当时的士族精英分子或说名士,才懂得情,所以情感丰富乃是一件可骄傲的事,标志自己是不同于下等人的上等人。当然他们还没有修炼到圣人忽略情感的地步,但这并不可耻,毕竟圣人只有孔夫子一个,谁敢自称圣人呢?既然不是圣人,又怎能忘情呢?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王戎的这句名言此后便成为魏晋士人在情感问题上的宣言和座右铭,魏晋名士坦然宣称自己敏感多情,并以此作为精英分子的自我标榜。情不仅正当,而且必需,多情不是缺点而是优点,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由于这种思潮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艺术便都有一种“尚情”的倾向,士人们的日常作风就是以感情丰富而风流自喜。 还有一个夫妻情深的故事,主角是荀粲。荀粲出生在一个大士族家里,他是荀子的第十四代孙,他的父亲是曹操的**谋士荀彧,他的堂兄荀攸是曹操的另一位重要谋士,他的叔祖父荀爽在汉末做过司空,他的另一个堂叔荀悦是汉末的大思想家和史学家,写过一部《申鉴》,还写了一部《汉纪》,这两部书到现在还有影响。荀粲自己也是一个思想家,可以说是魏晋玄学与清谈的先驱人物。跟王弼一样,荀粲也是一个少年天才,而且也英年早逝,死的时候才二十九岁(实际上是二十八岁)。他是怎么死的呢?爱老婆爱死的。荀粲爱老婆出名,他特别宣称,讨老婆别的都不重要,*重要是漂亮。他也果然娶了一个很漂亮的老婆(名将曹洪之女)。娶过来之后他疼惜得不得了,夏天晚上热,他就先在露天的天井里把自己摊凉,睡到床上把席子弄凉了,再让老婆来睡,免得老婆热着。到了冬天呢,他就先把自己烤热,钻进被窝里把被窝弄热了,才让老婆进来睡,免得老婆冻着。有一年冬天,他老婆感冒了,发烧,荀粲便像夏天一样跑到天井里先把自己全身冻得冰冷,再贴着老婆睡,想让老婆舒服一点。他睡一会再跑出去,再冻凉了,再跑进来,再贴着老婆睡。没想到这样反复几次,他自己也感冒了。*后老婆还是死了,荀粲悲痛得不得了,别人劝他说,你找老婆只重貌不重德,这样漂亮的女人并不难找,再找一个就是了。他却说,佳人难再得,我这个老婆虽然谈不上倾城倾国,但要再找一个这样漂亮的,也实在不容易啊。过分的伤心终于使他不到一年就送了命。看,荀粲这个人痴不痴,重情不重情? 再讲一个兄弟情笃的故事,主角是王徽之。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字子猷,他有一个弟弟叫王献之,字子敬。王献之才气纵横,字写得跟爸爸王羲之一样好,父子俩在书法**合称“二王”。王徽之**欣赏弟弟的才华,觉得自己不如弟弟。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很高深的老道可以把一个人的阳寿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就去找这个老道,说他弟弟才气过他十倍,他希望弟弟长寿,好多做点事业,愿意把自己的阳寿送给弟弟。没想到老道算了算,说没办法。王徽之问为什么,老道说:“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寿命都没剩下多少了,就算把你剩下的阳寿加到他身上也没有意义。”果然不久之后他们两个都病了,两家仆人跑上跑下传达兄弟两人的相互关怀。有**王徽之突然觉得几天没有弟弟的消息了,想到恐怕大事不妙,就不管自己重病在身,立刻叫仆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去看弟弟。结果一到献之家里,果然发现弟弟已经死了,刚设好灵堂。他没说话,也没哭,从墙上取下弟弟平常喜欢弹的琴,坐在灵前就弹了起来。弹了几次,都不成曲调,他长叹一声,把琴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人琴俱亡啊。”“人琴俱亡”这四个字一直传到**,还能够让人感受到王徽之对弟弟的深情和哀痛,胜过一切号哭。 再讲一个朋友情深的故事,主角还是王徽之。王徽之实在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不仅爱弟弟,也爱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戴逵,字安道,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东晋有名的画家、音乐家和文学家。王徽之和戴逵当时住在会稽一条叫剡溪的江边,但是相隔几十里。有一年冬天很冷,**夜里王徽之大概是冻醒了,推开窗户一看,一片雪白,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看了很开心,觉得很美,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吟诵左思的《招隐诗》,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逵,因为戴逵也是隐士。他便马上叫仆人准备好船,冒着雪溯江而上,要去看老朋友。仆人们划到天亮,才到达戴逵门口。王徽之却突然对仆人讲:“算了,咱们回去。”仆人问:“你不是要来看朋友吗?怎么到了又要回去呢?”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现在我已经满足了,就可以回去了,不一定要见到他。”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多情而率性的人。“乘兴而来”和“兴尽而返”从此成了两个成语,现在还留在我们的字典里。 *后再讲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主角是郗超。郗超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的人,他是桓温*信任*依靠的幕僚。桓温当时是大权在握的军阀,他有篡夺晋朝政权的野心,而郗超则认为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愿意帮助桓温成就大业。他们常常在桓温家里策划阴谋。有一次两人正在卧室里密谈的时候,突然谢安来了,郗超一时无处回避,便躲到桓温的床帐后边。谢安和桓温谈起朝廷的事, 郗超听得起劲,竟忘了自己是躲在帐后,居然插了一句嘴,谢安吃了一惊,但他很机灵,装作毫不在意,跟桓温开玩笑说:“原来你这里还有一个入幕之宾啊。”“入幕之宾”这个词从此成了“密友”(现在也常指“情人”)的代称。郗超帮桓温出主意是瞒着自己的父亲郗愔的。郗愔当时任司空,是一个忠于晋朝的老臣,父子两人政治立场刚好相反,但郗愔并不知情。没想到郗超在三十多岁的壮年得重病死了,郗愔白头送黑发,**哀痛。郗超跟父亲感情**好,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想到如果自己死了,父亲可能会哀痛得把老命送掉,就把一个密封的小盒子交给自己亲近的仆人,说:“如果老爷子只是一般的哀痛,就算了,如果他哀痛得不行,你就把这个小盒子交给老爷子。”后来郗愔果然哀痛得死去活来,仆人就照郗超说的把小盒子交给了郗愔。郗愔打开一看,盒子里面全是郗超为桓温写的篡夺晋朝政权的方案、步骤,以及跟桓温的往来密信。郗愔一看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好,早就该死了。”郗愔的悲痛就这样被愤怒抵消了,老命也就保住了。看,这父子俩多有意思,他们感情深不深、真不真呢?看来政治立场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父子的感情,至少没有减少郗超对父亲的爱敬。 情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必然会具备的。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阶层的精英分子中,出现了许多重情的人物和故事,以上数例只是比较**的。这种重情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重视抒情,而不大注重叙事,没有出现像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篇制宏伟的叙事诗,跟魏晋南北朝的尚情风气很有关系。魏晋南北朝正好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枢纽时期。魏晋南北朝以前,除了屈原,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诗人,大量诗人的出现是建安以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事。而这个时候重情的风气正好在士族阶层中流行,那么后来的中国诗歌主要向抒情一面发展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者对魏晋历史深有研究,征引大量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事实,对其进行解析、探讨,深入浅出,文笔通俗流畅,呈现出作者多年治学的精髓,是读者了解魏晋南北朝时代风貌的**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