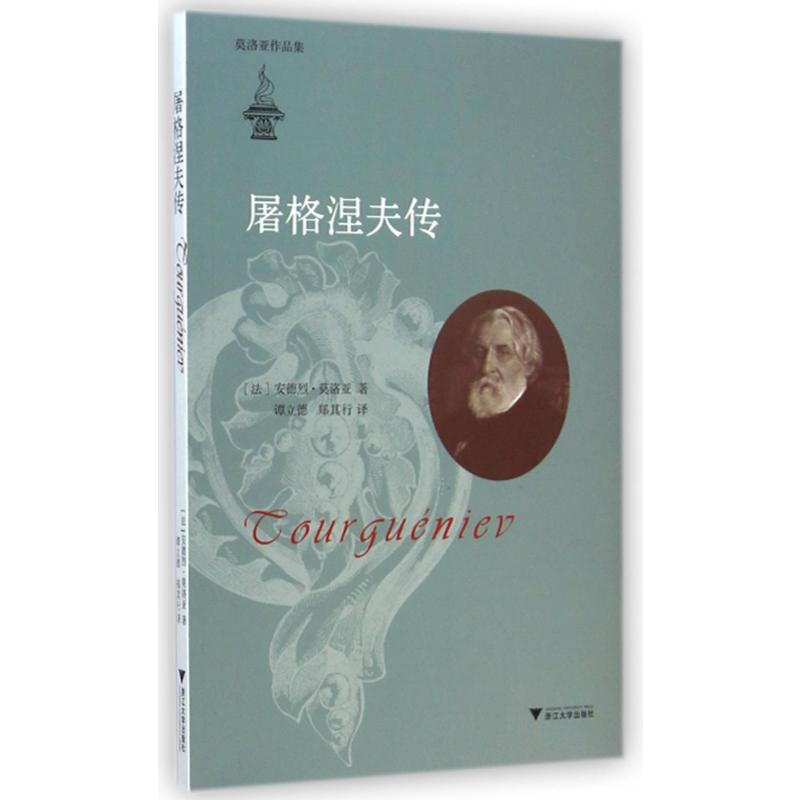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大学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0.80
折扣购买: 屠格涅夫传(莫洛亚作品集)
ISBN: 9787308139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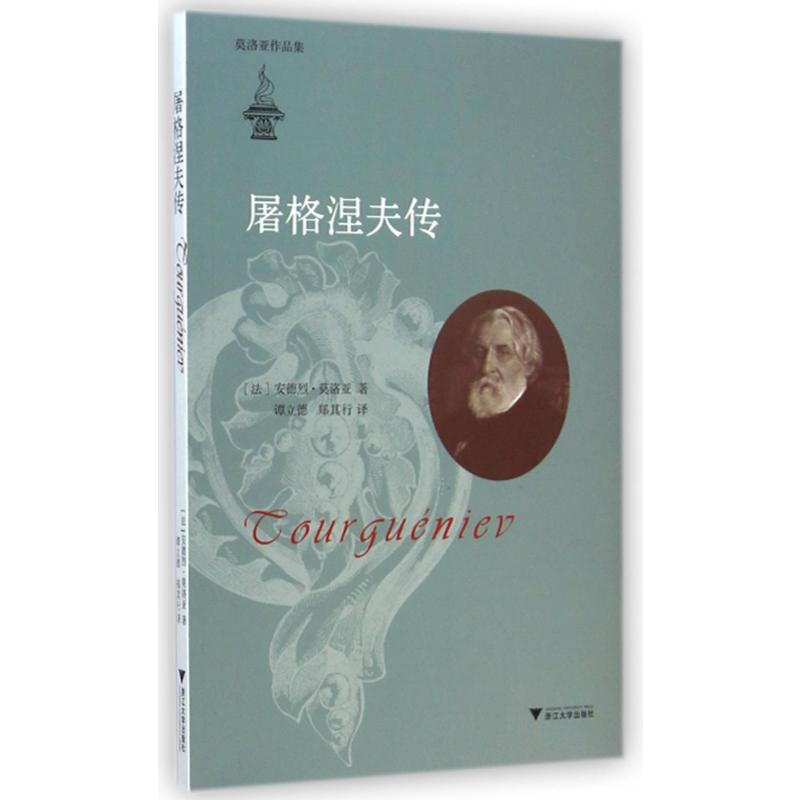
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为法国两次大战之间登上文坛的重要小说家,同时也是优秀的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莫洛亚特别擅长文人传记,所写的传记语言优美,情节生动,富有小说情趣。传记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在莫洛亚笔下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既有学术性、又有艺术性的一种文学样式。《雪莱传》、《拜伦传》、《屠格涅夫传》、《夏多布里昂传》、《乔治·桑传》、《雨果传》、《巴尔扎克传》等被认为是法国文坛最好的人物传记,为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由于在文学、历史方面的成就和对文化界的影响,莫洛亚于1939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65年,戴高乐总统颁令授予荣誉团一等勋章,表彰他一生在文化艺术方面的贡献。其他代表作品有小说《家庭圈子》、《幸福的本能》、《乐土》、《九月的玫瑰》,历史著作《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等。
尽管他幼时的这种家庭生活像在兵营里那样压抑 ,屠格涅夫对在斯帕斯克村度过的童年却始终怀着美 好的记忆。在那儿,富有俄罗斯风貌的景色,似乎具 有一种神秘的美,使熟悉它的游子至死也对它保持着 挚爱和惆怅的缅怀之情。屠格涅夫大概永远不会忘记 山坡上袅袅升起的雾气,婆娑生姿的桦树、山杨及柳 树,还有那收割下来的黑麦和荞麦洋溢在纯净而干燥 的空气中的芳香。 在斯帕斯克村,童年时代的屠格涅夫像那些在乡 村土生土长的孩子们一样,学会了辨别鸟类、树木和 树叶的本领。那儿有一些奇特的老师向他传授知识, 他们不仅向他传授自然知识,而且还有诗歌方面的知 识。屠格涅夫在他的一篇杰出的短篇小说《波尼纳和 巴波利纳》中曾描绘了一个爱好诗歌的农奴。屠格涅 夫同他一起坐在草地上,聆听他朗诵一些诗句。 最近,在俄国发表了一些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 表明,屠格涅夫上校也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教育。这些 信几乎都是写给他的长子尼古拉的。从信中,我们看 到了一个并不像《初恋》中所描绘的那么冷漠、与家 人那么疏远的人物。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屠格涅 夫亲自过问孩子们的生活状况。他在信中写道:“你 当然知道,我对你的学习情况是多么感兴趣……别草 草地只给我写:‘老师们都很满意,我尽力牢记您的 吩咐’。而要把各科情况分门别类详细地写信告诉我 。譬如,在法语和德语方面你学了这个;在拉丁语方 面学了一点、两点……在俄语方面,学了那个……同 样,在地理、历史方面我们学了哪些章节;最后,在 数学方面,我们又学了些什么,以此类推凡是你学的 所有学科,都要详尽地写下来。另外,也别忘记音乐 课程。”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提一下,因为这涉及 一个作家的成长。在这一点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 奇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不同,他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能 用无懈可击的俄语写信。他给他们写道:“你们经常 用法语或德语给我写信。你们为什么轻视自己祖国的 语言呢?……是时候了,确实是到了应该改变这种情 况的时候了!要通晓一门语言,不仅会说,而且要会 写。必定要用俄语来写信。要做到这一点,你们可以 用这样的方法记日记:星期一用法语写,星期二用德 语写,星期三用俄语写,就这样按顺序往复循环。” 约莫在一八二七年,屠格涅夫全家迁居莫斯科, 伊凡便在那儿上学。当初,莫斯科是一座充满神奇诗 意的城市。冬季里,在白雪覆盖的街道上,只能听到 轻轻的马蹄声和雪橇的嚓嚓声。涂了色的大教堂上, 金碧辉煌的圆屋顶在隆冬的静谧中闪闪发亮。在屠格 涅夫的一生中,这些教堂永远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十 四岁时的屠格涅夫是个温柔、懦弱而好幻想的男孩, 他喜爱诗歌与文学。他长得身材高大,略微有些驼背 。后来,进大学时,人家要他在一张纸上签字,表示 并未参加任何秘密社团,他便签了字。然而,出于对 家庭的反抗,他却是个共和党人,而且还在卧室里悬 挂了一幅富基埃·丹维尔的肖像。他周围的同学都自 认为是革命者。在莫斯科大学里,农奴主总是只被比 喻为像猛虎和蛇蝎那样凶狠毒辣。一下课,大学生们 便在宿舍里围坐在茶炊周围,整天谈论着。他们对理 论问题的讨论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兴趣。“请设想一 下,置身于五六个青年组成的集会上的情况吧。只有 一支蜡烛照明,大家喝着变味的茶,啃着硬面包。但 是,请您看一下我们的脸,听一下我们热烈的争论吧 。所有的人都脸上发烧,心情激动,眼睛里进射出热 情的光芒。我们谈论上帝、真理、前途,人类和诗歌 。这时候,天真而轻率的念头就层出不穷;不少荒唐 念头,不少口误激励着这股争论的热情;但是,这又 有什么不好呢?请回想一下发生这一切的那个凄惨、 阴郁的年代吧”。 嗣后,屠格涅夫从莫斯科转到被公认为比较严肃 的彼得堡大学去念书。那儿的教育是按德国的教育方 法进行的。屠格涅夫和他所有的同学一样,经历了一 个受形而上学思潮影响的阶段。当时,歌德的思想, 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十分流行。哲学辞藻使一些最简 单不过的举动都蒙上了一层神圣、晦涩的色彩。大学 生们专程跑到索科尔尼基去“沉湎于宇宙浑然一体的 泛神论情绪之中”。P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