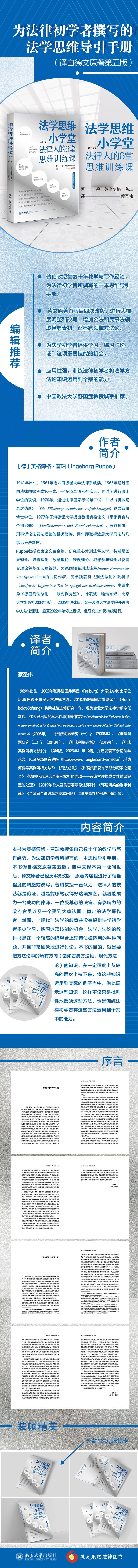出版社: 北京大学
原售价: 69.00
折扣价: 47.00
折扣购买: 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6堂思维训练课(第二版)
ISBN: 9787301350690

作者简介 英格博格·普珀(Ingeborg Puppe),1941年出生,1961年进入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就读,1965年通过德国法律国家考试第一试,于1966至1970年实习,同时间进行博士学位的攻读。1970年,通过法律国家考试第二试,并以《机械纪录之伪造》(Die F?lschung technischer Aufzeichnungen)论文取得博士学位。1977年于海德堡大学提出教授资格论文《想象竞合与个别犯罪》(Idealkonkurrenz und Einzelverbrechen),获颁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法理论的讲师资格,同年即取得波恩大学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教席。 Puppe教授发表论文百余篇,研究重心为刑法释义学,特别是因果理论、归责理论、故意理论、错误理论、犯罪参与理论以及竞合理论等基础法理议题,为德国知名刑法注释Nomos-Kommentar Strafgesetzbuch的共同作者,另单独著有《刑法总论》教科书(Straf recht Allgemeiner Teil im spiegel der Rechtsprechung,中译本为《德国刑法总论——以判例为鉴》,徐凌波、喻浩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006年退休后,续于波恩大学法学院开设法学方法论课程,直至2022年始停止授课,但研究工作仍持续进行。 译者简介 蔡圣伟,1969年出生,2005年取得德国弗莱堡(Freiburg)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学系,2010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Humboldt-Stiftung)奖助赴德进修研究一年,现为台北大学法律学系专任教授。迄今已出版的学术性单独著作有Zur Problematik der Tatbestandsalternativen im Strafrecht- 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Lehre vom strafrechtlichen Tatbestands-merkmal(2006年)、《刑法问题研究(一)》(2008年)、《刑法问题研究(二)》(2013年)、《刑法判解评析》(2019年)、《刑法案例解析方法论》(第4版,2023年)等书籍,并已发表百余篇法学论文,以及多场影音讲座(https://www. angle.com.tw/media/):《为何要学案例解析方法?》《刑法总则》《诈骗集团及车手所涉犯罪之竞合》《德国犯罪理论与案例解析的连动——兼论容许构成要件错误案型的处理》《2019年杀人及伤害罪章修法评释》《环境污染的刑事制裁》《台湾罚金刑改革之基本问题》《食安事件的刑法问题》等。
一、描述性概念 在今日,法律概念通常被称作规范性的(normativ),因为它们出现在规范当中,而且是在考虑过适用此规范所追求的结果后才被确定。 但规范性概念这个表述,暗示(有时也指称)了相关的概念——根据其内涵、意义来看——是在表达一个规范。在这种意义下,评价性概念,像“违反道德”“违反诚信”“特别可非难”或是“卑劣的动机”等,是规范性的概念。它们蕴含了规范,告诉人们应当从事或不要从事这些概念所指称的行为。反之,描述性概念则没有表达任何的规范。但只要描述性要素出现在法规范中,它们就会确定这个规范的意义,因此,在确定这些要素本身的描述性意涵时,就会考虑到相关规范产生的后果,也就是会根据这个规范应该具有的内涵来确定。现在,如果我们只是因为要通过相关规范应具有的特定内涵来确定这些概念,就把所有出现在规范中的概念都称为规范性概念,就是把决定概念内涵的理由和这个概念内涵本身混为一谈了。 我们可以用“人的生命”这个概念来说明此一区别。民法上的权利能力,也就是民法上人的生命始于生产结束。从这一刻开始,他便成为权利义务的承担者。这对继承权有其意义。如果胎儿是在出生后死亡,他就可以成为继承人,并且可以让这个胎儿的法定继承人继续继承。但他若是在生产过程中就死亡,那么在继承程序中就不会考虑到他。刑法上,人的生命则是始于生产开始,较精准地说,是始于阵痛开始。关于人的生命,刑法上的确定方式异于民法,这有其道理,希望借此在生产过程中就能够给予新生儿完整的生命保护,特别是针对过失的侵害,而不仅只是像现行法对胎儿所提供的那种不完整保护。规范性的理由则是在于,生产阶段特别危险,所以要求参与者(尤其是助产的医师)必须特别注意。无论是对于民法上人之始期的确定还是对于刑法上的确定,我们都可加以争执。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看法:就算是还在母体中的胎儿,也应当具有权利能力,并且应该在继承程序中被顾及。或者也可以采取以下的意见:生产过程中的婴儿只应该针对故意杀害而受到保护,但不应及于过失的侵害。这样的争执涉及规范及其内容和理由,因此被称作规范性。但这一点并不会影响以下的事实:这两个被争执的人的生命概念,都是纯粹描述性的确定。婴儿是否脱离母体(生产是否完成),我们原则上都看得到,生产过程(开启阵痛)是否业已开始,我们也可以通过阵痛测量器来确定。 有人主张,描述性概念(beschreibende Begriffe)就是指一种经由纯粹的感官知觉就能正确运用的概念,而无须对之进行心智上的理解(geistiges Verstehen)。《德国刑法》第311条第1项释放电离辐射罪(Freisetzen ionisierender Strahlen)中的“电离辐射”(ionisierende strahlen)这个概念,毫无疑问地是一个描述性概念;但若没有“心智上理解的动作”(Akt geistigen verstehens),我们就不可能正确运用得了这个概念。原则上,这适用于每一种概念,当然也包括了那些最简单、日常生活中最为一般的概念。凡是在心智上没有正确理解汽车或自行车这些概念的人,在看到一辆汽车或自行车时,就不可能正确地运用这些概念。描述性概念的特性在于,那些含有描述性概念并将之运用到某种情形上的语句,有真伪(假)之别,也就是说,描述性概念是在描述事实。 这可能是自然的事实,也可能是所谓制度性事实(institutionelle Tatsachen)。后者是指社会上的事实,包括权利与法律关系(Rechte und Rechtsverh?ltnisse)。在这里,“规范”这个时髦用语再度引起了混乱,因为描述权利与法律关系的概念也被称作(应与描述性要素对立的)规范性要素。然而,一个描述权利与法律关系的语句也会有真伪之别。若这个语句为真,那么它便描述了一个事实。当一个动产属于别人所有,这个动产对我来说就是他人之物,我是否有请求权,某个人合团体是否为民事法上的公司,等等。为了正确运用这些概念,都会需要心智上理解的动作;但这一点并不能区分规范性要素与其他描述自然事实的描述性要素二者。 二、模糊概念 若是把“如何在内容上确定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和“为什么是如此确定这个概念”这样的问题相混,就会把模糊的(vag)、不确定的(unbestimmt)概念称作规范性概念,甚至是评价性的概念。然而,模糊概念绝对有可能是描述性的。像数量上(quantitativ)的模糊概念,如《德国刑法》第315条之3的“贵重物品”(Sachen von bedeutendem Wert)、第248条之1的“价值轻微之物”(geringwertige Sachen)、第263条第3项第2款的“重大财产损害”(Verm?gensschaden gro?en Ausma?es)以及《德国麻醉药品法》第29条之1第1项第2款的“并非微量(nicht geringer Menge)的麻醉药品”。 我们可以规定出一个所谓极限值(Grenzwerte),将部分数量上的概念转换成数字,予以精确化。在确定这个极限值时,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确定会对含有这些数量概念的规范在适用上产生何种效果,但这并不会改变这些概念依其内涵是纯粹描述性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犬只管理法》(Hundegesetz)第11条,规定了所谓“大型犬”的饲养。饲养大型犬者,必须通知主管机关,证明其可靠并具有专门知识,为该犬投保主要责任险,以及用晶片作为犬只证明并标示其饲主。在公共街道上应使用牵绳控制大型犬。“大型犬”这个概念本身是模糊的,但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犬只管理法》第11条第1项将之定义为“肩部高度40厘米以上或重量20公斤以上”的犬只。立法者在描述这个立法定义时,肯定是受以下这个规范性的问题所导引:狗要到多高、多重时,源自兽性或不当饲养对待的危险,会大到需要适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犬只管理法》第11条所设的规定及限制,才能抑制这样的危险。于此要考虑的是,部分的类似危险也可能来自较小的犬只,但这不会改变此一“大型犬”概念的立法定义系属纯粹的描述性,且相当精确。这有益于法安定性以及行政机关操作的简化。倘若只有“大型犬”这样的模糊概念,主管机关就必须根据个案逐一认定相关犬只在该法的意义下是否已属大型,并有《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犬只管理法》第11条关于豢养限制的适用。这个为了法安定性所付出的代价,当然就是开始头痛的界限,肩高几厘米或体重重半磅的少许差异,就可能影响到有无《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犬只管理法》第11条规定的适用。 对于数量概念所做的数字定义,其优点和缺点在行政法上已众所周知,像空气污染保护法(Immissionsschutzrecht)。在《德国环境影响保护法》第48条中,就一再委由行政命令制定者【译按:相关事务的行政主管机关】甚或司法实务界,规定所谓极限值,对于这些数量概念提出数字定义,以求这些数值能够快速地适应相关法领域的事实变更以及自然科学上的新知。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曾经将重大财产损害这个概念精确化,将之定在5万欧元【译按:约人民币39万元】以上的损失。对此,最高法院有其规范面的理由。为了法安定性及明确性,最高法院放弃让重大财产损害这个概念取决于个别诈欺被害人的财产状况,让法安定性优先于公平标准所要求的区别处理。这个决定有其规范性的理由,并且我们也可以用规范性的理由来争执这个决定,但这都不会改变以下这一点:“5万欧元以上之财产损害”这个概念,依其意义是纯描述性的。我们的法律之所以运用这种模糊的数量概念,是为了让法院能够根据不同的状况调整其内涵,而无须因此更动法条文字。如果日后欧元贬值,最高法院就可以将重大财产损害这个概念改定为10万欧元以上的损失,而不必更动法条的文字。 然而,即便立法者自己立刻就能用数字来确定数量概念,也还有另一个支持立法者把这件事交由司法实务来做的理由,那就是标界的痛苦(Schmerz der Grenze)。举例来说,我们绝对能够证立,招致重大财产损害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诈欺,但这还是无法让人明了,为何这个重大损害要从5万欧元起算,而不是4.9万欧元或5.1万欧元。尽管如此,总还是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划出一条界限。没有某程度的恣意,就不可能办得到,因此不会公然出现在成文法中,而是现身在司法实务的怀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犬只管理法》则是一个反例,但在那里所涉及的法律效果,不像刑法中那么重大。 也有一些模糊的数量概念无法通过定义转化成精确的数字,尽管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因为,一如我们在知识论中所说,这些数值概念并非有效的概念。也就是说,要应用这种概念的人,无论是人民还是法官,都没有能力自行取得事实面的认知来查明数值。对此,危险(Gefahr)概念就是一个经典范例。我们只有在负面评价某个(危险判断所涉及的)事件时,才会使用危险一词;就此而言,危险概念具有评价成分。如果是正面评价一个事件,我们会把该事件发生的概然性称作机会。但是在概念上,我们可以将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然性与对该事件的负面或正面评价区隔开,然后获得概然性的模糊数量概念。人们一再尝试在量上去确定危险概念,像被负面评价的事件,其发生的概率必须大于不发生的概率。精确地说,这也就是意味着高于50%的概率。首先,这多少是恣意定出的。难道危险的概然性系数不也应该要顾及损害的大小吗?但无论如何,规定出这种数值的意义也不大,因为,不管是法官还是作为规范相对人的市民,在行为当下都没有办法指出或查明发生损害的概然性系数。举例来说,若涉及《德国刑法》第315c条道路交通中的具体危险,势必就要广泛地做交通上的统计调查。此外,就算这样也还是没有确定,调查时应考量个案中的哪些事实,以及必须将哪些事实抽象化。这些对于事件的概然性调查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人们不将危险这个模糊的数量概念转化成数值概念,而是尝试将之转化成一种质的概念(qualitativer Begriff),尽管这样从知识理论的立场来看是某种退步。实务与通说将具体危险定义成一种情状,在这种情状中,某个特定损害发生与否“仅取决于偶然。这个描述具有诱导性,严格说来,其实什么都没讲。第一,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取决于偶然;第二,仍旧不清楚的是,哪些建构危险或阻碍危险的事实在这里应该被当作(或不被当作)偶然。我则会这样解释危险概念:当其他交通参与者为了避免损害而被迫采取不寻常的措施,而这些措施成功与否要取决于他的能力时,就存有道路交通上的危险。 法律人,特别是法律学者,经常抱怨概念的模糊,并且习于指摘其对手的概念建议会导致无法忍受的区分困难(反之,如果是自己的概念建议会造成区分困难,那么这样的困难就是无可回避的)。当然对实务界来说,就如同业已显示的,反而经常会乐见概念某程度的模糊与弹性。我们也是倾向跳过那些法律概念可否适用于不具有争议的大部分适用范围,而将目光集中在概念适用的边界领域。 ? 普珀教授集数十年教学与写作经验 ? 为法律初学者撰写的法学思维导引手册 ? 德文原著首版后四次改版,进行大幅度调整和改写 ? 增加公法和民事法领域经典素材,凸显跨领域方法论 ? 训练法律初学者将法学方法论知识运用到个案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