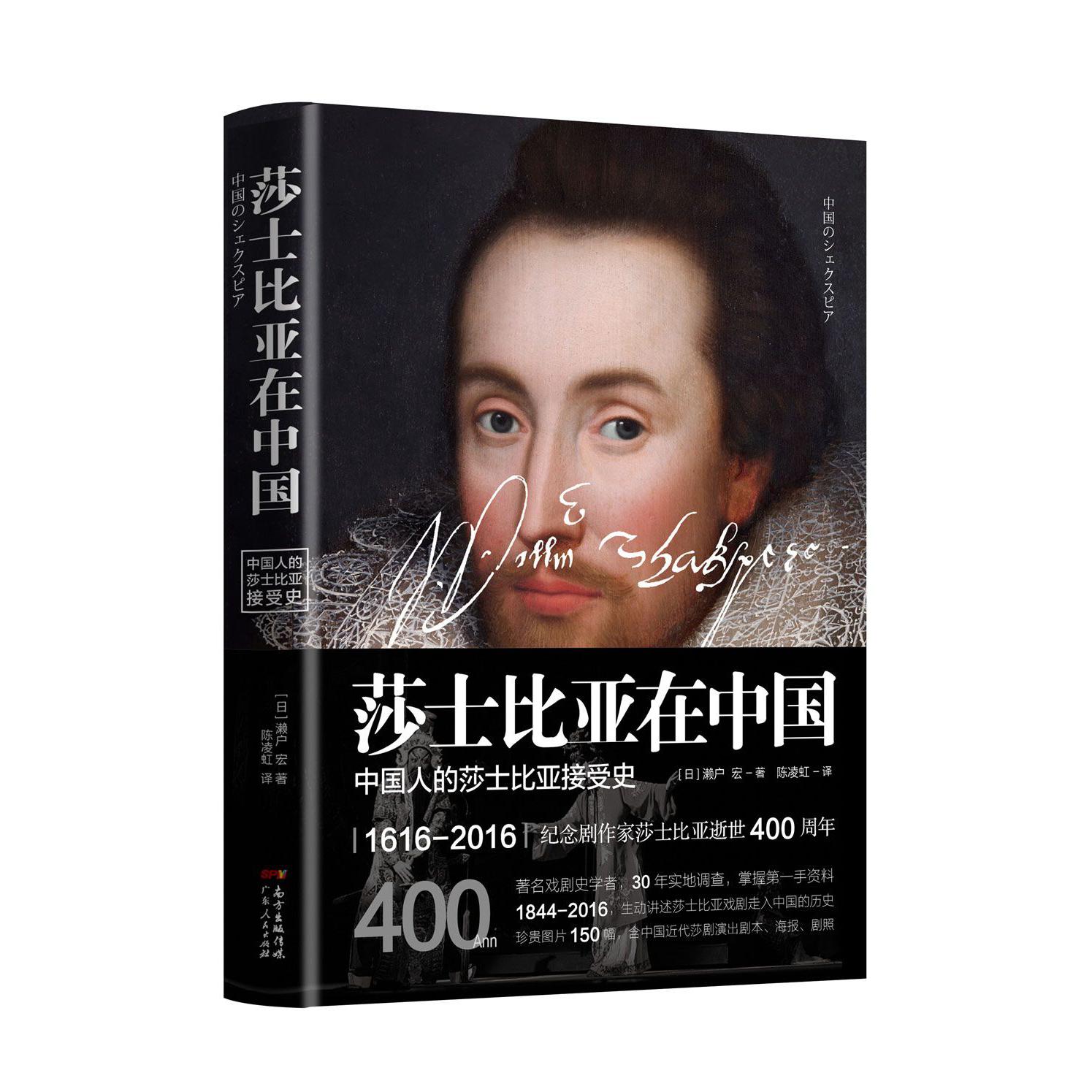
出版社: 广东人民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3.30
折扣购买: 莎士比亚在中国(中国人的莎士比亚接受史)(精)
ISBN: 9787218113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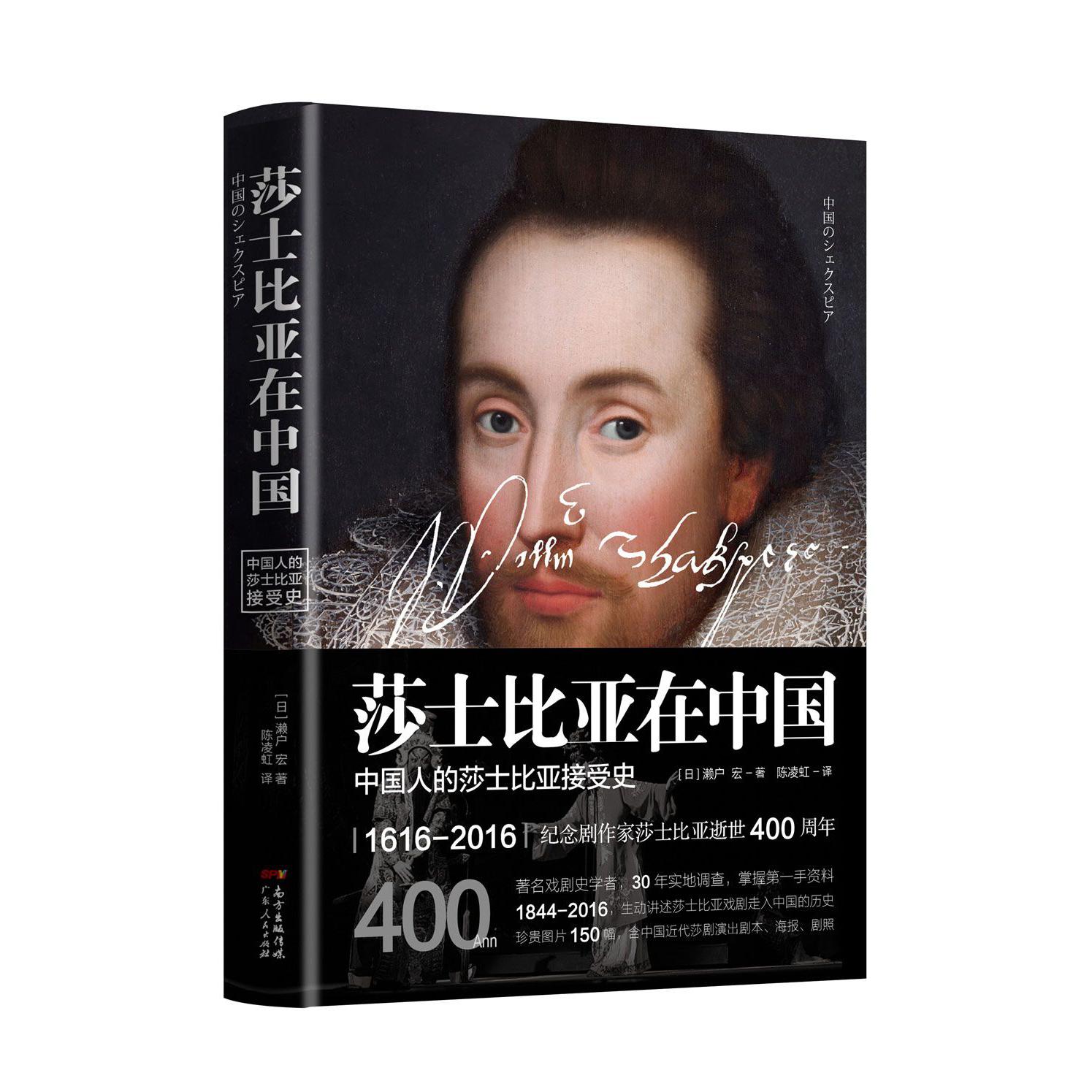
陈凌虹,云南昆明人,2012年在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取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日戏剧交流史、比较文学。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在中、日、韩三国的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沦文十余篇,2014年8月出版日文专著『同中演剧交流の诸相一中国近代演剧の成立』(思文阁),2015年6月获得第20届“日本比较文学会奖。 濑户宏,1952年生于日本大阪府。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博士(文学),现为摄南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困近现代义学和戏剧。、主要著作有『中国の同时代演剧』(好文出版,1991年,日文)、『中国演剧の二十世纪 中国话剧史概况』(东方书店,1999年,日文)、『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东方书店,2005年,日文)、『文明戏研究の现在』(合著,东方书店,2009年,日文)等。
两个月后,即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淹 没了林纾与新青年成员的这场论证。如前文所述, 1924年10月19日林纾作为清朝遗老离世。 林纾逝世次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1924年11 月号上发表了《林琴南先生》一文,“对林纾生平、 思想及其对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上的贡献作了全 面的评价”。27对于林纾晚年的守旧思想,郑振铎认 为“然而他的主张是一个问题;他的在中国文坛上的 地位,又另是一个问题;因他的一时的守旧的主张, 便完全推倒了他的在文坛上的地位,便完全堙没了他 的数十年的辛苦的工作,似乎是不很公允的”,给予 林纾相当高的评价。 对此,樽本先生认为“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 一文,标榜公正评价的同时从根本上就是不公正的。 此文正是造成林译小说冤案的发端”。樽本先生做出 这样评价,一是因为郑振铎误解林纾将莎士比亚(以 及易卜生)戏剧改译为小说形式,二是因为樽本先生 认为“介绍五四时期文学状况时多会引用郑振铎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中发表的导言。 既然郑振铎是当事人,那么可以认为他非常了解详细 情况……他是文学革命派的一员……我们在阅读郑振 铎的文章时应该注意其是有所偏向的”。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批判很难成立。 1919年时,《新青年》成员多在30岁左右,例如 陈独秀(40岁)、鲁迅(38岁)、钱玄同(32岁)、 刘半农(28岁)、胡适(28岁),他们和当时只有21 岁的郑振铎之间有着很大的年龄差。不过,也有傅斯 年(23岁)、罗家伦(22岁)这样20多岁的成员,因 为他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与此相对,郑振铎当时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如 今的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大学没有关系。 因为《鲁迅日记》中首次出现郑振铎的名字,是在他 迁居上海后的1921年4月11日。郑振铎后来在上海成 为《小说月报》编辑部的核心人物,与《新青年》成 员有了相近的社会地位,或许这个时候有机会知道当 时的情况,但很难认为1919年时郑振铎是《新青年》 的一员(当事人)。并且,多数《新青年》成员没有 加入文学研究会。笔者认为,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 大系》第二集导言部分说明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 的真相,不是因为“破罐破摔”,而是带着责任感和 良心去记录被隐藏的事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胡适、郑振铎是真的 以为“林纾将莎士比亚戏剧改译为小说形式”,而不 是故意扭曲事实。胡适曾编辑《新青年》戏剧改良专 号,郑振铎曾给《戏剧》第1卷第3期投稿《光明运动 的开始》,可见二人对话剧运动有着一定的理解,对 小说与戏剧的区别也相当敏感。前文也已经说明林纾 自身的翻译态度是引起误解的主要原因。樽本先生虽 然说定论“近乎捏造”引,但却无法断言这就是“捏 造”。 林译《雷差得纪》等文不是林纾将莎翁戏剧改译 为小说的译本,而是以奎勒·库奇的《莎士比亚历史 剧故事集》为底本的译本,樽本先生的这个发现非常 重要。樽本先生的发现是中国莎学接受史研究上重要 的研究成果,笔者对此毫无疑问。但是,如前文已经 论证的那样,引起郑振铎等人误解的直接原因是林纾 没有理解戏剧与小说的本质区别,并且没有明确记述 翻译底本。“林纾把莎翁戏剧改译为小说”这种定论 形成的原因在林纾本人。郑振铎指出,这不单是林纾 自身的问题,也是中国旧文人共同的问题,有着时代 和文化的缘由。总体来说,郑振铎的《林琴南先生》 一文对林纾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刘半农、胡适、 郑振铎等新文化运动活动家“恣意的断定”造成了定 论,从而使林纾蒙受冤屈的这种观点,不仅不符合历 史事实,更是对郑振铎等人附加的另一种冤屈。 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在此之前确实认为“《 雷差得纪》等文是林纾将莎翁戏剧改译为小说形式的 文章”。樽本先生提到了研究者的责任问题,那么在 樽本先生指正之后,大家可以尽可能地更正以往的记 述错误,这是研究者承担责任的方式,本论文的发表 也是笔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林纾 把不是莎翁作品的文章当作莎翁作品来译介也是事实 ,笔者认为没有必要修正郑振铎“林先生大约是不大 明白小说与戏曲的分别的”的观点,也没有必要为此 而改写中国莎士比亚接受史的主要线索。 P96-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