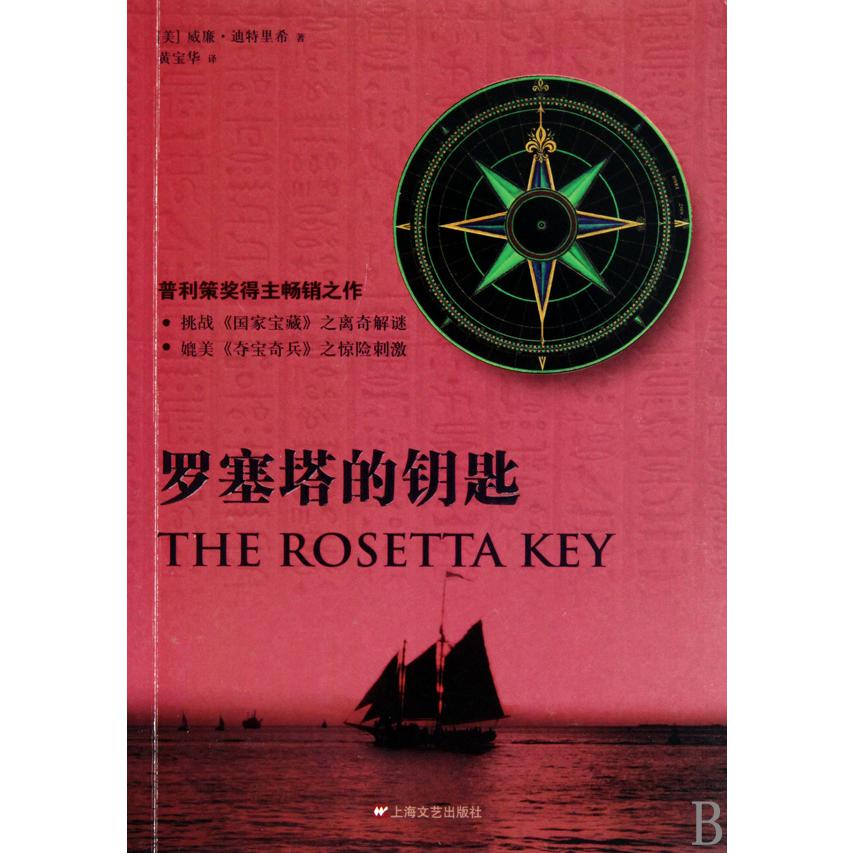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17.10
折扣购买: 罗塞塔的钥匙
ISBN: 9787532139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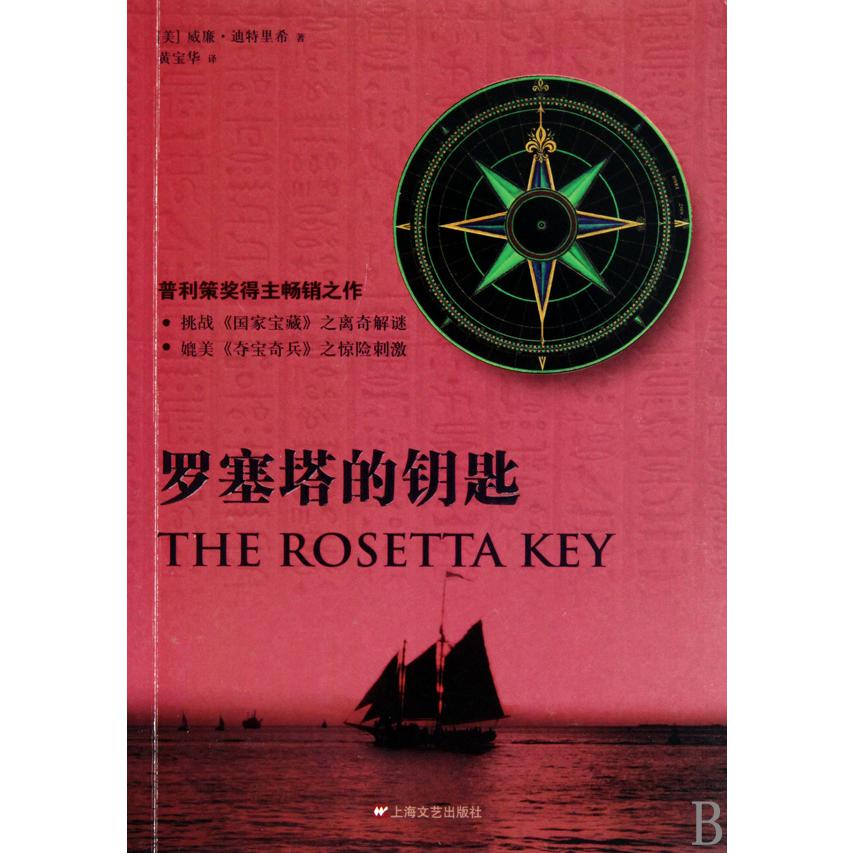
威廉·迪特里希,一九五二年生于美国华盛顿,后毕业于华盛顿大学新闻系。他是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为《西雅图时报》工作期间,撰写了许多杰出的科学报道,一九九O年获得普利策奖。 从小喜爱历史的威廉·迪特里希之前曾以罗马帝国为背景,创作了《上帝之鞭》等作品。《拿破仑的金字塔》是他的第一本畅销历史冒险小说,其续集《罗塞塔的钥匙》同样广受欢迎,从而使他跻身于畅销作家之林。
眼看着一千支毛瑟枪的枪筒对准了你的胸膛,势必会迫使你去思考,难 道我真的走错了道?我确实这么寻思来着,每一支枪的枪口看上去活像游荡 在开罗城小巷子里的杂种狗张开了血盆大口。但是,不,尽管我不免过分谦 虚,我也有自信正确的一面——而且,依我之见,误入歧途的不是我,而是 法国军队。这一点我原本可以向我先前的朋友拿破仑·波拿巴说明的,假使 他没有待在远处的沙丘上,远到连招呼声也达不到。他高高在上,却心烦意 乱,身上的纽扣和勋章在地中海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波拿巴在一七九八年率领他的大军在埃及登陆,那是我第一次在一处海 滩上跟他在一起,他告诉我,那些沉没于大海的人将永垂青史。如今,九个 月后,在巴勒斯坦的港口雅法雅法(Jaffa):巴勒斯坦城名,在亚柯之南, 濒地中海。城外,历史将由我来造就。法兰西的掷弹兵们正准备好了要向我 射击,同时还要射杀那些我混杂于其中的不幸的穆斯林俘虏。我,伊生·盖 奇,又一次想要设法谋划一条逃避厄运的途径。你能看到,这是一起集体大 屠杀,我跟原先试图与之交好的那位将军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在这短短的九个月间,我们俩分道扬镳,走得该有多远! 我在那些可怜的奥斯曼俘虏中所能发现的身材最高大的人,是一位来自 尼罗河上游的尼格罗尼格罗(Negro):原居住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一个 人种,以深色皮肤及浓密鬈发为主要特征,即一般所谓的“黑人”。巨人, 我将身子挪动到了他的背后,我估算着他身体的厚度足以抵挡住一颗毛瑟枪 的子弹。我们这批人活像一群晕头转向的牲口,被驱赶到了一处风光怡人的 海滩,黑黢黢的脸蛋上嵌着白又圆的眼睛,土耳其的军服五色杂陈,有猩红 、奶油、祖母绿、蓝宝石等不同的色彩,上面又沾染了经过野蛮劫掳而留下 的烟尘和血迹。人群中有肌体柔软的摩洛哥人,高大冷峻的苏丹人,凶猛好 斗、皮色白皙的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加西亚切尔加西亚(Circassian):高加 索人的一支,又译作“切尔克斯人”。的骑兵,希腊的枪炮手,土耳其的军 士——一个庞大帝国中四处募集而来的杂牌军团,全成了法兰西人手下的残 兵败将,而我,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美国人。不仅我被他们那些五花八门的 聒噪弄得一头雾水,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往往不知所云。这批乌合之众乱哄 哄地聚成一堆,他们的长夜已经死了,他们那种狼狈不堪的败军之相跟行刑 者们齐刷刷的队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排成了整齐的队列,仿佛要齐步 行进,接受检阅。奥斯曼土耳其的公然对抗激怒了拿破仑——你无论如何不 能将我使者的头颅砍下,再挑在长矛尖上示众——再者,这一大批饥肠辘辘 的俘虏势必成为大军的一个累赘,牵制着他的征讨行动。因此,我们被驱赶 着穿过了柑橘丛林,来到一处月牙形的沙滩上,就在那沦陷了的港口的南面 ,波光闪烁的大海在此形成了一道碧绿与金黄相间的优美动人的浅湾,山顶 上的城市则在闷火中慢慢地燃烧。我能见到一些青翠的果子依旧垂挂在被炸 毁的树上。我从前的恩主,如今的敌手,端居在他的坐骑上,就像年轻的亚 历山大大帝,正准备(出于孤注一掷或恶毒的算计)展示他无毒不丈夫的手段 ,以此为即将来临的许多大战役立威壮行,他手下的将领们对此会窃窃私语 ,而他却充耳不闻,毫不在意!此刻他正在读一本抑郁寡欢的小说,他有一 个好似吞书一般的习惯,读完一页就将它撕下来,然后递给身后的军官。我 双脚赤裸,满身血污,按乌鸦直飞的距离计算,离耶稣基督为拯救世界而受 难的地点此指各各他(Golgotha),又称“髑髅地”(Caluary, place of skull),在耶路撒冷城外,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仅四十英里。我 以往经受过迫害虐待和战争磨难的那些日子并没有让我信服我主耶稣的种种 努力已完全成功地改善了人性。 “预备!”一千支毛瑟枪的击锤往后扳动了。 拿破仑的忠实信徒们指控我是一名奸细,一个叛徒,这就是我为什么会 随其他的俘虏一起被驱赶到这海滩上来的原因。然而的确,情况表明这样的 说法也道出了若干实情。但是,无论如何,我在开始的时候并未怀有这样的 意图。我原先只是待在巴黎的一个美国人,凭着那点一知半解的电学知识— —也是为了逃避一桩完全冤枉的谋杀指控——我终于得以厕身于拿破仑手下 的科学家或智者的团队中,那是去年正当拿破仑大举进军埃及的时候。我还 养成了一种习性,每每在错误的时刻站到了错误的一边。我曾遭到来自马穆 鲁克马穆鲁克(Mameluke):原意为奴隶出身的人,后指奴隶出身的军人,他 们曾取得过对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控制权。骑兵、我所喜爱的女人、阿拉伯的 断喉杀手、英国舰船上的舷炮、穆斯林狂热分子、法兰西排枪队的火力攻击 ——我真是个招人喜欢的人! 我最近的一个冤家对头是一个名叫彼埃尔·纳贾克的法国人,这个无赖 恶棍既是个杀手,又是个窃贼,他始终忘不了那件事情,就是当他试图从我 身上抢走一枚神圣大勋章时,我曾从土伦的驿车下开枪击中过他。此事说来 话长,上一部书中已表过不赘。纳贾克就像一笔坏账,重又闯入了我的生活 。是他使得我混迹在那些俘虏的行列里,背上抵着骑兵的军刀,被驱赶着前 行。他期待着我即刻面临的死亡,就像一个人掐死一只特别令人憎恶的蜘蛛 时所怀抱的那种既洋洋自得又心存厌恶的情感。我一直后悔没有将那一枪瞄 得高一点点,向左移两英寸。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一切似乎都因赌博而起。早先在巴黎的时候,在一 局牌戏中我赢得了那枚神秘的大勋章,麻烦就此接踵而至。这一次,事情似 乎又简简单单地重新发生了——我在一艘英国皇家舰艇“危险号”上,把那 些晕头转向的水手身上的每个子儿都掳了过来,然后那些英国人将我抛到了 “圣地”圣地(Holy Land):指巴勒斯坦。的岸上——却什么也没有解决, 而且有一点能得到证实,即它事实上导致我陷入了目前的困境。让我重申一 遍:赌博是一种恶习,靠碰运气是非常愚蠢。 “瞄准!” 但我已超越了我自身。 我,伊生·盖奇,在三十四个春秋中,将大部分的时光用来设法避免种 种麻烦,摆脱过多的劳作。正如我的导师,还一度曾是我的雇主的已故伟人 本杰明·富兰克林会理所当然地评说的,这两种期望就像正电和负电那样是 正相冲突的。追求后者,即无需劳作,几乎肯定要使前者,即免于烦恼落空 。但这是一个教训,就如同喝过酒或背弃了漂亮女人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 头脑胀痛,这种教训多少次地记取,也就会多少次地遗忘。是对辛勤劳作的 厌恶促使我越加迷恋赌博,赌博让我赢得了大勋章,大勋章又将我带到了埃 及,连带着这个星球上一半的恶棍都随我接踵而至,埃及使我心爱的女人阿 丝蒂莎得而复失。她劝告我相信,我们务必将世界从纳贾克的主子,那位法 国和意大利种杂交的伯爵、巫师亚历桑德罗·西拉诺的手中拯救出来。所有 这一切,大大出乎我所预料的是,将我推到了波拿巴那错误的一方。随着事 态的发展,我爱上了一个女人,还找到了一条进入大金字塔的秘密通道,作 出了迄今最惊人的发现,结果让自己的心爱之物丧失殆尽,只落得被迫乘着 气球出逃。 我曾对你说过,此事说来话长。 不管怎么,那位美艳绝伦而又叫人神魂颠倒的阿丝蒂莎——她原本是来 取我性命的杀手,后来成了仆人,再后来则是埃及的女教士——跟我的敌手 西拉诺一起从气球上摔落下来,掉进了尼罗河。此后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想 打探到他们的命运,我的敌手最后对阿丝蒂莎说的话是:“你知道我依然爱 着你!”此事加倍增添了我的烦恼。每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心里会作何 感想?他们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怎么竟会同意让那个英格兰狂人 锡德尼·史密斯爵士,就在波拿巴的大军入侵之前,把我撂到了巴勒斯坦的 岸上去打听情况。后来事情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直至现在我站在这块地方 ,面对着一千支毛瑟枪。 “射击!” 但是,在我向你述说毛瑟枪闪出火光时发生了什么之前,也许我应当回 溯到我先前的那个说部中断了的地方,那是在1798年10月的晚些时候,当时 我正身陷在那艘不列颠舰船“危险号”的甲板上,它风帆鼓满,正劈波斩浪 在向“圣地”驶去。这一切显得多么生气蓬勃,英国的旗帜在风中飘扬,魁 梧壮实的水手们在雄赳赳的歌声相伴下,使劲拽着大麻编成的结实的绳子, 脖子坚挺的军官们头戴双角帽,在后甲板上踱步,林立的大炮被地中海的浪 花溅得湿漉漉的,水珠又干结成星星点点的盐晶。换言之,这恰恰是那种我 认识到要憎嫌的、富有阳刚气概的武装突袭。在金字塔之战中,我侥幸躲过 了一个马穆鲁克武士的闪电式攻击,又在尼罗河之战的“东方号”爆炸中九 死一生,还有一个名叫艾哈迈德·宾·萨德尔的阿拉伯拜蛇者不知多少次地 对我背信弃义,我都能逃过一劫,最终还将他送归他该去的地狱了。对于那 种生龙活虎般的冒险生涯,我已感到有点力不从心,真想赶快回到纽约的老 家,找一份像样的工作,譬如簿记员或卖干货的职员之类,或者做一个律师 ,去处理悲悲切切的遗嘱,它们被攥在一身黑衣的寡妇和羽翼未丰、不配领 受的遗孤手中。是的,一张书桌和蒙着灰尘的簿籍账册——这就是我所希求 的生活!可锡德尼爵士根本不想听我这一套。更严重的是,我终于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在意的是阿丝蒂莎。在还没有搞清楚她随着那混蛋西拉诺 坠落之后是否活了下来,并以某种方式获得救助之前,我怎么能一走了之, 径直回家呢? 当我没有操守准则的时候,生活往往更加单纯。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