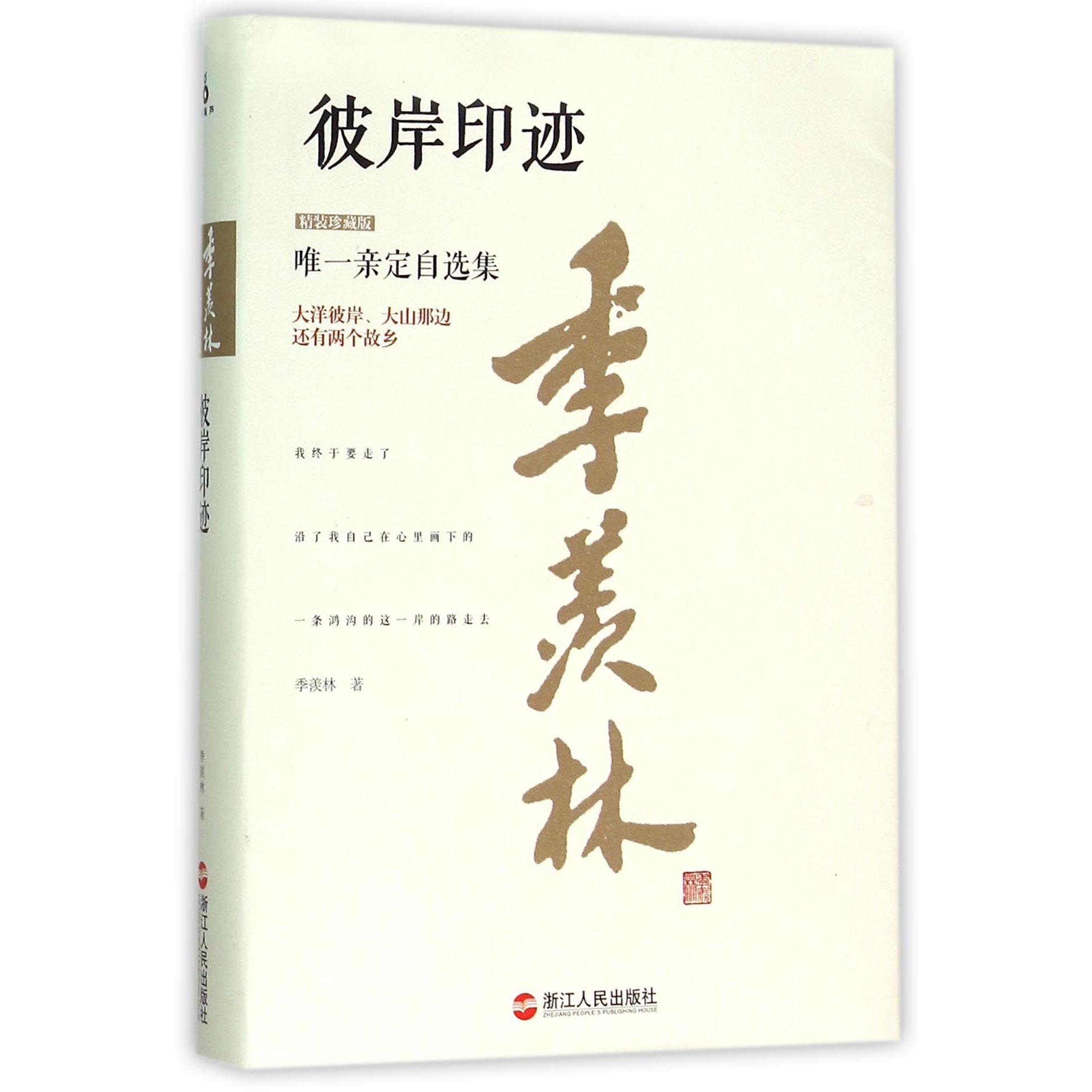
出版社: 浙江人民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4.80
折扣购买: 彼岸印迹(精装珍藏版)(精)/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
ISBN: 9787213069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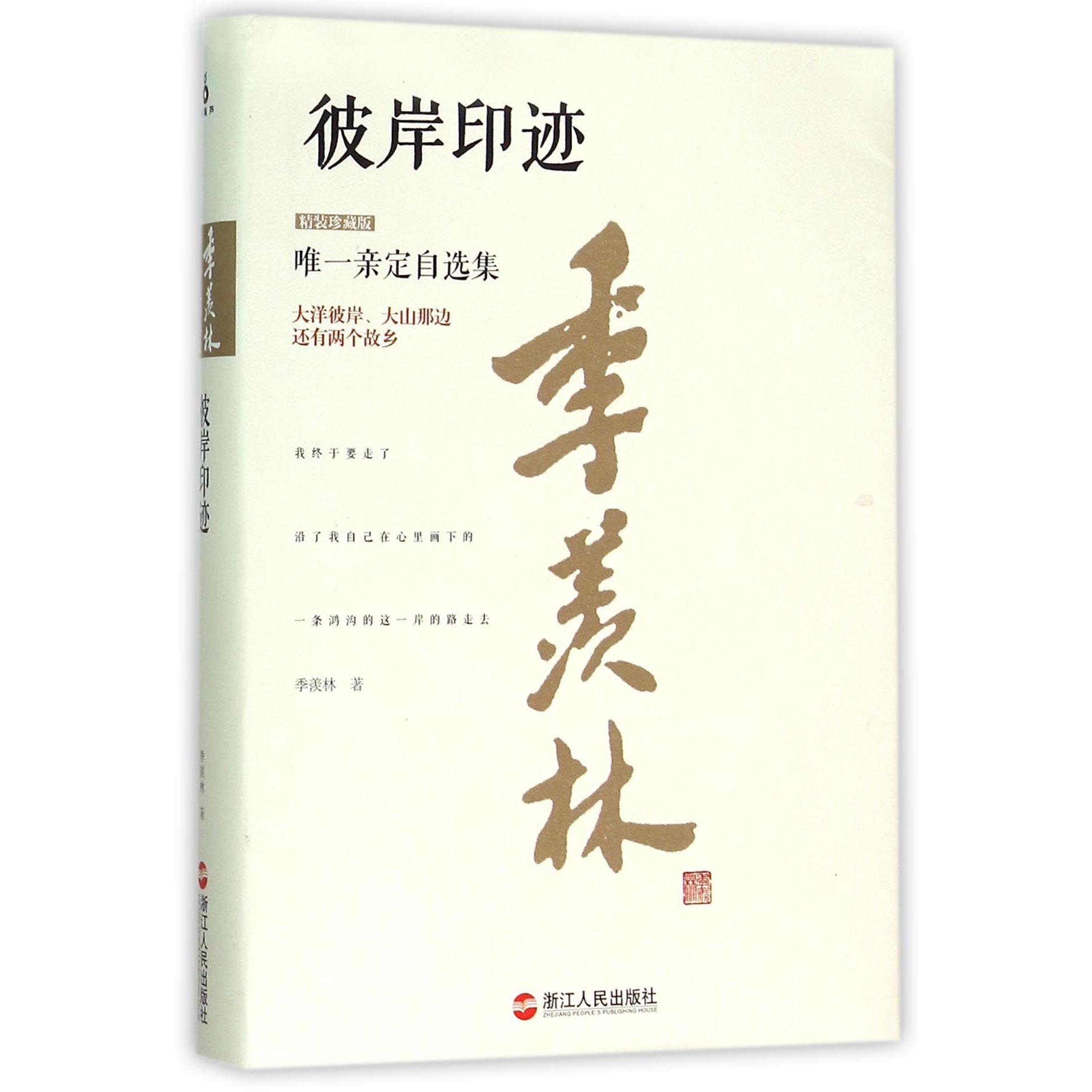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道路终于找到了 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指的是 梵文的学习。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将近六十年,今 后还将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时候。 这条道路同哥廷根大学是分不开的。因此我在这 里要讲讲大学。 我在上面已经对大学介绍了几句,因为,要想介 绍哥廷根,就必须介绍大学。我们甚至可以说,哥廷 根之所以成为哥廷根,就是因为有这一所大学。这所 大学创建于中世纪,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是欧洲 较为古老的大学之一。它共有五个学院:哲学院、理 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医学院。一直没有一座统一 的建筑,没有一座统一的大楼。各个学院分布在全城 各个角落,研究所*是分散得很,许多大街小巷,都 有大学的研究所。学生宿舍*没有大规模的,小部分 学生住在各自的学生会中,*大部分分住在老百姓家 中。行政中心叫Aula,楼下是教学和行政部门,楼上 是哥廷根科学院。文法学科上课的地方有两个:一个 叫大讲堂(Auditorium),一个叫研究班大楼 (Seminar geb?ude)。白天,大街上走的人中有一 大部分是到各地上课的男女大学生。熙熙攘攘,煞是 热闹。 在历**,大学出过许多名人。德国*伟大的数 学家高斯(Gauss),就是这个大学的教授。在高斯 以后,这里还出过许多大数学家。从19世纪末起,一 直到我去的时候,这里**是世界数学中心。当时当 代*伟大的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id Hilbert )虽已退休,但还健在。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友好。我 曾在一家书店里遇到过他,他走上前来,跟我打招呼 。除了数学以外,理科学科中的物理、化学、天文、 气象、地质等,教授阵容都极强大。有几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在这里任教。蜚声**的化学家A.温道斯( Windaus)就是其中之一。 文科教授的阵容,同样也是强大的。在德国文学 史和学术**占有重要地位的格林兄弟,都在哥廷根 大学待过。他们的童话流行全世界,在中国也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他们的大字典,一百多年以后才由许多 德国专家编纂完成,成为德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件大事 。 哥廷根大学文理科的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在这样一座面积虽不大但对我这样一个异域青年 来说仍然像迷宫一样的大学城里,要想找到有关的机 构,找到上课的地方,实际上是并不容易的。如果没 有人协助、引路,那就会迷失方向。我三生有幸,找 到了这样一个引路人,这就是章用。章用的父亲是鼎 鼎大名的“老虎总长”章士钊。外祖父是在朝鲜统兵 抗*的吴长庆。母亲是吴弱男,曾做过孙中山的秘书 ,名字见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总之,他 出身于世家大族,书香名门。但却同我在柏林见到的 那些“衙内”**不同,一点纨绔习气也没有。他毋 宁说是有点孤高自赏,一身书生气。他家学渊源,对 中国古典文献有湛深造诣,能写古文,作旧诗,却偏 又喜爱数学,于是来到了哥廷根这个世界数学中心, 读博士学位。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六年 ,老母吴弱男陪儿子住在这里。哥廷根中国留学生本 来只有三四人,章用脾气孤傲,不同他们来往。我因 从小喜好杂学,读过不少的中国古典诗词,对文学、 艺术、**等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乐森先生介绍我认 识了章用,经过几次短暂的谈话,简直可以说是一见 如故,情投意合。他也许认为我同那些言语乏味,面 目可憎的中国留学生迥乎不同,所以立即垂青,心心 相印。他赠过一首诗: 空谷足音一识君, 相期诗伯苦相熏。 体裁新旧同尝试, 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 气嘘大笔发清芬。 千金敝帚孰轻重, 后世凭猜定小文。 可见他的心情。我也认为,像章用这样的人,在 柏林中国饭馆里面是**找不到的,所以也很乐于同 他亲近。章伯母有一次对我说:“你来了以后,章用 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他平常是**不去拜访人的,现 在一到你家,就老是不回来。”我初到哥廷根,陪我 奔波全城,到大学教务处,到研究所,到市**,到 医生家里,等等,注册选课,办理手续的,就是章用 。他穿着那一身黑色的旧大衣,动摇着瘦削不高的身 躯,陪我到处走。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如在眼前。 他带我走熟了哥廷根的路,但我自己要走的道路 还没能找到。 我在上面提到,初到哥廷根时,就有意学习古代 文字。但这只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想法,究竟要学习哪 一种古文字,自己并不清楚。在柏林时,汪殿华曾劝 我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认为这是当时祖国所需要的 。到了哥廷根以后,同章用谈到这个问题,他劝我只 读希腊文,如果兼读拉丁文,两年时间来不及。在德 国中学里,要读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腊文。文科中学 毕业的学生,个个精通这两种欧洲古典语言,我们中 国学生**无法同他们在这方面竞争。我经过初步考 虑,听从了他的意见。**学期选课,就以希腊文为 主。德国大学是**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 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不懂什么叫入学考试。 入学以后,愿意入哪个系,就入哪个;愿意改系,随 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 科的可以选医学、神学的课;也可以只选一门课,或 者选十门、八门。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就 走;迟到早退,**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 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 (Anmeldung),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 (Studienbuch)请教授签;有的在结束时还需要教 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Abmeldung) 。此时,学生与教授可以说是没有多少关系。有的学 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或者甚至一学期换一个大 学。经过几经转学,二三年以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 大学,满意的系科,这时才安定住下,同教授接触, 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 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 经过几年努力写作,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 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在德国,是教授说 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预教授的决定 。如果一个学生不想作论文,*没有人强迫他。只要 自己有钱,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 恒的学生”(Ewiger Student),是一种全世界所无 的稀有动物。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由的气氛中,在**学 期选了希腊文。另外又杂七杂八地选了许多课,每天 上课六小时。我的用意是练习听德文,并不想学习什 么东西。 我选课虽然以希腊文为主,但是学习情绪时高时 低,始终并不坚定,**堂课印象就不好。1935年12 月5**记中写道: 上了课,Rabbow的声音太低,我简直听不懂。他 也不问我,如坐针毡,难过极了。下了课走回家来的 时候,痛苦啃着我的心——我在哥廷根做的**的美 丽的梦,就是学希腊文。然而,照**的样子看来, 学希腊文又成了一种*大的痛苦。我岂不将要一无所 成了吗? *记中这样动摇的记载还有多处,可见信心之不 坚。其间,我还自学了一段时间的拉丁文。*有趣的 是,有一次自己居然想学古埃及文,心情之混乱可见 一斑。 这都说明,我还没有找到要走的路。 至于梵文,我在**读书时,就曾动过学习的念 头。但当时**没有人教梵文,所以愿望没有能实现 。来到哥廷根,认识了一位学冶金学的中国留学生湖 南人龙丕炎(范禹),他主*科技,不知道为什么却 学习过两个学期的梵文。我来到时,他已经不学了, 就把自己用的施滕茨勒(Stenzler)著的一本梵文语 法送给了我。我同章用也谈过学梵文的问题,他鼓励 我学。于是,在我选择道路徘徊踟蹰的混乱中,又增 加了一层混乱。幸而这混乱只是暂时的,不久就从混 乱的阴霾中流露出来了阳光。12月16**记中写道: 我又想到我终于非读Sanskrit(梵文)不行。中 国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 系**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在德国能把想学的 几种文字学好,也就不虚此行了,尤其是Sanskrit, 回国后再想学,不但没有那样的机会,也没有那样的 人。 第二天的*记中又写道: 我又想到Sanskrit,我左想右想,觉得非学不行 。 1936年1月2*的*记中写道: 仍然决意读Sanskrit。自己兴趣之易变,使自己 都有点吃惊了。决意读希腊文的时候,自己发誓而且 希望,这次不要再变了,而且自己也坚信不会再变了 ,但终于又变了。我现在仍然发誓而且希望不要再变 了,再变下去,会一无所成的。不知道Schicksal( 命运)可能允许我这次坚定我的信念吗? 我这次的发誓和希望没有落空,命运允许我坚定 了我的信念。 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 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 下去。 哥廷根实际上是学习梵文*理想的地方。除了上 面说到的城市幽静、风光旖旎之外,哥廷根大学有悠 久的研究梵文和比较语言学的传统。19世纪上半叶研 究《五卷书》的一个转译本《卡里来和迪木乃》的大 家、比较文学史学的创建者本发伊(T.Benfey)就曾 在这里任教。19世纪末弗朗茨·基尔霍恩(Franz Kielhorn)在此地任梵文教授。接替他的是海尔曼· 奥尔登堡(Hermann Oldenberg)教授。奥尔登堡教 授的继任人是读通吐火罗文残卷的大师西克教授。 1935年,西克退休,瓦尔德施米特接掌梵文讲座,这 正是我到哥廷根的时候。被印度学者誉为活着的*伟 大的梵文家雅可布·瓦克尔纳格尔(Jakob Wackernagel)曾在比较语言学系任教。真可谓梵学 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极久,规 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据 说都是基尔霍恩从印度搜罗到的。这样的条件,在德 国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我决心既下,1936年春季开始的那一学期,我选 了梵文。4月2*,我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 **课。这是一座**古老的建筑,当年大数学家高 斯和大物理学家韦伯(Weber)试验他们发明的电报 ,就在这座房子里,它因此名扬**。楼下是埃及学 研究室,巴比伦、亚述、阿拉伯文研究室。楼上是斯 拉夫语研究室,波斯、土耳其语研究室和梵文研究室 。梵文课就在研究室里上。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第 一次上课,也是我**次同他会面。他看起来**年 轻。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 (Heinrich Lüders)的学生,是研究**出土的梵 文佛典残卷的专家,虽然年轻,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 颇有名声。可是选梵文课的却只有我一个学生,而且 还是外国人。虽然只有一个学生,他仍然认真严肃地 讲课,一直讲到四点才下课。这就是我梵文学习的开 始。研究所有一个小图书馆,册数不到一万,然而对 一个初学者来说,却是应有尽有。*珍贵的是奥尔登 堡的那一套上百册的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 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 各异。如果自己去搜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这样齐 全的,因为有的杂志**冷僻,到大图书馆都不一定 能查到。在临街的一面墙上,在镜框里贴着德国梵文 学家的照片,有三四十人之多,从中可见德国梵学之 盛。这是德国学术界十分值得骄傲的地方。 我从此就天天到这个研究所来。 我从此就找到了我真正想走的道路。 P5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