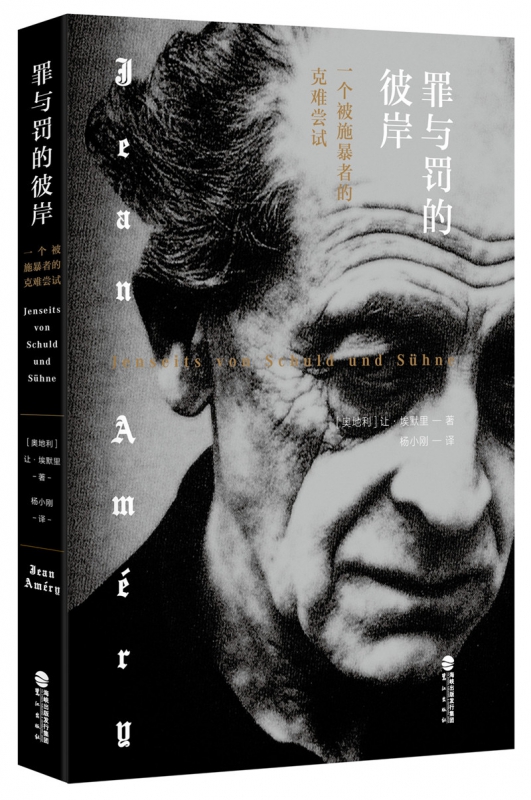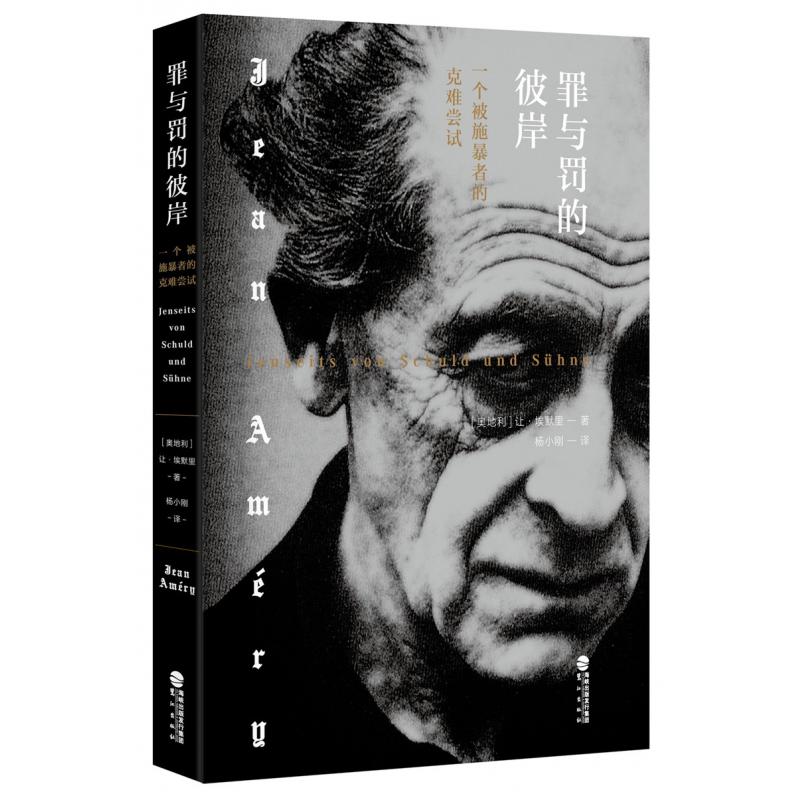
出版社: 鹭江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4.36
折扣购买: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精)
ISBN: 9787545914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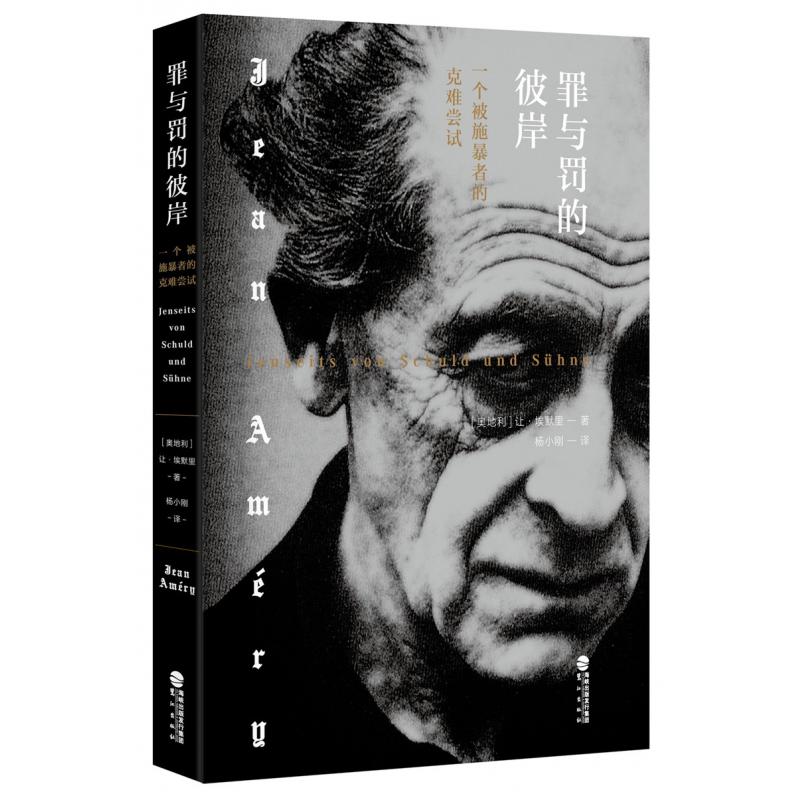
让?埃默里(Jean Améry,1912—1978),原名汉斯?梅耶(Hanns Mayer),出生、成长于奥地利维也纳,并在这座城市学习了文学和哲学。1943年,埃默里因散发反纳粹读物而遭逮捕,被押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军队进驻波兰后,他先后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森集中营,关押直至1945年才被释放。战后,埃默里在一家瑞士—德国报社做记者谋生。1966年,他出版了书写自己奥斯维辛经历的文集《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并因此广为人知。后又出版数本著作,包括他最著名的哲学论著《独自迈向生命的尽头》《变老的哲学:反抗与放弃》等。1978年,埃默里自杀身亡。
精神的界限 “您得小心些。”一位好心的朋友听说我准备谈谈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后,这样建议我。他恳切地跟我说,尽量少谈奥斯维辛,多谈思想问题。他还认为,可能的话,应该放弃把奥斯维辛放到标题里:公众对这个地理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概念过于敏感。毕竟已经有足够多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各种各样的奥斯维辛档案,讲述暴行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新东西。我不确定我的朋友是否正确,所以我不会听从他的建议。我不觉得关于奥斯维辛人们已经说了很多,比如像说电子音乐和波恩的联邦议会那么多。我一直在考虑,把一些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作为必读书目引入高等中学的高年级是否没有必要,在处理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是否不需要总是有很多顾虑。真的,我在这儿不打算单纯地谈论奥斯维辛,不想提供什么文献报告,而是计划谈论奥斯维辛与思想的对峙。但我不会完全围绕人们所说的暴行,围绕那些事件过程。面对它们,布莱希特说过,心肠是硬的,神经是脆弱的。我的主题是:精神的界限。这些界限刚好沿着让人厌恶的暴行延伸,这不是我的过错。 我想要谈论奥斯维辛里的知识分子,或者按以前的叫法,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den geistigenMenschen),首先就必须对我的对象,也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加以定义。按照我所使用的含义,什么样的人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是一个从事精神活动的人?肯定不是每一个进行所谓脑力劳动的从业者。正规的高等教育也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想到律师、工程师、医生,很可能还有语文学家,他们虽然聪明,甚至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内非常杰出,但鲜有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我理解的,是一个在广义上的精神脉络里生活的人,与其相联系的是一个本质上人本的或者说人文学科的世界。他有良好的审美意识,秉性和能力驱使他进行抽象思考。思想史上的一系列景象在每一个合适的时机都会在他脑海中浮现。如果有人问他,哪个名人的名字以“ Lilien”开头,他想到的不会是滑翔机设计者奥托?冯?利林塔尔(Otto von Lilienthal),而是诗人德特勒夫?冯?利里恩克龙(Detlev von Liliencron)。给他一个关键词“ Gesellschaft”,他理解的不是世故、善社交,而是社会学。引起短路的物理过程他没有兴趣,对宫廷田园诗人奈德哈特?冯?罗恩塔尔 他却了如指掌。 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这样的人,伟大诗篇的诗行烂熟于胸,对文艺复兴和超现实主义的名作了如指掌,对哲学史和音乐史如数家珍 —我们把一个这样的知识分子置于如此境地,在那里他所面对的,要么是证明自己精神的现实性与效力,要么将其看作一无是处,那是一个极限处境,那是在奥斯维辛。我自然也把自己置身于此。我曾经以双重身份,作为犹太人和比利时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伯根-贝尔森和其他一些集中营,除此之外还在奥斯维辛,准确地说,在附属集中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Auschwitz-Monowitz)待过一年。所以在本书中,只要我愿意的话,“我”这个小词必然常常出现,也就是在那些我不能将个人经历直接代入其他人身上的地方。 在我们的语境中,首先要考虑的是知识分子与所有人,包括那些脑力工作的从业者特有的外部处境。一个糟糕的处境,以极为戏剧化的方式在强制劳动下面临的生死抉择的问题中凸显出来。奥斯维辛-莫诺维茨中的工匠,只要没有被以一个这里用不着细说的随便的理由赶进毒气室,就会得到相应的职业分配。比如有个锁匠被赋予了特权,因为当时待建的染料工业集团工厂 需要他,他就有机会在有遮挡的、无须暴露在恶劣天气中的工棚里干活。电工、装修工、造家具的和盖房的有同样待遇。谁要是裁缝或者鞋匠,也许就有机会到专门侍奉党卫军的房间里去干活。泥瓦匠、厨师、无线电工人和汽车技师也有最微小的机会,获得一个可以忍受的工作岗位,从而幸存下去。 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遭遇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境。等待他的是和商贩一样的命运,他们都属于集中营里的流氓无产阶级。他会被分进一个小组,挖坑、埋线缆、搬运水泥袋和钢梁。在集中营里他成了没有职业资质的工人,不得不在野外干活,多数时候这相当于已经对他下了判决。肯定也存在差别。在前面提到的那些集中营里,化学技师仍然能从事他的本职工作,像我的狱友,来自都灵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写了一本关于奥斯维辛的书《这是不是个人》(Ist das ein Mensch?)。医生也有可能在一个叫作医护所的地方栖身,但并不是所有医生都如此。例如来自维也纳的医生,如今已是著名心理医师的维克多 ?弗兰克(Viktor Frank)曾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长年挖掘土方。一般而言,脑力劳动者在集中营里的工作处境极为恶劣。许多人因此试图隐瞒他们的职业。谁如果掌握一点小手艺,会做些工艺,就会大胆地装成一个手工匠人。当然,一旦他说的谎暴露出来,就得担上丧命的风险。多数人把自己说得身无所长,想借此撞撞运气。人文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在被问到自己的职业时,会胆怯地说“老师”,生怕招惹党卫军士兵和牢头的羞辱。律师装成普通的书记员,记者可能谎称自己是排字工,在必须提供自己的技能证明时这样做危险较小。大学老师、律师、图书馆员、艺术史学者、国民经济学家、数学家,他们拖拽着铁轨、钢管和木材,大多数时候他们笨手笨脚,体力透支。极少数情况下,苦力劳动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他们被带离工地,送到邻近的主集中营,那里矗立着毒气室和火葬场。 他们在工作场所处境艰难,在集中营里也好不到哪里去。集中营生活首先要求身体矫健和一种必需的、近乎残忍的血性。鲜有知识分子具备这两样长处,而他们经常看重的道德勇气,在这里一文不值。例如说,有一次,要阻止一个华沙的职业扒手偷我们的鞋带,这时候能派上用场的是一记下勾拳,而不是精神上的勇气,一个政治记者会出于这样的勇气发表一篇不受欢迎的文章而危及生命。毋庸多说,律师或者人文中学教师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出一记下勾拳,绝大多数时候他们挨得拳头远多过他们给别人的,他们更擅长挨揍而非揍人。集中营的纪律问题上也一样糟糕。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一般没什么铺床的天赋。我记得我那些满腹学识、教养良好的同伴,每天早上满头大汗地和被褥搏斗却弄得一团糟,以至于工作时像得了强迫症般担惊受怕,生怕回去后挨揍挨饿。他们既不擅长铺床,也不会机灵地行“脱帽礼”。恰巧碰上狱中年长的人或者党卫军士兵时,他们从来都不会那套几乎卑躬屈膝却又自知自觉的说话方式,学会那样说话有时候可以避开近在眼前的危险。所以在集中营里,囚犯里的头头和室友不尊重他们,在工地上的牢头和工人也瞧不起他们。 更糟的是,他们找不到一个朋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从生理上就学不会用集中营里的粗话直截了当地交谈,而这些粗话是唯一被接受的相互理解的方式。人们经常谈到现代的思想争论中存在的同代人间的交流困难,谈到那些突兀的、不如不说的蠢话。在集中营里交流障碍存在于知识分子和他们大多数的同伴之间,无时无刻不以真实、折磨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习惯了细致入微的表达方式的囚犯来说,要努力克服自我才可能说出“滚开!”或者只用“嘿,家伙”跟同伴打招呼。我清楚记得那种身体上的反感,每当一个别的方面都正常、随和的同伴不跟我说别的,只说“我亲爱的男子汉”时,这种感觉就会把我笼罩。知识分子忍受着“伙夫”“整弄”(指非法占有财物)等表达,即便像“运走了” 这样的词也要很勉强才会从他们嘴里蹦出来。 精彩书摘二: 酷刑 人们也许会把到比利时旅游的人临时领到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之间的布伦东克堡垒。这处设施是“一战”时的一个要塞,它当时遭遇了什么命运我不知道。“二战”时,1940年 5月,在比利时军队短短十八天的起义期间,布伦东克是利奥波德国王( King Leopold)最后的大本营所在。然后,在德国占领期间,它变成一座小型的集中营,一个“战俘营”,第三帝国的黑话就这么叫它。今天它是比利时国家博物馆。 布伦东克堡垒初看起来非常古老,如历史遗迹。它矗立在佛兰德斯永远阴雨绵绵的天空下,圆顶上长满杂草,围在灰暗的城墙内,仿佛 1870年普法战争时一幅忧郁的雕版画。人们会想到格拉韦洛特(Gravelotte)和色当(Sedan),会觉得手里拿着陆军帽、被击败了的拿破仑三世拥有的某处宏伟而又沉抑的城堡大门必定也是如此。必须靠近些,那些旧日时光的浮光掠影才会迅速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幅我们很常见的景象:哨塔沿着要塞周围的壕沟排列,外围是一圈铁刺篱笆。 1870年的雕版画突然被那个世界的残暴图像所覆盖,大卫?卢塞 把它称作“被挤压的世界” 。国家博物馆的学术委员们让一切一如其旧,保留了它 1940年到 1944年的原样。围墙上褪色的标语写着:“退后,违令击毙!”堡垒前立着一尊反抗组织纪念像,一个被强迫跪在地上的男子,昂着头,相貌带有明显的斯拉夫人特征。这尊雕像完全没必要,参观者不需要它来提醒自己身在何处,不需要它来提醒自己将被带入什么样的历史记忆。 穿过大门,人们立刻会进入一个房间,这里当时被神秘地称为“事务室”。墙上挂着一幅海因里希 ?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s)的画像,一张长桌上铺着一面纳粹党旗,几把光秃秃的木椅。事务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务,他们的是死亡。然后是潮湿的地下走廊,微弱和泛红的灯泡发着无力的光,跟以前一样挂在那里。囚室被几英寸厚的木门锁着。推开一扇扇沉重的铁栅门,最后会走到一个一扇窗子也没有的圆顶地窖里,里面放着一些弄不清名堂的铁制工具。在那里,任何喊叫声都传不出去。在那里,我受到了刑讯。 说起刑讯时要小心不要太夸张。我在布伦东克那间可怕的地窖里遭受的还不是最残忍的刑罚。没有人把烧红的铁钉钉入我的指甲盖下,也没有人用点着的纸烟戳我裸露的胸膛。我在那儿遭遇的事,稍后必然会讲。相对来说我算是幸运的,身上也没留下任何明显的伤痕。在过去二十二年后,基于一种经验,这种经验不可能测量可能事物的整个尺度,我却敢说:刑讯是一个人所能经历的最可怕的事情。 许多人记忆中都保存着同样的事情,可怕的事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西方许多国家,作为机构设置和审讯手段的刑罚在 18世纪末就已被取消。然而直到今天,两百年之后,仍有无数男性和女性有他们不得不述说的残酷刑罚,究竟多少,没人知道。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看到一张报纸,上面的照片是南越军队的士兵在折磨被捕的游击队叛军。英国小说作家格雷厄姆?格林 给伦敦的《每日电讯》(Daily Telegraph)写过一封信,里面写道: 英国和美国出版社出版的图册上最新奇的是,人们明显带着对刑讯打手的认可接受了这些图片,没有任何评论它们就出版了。这些内容仿佛动物学著作上关于昆虫生活的图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官方将刑讯视为审讯战时囚犯的合法方式?这些照片,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谓诚实的标志,因为它们说明,官方没有闭上自己的眼睛。我只是要问自己,这样一种无意识的坦诚难道胜过过去的虚伪吗?…… 我们中的每个人也会提出和格林一样的问题。承认刑讯,勇敢地——这难道不是一种勇敢吗?——将这?样的照片摆到公众面前,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可以解释,那就是良心的不安已不足为惧。人们会以为,这种良心对酷刑已习以为常。近几十年来,酷刑绝不只是在越南被使用。我不想知道,南非、安哥拉、刚果的囚犯都碰上过什么。但我知道,读者很可能也了解, 1956年到 1963年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地牢里都发生了什么。亨利?阿莱格 的《问题》(La question)以惊人的准确和清醒记叙了此事,这是一本已被禁止传播的书。目睹一切的证人报告,仅仅很简单地记录下这些恐怖,没有多余的延伸。 1960年左右还出版了大量其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书籍和论战小册子:知名律师阿莱 ?梅洛( Alec Mellor)博学的犯罪学论文,出版家皮埃尔 -亨利?西蒙(Pierre-Henri Simon)的抗议,一位叫维埃拉图(Vialatoux)的神学家的道德哲学研究。半数法国人反对在阿尔及利亚的酷刑,这是整个民族的光荣——人们并不能经常如此明确地宣称。左翼知识分子抗议,天主教工会干部和基督徒冒着安全和生命危险发出警告,干预刑讯;教会首脑提高了声调,尽管在我们看来这声音太过软弱。 不过这就是伟大、热爱自由,即便在黑暗时期也没有彻底丧失自由的法兰西。从其他地方传到世界上的呼喊声是如此微小,就像我曾身处的对我而言也显得陌生,可怕的喊叫声传不出去的布伦东克地窖。在匈牙利有一位总理,据说在某位前任总理治下曾被行刑手拔去了所有指甲。而所有其他人在哪里?都是谁?关于他们无人知晓,甚至可能永远没人知道。民族、政府、警察部门、姓名,人们知道,但没人知道他们。有人在某地受酷刑而惨叫。也许就在此时此刻。 我究竟为何仅仅把酷刑和第三帝国联系起来?当然,因为我刚好在这只猛禽展开它的羽翼时遭受酷刑。但不仅如此,与所有的个人经验无关,我确信,酷刑对第三帝国来说并非偶然,而是其本质。我听到激烈的质疑,我知道,做出这一论断是出于危险的理由。稍后我会尝试给出自己的理由,不过首先要讲一讲,我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在布伦东克堡垒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在 1943年 7月被盖世太保逮捕,罪名是散发传单。我所属的小组是比利时抵抗运动下面的一个小的德语组织,负责在德国占领军的拥护者中进行反纳粹宣传。我们准备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作为宣传资料,我们以为,靠这些就能够让德国士兵相信希特勒和他发动的战争的残酷与疯狂。今天我知道,或者至少以为自己知道,我们那些急迫的话语说给了聋子听。我有理由假定,穿着土黄色军装的士兵在他们的营房里发现了我们的小册子,翻了几下就直接交给了他们的上级,这些人则以同样的高效告知了安全部门。秘密警察们迅速找到我们的踪迹,把我们挖了出来。我在被捕时带着的一张传单上印着这么几句坚定却又笨拙的口号:“党卫军暴徒和盖世太保刽子手必亡!” 谁带着这样的传单被拿着手枪、穿着皮大衣的人抓住的话,就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种幻想在我脑子里停留不止片刻,因为我觉得,上帝才知道这一切,他了解这个体系,了解为它服务的人和它的手段的古老、被折磨透了的知情者。今天已然清楚,这样的感觉毫无道理。我相信,曾经的《世界新舞台》(NeuenWeltbühne)和《新日记》(NeuenTagebuchs)的读者,他们熟稔 1933年以来流亡者的集中营文献,早就预见我将遭遇的一切。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初,我就听说过柏林帕普将军街冲锋队营地的地下室。后来不久,我读到了据我所知的第一份关于集中营的文献,格哈特 ?西格 的小书《奥拉宁堡》(Oranienbury)。自那以后,我接触到许多前盖世太保囚犯的报告,以至于我那时以为,在这个领域不会再有什么新的我不了解的东西。将会发生的事情会迅速划分到相关文献中去。囚禁、审讯、殴打和酷刑—最后最可能的是死亡:一切都如此写下,也将继续如此发生。逮捕之后,有一次,一个盖世太保命令我离开窗子边,因为他清楚那种用绑住的双手砸破玻璃、跳上窗台的计谋。当时我虽然备感荣幸,他竟相信我有如此强的决断力和身手,我还是友好地拒绝听从他的要求:我既不具备体能上的条件,也完全无意以这样冒险的方式摆脱我的命运。我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我的承诺靠得住。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一: 奥地利著名哲学家、奥斯维辛幸存者、“大屠杀文化中的圣人”让?埃默里书写的一份超越问责与救赎的人性诊断。灾难过后,死亡营幸存者如何真正生还?意大利国宝级作家普里莫?莱维倾力推介。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二: 人的尊严是什么?我们需要多少个故乡?知识分子的受难比普通人更值得同情吗?让?埃默里在这本短文集中以坦白和沉思的方式,对奥斯维辛受害者的生存处境做了一次探究。他写集中营生活,写自己所受的酷刑,写怨恨背后的哲思,也反思做犹太人的必然性与不可能。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三: 埃默里说:“我反抗,反抗我的过去,反抗历史,反抗将不可理喻的事情以历史的方式冷藏,以让人愤怒的方式歪曲。” 在埃默里所描述的令人吃惊的历史细节与难以言表的苦痛情感中,读者能够以同样的节奏跟随他穿越这片他一步步点亮的黑暗。 《罪与罚的彼岸:一个被施暴者的克难尝试》特色四: 在这本书的每一个转折和每一个停息处,都刻着真相的印记。 ——欧文?豪(美国著名文学家、社会批评家) 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道德勇气的回忆录。带着诗人的耳和小说家的眼,埃默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家的奇迹,一个在纳粹统治及其大屠杀拼出的“黑暗谜语”之下的生存奇迹。 ——美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