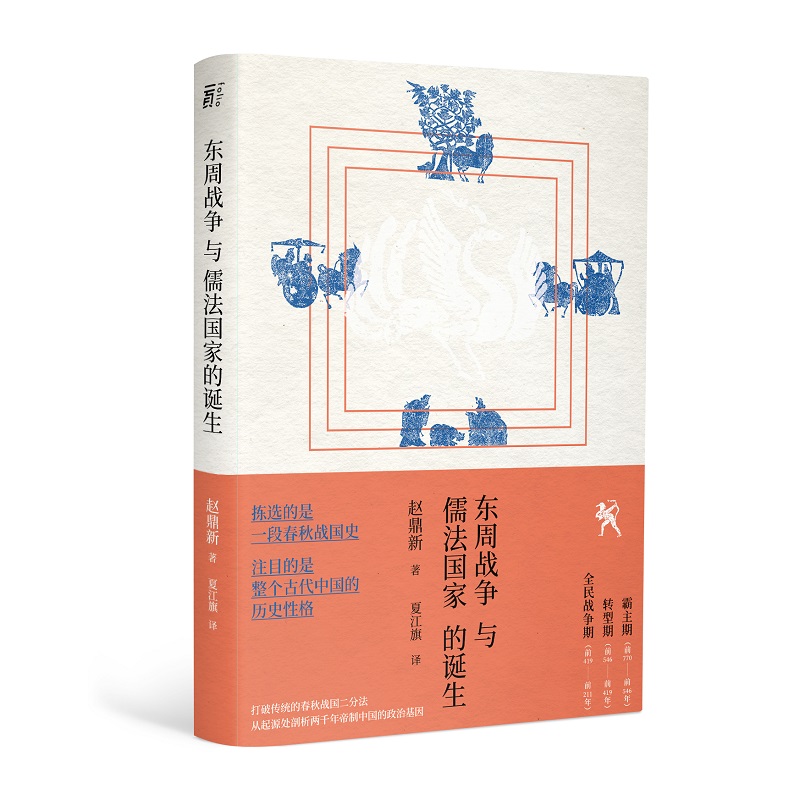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联合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5.96
折扣购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精)
ISBN: 9787559642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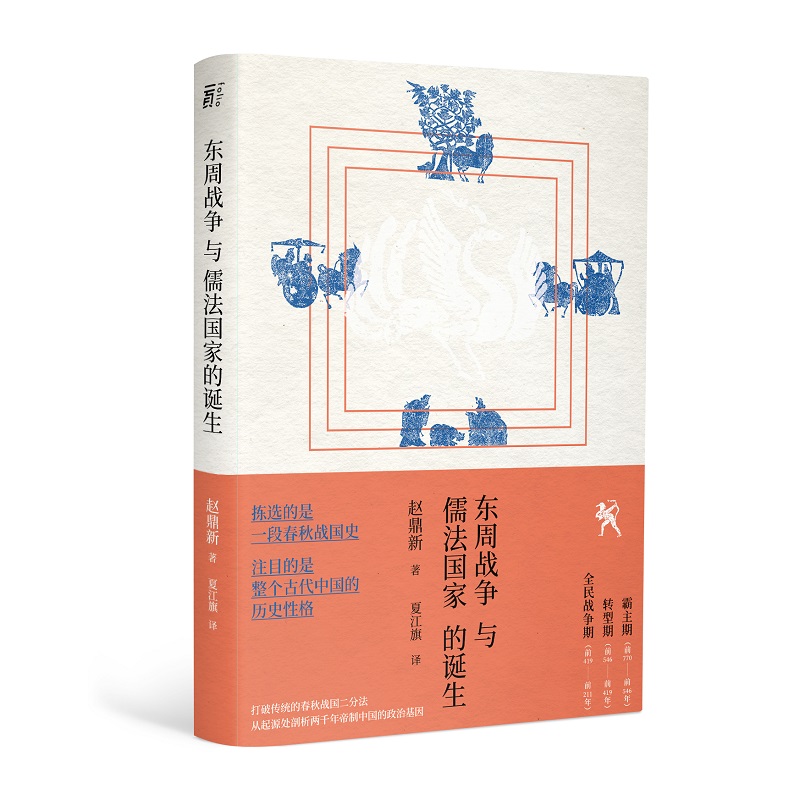
赵鼎新 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 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其观点与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均具有广泛的影响。 其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社会学视角》《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 代表著作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 : 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东周历史的分期 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期间,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要理解这些变化,首先必须提出一个能够真实反映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特征的历史分期方案,然后才有可能揭示出隐藏在这些社会转型背后的机制。虽然对于具体的起迄时间一直聚讼纷纭,但史学界一致接受将东周划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的观点。春秋时期的说法得名于《春秋》以及另一部对《春秋》一书有详细注解的、本书即将频繁引用的史书《左传》。《春秋》据称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所作,后经孔子编订,书中记载的鲁国历史上起公元前722年,下至公元前481年。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家便将公元前481年作为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分界点。 把公元前481年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点也许仅仅是为了方便,但这一分界方法并非毫无历史根据。因为《春秋》一书的历史记录止于公元前481年本身就是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历史性事件。自鲁文公(前626—前609年在位)即位以后,鲁国的政治逐渐为三个最有权势的贵族世家(史称“三桓”)所左右。到鲁哀公时(前494—前468年在位),鲁国朝政几乎完全为“三桓”所把持。鲁哀公被逼逃到越国,后在复位无望中郁郁而终。而鲁哀公以后的鲁国国君再也没有获得过正位。以上这一现象并不是鲁国一家独有。同样在公元前5世纪,其他一些诸侯国诸如晋、齐、郑、宋等均遇到了相同的麻烦。在一些国家中,某些封建世家已然坐大,互相争斗,僭夺国柄,并随后建立起科层制政府。《春秋》记史的中辍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标志。 尽管将公元前481年确定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通常所说的春秋与战国之间存在的历史差异却不是那一年前后遽然形成的。首先,虽然各诸侯国中豪门世族剧烈的篡权活动大多都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但这些篡权活动所标志的封建体制的瓦解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次,战国时期的历史所具有的一些主要特征也不是在公元前481年之后才突然出现的。比如,战国时常见的科层制政府、大规模的治水工程以及活跃的商业活动等都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渊源。因此,为了更好地把握东周社会的转型过程及其内在机制,笔者在这里提出关于东周史的三阶段分期说,即将东周历史依次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霸主期(前770—前546年)、转型期(前546—前419年)和全民战争期(前419—前221年)。 第一阶段霸主期(前770—前546年)以西周王朝的崩溃和诸侯国力量的上升为开局。其中某些诸侯国马上就变得野心勃勃,随之而来的是诸侯国之间战争数量的大大增加。在这一阶段,尚未有哪个诸侯国强大到足以将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消灭掉。因此,虽然势力较强的诸侯国在这一时期大量侵夺邻国的领土,甚至灭了不少实力薄弱的小国,但它们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于建立一个一统天下的帝国,而在于成为一个能够支配其他国家的霸主。就像周王对待它的属国一样,这些霸主不断在自己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对其他小国的内政(如封建秩序下的君位继承问题)和外交进行干预。故而,霸主体系在某种意义上维续了西周的封建制度。在该阶段,我们可以发现郡县行政体制的兴起、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效率驱动型文化的出现。我们还会发现在军事组织、政府结构以及土地所有制等方面发生的许多由国家主导的改革。所有这些改革都是为了达到如下两个目的:进行更为有效率的战争和维持本诸侯国国君的权力。 不过,霸主体系之下的诸侯国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内在困难。主要是,虽然在该阶段的早期,一些主要的诸侯国已经开始采用科层制这一国家管理模式,但显然,当时的主导性政治模式依然是封建制度:在当时的大多数国家中,作为国家官员的贵族世卿拥有自己的领地和私家武装。由于贵族世卿的爵位以及相应的权力可以代代相袭,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贵族世家的势力不断增长,最后增长到完全足以控制所在诸侯国的国家政治,从君位继承直到与外国交往等国家大政皆操纵在他们手中。这个问题对那些小国来说并不十分严重,小国的内政在相当程度上由霸主国家控制,其国内的贵族世家在国内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此外,小国人少地狭,没有多少土地可供国内的贵族世家争夺。相应地,一个国家的领土越大,上面所说的这一现象就越严重。特别是对那些通过军事征服获得广袤疆土的霸主国家来说,这一问题最为严峻。在这些霸主国家中,新近吞并的领土一般都分封给了一些世家贵族或军功新贵作为采邑。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最终只会对贵族有利。诸侯列国中贵族势力的崛起(史称“二级封建化”)及其带来的封建危机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发展有着关键性的重要意义。 这里之所以将公元前546年作为霸主期与转型期的分界点,是因为在这一年,当时两个敌对的霸主国家,即晋国和楚国,同另外十余个小国会盟于商丘,订立了休战协议,史称“弭兵大会”。晋、楚弭兵各有原因。楚国是由于受到了另一个刚刚崛起的强国—吴国的严重威胁,因而不愿两面受敌。晋国则是因为国内的几大世卿豪族陷入激烈的内争,对外已无暇顾及。弭兵大会尽管使晋、楚两国各自获得喘息的机会,但却加速了东周时期整个霸主体系的解体,从而将东周历史带入第二个阶段—转型期(前546—前419年)。 转型期始于封建危机的深化(这种情况在当时中原地区的几个诸侯国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终于科层制国家的形成。公元前546年弭兵大会之后,吴国对楚国的威胁日趋严重。公元前506年楚国甚至差一点被吴国彻底灭掉。 因此,外患便成为楚国在弭兵大会之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于晋国来说,弭兵大会的最大影响是使该国的内患加剧。一旦楚国不再对其构成威胁,迫使晋国几大世卿贵族团结起来共御外侮的压力便随之消失了。此后,晋国国君的权威进一步衰落,六大卿族开始最终的较量,他们首先根除晋君公室的贵族势力,然后便开始了长期的相互倾轧。 最后,在斗争中存活下来的韩、赵、魏三家在公元前453年将晋国瓜分。 由此形成的韩、赵、魏三国(史称“三晋”)都成了春秋战国时代下一阶段历史上的重要角色。 由于在弭兵大会之后,楚、晋两国不再充当霸主,一些二等诸侯国家便开始乘机谋求霸主地位,但它们无不以失败告终。此外,没有了霸主的控制,那些诸侯小国也企图在新的战局中分一杯羹,于是,邻国之间的战争便开始变得频繁起来。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了霸主国家的遏制,那些小国的贵族便得以公然扩充自己的势力以挤压国君的权威。上述种种变化汇成了当时社会演变之浪潮,大势所趋之下,中原地区最为重要的几个诸侯国,如鲁、齐、宋、卫、郑等国国君的权力相继易手给本国的世卿贵族,前面曾经提到的鲁哀公的悲惨遭遇只是整个封建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事例而已。换句话说,在晋国所发生的一切在当时并不是特殊现象。 在转型期,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同时刺激了其他方面的社会变迁。第一,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自西周初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官学教育体系逐渐瓦解。官学中的教师和学生不仅开始从事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私学教育,而且纷纷著书立说,向世人表达他们对时政及社会风气的看法和见解。他们中的一些人,即后世所说的法家和纵横家,将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二,诸如土地的私有化、成文法的制定、以能力而不是地位来选取政府官员的方法以及赋(用于军事)税(用于行政)分离等众多改革在这一时期都开始启动。这些改革不仅为下一历史阶段更具根本性的改革提供了经验与教训,同时也为其铺平了道路。第三,该时期军队的组织方式和兵法战术也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步兵方阵开始出现,水军作为一种兵种在许多国家相继建制,职业化的军事参谋人员开始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战争卷入的人口日益庞大,战争方式愈趋复杂,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第四,一些主要用于军事目的的大型水利工程开始营建或投入使用。最后,在霸主时期即已出现的重商主义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普遍,与此相应,商人和手工业者群体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力。 由于在封建危机中涌现出来的那些新生国家的执政者均出身于原来的贵族世家,因此,他们对封建政治体制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这些新生国家便通过向政府官员发放薪俸和推进政府职能的专门化,将发轫于春秋时期的郡县制度建设成更为完备的科层制度体系。在做出这一系列的调整之后,国家的权力得以集中,从而为推行更为彻底的改革提供了可能。这些改革大大提高了一些国家的战争能力,改变了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战争的性质。春秋战国时代由此进入最后一个阶段—全民战争期(前419—前221年)。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全民战争期的历史源起于在魏国开始的法家改革浪潮。尽管自春秋战国时代起始不久就已发端的各类改革,都为法家改革提供了先例和经验,但法家的改革却与以往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些新的改革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之下进行的,并有着极强的系统性。法家改革的目标并不在于调整个别的社会结构和政策,而是想创建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国家财政税收和军事力量的全权国家,以使国家能够在赢家通吃的战争局面中立足。这场法家改革的浪潮滥觞于“三晋”之一的魏国。我们不知道魏国改革开始的确切时间,尽管到公元前419年时魏国的改革肯定已经有些年头了。笔者之所以将公元前419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第二与第三阶段的分界点,是因为魏国在这一年开始向西扩张,并由此与另一个最终统一了中国的强国—秦国结下宿仇。 在全民战争期,从封建体制的束缚下摆脱出来的这些战争国家,在新近从改革中所获得的日益增长的国力的刺激下,其领土扩张的欲望迅速膨胀。扩张的野心急剧地改变了在春秋战国时代前两个阶段既已盛行的战争的性质。在此之前,诸侯国之间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或者是追求经济利益,或者是攫取政治霸权,现如今,扩充版图和削弱敌国则成了首要的目标。战争也因此而变得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复杂。战国时期的许多战争之所以被称为全民战争,是因为在这些战争中,参战国的大部分男性人口都被动员起来投入战争,并且,一个国家一旦输掉战争,它就很可能再也无法从随之而来的人口灾难中恢复元气。 在这一时期,军队将领与政府官僚之间出现了职能上的分化,兵法战术进一步成熟。同时,大规模的道路交通网络和水利工程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战争的效率和农业灌溉的水平。不过,即使一个工程的用途完全是为了农业灌溉,但其最终目的仍然在于战争,因为拥有更高农业生产力的国家更有可能在战争中获胜。在前两个阶段中已经萌芽的商业活动在该时期变得活跃起来,货币在经济交易中得到广泛使用,一批商业大都会相继出现,甚至一些经济理论也问世了,一些巨商大贾开始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魏国在法家改革后实力大增,并因此支配战国格局几近半个世纪之久。魏国的扩张迫使其他诸侯国家纷纷进行自我调整,从而在主要诸侯国家中引发了一个改革的浪潮。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350年,魏国之外的改革浪潮整整持续了五十余年,其中最为彻底的两次改革是由秦国分别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施行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遍采行科层制、奖励军功、严格管理地方人口(包括户籍制度)、废除井田制、依法保护土地私有制、提升人口中核心家庭的比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税收制度、统一度量衡(见对井田制和核心家庭的注释)。上述改革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权力,使秦国得以将其整个疆域组织成一个军事化国家。从此之后,秦国就一直保持着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优势,并最终于公元前221年消灭列国,一统天下。改革的成功使秦国势力大增,为秦国走向专制提供了条件。甚至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压制在其看来妨害统治的商业和学术活动。就这样,国家最终成了春秋战国时代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的唯一受益者。 在本书随后的三个部分中,笔者将更加详细地讨论战争是如何与其他结构性条件一起塑造春秋战国各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的。鉴于本部分已经对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演变的总体逻辑做出说明,为避免重复,笔者将通过对上述三个历史阶段中所发生的若干关键性变化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突出春秋战国时代历史演变的逻辑。 ★ 大历史观的回归。 本书堪称当代历史研究中罕见的具有大历史视野的著作。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赵鼎新以社会学的方法切入中国历史研究,从五百年的东周纷乱历史中,提炼出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基本模式,试图回答:中国何以成为中国。 ★ 建立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学新模型。 将频繁的战争作为推动东周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打破传统的春秋—战国二分法,将东周政治进程分解为三段:霸主期,转型期,全民战争期,建立透视这段关键历史的新框架,极具创造性。 ★ 从起源处剖析两千年帝制中国的政治基因。 在战争的推动下,东周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巨大转型,此后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郡县制、科层制、强国家等特征,皆起源于这个关键时期。在东周的尽头,一个儒法帝国冉冉升起,至今仍然笼罩着我们对历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