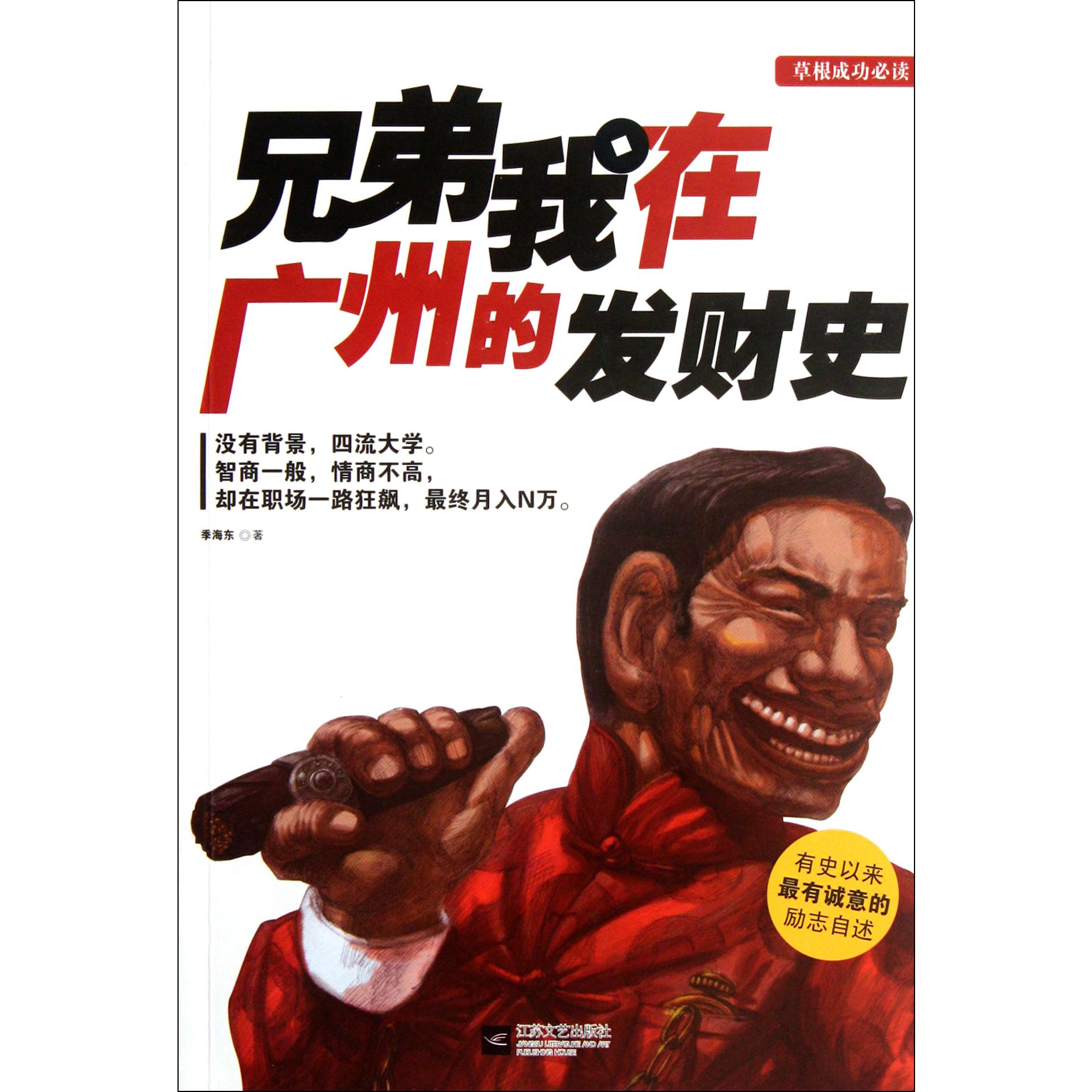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24.00
折扣价: 17.04
折扣购买: 兄弟我在广州的发财史
ISBN: 97875399482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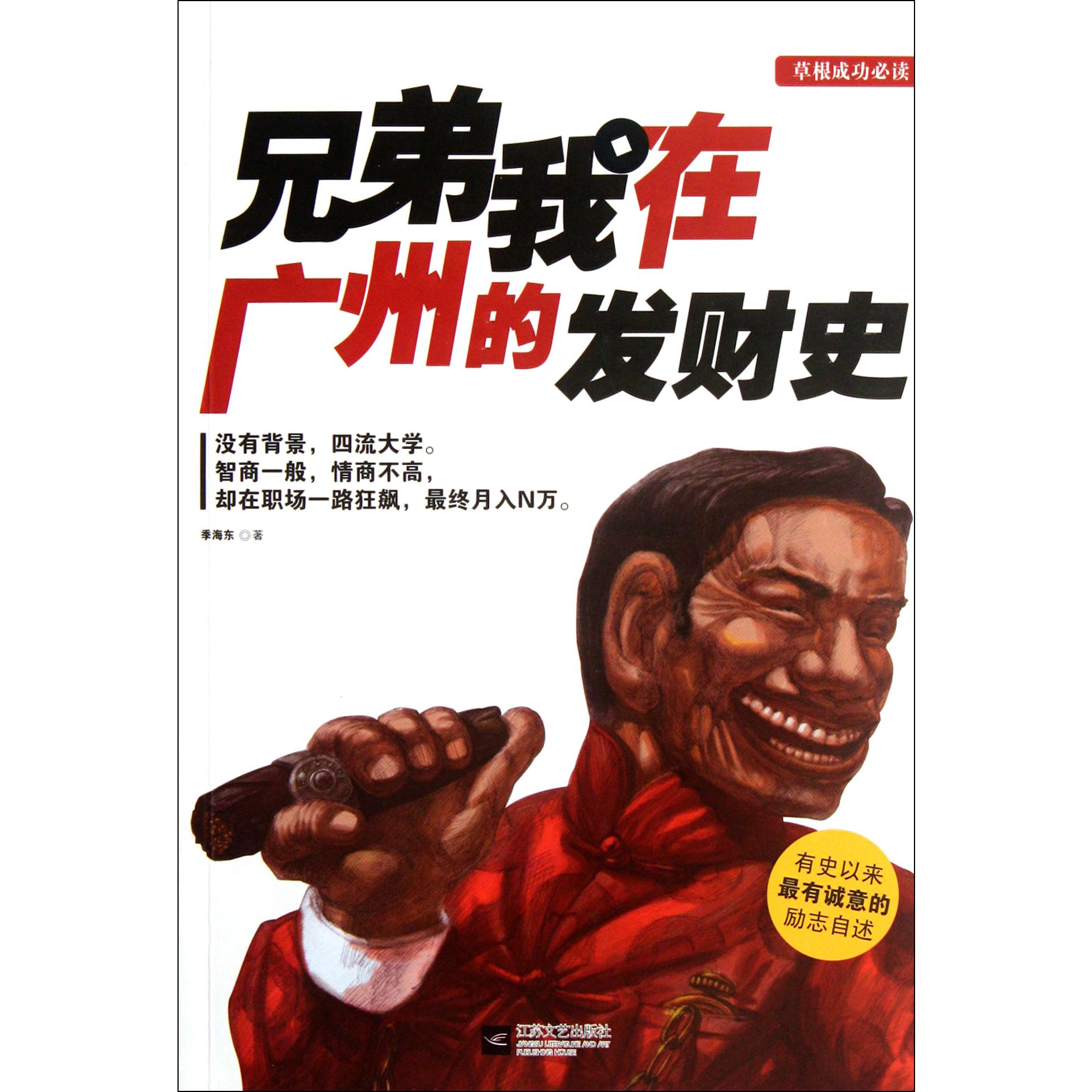
。。。
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 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动力。 这是一本我想起来就要流泪的书。 广东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无数的人来了,无数的人走了,无数的人来 了、走了、又来了。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产生,很多人的梦想在这里死亡, 甚至是个体的消失。一个偌大的城市,一条生命的消逝,绝不比垃圾箱里一 条已经僵硬的猫的尸体更加值钱。 我的意思是,写这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炫耀,不是“成功”后躺在沙发 上剔牙,顺便打几个饱嗝。相反,这本书里的许多内容我是不想提及的,假 若早几年,我也许会因为回忆而哭泣。我不是娘娘腔,动辄会为晴风雪雨而 哀愁,相反,我是一个坚强的人。在广东,一个不够坚强的男人的结局只有 一个,那就是卷好铺盖滚蛋,从哪里来,滚回哪里去。如果你对我的话产生 怀疑,那我告诉你我初到广东前三年的大体状况: 第一年没钱回家,第二年在《经济时报》,第三年回家时母亲已头发花 白,修自行车的父亲头发也掉光了。 双亲一个有糖尿病,一个有心脏病,哥哥车祸后赔了一大笔钱。我有一 个亲戚当时在镇上一所学校当校长,算是个很有体面的人,在这一方穷山恶 水里算是有些“人脉”的。有句话叫“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所以等我大学毕业后,家里人希望可以托他帮我谋一个糊口的职业,最好 能去学校当老师。看着父亲低三下四的求他,我的心里像被堵了一块巨石。 求人的滋味儿太难了,我拦住父亲,告诉他我不想做老师。我在心里暗暗下 决心,宁可死在外面,也绝不回家。 我父亲是个修车匠,经常把一摞毛票放在家里,我每天去上学,就从里 面抽三角钱出来“过早”(吃早饭),绝不多拿一分钱。后来,也许是看我 吃的挺多,小孩子要发育身体嘛,就由三角钱涨到了五角,但我还是只拿三 角,我知道家里赚钱的艰辛。 我从小就恨那些家里有钱的人,他们家里有钱,就可以欺负别人。偏偏 我这个人不吃那一套,因此挨了不少打,我右手的一根骨头就是被他们打断 的。可以说,对于家境相对富裕的那些人,我天生有着排斥心理。直到现在 ,如果一个人,他是穷苦人家出身,就能和我拉近许多距离。 我的父母是天底下最普通的父母,怕孩子惹事,怕孩子出事,我小时候 班里有几个同学,因为到长江里洗澡,所以夭折了。我们那里是“鱼米之乡 ”,湖泊星罗棋布,都是长江分出来的支流。湖多,鱼也多,因下河洗澡捕 鱼而失足溺水的事很多。我的那几个同学,起初只有一人落水,既而施救, 不断被拽入水中,遂成一惨剧。溺水而亡的尸体一时半会浮不上水面,就有 小舟来回逡巡,用五爪铁钩探寻。当事者的父母在水边哭的死去活来,晕厥 数次,跪求得一完尸。盖因尸体如不当天找到,会被流水带到下游,于隐蔽 处发臭腐烂,也不得而知。大约快天黑的时候,铁锚一沉,就听人喊:在这 里!紧跟着的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我的父母于是很怕我也死掉,对我看的很紧。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 让我随便到一个乡里去,当一个老师,每月拿三四百块钱的薪水,闲时搞一 下家教,补贴家用。这当然是个谋生活的途径,我相信凭借我的能力,也是 早晚能达成所愿的,但我不想就这么活着。我说我想出去,他们拦着我,不 让我走。 我问:“你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不走,你们能给我提供什么?”当 然什么都没有,于是只能放我走。 在农村,作为一个儿子,我其实做的挺糟糕的,因为我实在太想卓尔不 群了。我想起了以前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五条原则”:不要思考;如果思考 了,不要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不要写下来;如果写下来了,不要签名; 如果签名了,发生什么事,都不要惊讶。 我是一个农村土生土长的穷小子,但是我从小就喜欢争论,热爱思考, 这直接导致了我大学毕业后的离家出走。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我应该留在 农村,找个月薪七八百元的稳定工作,娶妻生子,赡养老人,每晚七点准时 收看《新闻联播》,并被晚会上人工掀起的小高潮感动的热泪盈眶。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但很多人希望,至少我的父母是这样吧。他们应 该从小给我也定了个五原则:不要瞎想;如果瞎想了,不要嚷嚷;如果嚷嚷 了,不要当真;如果当真了,不要说走就走;如果说走就走,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惊讶。 我当时给自己立下三个原则: 我不当老师; 我不进工厂; 我不求人。 第一条原则我是很坚决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师范毕业,对教育已经心灰 意冷。我毕业的那个学校,是全国三类的专科院校(后来升本),录取分数 线很低,可想而知,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会拥进来,里面的大部分人只 为了拿个大学毕业证。抱着这样的“伟大理想”,校园生活有多精彩你就可 想而知了,完全没有未来老师的样子,整天拿着家长的钱干一些乌七八糟的 事情,真难想象他们今后怎么在三尺讲台上为人师表。 我大三的时候,谈了一场黄昏恋,和一个大一的女孩子有了一段不太成 功的感情。我们当时还小,幼稚得吓人,考虑问题不周到,后来肯定是要分 手的,到最后,她给出的分手理由是,她的家不在本地,所以“我们是不可 能”的。这个曾经的小女友,后来找了个老公,也在广东打工,每月挣一千 八百块钱,买不起房,就想离婚。我当时已经混的人模狗样,她在电话里诉 苦,说还是很想我的,能不能念个旧情,借点钱给她,好让她的老公买房。 或者,直接离婚,跟我过。 我当时在想,大学时你嫌地方远(其实也就是一个市里的两个县),现 在我在广东,你反而要投怀送抱。这样的女人坚决不能要,好马不吃回头草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也许我真的很绝情吧。我也很看不起她的男人,没钱 买房可以想办法,但是把自己的女人像鹰一样撒出去,用肉体换钞票,实在 是下下之策。 这些事情对我有些影响,但是不算深,其实我之所以不想当老师,是因 为我觉得这个职业太清苦,社会地位很低。可能这两年好了点,但是我刚毕 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除了不想当老师,我还不想进工厂。在广东,进工厂的含义就是背着铺 盖卷,变成一个廉价劳动力。也不是没有晋升的可能,但过程很难,男的要 舞刀弄枪,女的要牺牲色相,总之不容易。 我有几个亲戚,年轻时在工厂里混,老了就下岗,住在低矮潮湿的黑屋 子里。一家四五口人,屋子只有二十多平米,竖条结构,像一枚巨大的口琴 。唯一的“福利”,就是可以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工厂里加工的衣服,除此无 他。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我从小就受穷,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好大学)毕 业后,再也不想过以前的日子了。 再加上在我周围,教师和工人职业的亲属朋友,很难有快乐的生活。这 不得不让我沮丧,也对我的择业观产生了影响。 至于不求人,就是性格方面的事了,我是个非常清高的人,自尊心很强 ,永远不会在熟人面前卑躬屈膝。 在大学期间,我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大概是什么样。 我在那所师范大学里待了几年,谈过“黄昏恋”,玩过“夕阳红”,但 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我当过家教,开过补习班,还卖过电脑,通过 这些赚了一些钱。电脑当时还是比较稀罕的东西,组装一台电脑的利润也比 较可观,但我最初并不了解这些东西,只知道我要靠这个赚钱。为此,我专 门去了武汉的电脑城,专门跟踪那些从事电脑生意的商人。比如,他们是在 哪里拿到的显卡,哪里的机箱是最便宜的,谁是一级代理商,通过跟踪都可 以查清楚。有时候跟踪的肚子饿了,就随便吃一碗热干面,接着跟踪。这样 ,十几天下来,电脑生意的整个流程,找谁买哪些零件最实惠,就全明白了 。 我当时在学校里是个小官,就召集班干部,让他们在班里宣传买电脑, 就说“他们的表哥”在武汉从事电脑生意,找他们买可以享受优惠,每台给 他们四五百块钱的回扣。就这样,我算是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知道 自己有经商的头脑。当时在学校,和我一样想办法赚钱的人不多,百分之九 十的学生,都在等着毕业后找个老师的工作混吃等死,剩下的百分之十,一 半经商,一半从政。这段经历为我以后的人生也埋下了伏笔。 当然不管怎么说,大学生活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学生时代是很幼稚的 ,一个班级,八九十条枪,头皮凑在一起,能吃一个盒饭,就是兄弟。但是 踏入社会,一切都变了。我认识几个同为中文系的校友,大学里开始谈恋爱 ,小鸳鸯成双入对。毕业后,随着打工潮一起去了广东,身无长物,听到昔 日同窗有发迹者,赶去投奔。寄人篱下,仰人鼻息,自然要拍些马屁,反而 为发迹者所不齿。我曾听一个混的比较不错的同窗,很得意地跟我讲这些事 ,反问我:“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求我的吗?” 然后一脸鄙夷地说:“就像狗一样。” 我观察过一些大学毕业后“飞黄腾达”的校友,之前在校园里,我认为 校园是一块净土,而且是人的一生中唯一的那么一块。在校园里遇到的善良 人、好兄弟,到了社会也许会变;在校园里遇到的极品,几年之后也许会成 为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外打拼那么多年,我这才意识到,一个人以前是 什么样子,被社会浸染、熔炉,他还是什么样子。 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读书,现在还有读书看报的习惯,无论工作多忙, 多累,我都会坚持多读书,这为我的成功提供了很大的精神助力。 新西兰《奥塔戈每日时报》网站曾经刊发一篇文章,原文标题为《中国 未来的举止仍难预测》,语出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戴维·香博。戴维·香博先 生在新西兰奥塔戈大学发表过一次演讲,主题是“中国的全球身份认同:精 神分裂的超级大国”。演讲中,戴维·香博先生不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融 入国际社会,其未来的行为举止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事实上 ,他将变得越来越像中国,而不是像西方”。 我的同学,昔日的大学校友们,和这个国家一样。他们在大学是一个什 么样的人,尖酸、刻薄、冷漠、温情、善良、不温不火,等等,十年之后, 他们还会是这样的人,不仅如此,还会加倍。 我们从来都不缺乏梦想,缺的只是追求、坚持以及珍惜梦想。只有在你 不停的去主动靠近它的时候,它才有可能照进现实。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