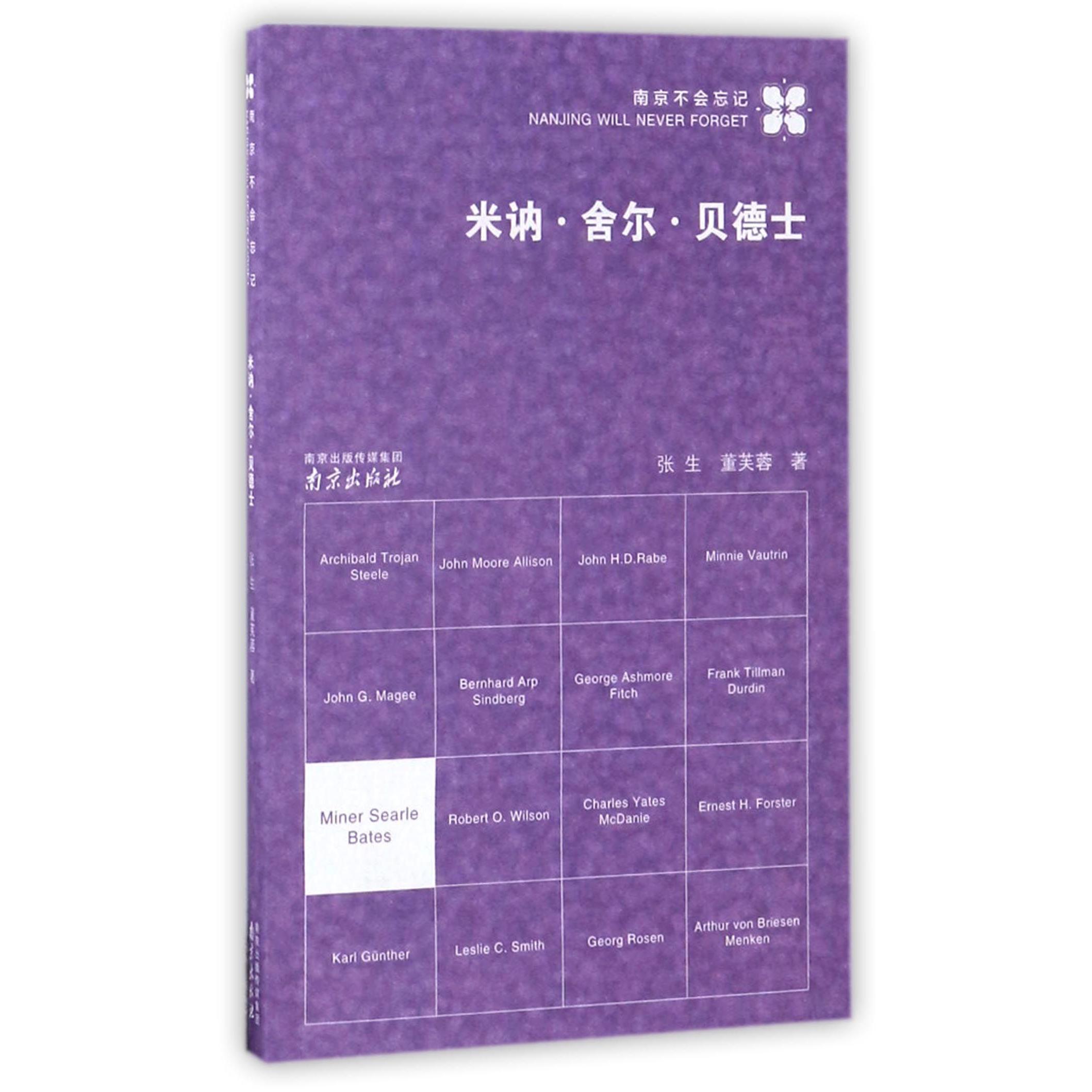
出版社: 南京
原售价: 15.00
折扣价: 8.58
折扣购买: 米讷·舍尔·贝德士/南京不会忘记
ISBN: 97875533158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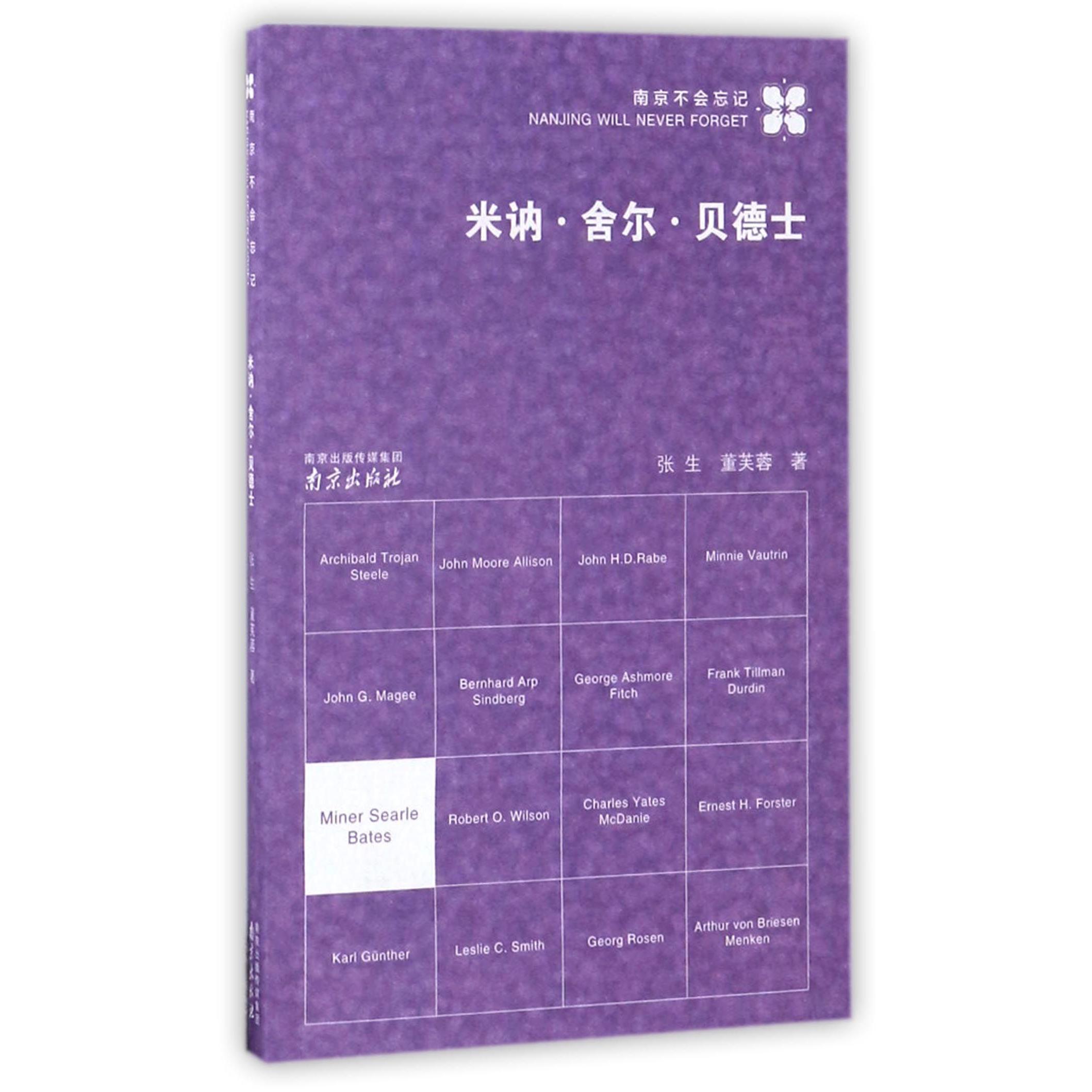
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成立于1936年,隶属 金大文学院。1935年, 颁布《大学研究所暂行 组织章程》,要求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文学院根据这 一章程,在国学研究班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文科研究 所史学部和文学部,并为此专门成立委员会,时任历 史系系主任的贝德士被推举为委员,另外两位委员是 文学院院长刘国钧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主任徐养秋。 委员会成立后,贝德士等便拟定规章、课程和招 生简章等,送 审核,1936年获 核准,文 科研究所史学部正式成立。 根据《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暂行简章》规 定,史学部选聘教授4至6人,生源为“国立省立及经 立案之私立大学文学院或独立学院文科毕业生 以史学与中国文学为主辅系者,或其他各系毕业生愿 研究史学而毕业成绩在中等以上者”。在大学生尚为 凤毛麟角的时代,贝德士等人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培 养史学人才,令人感慨万千。今天,贝德士虽然已故 去近40年,但他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一位可亲 、负责的老师,长久地活在金陵大学师生的心目中。 1920年贝德士来到金大,由于当时金大的教工宿 舍并不宽裕,他只好借住在社会学家谢伟师家中。据 谢伟师回忆,当时他们必须为贝德士腾出两间房,一 间住人,一间装书。待贝德士将所有的书拆包后,竟 连日常生活用品都没法安放,贝德士是南京的外国人 中私人藏书最多的一位,由此可见贝德士对知识的渴 求。这种渴求也成就了他的博学多才,他的学生陈宗 熙回忆说:“其学问的渊博与为人的和蔼,固属有口 皆碑,对于历史上‘人,‘时’‘事’‘地’‘物’ 的记忆力之强,尤其熟极若流,如数家珍。”听过贝 德士演讲的外国学者索尔博也说:“1943年在耶鲁, 贝德士在我选修的一门中国区域研究课堂上演讲,我 特别倾服于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与记忆。我仍然清 晰地记得,座位离他很近,两小时提供大量细节,诸 如互相比较的数位,1900年、1910年、1920年、1930 年、1940年中国铁路有多少英里,硬型路面公路的类 似数位等。演讲之后与贝德士交谈,我发现他的讲演 稿只有三个词用以概括主要范围。”还有曾任金大校 董的杭立武回忆起贝德士:“至于贝德士先生,确实 是一位积学之士。他治学的态度很严谨,无论讲课、 改卷子,或讨论问题,绝不含糊。他寻求理解,必有 所依据,对于搜集材料,十分的认真。”贝德士刚来 中国时,并不精通中文,通过在金大华言科的努力学 习,“已可博览群书。他每日必看《中央日报》,同 学中有以中文撰写作业者,他也照样可以批改”。 贝德士讲授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陈宗熙说:“ 在校四年,可资纪念的事物太多了,正如白头宫女闲 话天宝遗事,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而在记忆中最凸 出、最清晰、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人,是教授我们政 治学和历史的贝德士教授。……在教授的时候,娓娓 道来,不疾不徐,旁征博引,循循善诱。因此他所教 授的科目,都为同学们最感兴趣的课程。” 贝德士善于提携后进,培养史学新苗。他说:“ 我试图扶植中国青年教师,让他们得以顺应自己的兴 趣与长处,而我则只有担任其余的历史课程。重要影 响已逐步显示出来,但这却意味着我要像新教员那样 ,不断从一门课程转移到另一门课程,同时还要遵循 部颁教学计划的不时变化而担任新课教学。结果已表 明这一决策完全正确,例如我现在的主要同事王绳祖 与陈恭禄,还有此前的三四位同事。王、陈不仅教学 出色,他们的著作已有并将继续增长广泛的影响,因 为他们编写的大学教材已成范本。”所以,在王绳祖 出版的《现代欧洲史》与陈恭禄出版的《中国近代史 》的扉页上,都特别写上“献给贝德士教授”,以感 谢他的培育之恩。贝德士为金大历史系的发展所立下 的汗马功劳,是全校师生一致公认的,“他在文学院 虽仅是历史系主任——一度也担任过副院长——但因 为年代久,资望高,所以对于整个院务,甚至全校校 务,都有很大的贡献”。 课堂之外,贝德士也尽力去帮助学生。据史学家 章开沅回忆:“在我们金大历史系校友的心目中,贝 德士主要还是一位好老师。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 特别是乐于帮助学生。他常利用周末进行家庭茶叙, 轮流邀请部分同学做客,不仅作为史学的第二课堂, 还借以训练我们英语的口头表达能力。他与贝师母都 非常和蔼可亲,以助人为乐。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异想 天开,突然对研究印第安民间文学兴味甚浓。他们不 仅没有批评我不务正业,反而设法帮助我向美国新闻 处和英国文化委员会借阅有关新出版的著作。”陈宗 熙也说:“如果在课余到他私人住处去请益,他更不 惮其烦地详加指示,真是如坐春风,如同家人般的亲 切热诚。此种情形,如今在台同窗学长当能为我证明 。我之所以选读政治,完全是受了他的影响,假如说 略有心得,也完全是受他之赐。” 可以说,贝德士作为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假使 没有南京大屠杀期间的经历,他也会因为对中国现代 历史学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后人铭记。但因为那一段峥 嵘岁月,今天,任何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学者,都不 会忽略他的存在,他已经被书写进了世界历史。 P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