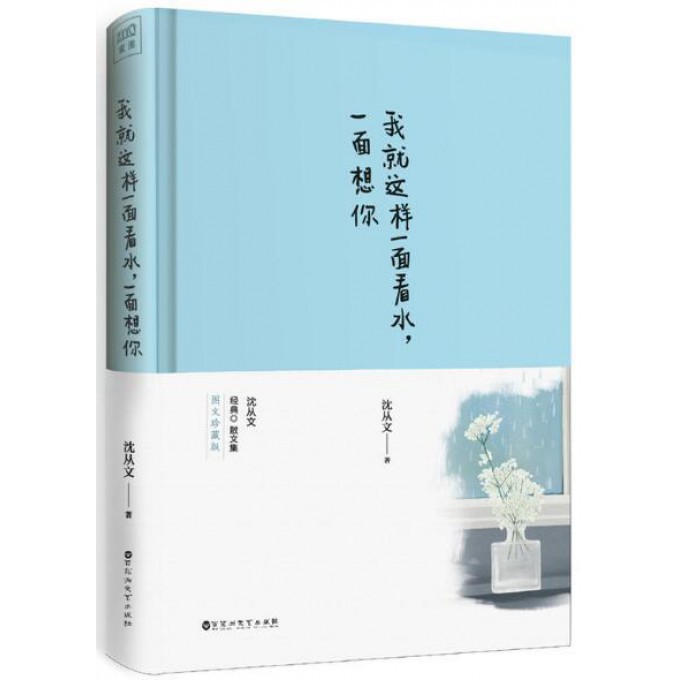
出版社: 百花洲文艺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3.70
折扣购买: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精)
ISBN: 9787550022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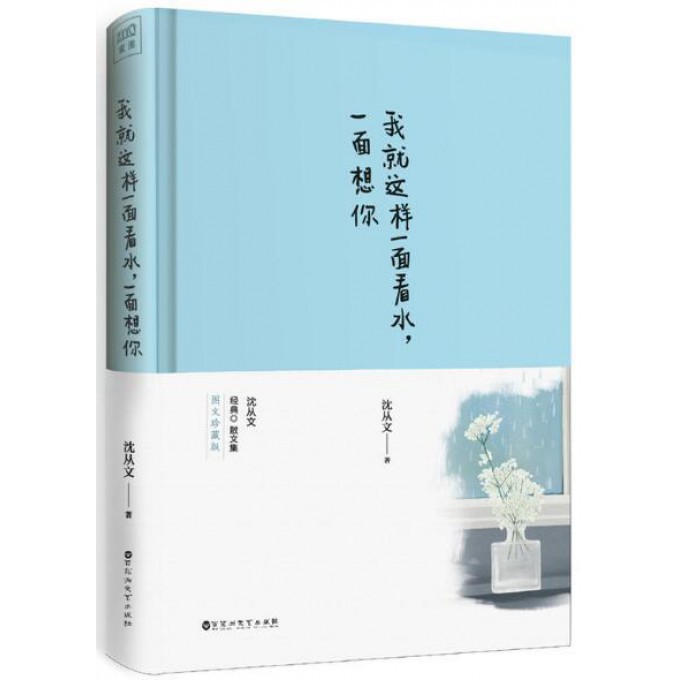
沈从文(1902—1988) **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 湖南凤凰县人,苗族。 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 作品有小说《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 曾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
船是只新船,油得黄黄的干净得可以作为教堂的神龛。我卧的地方较低一些,可听得出水在船底流过的细碎声音。前舱用板隔断,故我可以不被风吹。我坐的是后面,凡为船后的天、地、水,我全可以看到。 我就这样一面看水一面想你。我快乐,就想应当同你快乐,我闷,就想要你在我必可以不闷。我同船老板吃饭,我盼望你也在一角吃饭。 ——《小船上的信》 风大得很,我手脚皆冷透了,我的心却很暖和。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原因,心里总柔软得很。我要傍近你,方不至于难过。我仿佛还是十多年前的我,孤孤单单,一身以外别无长物,搭坐一只装载*服的船只上行,对于自己前途毫无把握,我希望的只是一个四元一月的录事职务,但别人不让我有这种机会。我想看点书,身边无一本书。想上岸,又无一个钱。到了岸必须上岸去玩玩时,就只好穿了别人的*服,空手上岸去,看看街上一切,欣赏一下那些小街上的片糖,以及一个铜元一大堆的花生。灯光下坐着扯得眉毛极细的妇人。 ——《夜泊鸭窠围》 一个白*带走了一点青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忍*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由达园给张兆和》 以我这么一个人间摈弃者,在过去与未来的生命**,还加上许多疑问符号来维系自己生趣,你又何苦这样用酒精来作践自己? 爱,是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使世界生物在*月无情的转轮下不至灭亡的原故,同时颁给人的。因为这在实际上便是—种传衍族种义务的报酬,*可以说是单纯的义务。不过,义务虽是义务,但从这中可以得生命的愉悦,是以人人都不以这义务为烦苦(除了生在特殊病态下的少数人)。 失恋,想恋,得来的苦闷,不过是一个人应负责任面不得尽责时一种神的惩罚罢了!这惩罚似乎是把人 一九三七年抗战后十二月间,我由武昌上云南路 过长沙时,偶然在一个本乡师部留守处大门前,又见 到那表兄,面容憔悴蜡渣黄,穿了件旧灰布*装,倚 在门前看街景.一见到我即认识,十分亲热的把我带 进了办公室。问问才知道因为脾气与年轻同事合不来 ,被挤出校门,失了业。不得已改了业,在师部作一 名中尉办事员,办理散兵伤兵收容联络事务。大表嫂 还在沅陵酉水边“乌宿”附近一个村子里教小学。大 儿子既已失踪,音信不通。二儿子十三岁,也从了* ,跟人作护兵,自食其力。还有老三、老五、老六, 全在母亲身边混*子。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 ,常害点胃病,性情自然越来越加拘迂。过去豪爽洒 脱处早**失去,只是一双浓眉下那双大而黑亮有神 的眼睛还依然如旧。也仍然欢喜唱歌。邀他去长沙著 名的李合盛吃了一顿生炒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 问他还吸烟不吸烟,就说,“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 它”。可是我发现他手指黄黄的,知道有烟吸还是随 时可以开戒。他原欢喜吸烟,且很懂烟品好坏。第二 次再去看他.带了别的同乡送我的两大木盒吕宋雪茄 烟去送他。他见到时.憔悴焦黄脸上露出少有的欢喜 和惊讶,只是摇头,口中低低的连说:“老弟,老弟 ,太破费你了,太破费你了。不久前,我看到有人送 老师长这么两盒,美国大*官也吃不起!” 我想提起点旧事使他开开心,告他“还有人送了 我一些什么‘三五字’、‘大司令’,我无福享*, 明天全送了你吧。我当年一心只想作个开糖坊的女婿 ,好成天有糖吃。你看.这点希望就始终不成功!” “不成功!人家都说你为我们家乡争了个大面子 ,赤手空拳打天下,成了名作家。也打败了那个只会 作官、找钱.对家乡青年毫不关心的熊凤凰。什么凤 凰?简直是只阉*,只会跪榻凳,吃太太洗脚水,我 可不佩服!你看这个!”他随手把一份当天长沙报纸摊 在桌上,手指着本市新闻栏一个记者对我写的访问记 ,“老弟,你当真上了报,人家对你说了不少好话, 比得过什么什么大文豪!” 我说:“大表哥,你不要相信这些逗笑的话。一 定是作新闻记者的学生写的。因为我始终只是个在外 面走码头的人物.底子薄,又无帮口,在学校里混也 混不出个所以然的。不是抗战还回不了家乡,熟人听 说我回来了,所以表示欢迎。我在外面只有点虚名, 并没什么真正成就的。……我倒正想问问你,在常德 时,我代劳写的那些信件,表嫂是不是还保留着?若 改成个故事,送过上海去换二十盒大吕宋烟,还不困 难!” 想起十多年前同在一处的旧事,一切犹如目前, 又恍同隔世。两人不免相对沉默了一会,后来复大笑 一阵,把话转到这次战争的发展和家乡种种了。 P44-45 睡于蔚苍苍的天宇下的一张绿色天鹅绒摇椅上,强制他数算眨眼的星星;大概谁都乐意。 因此你那囚犯似的颓丧,在我并不以为奇怪。 ——《给低着头的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