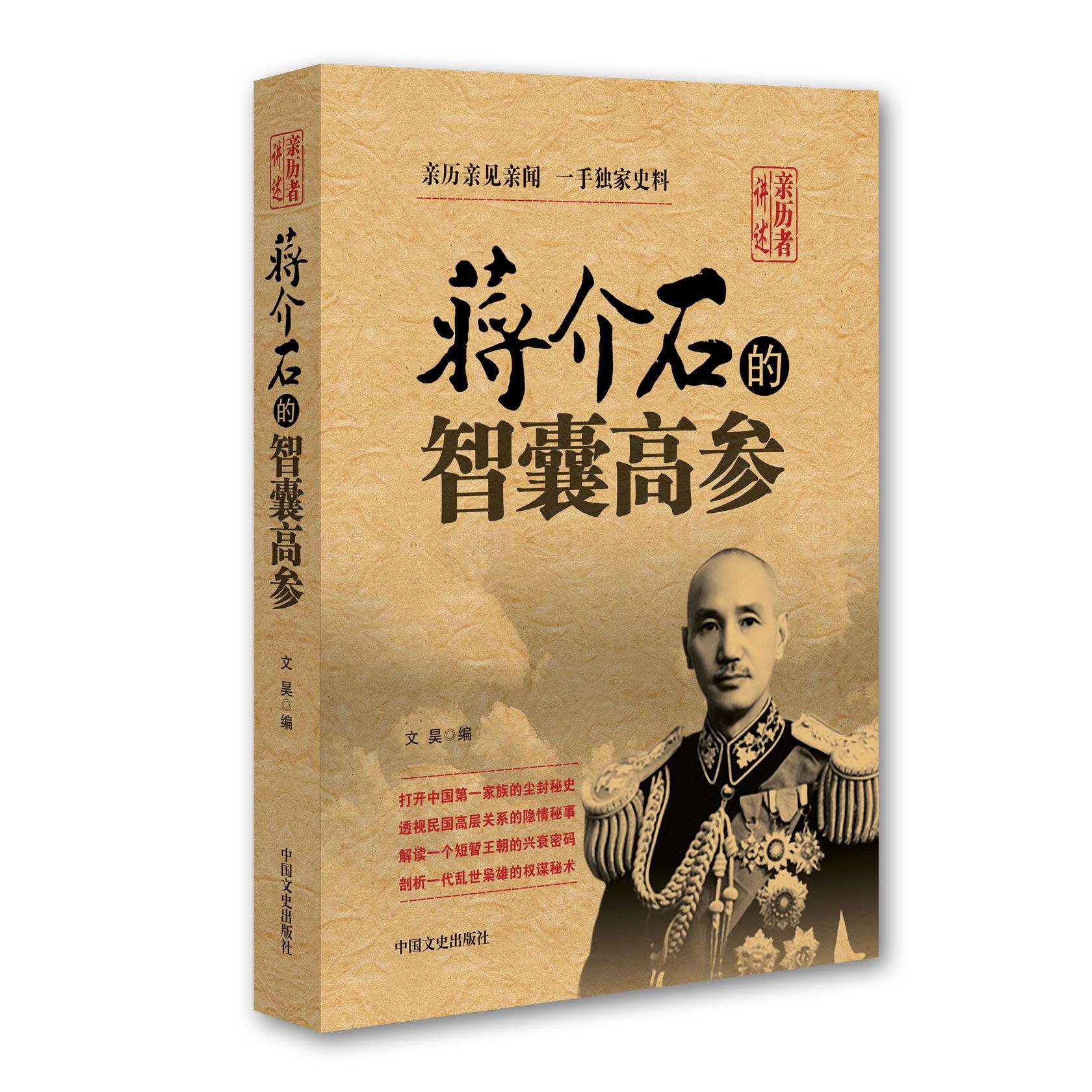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文史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30.15
折扣购买: 蒋介石的智囊高参(亲历者讲述)
ISBN: 9787503429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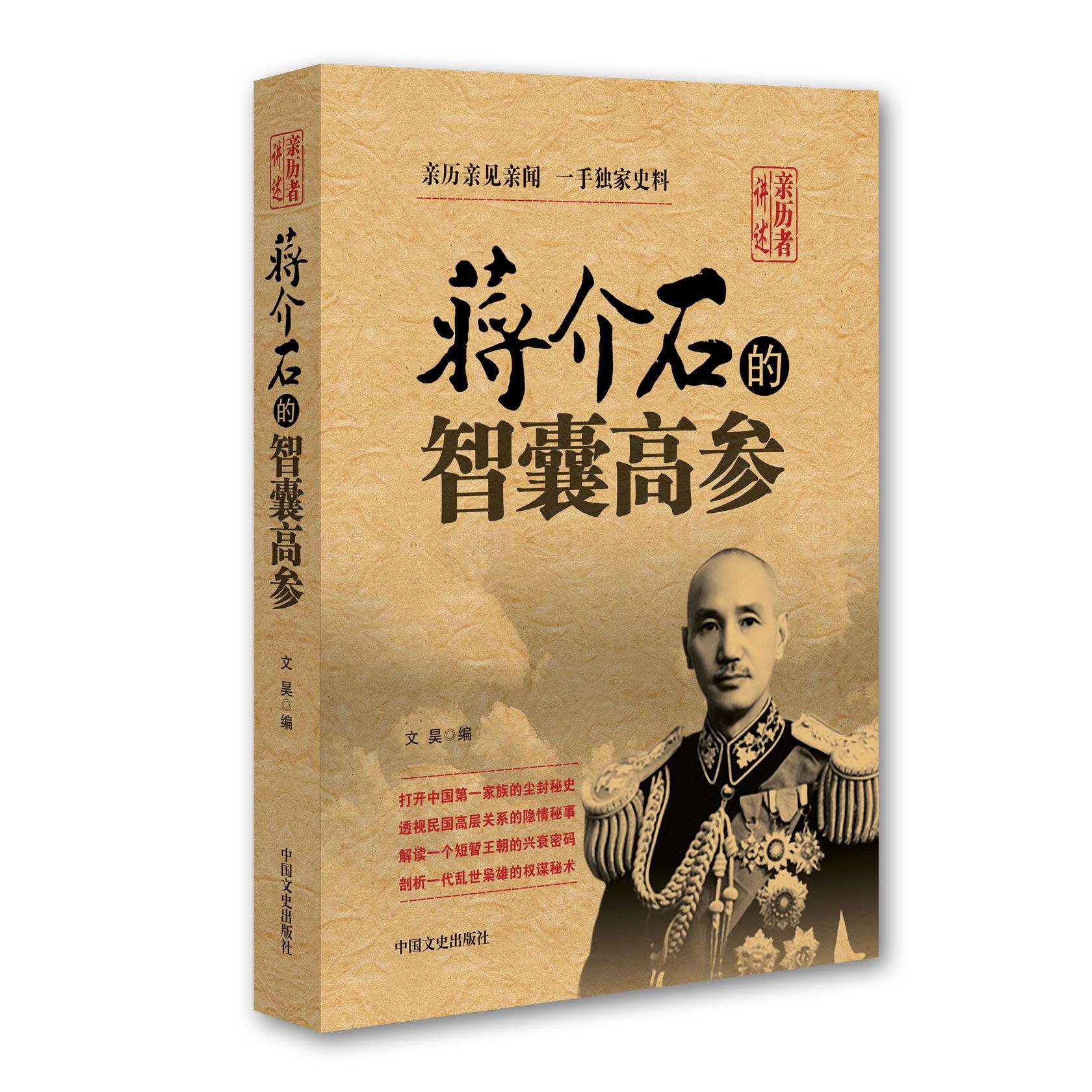
一、我的舅父陈布雷 曾经担任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的冯乃超 ,1979年10月建议我给陈布雷写一篇传记性的文章。 他信上说:“你对陈布雷比较熟悉,找资料可能有较 多的线索。为这一走错了路的知识分子写个传如何? 给蒋介石拿笔杆子,想来不会愉快,我不知什么原因 ,似乎觉得他当时是感到痛苦的……对中国老一辈的 知识分子的分化过程,应作一番客观的分析,单看进 步的一方面的人们是不够的。”四个月后,他给我的 信中又提到此事:“《民国史》编写的任务,我想各 校都有分担责任。《陈布雷传》你独立写一篇何尝不 可?要有决心上图书馆(报库)里泡一段时间。这样 也可能是一种锻炼。” 可是,我却迄今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布雷先生虽 是我的舅父,我的父亲翁达(祖望)在陈的身边担任 秘书工作多年,但我对陈了解不多,不深透,他是一 个极为复杂的人物。这几年中,我写过几篇有关陈布 雷的短文,发表后引起相当普遍的注意,但全面性的 传记却一直未敢动笔。现在,我就权以本文替代那至 今未能完成的陈布雷传记的撰写任务罢。 写了一生文章,却无著作传世 陈布雷是一个文人,“一介书生”,一生写了很 多文章。二十二岁(1911年,宣统辛亥),他方毕业 于浙江高等学堂,即就任上海《天铎报》撰述。当时 规定的任务是,每天写短评两则,每十天写社论三篇 。以后,他在上海《商报》任编辑主任时,写的文章 更多。在《天铎报》时,一部分评论用“布雷”署名 ;后来在《商报》写的社论,则大都改用“畏垒”署 名。可是到了后半生,他主要是为蒋介石代笔写文章 ,用自己的名字写的文章就极少了。偶有,多半也是 为至亲契友写的寿序、悼文之类。这本《回忆录》是 从他1890年(光绪十六年)出生写起,到1939年五十 岁(虚岁)为止,以年为经,以事为纬,记述了他家 庭生活、求学经过以及办报和从政的经历。原稿是用 老式红格十行本墨笔写的(他习惯用这种簿子)。分 两册:第一册是1936年夏他在庐山写的,写到1921年 ;第二册是1940年在重庆老鹰寓所养病时续写的(正 是他五十生辰后一年)。出版时合成一册,二十开本 ,共九十五页,约七万字,还附了十帧照片,人们可 以从这一本《回忆录》约略了解他的一生,可惜写得 早,抗战胜利后就没有接续撰写,以致不能包括他一 生最后九年的记录。《回忆录》前,陈夫人王允默写 的“前记”中,虽述及“至五十岁以后所记,以及论 文、书札、小品等作,亦在整理搜集中,一俟有成, 即当陆续付梓”。但后来很快全国就解放了。据我所 知,陈夫人对陈一生中发表的重要文章,大抵剪贴成 册(据说有两本)。同时陈自己从1935年3月起,天 天都写日记。未尝中辍,到他去世为止,也有十三年 半,十行簿至少得几十本。这些材料,在“文化大革 命”抄家风中全被抄走,一度以为已经散失。现已查 明存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就史料说,应该是件幸事 。因为这是第一手材料,不仅对研究陈布雷本人十分 有用,即从研究中国现代史角度看,也是很有价值的 。 孝父忠“君” 不少人说陈布雷的封建意识相当浓厚,这是事实 。陈布雷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父亲依仁府君有 两个兄长。兄长生了一子(陈训正,字屺怀)二女; 仲兄无子。依仁府君却有七子七女,陈布雷居长(后 来过继给二房了)。陈对父母极尽孝道,事事向父请 示。父有命,从不敢违。十四岁时,父命应童子试, 尽管心里极不愿意,还是去应试了。十七岁时,他在 慈溪县中学堂求学,奉父命转学于宁波府中学堂。次 年,因故在宁中辍学,得友人介绍而投考浙江高等学 堂预科,也是请示父命而成行的。1910年夏,是他结 婚后一年,在浙高正科还未毕业,却值浙省议送官费 生十名赴欧美。他得到了浙高老师、岳父杨逊斋(号 敏曾,历史学家,后任北大国史教授)的赞同和鼓励 ,在已考国文、英文、数学三门主课后,由于父亲以 家庭原因去信劝阻,他也就遵命放弃了这一机会。 1911年6月,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在《天铎报 》担任半年撰述,很快以长于撰论出名。当时,戴季 陶创办《民权报》,叶楚伧创办《太平洋报》,陈陶 遗接盘《申报》,都对陈有相约之意。陈自己不敢做 主,请命于父。思想保守的父亲,认为上海“洋场” ,非青年所宜久居。正值从兄参与发起创设宁波效实 中学(1912年,即民国元年3月),所聘教师多是上 年浙高毕业的同学如文科的董世桢(贞柯)、理科的 冯度(威博)、王子让等。陈又从父兄之意,受效实 中学英文、史地教员之聘,而放弃继续办报之机会。 1914年7月,依仁公忽病故,遗子女多人,陈哀痛逾 恒,且根据其父遗愿,毅然摆脱一切,家居达五年之 久,专门经纪家务,并继父志处理家族事务以及乡里 公益事业等。这同他个性格格不入,但还是一心一意 地去做了。而且在父丧后两年中,还谢绝在甬兼课之 约,显然还有“重孝”不出的用心。1916年,效实同 事虑陈乡居苦闷致病,力请兼课,始每周去甬任课若 干小时。直至1918年发妻杨氏以产后子痫症去世,始 于次年辞去族中事务而去上海。(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