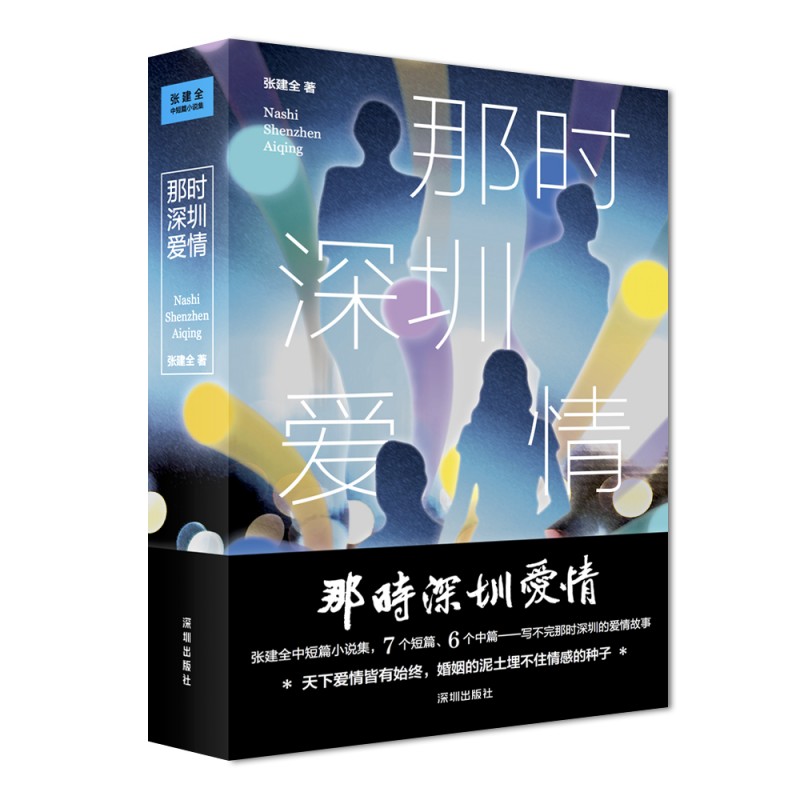
出版社: 深圳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2.20
折扣购买: 那时深圳爱情
ISBN: 9787550740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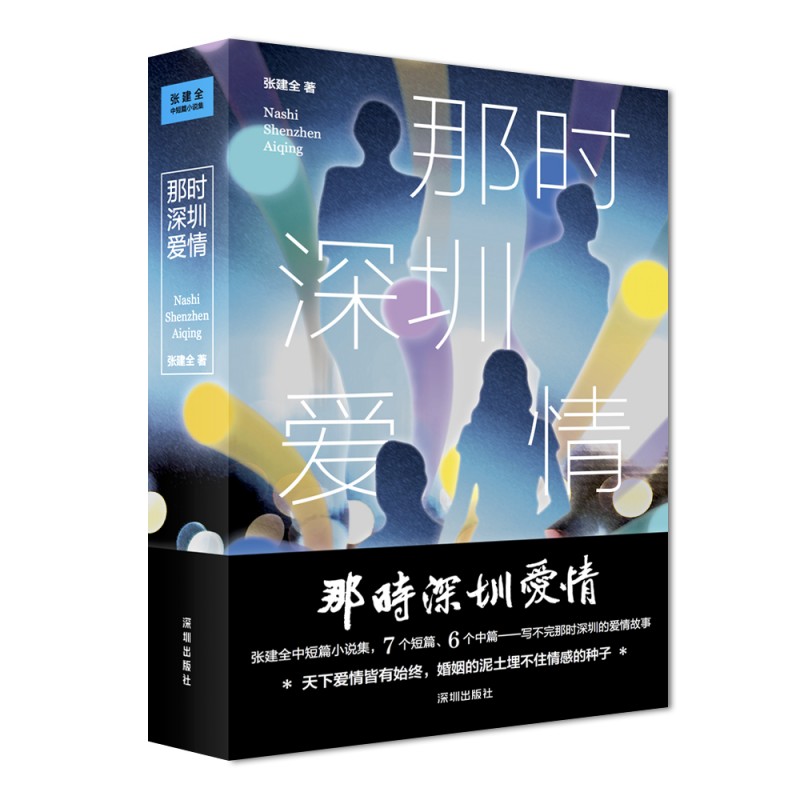
张建全,作家,词作家;籍贯陕西,现居北京;中共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曾出版散文集《我的商海往事》《鲜活的面容》。《再见已过四十年》获2021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十佳散文奖,《我的商海往事》获2022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一等奖,《河南第一味》获2023年度中国散文年会奖十佳散文奖。
序 都市繁华下的幽微人性 ——评张建全小说集 张鸿 爱情,文学创作的永恒母题。古今中外的小说,不论主题 是战争、家国还是江湖,大多会以爱情作为推动情节的关键。在 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爱情也变成了生活中的一种快餐式的交 流。那么,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谈论爱情还有意义吗? 对于这个问题,张建全的中短篇小说集《那时深圳爱情》必 定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从表象上看,爱情的表达方式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但深入探究,它所蕴含的情感仍旧是真诚、深刻 的,尽管它的保鲜时间发生了变化。在这部作品中,张建全运用 平实的笔法,通过 7 个短篇小说、6 个中篇小说讲述了关于深圳 的故事,抑或是爱情,抑或是亲情,抑或是友情,故事的主线都 离不开人生中必然会经历或渴望拥有的东西。在后记中,张建全 提到了“不由自主写爱情”,但我们需要看到,作品中,在爱情 谎言背后,他想要给我们传达的、更为深层的意义。他或许是想 经由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他体悟到的人生道理,又像是在记录世 间被忽视的情感经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要 读者能从这些故事中获取各自的人生感悟,张建全就是成功的。 小说的主题和意蕴,对于故事的完整性和现实性是极为重要 的。故事的完整性和现实性是小说的灵魂所在,而小说给我们传 递的思考,就需要以情节为载体得以呈现。尤其是支撑小说发展 的诸多情节,作者皆能精准呈现并有所升华,营造了一个又一个 看似平凡而意义深远的故事,阐发了他对于人生三大主题——爱 情、生命、理想的感慨与反思。 在《狗眼看人》中,作者透过狗的视角让读者看清了人性的 复杂和世间温暖,并通过命运的流变道出其难以言说的孤独和无 奈。小说中描述的狗眼看人低是准确的,它的视野也一定是独特 的,在它的眼中,在它的经历中,人性的冷漠和温暖,在兜兜转 转的抛弃、回转缘分中留下了温暖。在人世间,人与人的缘分, 都是阶段性的,有开始,必然会有结束。何况人与狗呢?“去旧 迎新”的事情时刻都在发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真正治愈你的, 从来都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释怀和格局,只要你的内心不慌 乱,世界都不能影响你分毫。巷子里的猫很自由,却没有归宿; 围墙里的狗有归宿,却始终低着头。没有人能逃避这个选择题, 最终的结果只会有两种:一种是为了自由流浪他乡,另一种就是 为了归宿禁锢终身,但愿我们都能在这样的选择中获取温暖和救 赎。故事并不是作者虚构的,而是他在生活中所亲身经历或者听 来的故事,他通过小说向我们抛出命题,而内里深刻的蕴涵需要 读者自己领悟。 一个女人,还是从农村出发来到深圳这座大都市的女人,从 一个男人的身边到另一个男人的身边实现了阶级跨越,不仅是自 身,还带着父母一起转变身份。小说《出嫁》应该就是现实版的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作者的笔触并没有表现出不满或者是鄙 夷,字里行间总会让人感觉到对人物的惋惜与怜悯,涂抹着忧伤 的底色。现实社会总是给了男人更多的宽容,女人只有舍弃某些 东西才能赢得幸福。莎士比亚说过:“爱情里面要是掺杂了和它 本身无关的算计,那就不是真的爱情。”这样爱算计、会周旋的 人得到了一切,故事却在中途戛然而止,就像童话故事里的最后 一句话——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生活怎么会总 是幸福的呢?作者的叙述娴熟且真诚,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给出 了寓意深刻的答案,故事的留白也给了读者更多自由探索的空 间…… “ 招聘员工时,有时候外表形象是现时增分项,学历能力是 未来增分项。未来既然无法测评,那么形象就加重了录取的砝 码。”读罢《绯闻主角》,我似乎读懂了作者对王秋月这一陷入绯 闻的女秘书的苦心经营。作为“绯闻”的当事人,王秋月所承受 的指指点点不可估量,但她绝不是“硕果仅存”的,像她这样的 人还有很多,更多的人生故事还在继续。而她对自身命运的无力 感,则是作者力图表达的。 一个女人的成功就是从过去的青春气息被风尘味所代替而开 始的,然而,久见风月如烟尘。《两代人》里,方大姐说的一句 话特别有现实意义:“这种事处理得好,朋友还是朋友。机会嘛,什么时候都有。”很多事情都是一念之间,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 云泥之别。在《于小姐》中,当于妹仔从渔家姑娘成为深圳 S 集 团公司下属的免税商场营业员时,丑小鸭变成天鹅的天时、地 利、人和都具备了,在时间的发酵下终于变成了于美凤。虽然她 坚持“我嫁不出去就不嫁人,我能养活自己”,但心里的失落还 是只有自己最清楚。作者笔下的于妹仔用爱情换取财务自由之后 还不忘追求爱情,但是人生的复杂便在于此处了,舍弃过去的动 力哪里又那么容易找回呢?又如《能够说什么》中在歌舞厅工作 的吴小迎、《走过泥泞》中在图书馆工作的晶晶,她们的职业身 份千差万别,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却是一致的。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你意外地成为上一 个情感故事的倾听者时,下一个情感故事的开头就已经写进了你 的人生。但是,猜到了故事开头却没有猜到故事的结局,你以为 已经胜券在握,哪知道早已经被踢出战场,失去了竞争的资格。 在《祸福》中,作者对于祸福的叙述是十分中肯的,他不但描摹 了主人公内心无法停歇的波澜,还善于捕捉其内心深处所散发的 幽微之光。 不管是美好的结局还是悲伤的结局,每一个故事都有自己结 束的时间节点。在《人面桃花》中,作者通过一女(赵美伶)三 男(郑一豪、于海和章亚军)讲述了一个在人欲横流的都市中, 发生的畸恋与弑妻的悲剧故事,读来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深思。 再如《劫后余情》里,具有 10 余年深漂史的东北姑娘那美,尽 管遭遇家庭变故和个人凌辱,但却能凭借其独立意识与坚强个性,遇事淡定而有分寸。小说中那些泛着暖意的动人瞬间,被作 者写得情真意切、耐人寻味。 婚姻在不同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不同的地位,但婚姻的真谛或 许要在失去之后才能领悟。“就当是曾经有过的逢场作戏罢了!” 在《婚姻》中,尹小洁来来去去 10 余年的感情就用这句话画上 了句号。华灯初上,细雨沥沥的气氛正适合爱情发酵,干柴烈火 的引诱下双方都抛弃了自己的家庭,忘记了自己的婚姻,用报复 的心理、补偿的心理获得了心理的平衡,她用实际行动,在另一 个层面上找到了夫妻之间新的平衡,但时间总是会给你很多不同 的答案。作家贾平凹曾说:“人活着的最大目的是为了死,而最 大的人生意义却在生到死的过程。”在作者看来,婚姻是一种在 世俗生活中的修行,尽管人类社会的生活大多数是以婚姻为形式 的,但生活的终极目的却不是婚姻,而是快乐与幸福,许多人都 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历经沧桑,从世 事中超脱出来,你才能在纷繁复杂的事情中抽丝剥茧,窥探真 相。作者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不要沉迷于表象,一定要 透过表象抓住本质。 “世上爱情,皆有始终。”这是《高成就爱情史》的题记。小 说讲述了画家高成就曲折的爱情史,主人公名为“高成就”,但 成就恰恰不算高,极具戏谑意味。从有名无实的婚姻到有实无名 的婚姻,从渴望爱情到抗拒爱情,高成就的选择总是会经历很长 一段艰难岁月和世事变化,是忠于爱情还是忠于金钱,这个问 题甚至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作者并没有说出他的答案,只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主人公选择后的结 局,剩下的都留给我们去琢磨。他只是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 是故事的评说者。 “ 歌手诉说着那个伤怀的故事,给观众点缀着轻松的夜晚。 那是别人的悲哀,可作自己的欢乐。”对于读者而言尝不是如 此。在看似世俗的选择中,总有一些人还是会遵从自己的内心, 奔向梦想的远方。在《阿美娜》中,我们感受到主人公的快乐、 悲伤、无奈等情绪,自然也会将自己带入这些情绪中,想起那些 似曾相识的故事,类似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 商海浮沉,爱恨情仇。中短篇小说集《那时深圳爱情》语言 精练、情节紧凑,张建全笔触细腻而深刻,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 界和情感变化,使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人物的心路历程,时有细节 令人拍案叫绝。他对于深圳、对于爱情的阐释,正是他与自己人 生境遇的和解过程。相较于每一个故事的内容,作者更重视这部 作品在读者心中掀起的波澜,同时也期待与读者进行心灵交流。 从故事的书写到对爱情的解读,再到读者内心所得,张建全 仿佛在述说着一种深思熟虑的创作感悟:读小说不是猜谜,而是 一种从自我到作品,再从作品到自我的“内循环”。在阅读小说 的过程中,复制作者的心境我们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是,听 从自己的内心寻找那份自己理解的情感。小说中那种幽微杳渺的 心灵境界,只能慢慢去感触。作者笔力深厚、情感细腻,能把人 写活,把故事写透。藤蔓般的情感纠葛,颇为精妙的叙事策略, 既烛照出城市生活的内在本相,又描摹出城市小说创作的别样风貌,使人物身处尘世却有超然物外之感。 纵览全书,张建全对于爱情、对于人生的理念和思考跃然纸 上,伴随着命运遭际的不断变化,文字蕴藏的内核也随之变化。 在饱满的人性观照下,小说的人物对话充满了良知和睿智,如同 一个个直指人心的镜头。从张建全的文字不难看出,小说集《那 时深圳爱情》能让读者陷入沉思。它摆脱了思想束缚,不拘泥于 固有的章法,追寻爱情的本真,既有“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的豪放有趣,又不失“婚姻的泥土埋不住情感的种子”的豁达开 阔,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作者系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副主编, 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后记 不由自主写爱情 古今中外的小说名家名作,多与爱情故事紧密相关。也许, 这就是爱情是文学永不过时的主题之一的说法的依据。 我年轻时写小说,相隔几十年后再写小说,竟不由自主地 都把爱情当成了写作内容,或者说当我写我熟悉的生活时,又 不由自主地把生活中的爱情故事纳入笔端。而且在我的生活中, 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关于爱或者不爱的故事,仿佛从来都不 曾远离。 我十分佩服具有天马行空般虚构能力的作家,但我自知我 要写出好小说,还得依靠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积累中寻找故事线 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只是个故事的讲述者,而不是故事的创 造者。 这本小说集就是我常住深圳或者往返深圳的生活写照,是我 关于深圳的文学报告。 我在用我的文字,试图再现不同时期的深圳男女们的感情生活和他们在人生历程中的风花雪月。 回望公元 1979 年末,“两万工程兵”作为最早参加深圳经济 特区建设的有生力量,已经陆续进驻深圳并在深圳的东南西北无 数个施工点上“大干快上”。在这支即将摘掉领章帽徽、集体转 业并安家深圳的部队里,就有我转业前,在担任连队文书时所在 部队的 100 多个战友。 此前大约半年前,我因升任团部政治处新闻报道员,而与战 友们分别于湖南郴州。我到团部位于北京的指挥所报到上班,他 们则直接南下进入深圳,且在莲花山(今邓小平铜像所在公园) 安营扎寨。 我那时浅薄无比。仅仅因为工作关系进入北京而心里充满了 优越感,心想全连战友离开湖南后,去了远离省城广州的深圳, 而我却可以在周末假期随便到天安门广场散步……我是何等的幸 运啊! 可是北京户口对于那个时期想转业后进京落户的基建工程兵 部队官兵来说,几乎是大门紧闭。当深圳早已拥抱“两万工程兵” 官兵时,我却不得不在 1984 年春,流着眼泪离开北京,转而通 过我们同一部队另外一个团一道转业落户西安。 即便如此,当时我在相比深圳的战友们时,心里仍然残存着 一点优越感。我在心里嘀咕:“我在省会西安呢!总比那个宝安 县(深圳前身)强一些吧!” 可是同年年底,我因出差去湛江,返回西安途经广州时,却 因春运期间火车票紧张,而不得不滞留广州。无奈之际,我临时起意,就搭车到了深圳参观游览。 巧的是,在没有手机、没有座机电话号码、没有通信地址的 情况下,我因给《深圳特区报》送自己临时写的稿件而路过红岭 路时,碰到了我们连的战友郑开金。郑当即带我到红岭路建设集 团公司(“两万工程兵”转业后单位名称)家属院,我们连指导 员李国栋就住在那里。 正值春节,指导员家里热闹非凡,酒肉管饱。我在连首长 的家宴上,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战友们,他们个个意气风发,志 得意满。他们这时早已不屑于比较什么城市的大小,而更看重 眼前这块热土充满着希望与活力。我联想到几天来看到的处处 有高楼、处处是工地的繁荣景象,便对指导员表示——“我想 调入深圳工作!” 李国栋指导员时任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公司政工人事部主 任,他端着酒杯笑着说:“欢迎文书归队!” 人生最缺是贵人。我却轻易遇到了。当我当兵还不到一年 时,就遇到部队扩编。新任指导员李国栋当即选调我当了文书, 于是 19 岁的我成为在连首长身边工作的人,半年后我就入了党。 随后又在指导员的支持下,上调到团部,成为令全团战友羡慕的 机关兵。之后两年半时间,我能顺利提干,成为军官,显然与我 在连队打下的良好基础分不开。 而当我想调入深圳时,竟然又巧遇李国栋主任(指导员这一 时期的职务)正在为物业集团公司招兵买马。 于是几个月后的 1985 年 4 月,我便如愿调离西安,从而成为一个正牌的深圳人、一个深圳的未婚青年。 那一年,物业集团开发建设的“华夏第一楼”——高达 53 层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主体工程刚刚完成,铅合金玻璃幕墙工程 与室内装修工程正在紧张地进行中。 我先是担任集团公司的党办秘书,三年后外派到集团所属的 海南新达开发总公司担任贸易部经理、总经理,直至 1995 年辞 职“下海”。 我下海的原因之一,是想从海南返回到深圳,想让家庭生活 回到正常轨道,随后我安居在深圳市福田区白沙岭百花二路的南 天花园小区。这处宽大的住宅是物业集团分配给我且在房改完成 之后,成为我的私人财产。 有人说,拥有产权的房子,才是安家的房子,也才是安心之 所。我深以为然。我拿着“44030……”开头的身份证,在这所 属于自己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我心里早已认定:我是深圳人! 可当时间来到 1998 年末,我却不得不因夫人工作调动的原 因而举家迁居北京。这时,我蓦然感到,我当深圳人的历史,至 此便不得不暂时画上句号了。 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多年?这个生命历程长乎短乎?一 个人从 20 多岁到 30 多岁,这个年龄段重要与否?一个人从未婚、 离婚,又到再婚、生子的 10 多年,会有什么样的情感经历与心 路历程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正面说是丰富,负面讲是复杂。 作为曾经的部队新闻干事,亦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在深圳、在海南的工作阶段,于繁忙的商务生活间隙,仍然放不下 写作。写作好像成了我的兼职工作。这期间,我写了三部中篇小 说——《阿美娜》和《能够说什么》发表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的深圳《特区文学》;《走过泥泞》发表在 90 年代初的海南《天涯》; 《阿美娜》在香港《文汇报》被冠之以“内地女性问题小说”连载, 亦被收入特区文学《百期精选》一书;《能够说什么》被深圳出 版社收入《优秀中篇小说集》。我凭借上述作品先后加入了广东 作家协会、海南作家协会。 著名导演郭宝昌(电视连续剧《大宅门》的导演、编剧)就 职于深圳影业公司期间,曾约我到他位于滨河新村的家里,讨论 《阿美娜》的影视改编事宜,后因投资方的人事变化而放弃。想 来难免令人遗憾。 这之后更令我惭愧的是,我被商海中的一波又一波巨浪打 得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热情与冷静,写的东西极少。直至岁月推着 我进入花甲之龄,我猛一激灵,这才发现,原来提笔写作,才是 我的安心之道。我于是又匆匆提起笔来,并且用新出版散文集之 举,敲开了北京作协的大门,之后又担任了中国林业生态作家协 会的理事。 我好像从商人的岗位上退休了,又走上了作家的岗位。 如果单从时间上说,经商这些年,我是耽误了写作的。但当 我的散文集《我的商海往事》受到读者欢迎时,我反倒觉得商务 生活未尝不是我文学生活的必要准备。我有理由认为,商海是我 的文学故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我正因为有了当年的“弃文从商”,才有了我的独特的生活积累,今天反过来“转身从文”时, 我才能感觉到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写,才有了“置身于故事之中” 的写作角度。 我知道,我的文学才情是有限的。因此,我更愿意在非虚构 写作的道路上跋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之前写的中篇和新近完成的中短篇,都 是非虚构写作的尝试。 我理解的非虚构其实不是不虚构,只是我小说中的人物几乎 都有生活原型,我是通过真实的原型与虚构的细节来完成人物塑 造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以前的三篇中篇小说,反映了我 年轻时的情感生活,而后来创作的小说,则是我看到的身边人的 情感生活。 我绝对想不到当年《文汇报》在连载《阿美娜》时,把它归 类为“内地女性问题小说”。 当我有意将过去的三篇旧作结集出版时,我才发觉内容太单 薄了,且由于是“太旧的旧作”,小说人物无不是生活在没有手 机的年代,他们的思想意识与爱情观念,与今天的深圳人,已经 存在明显的代际之差。于是,我连忙写了部分新作。这样,《那 时深圳爱情》似乎才像一席菜。 《人民文学》原副主编宁小龄先生的住所与我居住的小区很 近,我们心理上互认对方为邻居。我把几篇新作交宁兄求教,他给我手书了两页半 A4 纸。有肯定,有批评,有建议,令我印象 深刻的一句话是:“你的小说提出了不少婚姻问题,值得探讨。” 在我看来, 无论是之前的“女性问题”,还是现在的“婚姻问 题”,我想,它们其实都是情感问题。而情感问题便是最大的人 性问题。 但我知道,好的小说并不是为了提出问题的,小说的使命是 人物,是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愿把这一本小说的评价,交由读者朋友 来完成。 如果要让我对自己的作品排一个优劣顺序,我好像会按完成 的时间顺序,倒着数,即,第一是《人面桃花》,第二是《高成 就爱情史》。当然,这只是作者的偏见而已。 2023 年 11 月 18 日 于向阳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