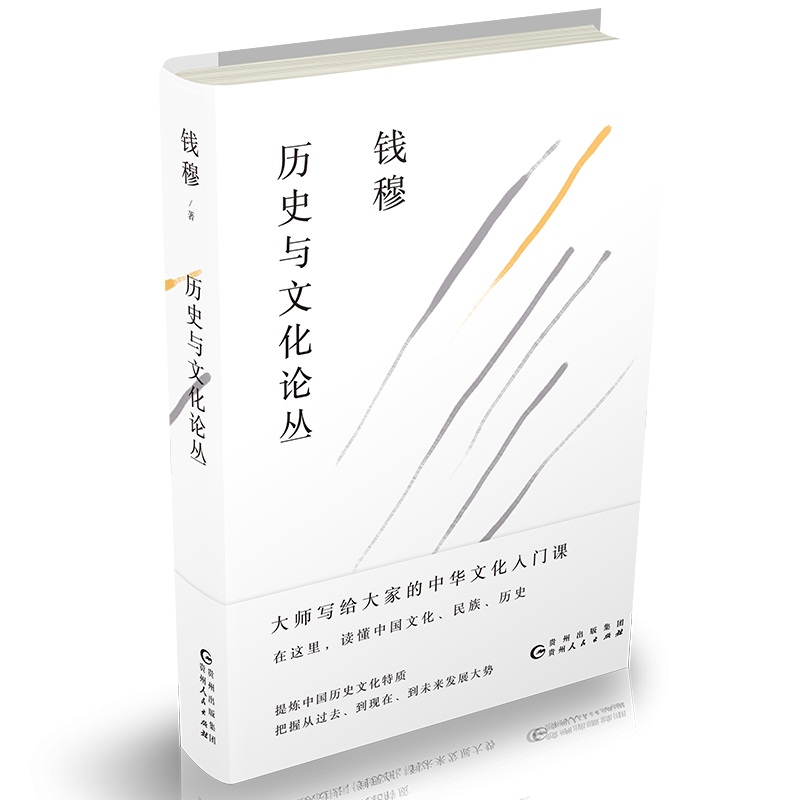
出版社: 贵州人民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7.40
折扣购买: 历史与文化论丛
ISBN: 9787221152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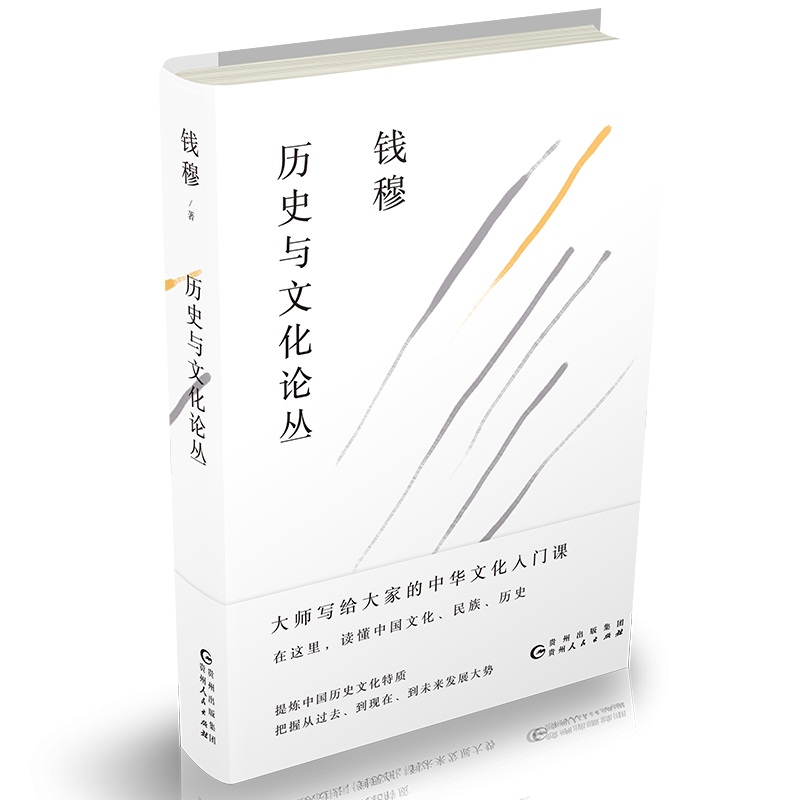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1912年起担任小学教师,历中学而至大学。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教职。1949年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先生学识博达,一生著述八十多部,被誉为“一代通儒”。
文化三阶层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整全体,我们要研究此一整全体,必先将此复多的、连绵的整全体试先加以分剖。分剖的方法,也可有两大步骤。一是把此多方面的人生试先加以分类。二是把此长时期的人生试先加以分段。前者是对人类文化加以一种横剖面的研究,亦可说是平面的研究。后者是对人类文化一种纵割性的研究,亦可说是直线的研究。但人类文化同时又是时空交融的一个整全体,因此我们的分类分段,横剖纵割,又盼能两者配合。划分段落与分别部门这两工作,我们又盼它能有一较自然之联系。 (一) 我们本此意向,暂把人生分为三大类。第一是物质的人生, 亦可说是自然的人生,或经济的人生。一切衣食住行,凡属物质方面者均归此类。人生本身即是一自然,人生不能脱离自然,人生不能不依赖物质之支持。此是人类生活最先必经的一个阶段, 我们称之为文化第一阶层。没有此最先第一阶层,便将不可能有此下各阶层。 然而人生是多方面互相融摄的一个整全体,所谓物质人生中,早已含有很多精神的成分。若人类没有欲望,没有智慧,没有趣味爱好,没有内心精神方面种种活动参加,也将不会有衣食住行一切物质创造。因此衣食住行只可说是较多依赖于物质部分,而并非纯物质的;只可说是较接近于自然生活,而非纯自然的。只要我们称之为人生的,便已归属到人文界与精神界,绝不能再是纯自然、纯物质的。此层须特别说明。即就环绕我们的自然界而言,如此山川田野、草木禽兽、风景气象,试问洪荒时代的自然界何尝便如此?这里面已经有几十万年代的人类精神之不断贯注,不断经营,不断改造,不断要求,而始形成此刻之所谓自然。这早已是人文化的自然,而非未经人文洗炼以前之真自然。一切物世界里面,早有人类心世界之融入。此所谓物质人生,则只就其全部人生中之较更偏近于物质方面者而言。 其次是社会的人生,或称政治的人生、集团的人生,这是第二阶段的人生,我们称之为文化第二阶层。在第一阶层里,人只面对着物世界,全都是从人对物的关系而发生。在第二阶层里,人面对着人,这些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生活不先经第一阶层,将无法有第二阶层。但人类生活经历了某一段时期之相当演进,必然会从第一阶层跃进第二阶层。第一阶层只是人在物世界里过生活,待其跃进第二阶层,才开始在人世界里过生活。此如家庭生活、国家法律、民族风习,全属此一阶层。 最后才到达人生之第三阶层,我们可称之为精神的人生或说是心理的人生。此一阶层的人生,全属于观念的、理性的、趣味的。如宗教人生、道德人生、文学人生、艺术人生皆是。此是一种历史性的、超时代性的人生,此是一种可以长期保留、长期存在的人生。孔子、耶稣时代一切物质生活,一切政治、社会、法律、习惯、风俗,到今全归消失,不存在了。在他们当时第一、第二阶层的人生,到今已全变质,但孔子、耶稣对人生的理想与信仰,观念与教训,凡属其内心精神方面者,却依然留存不灭, 而且千古常新。这是一种心的世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只可用你的心灵来直接接触的世界。 人生必须面对三个世界。第一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物世界, 第二阶层里的人生面对着人世界,须到第三阶层里的人生,才始面对心世界。面对物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物质人生。面对人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社会人生。面对心世界的,我们称之为精神人生。我们把人类全部生活划分为三大类,而又恰恰配合上人文演进的三段落、三时期,因此我们说文化有上述之三阶层。 此三阶层,把个人生活的经验来看,也甚符合。婴孩出生便哭,那时他只见光受惊,骤觉寒冷而不安,饿了倦了,想吃想睡,都会哭。那时他所面对的,完全是物世界。稍后慢慢懂得谁是他的父母兄姊,又懂得谁是他的熟人亲近,这才逐步踏进了人世界。更后渐受教育,懂种种心理,自己的,别人的,大至国家民族的观念,远至几千年前的历史,以及宗教、文学、艺术种种智识,这才闯进了心世界。人生三阶段,循序前进,个人如此, 整个人生也如此,并无大分别。 (二) 上述文化三阶层,每一阶层,都各有其独特自有之意义与价值。每一阶层,都各有其本身所求完成之任务与目的。而且必由第一阶层才始孕育出第二阶层,亦必由第二阶层才始孕育出第三阶层。第二阶层必建立于第一阶层之上,虽已超越了第一阶层,但同时仍必包涵第一阶层。第三阶层之于第二阶层亦然。现在先简率言之,第一阶层之特有目的在求生存,即求生命之存在。第二阶层之特有目的在求安乐,即求存在之安乐。存在不一定安乐,而求安乐,必先求存在。于存在中孕育出安乐,安乐已超越存在,而同时又包涵着存在。第三阶层在求崇高,在求安乐之崇高。安乐不一定崇高,崇高已超越安乐,但必由安乐中孕育而有,亦必包涵安乐,乃始见其崇高之真意义与真价值。 物质人生,在求生命之存在。食求饱,衣求暖,饱暖在求生存。生存即是其最高目的,饱暖只是达到此目的之手段。饱了暖了,失却生存,饱暖即无意义。若使不饱不暖亦可生存,饱暖亦无价值。物质人生全如此。 但一进到社会人生,意义又别。孟子说:“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俱指第一阶层之人生而言。饮食只求自己生命之存在,男女则求自己生命之绵延,不独人类如此,禽兽亦如此,此俱属自然生活。在自然生活中,雌雄相遇,其视对方,只如一物,求能满足我自然的生存而止。但人文进化,不肯老停留在一男一女的阶段上,于是由一男一女转进为一夫一妇,此一转进便踏上了文化第二阶层。试问若仅求生命绵延,雌雄男女交媾配合,早够了,何必又在一男一女之上再来一个一夫一妇的婚姻制度呢?可见夫妇婚姻,其目的已并不专在求生命之绵延,而必在生命绵延之外之上另增了新要求,另添了新意义。猫与狗只求生命延续,不需要夫妇与家庭。人类偏要夫妇家庭, 可见其意义已不尽在生命延续,而另有所求。 人必感到只此一男一女,心终不安不乐,必待此一男一女成为一夫一妇,此心始安始乐。一男一女的相互对方,只是满足我自己性欲之一工具一物。一夫一妇的关系则不同了,把对方当作自己一样看待,我是一个人,对方同样是个人。我是一个我,对方同样是一个我。满足了自己,还同样希望满足对方。非如此则吾心不安不乐,因此人生进入了第二阶层。所面对的已不是物世界,而是人世界。不仅要求自我生命之存在,抑且还求其生命之安乐。而自己之安乐,则有待与对方、与我相类的别人之生命的共鸣。 鲁滨孙漂流荒岛的故事,人人知道。人常说:“鲁滨孙只身在孤岛上,生活何等不方便,不舒服,因此人类生活应该不脱离社会大群。”这一说法,似乎把第二阶层的人生,转化成第一阶层人生之手段。试问若使科学昌明,把鲁滨孙依旧安置在孤岛上,想吃便有吃,想穿便有穿,一切生活绝不成问题,鲁滨孙心里是否即感满足,是否感得已安已乐,可不要再回入社会人群呢?可见第二阶层的人生,并非即是第一阶层人生中之一种手段,而实另有其较第一阶层更高的目标与理想。 人类不仅要求生命之存在与继续,而且要求在此存在与继续中得有一种安乐的心情。安乐是人世界中事。若根本无存在,自无安乐可言。故安乐必建筑在存在之上,又必包涵存在在内,但其自身意义实已超越于存在之外之上。今之所求,乃既存在,又安乐。只有第二阶层可以包涵第一阶层,生命安乐当然必存在。而第一阶层则包涵不到第二阶层,因生命存在不一定就安乐。因此第二阶层可以决定第一阶层,而第一阶层则断不能决定第二阶层。一夫一妇包涵了一男一女,但一男一女不包涵一夫一妇,因一男一女不一定便是一夫一妇。猫与狗只有雌雄,并无夫妇。夫妇建筑在男女基础上,但已超越了男女基础,而仍包涵男女基础,此乃人类文化阶层演进之大体轨范。 一男一女是自然人生,那是原人时代的人生。一夫一妇,始是社会人生,但社会人生,亦只是人与人的生活,而非心与心的生活。现在在此一男一女一夫一妇之间,更加进一层更纯洁、更高贵的爱情,而形成一对更理想的配合,那才是文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男女结合与夫妇婚姻,这才又踏进了人生第三阶层,即精神的人生。上文已屡说过,人生本是融凝一体,不可分割的。即在一男一女异性相追逐的时候,早已有情爱之流露,但此种情爱是粗浅的、短暂的、性的要求满足,此种粗浅短暂的相爱之情亦即消失,归于无有。夫妇结合,此种爱情即进了一级,但夫妇只是夫妇,不一定具有圆满的爱情,不一定相当于文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理想所标指。人类文化必然要演进到第三阶层, 才始有文学,才始有艺术,才始有道德,才始有更崇高的理想。我们所希望者,乃在要有文学的、艺术的、道德的夫妇,比较我们仅要求法律的、社会的夫妇更进一层。没有第一、第二阶层, 不可能有第三阶层;但第三阶层虽孕育于第一、第二阶层,却已超越了第一、第二阶层,但仍包涵第一、第二阶层。 第一阶层之人生,在求存在,第二阶层在求安乐,第三阶层则在求崇高,崇高已超越了安乐,但仍包涵安乐。第三阶层之人生,在求既安乐又崇高之存在。它所面对者,已不仅是当面觌体的物世界与人世界,而更高深更广大,上下古今,深入到人类内心所共有的一些祈望与要求上。文学、艺术、宗教、道德都从此种要求上植根发芽,开花结实。孔子之“栖栖惶惶,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一番传道救世精神,耶稣钉死十字架上的一番牺牲博爱精神,他们所面对者,已不尽于当前的一个社会与人群,而已面对着从有人类,上下古今的一种人心内在之共同要求。他们亦感得我非如此则心终不安不乐,然而他们所求, 实已更高出于普通所谓安乐之上,但亦绝不是不安不乐。此心不安不乐,不算得是崇高,而求崇高之不尽于求安乐,亦正如求安乐之不尽于求存在。安乐中涵有存在,崇高中涵有安乐, 文化阶层一步步提高,人生意义与价值一步步向上。下一阶层之目的,只成为上一阶层之手段。只有目的决定手段,不能由手段决定目的。因此存在不一定安乐,安乐不一定崇高,只有崇高的必然安乐,必然存在。 固然没有存在,哪有安乐崇高可言,然而此等只是一种反面、消极的决定,并非正面、积极性的决定。没有第一阶层,不可能有第二阶层,此是第一阶层之消极性作用,亦即其消极性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但有了第一阶层,不一定必然有第二、第三阶层,但有了第二阶层,则必然融摄有第一阶层。有了第三阶层,必然融摄有第二阶层。这一个人类文化三阶层递进递高、递次广大融摄的通律,可以用作衡量、批判人类一切文化意义与价值之基本标准。 钱穆,与吕思勉、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四大家”之一,20世纪最有中国情怀的史学家,黄仁宇、顾颉刚、余英时等人同声推崇的国学大师。 其人其时身处历史低谷,却对中华文明保持顶级崇拜与自信。抵御“历史虚无”,反击“国民劣根性”,一场澎湃热烈的思想盛宴,一次提气解惑的文化旅途。 感性与理性交融,严谨与激情并行,历史追溯与现实关怀俱备。理解国学的极佳入门书,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不二之选。 典雅装帧,考究用纸,尽显经典沉淀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