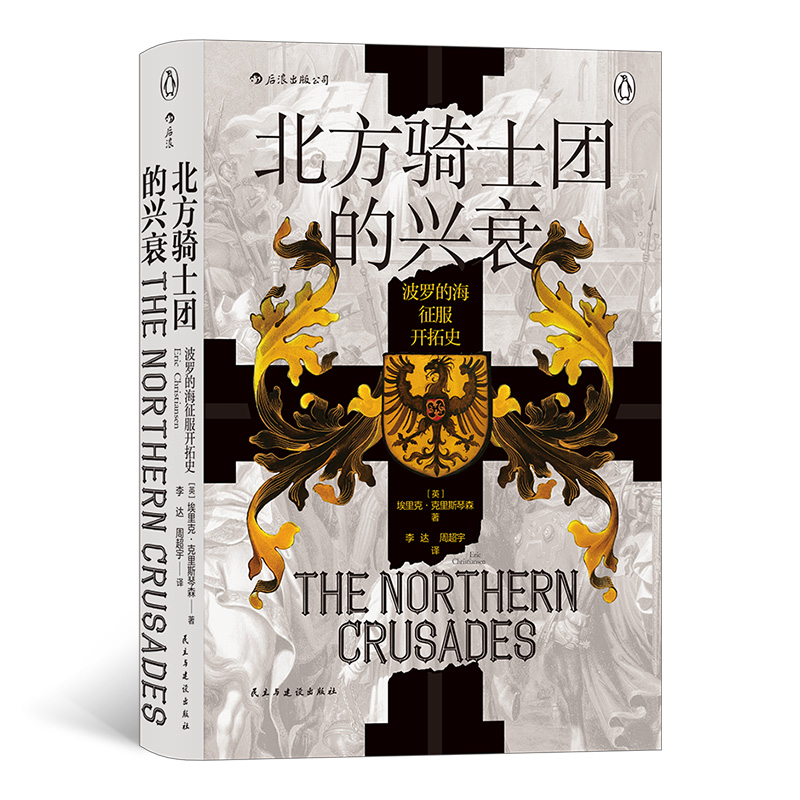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原售价: 82.00
折扣价: 52.50
折扣购买: 汗青堂086:北方骑士团的兴衰:波罗的海征服开拓史
ISBN: 97875139340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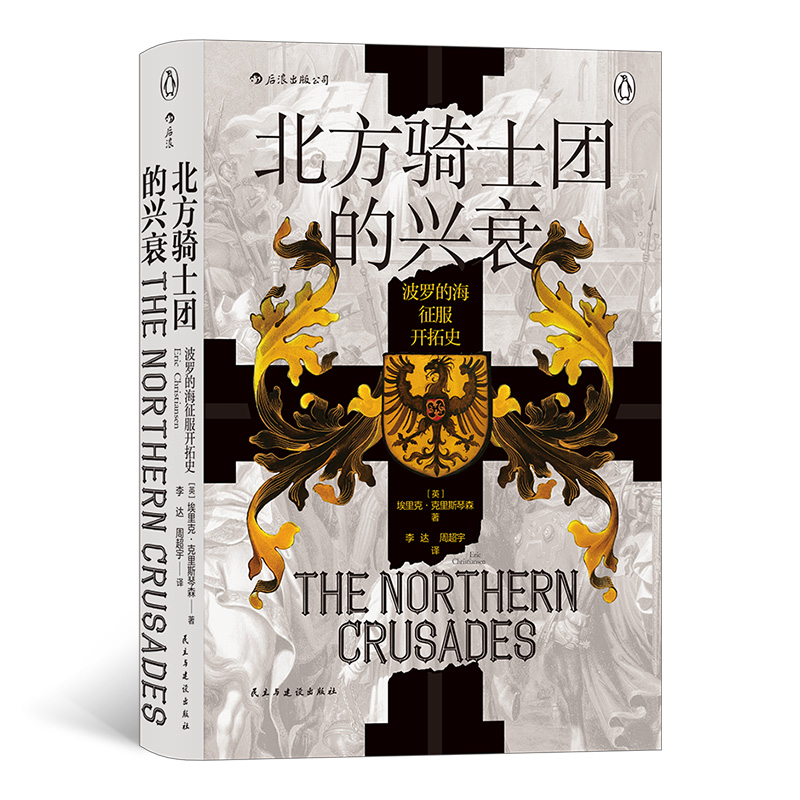
著者简介 埃里克·克里斯琴森(Eric Christiansen),牛津大学新学院荣休研究员,主要研究中世纪的欧洲北部历史,曾在伦敦、哥本哈根和佛罗里达讲学。 译者简介 李达,浙江大学毕业,中世纪军事历史爱好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世纪军事史、拜占庭帝国制度史、中世纪东地中海-黑海交流史等。曾自译数本军事典籍与编年史。 周超宇,山东大学硕士毕业,参与翻译工作数年,中世纪欧洲历史爱好者。
坦能堡之战及其后续,1409—1414 征服了萨莫吉希亚的大团长康拉德·冯·永京根,在1407年3月30日逝世。按照劳伦丘斯·布卢梅瑙的说法,他既是殉道者,也是预言者:殉道是因为尽管医生宣称他和妇女交合可以医治他的胆结石症,但他拒绝遵从医嘱,因而病逝;预言是因为他警告了自己的骑士团弟兄们,不要选他的亲兄弟乌尔里希继任大团长,因为他对波兰人的憎恶已无可救药。然而布卢梅瑙记述这些内容之时已经是 50 年之后,同时代的记述根本没有提到这两件逸事。乌尔里希当选为继任的大团长,两年后便和波兰宣战,原因并不是他厌恶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而是因为他的兄长挑唆波兰与立陶宛交战的政策已经破产了。萨莫吉希亚人开始叛乱,并得到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的支持,而瓦迪斯瓦夫则拒绝约束维陶塔斯。显然,他不打算听从条顿骑士团的命令了。1409年,入侵多布任以及他的其他领土,便是一个虽不明智但符合逻辑的手段,有望迫使维陶塔斯降服。 乌尔里希误判了形势:他并不认为维陶塔斯和瓦迪斯瓦夫会结成联军对付自己;他也希望他的盟友匈牙利国王日格蒙德(西吉斯蒙德)能够进一步积极对抗波兰。但事实上,维陶塔斯和瓦迪斯瓦夫合兵一处,集结起了比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的总兵力还多的联军;而日格蒙德收了贿赂,决定按兵不动。在九个月的停战期之后,显然立陶宛和波兰至少想要夺回库尔姆,而条顿骑士的盟友都不会提供支援,甚至利沃尼亚分团长冯·菲廷霍夫都向维陶塔斯许诺,在与他开战之前三个月会递交警告书。 1410年7月1日,瓦迪斯瓦夫和维陶塔斯在维斯瓦河畔的切尔维延斯克(Czerwinsk)会合,随后率领一支由波兰人与立陶宛人组成的征召军,由捷克人、摩拉维亚人、瓦拉几亚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组成的雇佣军支援,迅速向北进军。他们在越过普鲁士边境几英里之后,遭遇了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率领的普鲁士骑士以及十字军志愿者,双方于7月15日在坦能堡/格伦瓦尔德(Grünwald)展开决战。乌尔里希·冯·永京根显然希望圣母能够再度护佑信徒们,让他们以少胜多;但在这一天结束之时,骑士团的最高指挥部以及普鲁士的大部分部队被全部歼灭,大团长、骑士团元帅、大指挥官、司库官、其他一干指挥官和400名骑士团成员阵亡,余下的战士或者被杀,或者被俘,或者溃逃。这一战结束之后,波兰-立陶宛联军似乎就此消灭了敌人,普鲁士已经无人防守了。 然而,条顿骑士团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及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坦能堡的损失,而得到了解救。此前负责防卫东波美拉尼亚的海因里希·冯·普劳恩接手指挥余下的部队,在马林堡坚守了57天。当普鲁士主教和他们的封臣们向瓦迪斯瓦夫投降之时,冯·普劳恩拒绝谈判。他要等待恶劣天气、疫病、利沃尼亚的援军前来,又或者匈牙利国王日格蒙德出兵。9月19日,瓦迪斯瓦夫决定撤围:他的火炮没什么效果,军队之中爆发了痢疾,利沃尼亚部队调动的消息已经传来,日格蒙德也开始进攻他在西里西亚的盟友,而且他也没有资金来支付波希米亚雇佣兵的薪酬了。在返回途中,他俘虏了条顿骑士团的新任元帅米夏埃尔·库赫迈斯特·冯·施滕贝格,但乘胜夺取整个库尔默兰的机会已经不复存在了。1411年2月1日,他在托伦同意和谈,条顿骑士团保留了他们在1409年之前控制的大部分土地,仅有萨莫吉希亚交给维陶塔斯和瓦迪斯瓦夫二人终生统治。骑士团还要支付价值85万英镑的赔款——这超过了英格兰国王十年的平均收入。 条顿骑士此前也遭受过惨败,但那时,他们的敌人是多神教徒,阵亡者被视作殉道者。阵亡的骑士战友的鲜血荣耀了骑士团,也刺激其他人加入骑士团,或参与十字军。坦能堡之战若可以被看作基督教的战败,则算不上是这般的灾难,因为志愿者就会纷纷涌入普鲁士挽救危局,然而此时条顿骑士团已经很难如此宣传了。尽管他们强调瓦迪斯瓦夫取胜的军队之中有异教徒鞑靼人和教会分裂派的罗斯人,但欧洲地区并不因此而愤怒;同时代的记述称这一战为不幸的悲剧,但这场悲剧条顿骑士团也有责任。一位吕贝克的编年史家声称,条顿骑士团被上帝的意志击败,因为他们傲慢,也因为“据说他们对贫穷的臣民过于严苛”。一名英格兰的评论者的说法,被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引用,并由卡普格雷夫译出,其中提到“克拉科夫国王”请求“普鲁士人”支持他对抗萨拉森人,然而,他们却: 从他的背后发动进攻,只为了消灭他。看看他们对我们的信仰做了什么吧!他们本要奉命守卫我们的信仰,而现在他们却调转方向攻击他,要毁灭信仰!那位刚刚成为基督教之子的国王,决定要对抗这些背教者。他与他们作战,让他们溃逃,并征服了他们的所有据点,让他们遵守自己的旧法律和习俗。 乌尔里希·冯·永京根的部队之中有不少德意志十字军。在圣格奥尔格的旗帜之下,部队的成分一如既往地混杂,还有来自威斯特伐利亚、施瓦本、瑞士和莱茵兰的志愿者队伍。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对这次惨败的反应是有利于条顿骑士团的,支援部队在不久之后开始前来,由维尔茨堡主教率领。然而,非德意志的十字军,在坦能堡之战前十年就已缺乏,蒙斯特勒莱(Monstrelet)记载称,只有少数来自诺曼底、皮卡第和埃诺(Hainault)的骑士前来;而英格兰和法国在这一战之后无动于衷,足以说明条顿骑士团的国际影响力大不如前。国王亨利四世是老资格的普鲁士十字军战士,向来自称是条顿骑士团的好友,也对波兰人1410年1月的宣言嗤之以鼻,然而他突然之间不愿为被英格兰海盗抢走的普鲁士航船支付赔偿了。条顿骑士团从未如此急需一万英镑的款项,但国王认为,普鲁士有可能落入异教徒手中,自己若支付赔偿就不明智了。 一支勃艮第部队,包括吉尔贝·德·拉努瓦,在1412年出发“前往普鲁士抵抗不信神者”,并参加1413年的侵袭,与瓦迪斯瓦夫开战。然而这似乎是非德意志的十字军最后一次为条顿骑士团作战了。他们停止前来,一部分原因是英格兰与法国再度开战,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全都忙于在西欧战斗;另一部分原因是,维陶塔斯和瓦迪斯瓦夫也成功说服欧洲其他地区承认他们天主教徒的身份,他们既不是“不信神者”,也不是“萨拉森人”。人们普遍认为,未来对抗异教徒——罗斯人和鞑靼人——的十字军活动,应该由普鲁士、立陶宛和波兰共同承担;让天主教政权互相攻伐,削弱天主教世界的实力,绝对称不上功劳。因此,《托伦条约》中有一个条款规定,维陶塔斯和条顿骑士团同意他们会在未来共同进取,征服异教徒,或令其皈依。若是东欧的三个天主教强权依然保持敌对,这些就不大可能发生。 对条顿骑士团而言,这便是坦能堡之战的一个严重后果;此后他们几乎要完全依靠德意志的盟友和志愿者了。这意味着德意志王公们的意愿对他们愈发重要,特别是1414年加冕为德意志国王的西吉斯蒙德(日格蒙德)。另一个问题就是普鲁士内部的危机,当地的市民、世俗骑士和主教开始反对条顿骑士垄断政治权力的行为,但泽向条顿骑士团宣战。大团长海因里希·冯·普劳恩(1410年11月即任)试图召开一次“地区会议”(Landesrat)来安抚臣民,召集各个城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的代表和他共同商议政务,然而他真正赞同的政事是尽快反击波兰。但他麾下的指挥官、主教以及世俗封臣,都不想冒险再来一次坦能堡的惨败。他迫使他们在1413年9月发起一次短暂的征战,而后他的元帅在等级会议(Estates)的默许下将他罢免。此后,普鲁士的政府由条顿骑士团和等级会议共同管理,而双方都愈发厌恶对方。内部不和让波兰人得到了成功入侵的机会。 瓦迪斯瓦夫同意由西吉斯蒙德来裁决他和条顿骑士团的重大分歧。但1414年,这位国王的“布达判决”(Award of Buda)命令波兰承认《托伦条约》中的条款,保持和平,放弃声索普鲁士境内那些古老的波兰领土,于是波兰决定再度开战。大军向北进军,围攻德尔文察河畔的施特拉斯堡;新任大团长米夏埃尔·库赫迈斯特·冯·施滕贝格切断了瓦迪斯瓦夫的补给线,波兰人的战争沦为“饥饿之战”。教宗约翰二十三世的使节前来安排停战,入侵军就此撤走。 新任大团长库赫迈斯特高大壮硕,颇有学识,也擅长政治手腕,相比之前两位冲动的英雄人物,他更适合此时的条顿骑士团。1414年的战争让他确信,如果普鲁士想要免于被波兰征服,那他们就必须唤起欧洲其他地区的十字军本性,重新拉回权势的平衡。教宗约翰出于自身利益,自然不会批准对信仰天主教的波兰发动公开的十字军行动。西吉斯蒙德以及其他处境良好的德意志领主,也不肯冒险公开为条顿骑士团的利益而战。然而1414年11月,天主教欧洲的当权者和高阶教士集聚在康斯坦茨,讨论对抗胡斯派异端、结束教廷分立与改革教会的事宜;如果此次大公会议被说服确认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的主权,并重申支持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使命,那么瓦迪斯瓦夫就无法坚持他的权利主张了。一次成功的宣传将能让条顿骑士团避免一场他们无力取胜的战争。1414年12月,条顿骑士团的代表团在德意志分团长(Deutschmeister)和里加大主教的率领下来到康斯坦茨,随行的有11辆车,以及条顿骑士团大团长的代理人彼得·沃尔姆迪特(Peter Wormditt)的申诉书。 在波罗的海地区,条顿骑士团的开拓以及北欧各国的十字军运动,虽不如在圣地的十字军那么盛大壮烈,但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 本书不仅梳理了波罗的海和北欧地区的地理环境、诸民族的社会状况,也论述了条顿骑士团和十字军在这片新地域的军事活动和殖民管理,展现了西欧天主教文化在新地域的传布、维持、适应和发展,兼具人类学和历史学价值。 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有清醒公正的认识,不避骑士团的罪恶,也不忘文明传衍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