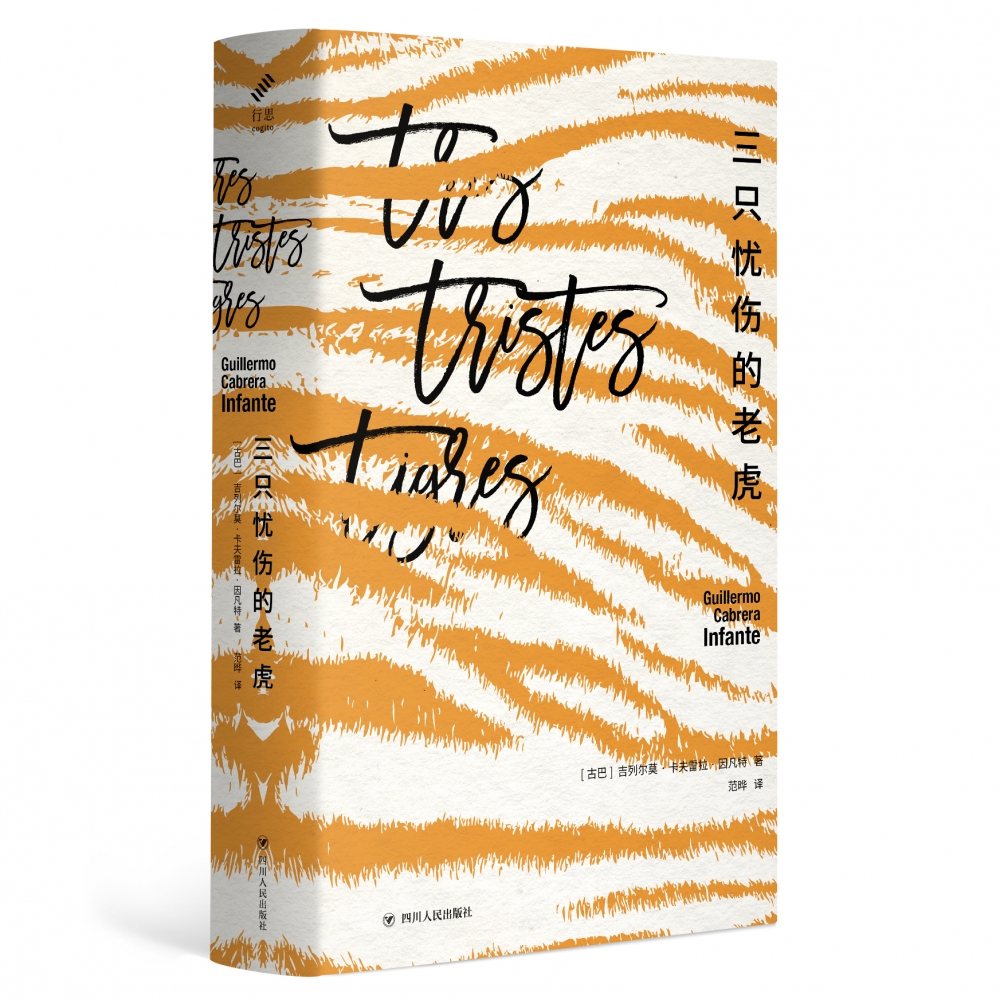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人民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三只忧伤的老虎
ISBN: 97872201236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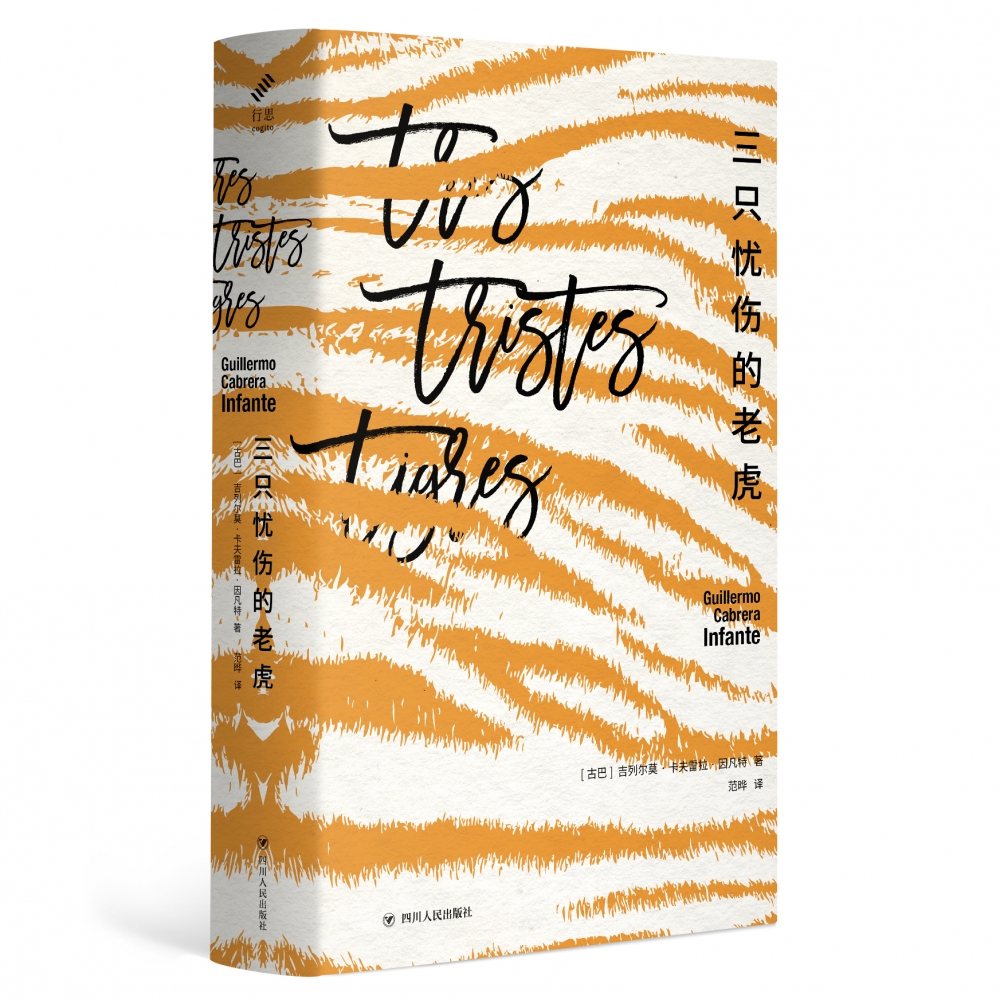
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凡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1929—2005),古巴国宝级作家,拉丁美洲第二代新小说家代表人物,于1997年获得塞万提斯文学奖。早年从事电影评论工作,1960年开始文学创作,小说《热带黎明景色》获西班牙\\\\\\\\\\\\\\\\\\\\\\\\\\\\\\\"简明丛书奖\\\\\\\\\\\\\\\\\\\\\\\\\\\\\\\"。1965年流亡国外,后加入英国国籍、定居伦敦。代表作有《三只忧伤的老虎》《因凡特的哈瓦那》《神圣的烟草》等。 译者简介: 范晔,七七年七月生,象寄门下临深履薄堂仓皇右使。猫科动物之友。任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译有《百年孤独》《万火归一》《致未来的诗人》《未知大学》等西语文学作品数种。
阿莱霍·卡彭铁尔[《日西坠》(El ocaso)戏仿卡彭铁尔的名篇《追袭日》(El acoso)。] 日西坠[忠告:译者先生,你可以把标题译作“老人与海上日落”——原注] 应当在Pavane pour une infante défuncte[法文,意为《悼亡故公主的帕凡舞曲》(1899),法国作曲家拉威尔所作。]一曲持续的时间内读完,每分钟33转。 一 L?importanza del mio compito non me impede di fare molti sbagli…[意大利文,意为“我使命的重要性并未阻止我犯下许多错误”。]老人凝神停在因打嗝的折磨而中断的那句话,心想道:“我于对话有一种神圣的恐惧”又在头脑中把它译成法语来听听音韵如何,在他可敬的,受尊敬的,令人起敬的面容上勾勒出一个甘草汁里的苦笑,或许因为窗户敞开,新漆过的百叶窗,紧闭的百叶帘,高处的横撑在安特卫普舶来的轻盈的麦思林纱帘幔后依稀可见,金黄的合页,同样泛黄的青铜色灯饰,金属的乌光与木件惊人的白色相辉映,镶板,插销和胡桃木的碰口条也被亚麻籽油漆刷得发白,宽石凳上摆满花盆,盛土的陶盆或瓷罐种着头巾百合或地肤,但他没有在皎皎的辉光前后看到花朵因为没有种在窗台而是在红砖阳台上,离开挡雨檐带纹路的遮庇,曝露在晌午,就像亚他拿西娅,熟谙民间俗语的女侍所说,出人意料的甜蜜韵律经过光辉的空洞到来。那音乐的来处比花腔袅袅流溢故乡风情的留声机更遥远,不是高音笛不是诗琴也不是大扬琴,比韦拉琴,埃及叉铃,维金纳琴[维金纳琴(virginal),十六、十七世纪的一种古钢琴类乐器,多由少女(virgin)演奏,故名。],三弦琴,笛号,西塔拉琴或索尔特里琴,而是一种巴拉莱卡琴[巴拉莱卡琴(balalaika),似吉他,又称俄罗斯三角琴。],轮弹中呈现泰勒明电子琴[泰勒明电子琴(theremín)由俄国工程师泰勒明(Leo Theremin, 1896-1993)发明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被称为世界上唯一不需要身体接触的乐器。]的声响,基辅[基辅(Kiev)乌克兰首都。]风格,“基辅斯基·泰勒明那”,带来乌克兰生涯的回忆。“我于对话有一种神圣的恐惧”,他说,用法语,同时想着如果用英语说听来如何。那男人,两个人中更年轻的那个,因为有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人,相对而言必定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年轻,就是后者看着他,此刻笑着,流露出难称自然的狂喜,这句话注定日后被引用。那老人,因为必得有个老人,两个人在那间铺着伊尔库茨克长毛绒地毯的房间里,其中一个必然更老一些,因为岁月与记忆的重负,就是他向后上方望着,看着另一个人在透视中大张着心腹门生的巨口构成视觉的auri sectio,[拉丁文,意为“黄金分割”。]看他做笔记的同时,自己也在头脑中记录,嘴唇(两片),颚,后柱,悬雍垂,咽部,扁桃体(或其空洞,因青春期扁桃腺炎的缘故已被摘除),政治上赤红的舌头和牙齿(将近三十二颗),名副其实的牙齿分布于颌下部和上部,切牙,尖牙,前臼齿,臼齿和智齿,此时还在笑,除了追随者的谄媚之外并无其它动机,在周边的湿润中他看见软腭,缝际,悬雍垂(又一次),咽部,软腭前柱,又是舌头(或另一条?),扁桃腺空穴和软腭后柱,在齿科学的疲惫中转回书本。那年轻人,因为他是两人中更年轻的一个,两人所望着的那部煌煌大作在可憎的和被憎恶的大师拿在手中,在愤懑的视网膜上记录以下事物:衬页,书脊,封皮,书名人名;烫金,书背,皮脊,装订线,花饰,印花标签,堵头布,布护封,纸护封,印张缝装或纸沓,上切口,下切口,书口,插图,天头,边白,腔背,外封,腰封,并向书的内文扫了一眼。现在他把注意力从装帧艺术、书目文献、书籍命名法上收回,转向在热浪肆虐于高原的热带伏天里还一丝不苟地扣紧的大衣之下,精心剪裁的上装之侧,用手肘和前臂比量小快斧白柚木抛光短柄尽头的锋锐利刃。他的目光从书籍转向白发苍苍的高贵头颅,思考如何刺穿头皮,枕骨并穿过脑膜(a,硬脑脊膜;b,蛛网膜;c,软脑脊膜)破开大脑,刺透小脑并有可能抵达延髓,一切都取决于起初的力量,足以改变弑人惯性的动量。“我于对话有一种神圣的恐惧”,老人又一次说道,这一回用俄语,但同时想着如果用德语听来如何。这句回奏曲式的话激发了他敲击的欲望。 二 他扔掉用玉米纸卷的烟因为无法解释地带有童年玉米糊的味道,餐后玉米布丁,圣地亚哥玉米粽塔悠悠的味道,他看着那发白的发射物如何蓦地落在垂直粗重的铁质多面体组成的花饰栅栏侧畔,那些铁条在顶端盘织出巴罗克的精美,化作对称的倒三角形,图形诗的线条和剔透的随机边饰。栅门是由曲柄,滑轮,钢缆,弹簧,转栏,螺栓,滑车,齿条,轴承,栓孔,主轮,齿轮,凹槽组成,以及最终,由轮值门卫的手偶尔启动,只需以他男中音的嗓音吟诵出那个简单易记的暗号: Queste parole di colore oscuro vid?io scritte al sommo d?una porta; per ch’io: “Maesto il senso lor m?e duro”[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歌: “我看到这些文字色彩如此黝暗, 阴森森地写在一扇城门的上边; 我于是说:“老师啊!这些文字的意思令我毛骨悚然”。(黄文捷译)] 他为自己精妙的意大利语发音感到欣慰,以格里高利式的挽歌风,朗诵腔从唇间流淌而出,但那水乳交融于但丁式terza rima [意大利文,意为“三行体”(即《神曲》中所用的诗体, 三行为一节, 每节的第二行与下一节的第一、三行押韵, 如:aba, bcb, cdc)。]的微笑却即刻消亡在看门人回复的瞬间,后者以完美的复古版托斯卡纳方言悠然唱响冥界之歌: “Qui si convien lasciare ogni sospetto; ogni viltá convien che qui sia morta Noi siam venutti al loco ov?io t?ho detto che tu vendrai le genti dolorose, c?hanno perdutto il ben de lo?nteletto.” [意大利文,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歌: “来到这里就该丢掉一切疑惧; 在这里必须消除任何怯懦情绪。 我们已来到我曾对你说过的那个地方, 在这里你将看到一些鬼魂在哀恸凄伤, 因为他们已丧失了心智之善。” (据黄文捷译本)] 此刻他只盼望这些原始的隐秘的起重机械能尽快吊起以猬集的尖矛插入钢筋混凝土预制件的铁锈斑驳的大门。他走过海岸卵石铺成并以火山岩毛石为路沿石的二裂性小径,向赫然在目的威严的chateu-fort 望去。他看见建筑各个立面形成风格的狂热杂糅,布拉曼特和维特鲁波埃,与埃雷拉和丘里格拉[布拉曼特(Donato d’Angelo Bramante, 1443-151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建筑师和画家,米开朗基罗的竞争对手;维特鲁波埃(Vitrubio),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建筑师;埃雷拉(Juan de Herrera,1530-1597)西班牙建筑师和数学家,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的代表人物;丘里格拉(Churriguera)西班牙建筑师家族,此处指18世纪前期的西班牙巴洛克建筑装饰风格。]争夺主导,早期银匠风与晚期巴罗克混融一色,山墙看似古典三角,希腊式或锐角式,实则是无聊的猜谜游戏,因为门廊的尖端根本不是三角形,而在柱顶楣构的若干部分,幕墙和柱顶过梁之间,他察觉到雕带并在左右檐有侧拱支撑着加泰罗尼亚式拱顶仿佛空洞的教堂地下室,虽然挑檐带显示出至少具备审美方面的功用,但还是令他非常担心拱腹内弧面会使拱楔块引发不可预测的玄思。此处不能不提及上隅撑,其突出的扶壁看似经受了过度的线脚雕划,让他想到浓缩洛可可精华的华丽托饰。然而,那三个明显不对称的尖穹隆是怎么回事:一个等边形一个浮夸风还有一个摩尔式?就是说这些侧剖面是四分之一圆的凸线脚,本身是椭圆?会不会成为更多偏离的枢轴?堪称奇特,抑或悖论式的主立面建造模式,因为线脚圆饰并非像我们所有人初看上去那样呈凹面,从其四分之一圆的侧剖面即可辨认,而是消解在边界处并在升至柱头时采用离心圆,而在柱头以下构成某种形式错谬——突然间fa?ade[法文,意为“立面,建筑物外观”。]呈现为病态的柱式大全:爱奥尼亚柱式,科林斯柱式,多立克柱式,多立克爱奥尼亚柱式,所罗门柱式,底比斯柱式,并且在柱头和柱础之间,柱身或柱体奇怪地延伸,我们的访客惊异地发现柱础位于柱基和下檐口之间,临近柱墩而非位于雕带和柱顶过梁之间,就像之前的访客赞颂这片异国土地上的大匠大师时所说的。关键之处,很奇怪,关键在于用作柱头的石材——而就在这一刻他知道自己走在正确的路上,并未舛误,因为这里出现了期待中的红紫色柱端环带,斑岩柱顶过梁,以及柱头与柱身连接处的chartreuse[法文,意为“察吐士酒的淡黄绿色”。]配洋红色凹纹反圆线。这里便是他与历史宿命的相遇点,他感到的不是血浆而是水银在外周动脉和副动脉中奔涌循环。他来到叠覆着过剩齿状饰的入口,垂挂有花帘布和细绳条起到防雨罩的功用,决定叫门。在此之前他看了一眼那值得纪念的门扉,上面已经无须刻上铭文:“Per me si va ne la cittá dolente…lasciate[意大利文,同引自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三歌:“通过我进入痛苦之城……抛弃(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由此进入的人)”。], etc.” 三 奇怪的门,他险些在心里说出来,同支脚,属于古典框架,却用的是石英,长石和云母,这些元素合在一起,他知道就是构成花岗岩的成分,那些门扇如果不是钢的他会认为是铸铁,附带的保洁护板盖住了本应是锁眼的地方,好在扣环,青铜制,恰好在它应在的位置:在门框上,隔开上下嵌板,引向三处同样金黄色的铰链之一。他没有敲门。何必呢?假若要敲的话则有必要带上铁护手。 门开了,估计是魔法眼或光电管的作用,他走进去,在过梁下迈过门槛,毫无困难亦无惊异。但当沉重的大门在他背后关闭,他立刻感到恐惧并试图在侧柱之间寻找依靠,当他感觉到背部挨上俄亥俄州阿克伦城铸造的铁护板,顿时瘫靠过去。他眼前的景象无法言说。从街上看过去整座大宅仿佛城堡,堡垒或碉楼赫然在目,因其仿似多立克式雕带的拇指圆饰的凸起上未见三陇板和排挡间饰,因为在规则的倒置阶梯上并未凸显底面,因为透雕格栅的某些部分其实是壁垒护墙,因为梁托在直角处经过加固,不仅是足以摧毁一切秩序的极度不规则,更因为他发觉了那些瞭望塔,射击孔,隆起物,看似暗门的隐蔽口,不通风甚至密闭的小窗,饰面上充当射垛的城齿保护凹半圆线脚以上的屋顶和天台,而庭院内则有坚固的护墙和扶垛拱卫厚实的外墙,不远处是天真的格栅,泄露出幽深处凉亭百叶窗费猜忌的神秘,环绕的是篱架上开放的素馨花,在上方,屋顶上,天沟凭借院墙末端的tromp-l?oeil [法文,应作“trompe-l?oeil”,意为“欺骗眼睛,错觉画法”。]掩饰粗麻袋和枪眼,而亚述-罗马形制的雉堞则伪装成哥特式拱扶垛,在明显过量的中分拱顶窗和联拱顶窗和天窗之间同时出现了喇叭口型铳,投石砲,时代错乱的弩架,骑兵马枪,而从山墙,滴水嘴和鹰头马身滴水兽之中很可能出现一名精准franc-tireur[法文,意为“狙击手”。]以及由之而来的可怕的非对称。看到这一切他感觉自己在同志们中间:都是武装起来的人。然而,此刻,一旦步入院内,就成了迷狂的室内设计师的cauchemar[法文,意为“噩梦”。]。的确,噩梦已在庭院左翼开始,在那里,作为一处幽僻凉亭的pendant[法文,意为“对称物”。],设有一座单列圆柱式的古旧庙宇,经过柱间,穿过精致的柱廊,在沉默的壁柱之间,可以看见明显为丧仪所设的石碑。然而,这,这样的话……是否还要徒劳一击,或者索性溜之大吉?不可能,因为门已经紧闭,插销,弹子锁,门栓,横木,碰簧锁,铁锁以及明显能够抵御突击或赫拉克勒斯式大力推搡的铁栓,那样做的话不会有任何结果除了弄脏imper[法文,意为“雨衣”(imperméable的缩写)]的肩膀和袖子,而该外衣之下藏匿的就是那柄钢制登山镐,将要伸张正义——或残忍刺杀,取决于诠释者和诽谤者的不同看法。 记忆此刻在他脑海中涌现,在巨细无遗的笔记中忘记了华丽的柱顶过梁,花岗岩墙基下碎石砌起的柱脚以及目测立面的大小(该死的韵脚!)。他又回到现实,望着地面上的瓷砖在白色马赛克上拼出绿色回纹图案,毅然决然面对自己的疑惑,走向倚在凹槽方石的挑檐带上的呈螺旋形的拱门缘饰。比起后面的事情而言,这只能算peccata minuta[拉丁文,意为“小过失,轻罪”。],当他向客厅望去,那是门厅,场囿也是迷宫,有半圆拱,马蹄拱,三叶拱,葱形拱,披针形拱,二尖拱,弓形拱与平拱的集群,无声杂糅着新古典风的倒置金字墩,art nouveau[法文,意为“新艺术”,指流行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一种装饰艺术风格。]风格的锒板,内拱肩,侧拱支撑的所谓的圆拱穹顶和用尽了光谱颜色的拱腹犹嫌不足,还有迷醉的倒挂金钟在互补的颜色中映衬着各色装饰,齿形,珍珠形,带花冠,回纹,环卷,饰边,凹纹,网格和网眼,然后在下方,是桃花心木的嵌条分开内雕带或柱脚,被本地人坚持称作边饰,这些都覆着紫红的丝绸。在里面,在壮观的楼梯侧畔,仿佛在引领这形式的混沌,挺身矗立,一只手臂和山羊胡一样苍白,蒙古人种模样,长大衣,鞋子或宽领带,依然能言善辩,或至少指点江山,立于底座上,正是弗拉基米尔·乌利特茨·乌里扬诺夫[弗拉基米尔·乌利特茨·乌里扬诺夫(Vladimir UlitchUlianoff)戏仿列宁的原名。]或他的大理石复制品,铭文也镌刻于大理石,在伟人塑像的下方,用西里尔字母注明:列宁。看着那些玻璃柜,数着花纹大理石楼梯的台阶,记录的视线沿着同样是石灰岩的栏杆下行,他迷失在涡旋,螺线,曲线,叶状的装饰物,栏杆和过道中的垂直搁栅的铁艺之间,陷入沉睡,但没忘记睡前在永恒的惊异中挨近一张极具马塞尔·布劳耶[马塞尔·布劳耶(Marcel Breuer,1902–1981)出生于匈牙利,美国著名建筑师。]风格的扶手椅,在那里找到了慰藉。 四 他被瓷砖地上的脚步声惊醒,透过睡梦和睫毛的网眼隐约看见,开始以为是军靴,随后又觉得像土著皮凉鞋而现在看见就是普通的鞋子,由鞋底,护皮,鞋垫,鞋底边,在本地被称为坎夫雷拉的鞋内底,鞋后跟,脚后跟,鞋面,鞋舌,在这美洲的穷乡僻壤被称为鞋襻儿或鞋耳朵的部件组成。在这一切之上走来一个男人,裹在老式色调的衣服里。在这人身边还有另一个男人,他看见,两人中的一个有着长颈子,他进而推测其构成:舌骨,甲状舌骨膜,甲状腺软骨,拉蒙·所培那出版社[拉蒙·所培那(Ramón Sopena,1867-1932)西班牙出版人,1894年建立同名出版社,以百科全书和辞典闻名。],环状甲膜,环状气管软骨,用唯一的眼睛看向他(另一只眼睛戴着眼罩形似埃沃利郡主或“奥洛纳人”文森特·诺[埃沃利郡主(princesa de ?boli)即安娜·德·门多萨·德拉·塞尔达(Ana de Mendoza de la Cerda, 1540-1592)西班牙著名贵族,以戴着独眼罩的肖像流传后世;“奥洛纳人”文森特·诺(Vicente Nau El Olonés)应指Francisco Nau El Olonés, 即Fran?ois l''''Olonnais或Jean David Nau,十七世纪著名的法国海盗,横行于加勒比海一带。])仅用一只眼睛但他知道仍包括以下部分:角膜,虹膜,脉络膜,晶状体,巩膜,视神经和视网膜,而视网膜:上颞动脉,巩膜,鼻上动脉,鼻下动脉,视神经乳头,下颞动脉和视网膜黄斑,从这一黄斑他得知在另一个人眼中自己至少是二维图像,且为彩色成像。 至于那人的同伙,他仅看到一只耳朵,尽管这始料不及的押韵令他极度不适,他还是一一计数,为了驱散不快,计算可见的诸部分,耳轮,前耳轮,耳蜗,耳垂,耳屏,对耳屏,耳郭(可想见其覆住糊满耳垢的耳道),前庭,鼓膜,砧骨和锤骨,外耳,中耳和迷路。他们中的一位向他挥手致意但他无法确知是哪一个(人还是手),但诚然知道不仅仅是人和手:腕关节,小鱼际隆起,手掌,小拇指,无名指,中指,食指,大拇指和鱼际隆起,跗骨,蹰骨和手指头,更不用说各色骨骼(见鬼!)肌腱,肌肉和起保护作用的真皮。他举起手回应致意,当动作结束时翻转掌心就看见掌纹和逻辑区,本能区,意志区,智慧区,神秘区,木星丘,土星丘,太阳丘,水星丘,分别掌管财富,心灵,健康,火星丘,智慧线,月丘,生命线,爱情线,他心中同时置疑自己会不会有好运,以及金星丘[金星丘(Mons Veneris)在手相学上意为手指根部在手掌上的微小凸起,同时也指女性阴阜,即“维纳斯丘”。]旁边的红斑是疱疹还是淤青。 他听见杀手们在方砖镶嵌的地上高谈阔论各种战争话题,出于分析的积习他不禁为人间王国的一切事物列出纵览表。于是他听见来复枪就想到枪管,准星,枪箍,填弹夹,推弹杆,枪栓,扳机,扳机护圈,枪托;子弹,据他所知,组成部分有铅,钢,燃烧弹或曳光弹(Arm.),穿甲弹,开花弹和狩猎弹,都有黄铜弹壳,铅芯,硝石和底火;手雷,他想起撞针,保险销,保险握片,铅合金的阻铁,雷管和引信—— 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标的或靶心。他们继续向前,而他又独自一人,但没有多长时间,因为很快就有外来入侵和原生昆虫的嗡嗡声相伴,在其中他辨认出:头,复眼,足(第一对),前胸节,足(第二对),蛰针,腹部,后胸,脊,前翅,后翅和足(第三对)。是一只马蜂吗?他感觉自己的情绪变得透明,恐惧变得隐喻化,意图在自我抑制中反而袒露无遗。由此推断一只入侵的膜翅目生物能催生极大的不适和重大的披露,只需一步而且那不会是消失的一步[戏仿卡彭铁尔的长篇小说标题《消失的脚步》。],因为迈出这一步他们就会把白昼的恐惧与邪恶的意图相联系,将会知道他就是某种姬蜂,在奥里诺科丛林中奔波寻找蜘蛛,为的是在它后颈刺下致命的一针。或者是只工蜂,蜂王或雄蜂?为了摆脱终极的恐惧和可能的失眠,他望向客厅的另一端,看见那里有旗帜,但远在辨认出党最初的和正统的旗帜之前,发现像所有的旗帜一样,分成环索,套边,幅面,针脚,织边,垂穗,流苏,织边(另一边),接缝和竿梢,不是燕尾旗也不是长条旗更不是盾形旗却是方形旗,他知道就是可敬的那面旗,尽管没找到交叉的锤子与镰刀,而且旗面在眼中是蓝色不是红色。色盲症?为了勘破假说的对与错(又来这套前后割裂的押韵!)他望向左右仿佛在守护旗帜的四面盾牌,在认出一面西班牙,一面法兰西,一面波兰,一面瑞士之前,他看见的是不同的分区:盾顶右,盾顶中,盾顶左,右翼,中点(或中心位),左翼,底部右,底部中位,然后盯着盾脐看(盾牌的肚脐,四面盾牌,四个不同的盾脐但只有一个真正的)然后数起金色,银色,红色,蓝色,绿色,m. 紫色,黑色,灰色,作为背景或区别于:栎树,斜十字,带叶树,悬绳号角,狮口斜条饰,联冕,竖堞形,锯齿形,四分形,链接形,横纹形,包边形,拼合形,反松鼠皮,棋盘格,菱形,中孔菱形,T形端,对分形,边饰,缘饰以及跃立狮,探爪鹰与蜿蜒蛇。 他走向前去观察更细微的区别,这时走来一位听差,扈从或书办,对他说请上楼,大师(这是照录的原话)接见,已经在等他——此处大可加上一句,耐心是不耐烦的前奏,按本地的说法:谁期望谁绝望,因为他看见了(并记下)那执拗或傲慢的表情。他精准转身九十度,稳稳踏在中心马赛克圆周里铭刻的百合花中的一朵,然后开始行进,以乔装的门徒的步态,走向hereticus maximus [拉丁文,意为“最大异端”。]的营地。他一级一级走上楼梯,不时停下来观察在栏杆上方,顶端的扶手,琥珀色大理石嵌入板岩的纹路与同样琥珀色大理石的楼梯上板岩绘出的路纹相吻合,尽管脚下踩着的是红氍毹,不是大理石台阶,上面由铰链销和青铜色的铰链构成美丽的映衬。最上层楼梯平台的左侧有一副Quattrocento 时期[意大利文,意为“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全身甲胄,带护眼罩的头盔,护喉甲,护肩甲,上臂铠,前臂铠,腿罩,插矛皮套,护膝,护腿,护胫甲,大盾(或盾),护胸甲和斧戟,托雷多钢刃横在圣栎木矛尖。虽然对浅浮雕纹样装饰的胸甲和带凹纹的肩甲都兴趣不大,但他的确想知道头盔是全盔抑或只是无面甲高顶盔附带延展向上的护喉甲,就凑近过去,几乎(墙壁妨碍了观察)绕到背后,在挨近时发现,所谓的护喉甲只不过是宽一些的护颌或在眼罩处穿孔开缝的鍪胄,由此得出结论这只能算半盔不是全盔——在弯腰时风雨衣里的斧戟让他想起必须上楼面对自己的敌人,就在他做出决定的瞬间楼梯平台上的玫瑰窗攫住了他的眼神。然而他奋力抵御住分神的诱惑终于毅然决然登上了楼梯。在上面,在入口处殖民地风格凹凸雕花的门帘匣,他看见了门和框架(或支脚),镶板,撑架,板条和门楣的材质是西班牙橡木,虽然没有保护性的门牌但确实有锁眼和扣环,明显都是青铜,以及同样合金材质的铰链销,他创造历史的手抚过凸起的线脚,而后攥起一只马克思主义的拳头用青筋暴出,紧张暴露的指节叩响门扉。 五~五十五 (在审视房间内所有器具物品并开列清单之后,雅克·莫纳尔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呈交了“八开纸习作”,就像阿莱霍·卡彭铁尔所说,当大师沉醉于阅读之时,他成功地掏出暗杀的铁锛——之前并未忘记依次数点这位伟大死者的每一处解剖学的,特异性的,个人的和政治的特征,因为刺客(或作者)罹患的正是法国文学圈所称的Syndrome d?Honoré [法文,意为“奥诺雷综合征”,即对法国作家奥诺雷·巴尔扎克的病态模仿。])。 ?古巴作家卡夫雷拉·因凡特是拉美“文学爆炸”中的一颗巨星,曾获得西语文学的最高奖项塞万提斯奖。 ?本书是“文学爆炸”迟到的经典,地位毫不逊色于马尔克斯同年出版的《百年孤独》,被誉为拉美的《尤利西斯》、哈瓦那夜店版的《追忆逝水年华》。 ?本书具有高度实验性,全书充斥着大量的语言游戏(俚语、笑话、谐音、双关)、文体实验(戏仿、拼贴、互文),以及形式设计(比如在文字中夹杂图示,篇章中加入黑页或白页,整页文字反向排版等),体现了惊人的创意、丰富的巧思与绝佳的幽默感。 ?作为一个“包含一切文本的文本”,这本书给各国译者带来了极大障碍。中文版为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引进,由《百年孤独》译者历时八年完成。 凭借《三只忧伤的老虎》,卡夫雷拉·因凡特跻身拉丁美洲小说家的前列。这本书可与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多诺索的《污秽的夜鸟》媲美。——《纽约书评》 《三只忧伤的老虎》是一本了不起的书。我怀疑自《堂吉诃德》以来,还没有一本更有趣的西班牙语书……它也是拉美地区最具创造性的小说之一,这一点很有说服力。——《纽约时报》 有史以来用西班牙语写的最好玩的书。现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具原创性的声音之一。——《卫报》 一首对孤寂的夜晚、对哈瓦那的炎热、对街头俚语的赞歌。——《西班牙自由数字报》 这部小说改变了西班牙-美国文学的生态。 ——《西班牙国家报》 文字游戏的大师和记忆的守护者。他把哈瓦那变成了古巴的一个隐喻。——《古巴聚会》 《三只忧伤的老虎》是最激动人心/最性感/最有趣/最吵闹/最有想象力/最令人回味的小说,任何人,即使是(不爱读外国小说的)英国人,都希望能读到。——萨尔曼·拉什迪 为了实现调侃、滑稽模仿、一语双关、智力的高难度杂技以及口语中的跳跃,卡夫雷拉·因凡特总是准备着与全世界人为敌,准备失去朋友甚或自己的生命。因为幽默在他这里与在普通人那里不一样,它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消遣、用来放松头脑的解闷,毋宁说,它是一种被迫的、向现存世界发起挑战的手段。——巴尔加斯·略萨 难以想象哪个作家能在他的文字里把不同的语言融合得如此巧妙;纳博科夫、贝克特和卡夫雷拉·因凡特总能带给我们这样的惊喜。——苏珊·桑塔格 一本由健谈的人写给健谈的人的健谈书,它庆祝健谈的人在简略之中逐渐消失。 ——莫里斯·那多,文学评论家,法国最佳外国小说奖评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