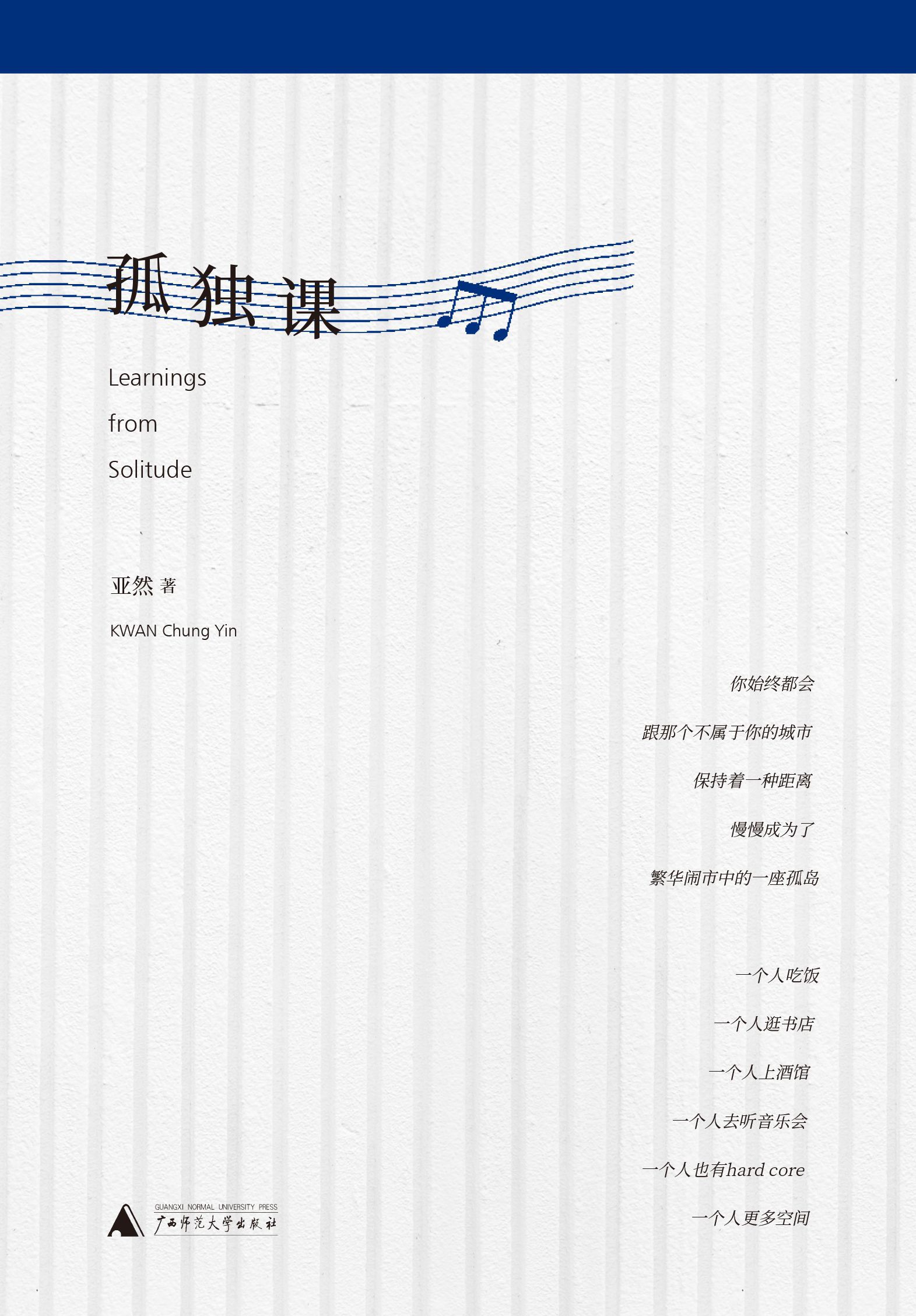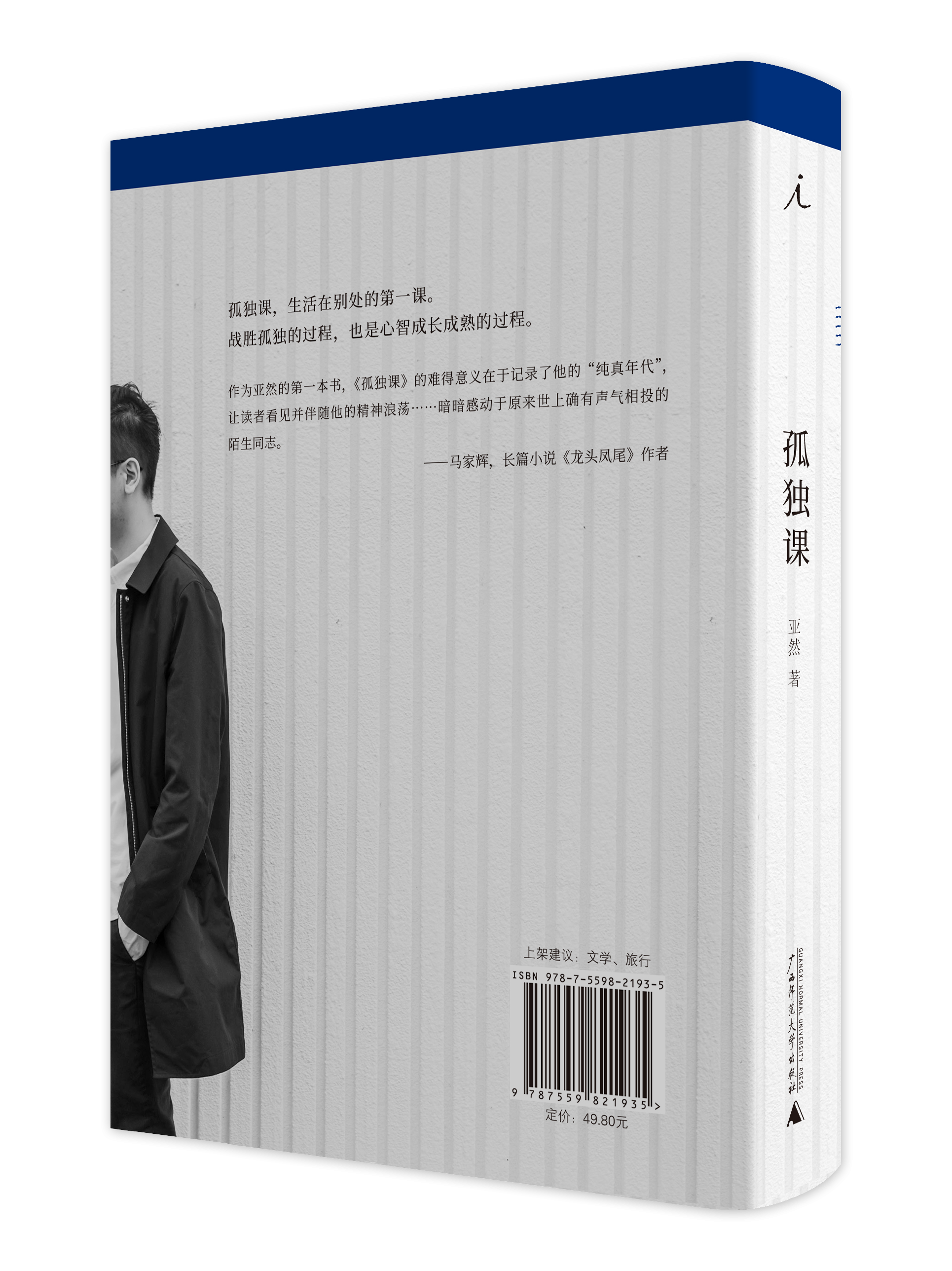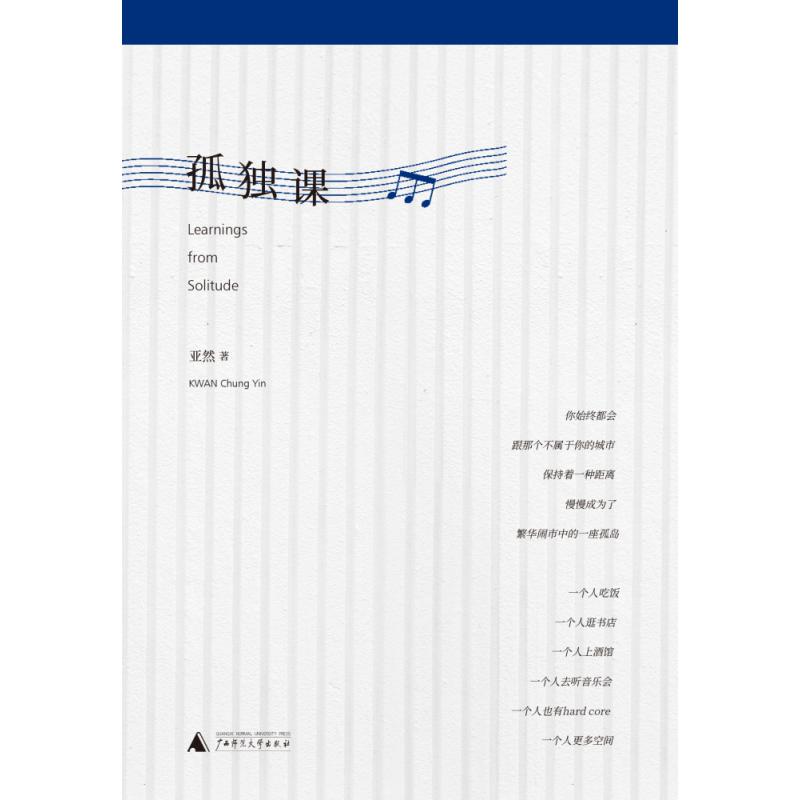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49.80
折扣价: 30.90
折扣购买: 孤独课
ISBN: 978755982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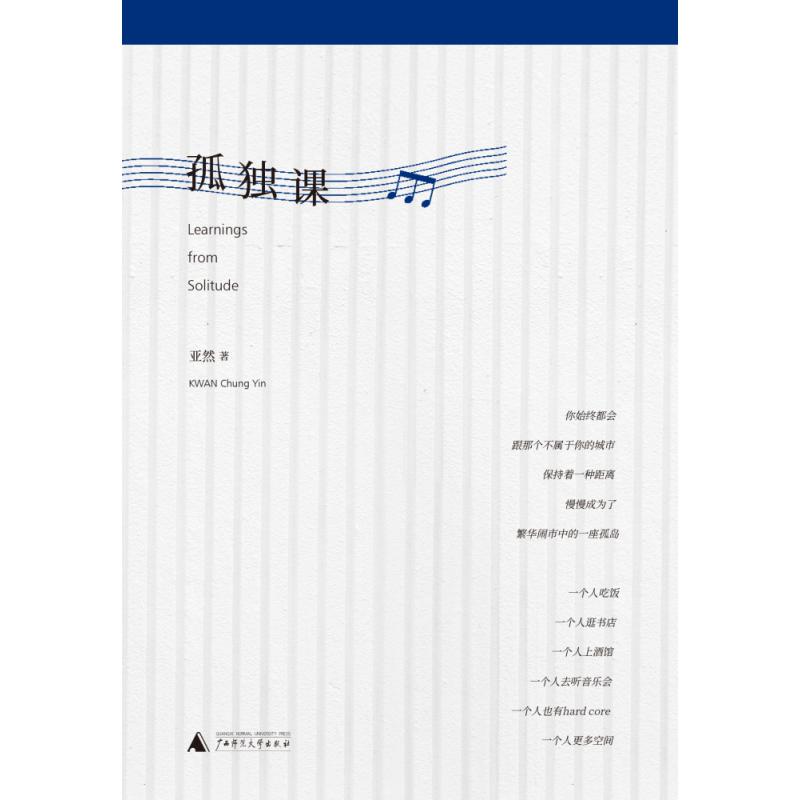
亚然,本名关仲然,1993年生,“一位up and coming的新一代文化人、专栏作家”。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候选人。学术研究之外,兴趣涉猎甚广,对音乐、足球、威士忌都有研究。专栏见于《明报》等,同时为学术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等撰写书评。 亚然的“开箱之作”《孤独课》,跟当年董桥一样置身伦敦,外面的世界,行囊里的中文,也跟前辈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马家辉《*月》和周保松《相遇》一样,都写他们的年轻、念兹在兹的异域求学时光。
【《村上春树的威士忌》】 连续啃了两本学术书之后,伸一个懒腰,奖励自己继续留在书房,读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小说一二两部合共800多页,转眼就读完,如果读学术书有这样一半速度就好了。 村上的小说,总有古典音乐,像《海边的卡夫卡》的贝多芬“大公”,像今次新小说里面的李察·史特劳斯歌剧《玫瑰骑士》。所以唱片公司每隔几年,就会推出什么“村上的古典课”之类的古典杂锦CD。不过,这门生意在串流音乐App(像Spotify)出现之后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在Spotify中,可以自行制作播放列表(playlist),找回小说里面乐曲的**版本,就像今次的《玫瑰骑士》,听萧提爵士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版本,才算玄门正宗原汁原味。 除了古典音乐,村上春树的小说还有威士忌。这两种元素是村上写小说方程式的常量(constant),与其说两者必然会出现在小说,不如说是音乐和酒将故事连结起来。村上本身当然是个hard core的威士忌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去艾雷岛写游记。所有人都喝白兰地或调和威士忌的时候,他很早就喝sin**e malt(跟大家温习一下:单一麦芽,即一间酒厂以麦芽为原料制造的威士忌)。不过在小说中,村上小说的角色们一向都喝得随便,*常提到的只是便宜调和威士忌Cutty Sark(如《1Q84》《听风的歌》)。 在《刺杀骑士团长》,喝得*多的是另一款调和威士忌Chivas Regal。有位报纸老前辈还算眼利,找到书中的一个错误,他说“繁体字译本居然把Jura译成艾雷岛实在有点张冠李戴之弊”。错是错了,不过不是翻译的错,而是编排的错,前辈的“指正”也一样张冠李戴。 事缘发生在第二部的113页,我找K这个*本通帮我从*本原文中求证。艾雷岛是没有错,错的是把“Isle of Jura”这个注脚落错位置。正确的话,应该落在下两行的“汝拉岛”旁边。其实想一想,村上春树的艾雷岛游记,也是由赖明珠翻译,如果以为赖明珠会弄错地名,也未免太过少看翻译了吧。 前辈那篇谈村上的文章还如此写道:“其中提得*多的是*爱喝的苏格兰威士忌包括Sin**e Malt Whisky,小说角儿们有什么紧要的话说,有什么难解的谜都免不了来一杯Scotch。”懂酒的人,一看就觉得怪。如果我将这句说话的威士忌改成红酒的话,你就明白有多怪了:“其中提得*多的是*爱喝的法国葡萄酒包括red wine。”老前辈看来*近好酒,去一转苏格兰、访了艾雷岛和高地等等,写了几篇游记之后,就连专栏的名字也改成一副专家模样。不过从这些文章看来,前辈还是威士忌初哥。 早两个月我写了一篇爱丁堡威士忌学院的创办人访问,当中写到“现在有互联网,有关威士忌的资讯多得离谱,但*要命的是资料孰真孰假无人知晓”,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相约在音乐厅的顶楼》】 这几年在伦敦,每十天八天就去巴比肯听伦敦交响乐团,或者到泰晤士河河边的皇家节*音乐厅看爱乐乐团的演出,在专栏都写过不少。但如果我说自己住在伦敦、喜欢古典音乐,却不写不提全世界*大型古典音乐节之一的BBC逍遥音乐节(BBC Proms),你大概会怀疑我根本不喜欢音乐,甚至质疑我根本不是住在伦敦。 夏天本来是乐团休季的时间,伦敦的乐团在这段时间要么休息,要么世界巡回演出。不过我早就说过很多遍,伦敦是个听古典音乐的好地方,恒常的乐季休息,但有逍遥音乐节顶上。 每年夏天在伦敦举行的逍遥音乐节,一连八星期、每天至少一场音乐会,在海德公园旁边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上演。七十几场音乐会,几乎所有古典乐界的大名都有出现,像夏伊、拉陶,像巴伦邦、MTT(Michael Tilson Thomas)。乐团方面,虽然今年没有柏林爱乐,但同样是欧洲***的维也纳爱乐、阿姆斯特丹的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还有东道主伦敦交响乐团都有演出。一些热门的音乐会(像演奏马勒的那几场),门票一发售就卖得七七八八,想要买到门票,*便宜也*容易的方法(不是在音乐厅门口买黄牛),是在演出当*的朝早九点,上网买音乐会的“站立位”(未计手续费,一张站着的门票盛惠六镑)。 皇家阿尔伯特是非一般的音乐厅,可以坐五千多人,但空间太大、太多观众,对音响效果都造成很大影响。简单来说,这不是一个适合管弦乐团演出的音乐厅。但索尔福德大学的工程系教授Trevor Cox说得好,去逍遥音乐节:There is more to a concert than just the sound. Seeing a concert in the iconic hall is a great social event.(音乐会不只是去听那么简单,在标志性的大厅里欣赏音乐会是一场盛大的社会活动。)见到舞台前面站满人的画面,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场古典音乐会是social event了。 舞台前的站立位,真的要“站”起来,而且永远都站得密密麻麻。见到那些上了年纪、着得整齐的ladies and gentlemen,全神贯注企足全晚,而且站得笔直,实在厉害。而音乐厅顶楼的站立位,我想也是逍遥音乐节*逍遥的地方了。在音乐厅*高的五楼,除了倚着围栏边的人会站着看音乐会之外,大部分人都坐在或者瘫在地上。 音乐会七点半开始,而音乐厅六点半就会开门。那些auntie、uncle带齐装备,有席有被有枕头,准时六点半就直奔五层,去到那个属于他和她的老地方。他们本来不认识,但他和她都已经不知第几个年头,一起在音乐厅的五楼,一起度过夏天了。他们铺好席、脱鞋、盖被、合上眼,就这样躺在地上,一直到音乐会结束,然后静静离开。没有约定,但却比约定还要可靠,他们一定会相见。 每年暑假的逍遥音乐节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夏天的每个夜晚,他们都在这里。当去到音乐节的*后一晚,奏起艾尔加(Edward Elgar)的《威风凛凛进行曲》,他们会从背包拿出米字国旗,站起来,一边挥动,一边合唱。当这一晚结束之后,又要等待一年的过去。然后约定明年**,再次在五楼见面。 【《暂别英伦》】 来到十二月,准备动身离开伦敦。不过读者不必恭喜,不要以为我已经学有所成终于毕业,因为现实是:距离可穿着火红长袍(亚非学院的博士袍是火红色的)的*子尚远,前面还有一万里。离开伦敦,是因为要到**进行“田野调查”,收集数据。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而学术以外的人又总会觉得读书做研究的人*好,因为生活没有“朝九晚五”的规范,因为我们对“*近忙什么”这问题的答案,永远都是“看看书、写写东西”,听起来都无所事事。不想过分victimize学术生活,初尝学术研究生活几年,时间的确比大部分人都自由。只是各行各业各有难处,象牙塔里生活孤单、消磨意志。 做学术研究的“好处”是常常飞来飞去,但实际上就跟我之前说过一样,是居无定所,像杜甫说的“漂泊西南天地间”。现实生活不像电影里面的主角一样,总可以在两秒之后,换个镜头,就从这个城市搬到那个城市。每搬家一次,都耗尽心力,什么应该留在伦敦、什么应该搬到**、什么又应该寄返香港。搬了几次之后,东西散落各地,我几乎连自己此刻身在何地也快搞不清…… 收拾好之后,还有三两天时间,将平常在伦敦*喜欢做的事都做一次。要暂别这个城市,竟然有点不舍。我走到伦敦的南岸,天早已黑了,冷得要命,在河边特别大风。但我还是想在河边走一会,因为这一段路是我在伦敦*喜欢走的路。将大衣扣好、用颈巾把自己裹着,迎着风,每一步都觉得自己在跟世界对抗着。从伦敦桥起行,终点是西岸的国会西敏寺,途中走过博罗市场(Borough Market)、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等等。 走入皇家节*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旁边的**剧院(National Theatre),那是粗犷主义的其中一座代表建筑。建筑师是Denys Lasdun,亚非学院图书馆也是他的作品。*喜欢到剧院的餐厅,点杯咖啡、一件布朗尼,严寒天气总是摄取多点热量的*好借口。充一充电之后继续向前走,走到大摩天轮。伦敦眼给灯光打成红色,因为都给可口可乐赞助了。 迎面走过的是一对恋人,男的拖紧女、女的抱着狗狗毛公仔,一脸幸福快乐。在冬天,伦敦街头的情侣都是这样,都是去完海德公园的冬*仙境(Winter Wonderland),那个男的要么“掷彩虹”、要么“跑企鹅”,中了奖,赢了一只毛公仔,也赢了善女子的心。 离开伦敦,短暂停留香港之后就会转到**,待到明年九月才回伦敦,所以专栏也慢慢从写伦敦变成写**。董桥先生当年写《旧时月色》,说的也是伦敦和**的故事,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同样的地方写人和事,是我*大的荣幸。